重回武汉
宰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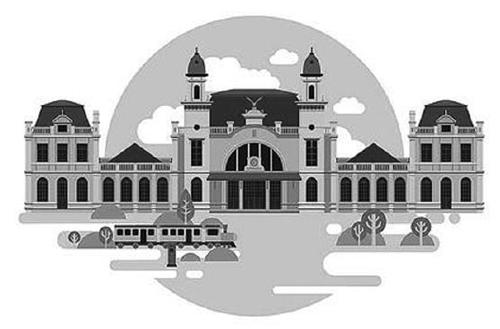
我常常在想,是什么让一个人感动。首先当然是情,爱情、亲情、友情……那些柔软、温暖的情绪。此外,还有义——把个人追求置于伟大事业中,舍生取义、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
“解封”半年后,武汉的大街小巷里,行人、汽车、灯火、各类买卖,处处可见。它恢复了过去的模样。只是,对于极少数人,那些记忆还停留在“封城”时刻的人,今天的武汉却陌生而反常。
今年二月初,我作为报社特派记者,在离汉通道关闭后进入疫情正吃紧的武汉。三月底,在武汉重启对外交通前夕,我完成报道任务回到上海。一个多月里,我见惯了一座空城。
当时的武汉像是无声的。我除了在医院采访、在餐厅取盒饭时会听到别人说话,其他时间几乎不闻人声。至今不忘的,除了寂静,只是大自然的声响:黄鹤楼下长江水日夜拍打堤岸哗哗作响,二月里的那场狂风掀动门窗让人一夜无眠,鸟雀在金银潭医院住院楼前的树丛里鸣叫,东湖湖畔的村落里看门狗听到院外的动静不时吠叫。如果不是因为疫情,2020年初春的武汉倒像是陶渊明诗中的田园。
十月的一天,离开武汉半年多后,当我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耳膜始终被人类活动制造的声波冲击着,让我觉得这座城市处处陌生。首先是汽车喇叭,不论是在街道上,还是在房间里,嘟嘟的鸣笛让人无处可逃。步行街附近的一小片空地上,广场舞的旋律压过了商家的叫卖。酒店隔壁,一家商场正在改建,机械撞击声穿过窗玻璃一阵阵传来。还有武汉话——我半年前在武汉几乎从未听闻,现在却不绝于耳的爽朗的方言。
城市的声音无处不在,不断洗刷着我的记忆,仿佛在说:这才是一个千万人口大都市的原貌,这才是它的日常。
新 生
朱超约了我下午四点在江汉关附近碰面,到了四点,却发短信向我致歉,说要晚些才能到,因为堵在路上了。那天恰好下着小雨,本来就堵车的武汉更加堵了。不过,经历了疫情期间足不出户的70多天,武汉人对拥堵显得十分宽容。
朱超是上海三联书店Readway武汉项目的负责人,他们正把江汉路地铁站口的一座四层楼房改造成一家新型书店。现在,他们一面在整修建筑外立面,一面为书店项目招商。朱超刚刚去见了一位潜在客户。
三联Readway落户江汉路步行街本是去年就计划好的项目,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断了方案,直到前不久,项目才正式启动。朱超说,这家三联Readway的目标是“武汉青年文化商业第一站”,行业内的一些头部品牌在书店一层必不可少。这些天,朱超和他的团队穿梭于武汉各处,一天要见好几拨品牌客户。
不只是三联Readway在忙,它所在的江汉路步行街整条街都在忙。这是一条百年商业街,2000年改造成步行街。它对于武汉,就像王府井对于北京,南京东路对于上海。国庆节前夕,江汉路完成改造开始试运营,以全新形象示人。十月一日,江汉路步行街区的游客量已经逼近去年同期。
步行街区管理部门却把眼光放得更远,他们知道,千里之外,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刚刚东扩到了外滩。相较之下,江汉路虽然更新了,但未来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比如业态提升、品牌定位、历史建筑的修缮。
武汉人对于这座城市的商业繁荣有着历史温情。1861年汉口开埠后,特别是1898年张之洞督鄂推行“湖北新政”后,汉口(武汉)迅速崛起为内地最大的外贸大埠。处于长江中游,汉口下接上海,它担起上海—内地中转的枢纽。在19、20世纪之交的40多年里,汉口身居中国外贸第二大港。这个时期,它作为中国内陆唯一的国际性城市,与上海一样享有广泛国际知名度,被称为“东方芝加哥”。
“东方芝加哥”这个绚丽的名字背后,既有旧时商业鼎盛的荣耀,又有列强控制租界的屈辱。面对外资洋行纷纷进入武汉市场,民族资本主动应对开放格局。中日甲午战争后,武汉民营企业数量发展至120家,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
由民族资本修建、意与洋人一逐高下的“争气楼”也在这期间竖立起来。江汉路鄱阳街口的四明银行汉口分行大楼就是“争气楼”之一。大楼建于1936年,平面呈梯形,现代主义风格,是中国建筑师在武汉设计的第一座钢混结构建筑。
武汉人自古以来对文明有异乎寻常的包容。他们接纳了洋货、洋行,也曾把近代科学、技术、文化逐步移植到城市建设、管理中。这种包容性源于武汉移民城市的特性,也源于它“九省通衢”的枢纽位置。大武汉、大上海,大,当然是指面积,也是在说视野,在中国以“大”字冠于市名前的并不多。
家 国
十月中旬的一个清晨,我在武漢再次见到了87岁的“落日余晖老人”王欣。上次见他是在半年前,那时他感染新冠肺炎尚未痊愈,还躺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20病区的病床上。病中,他和中山医院医生刘凯一起看夕阳的照片被一位志愿者抓拍到,温暖的画面中蕴含的力量曾经感动了全中国人。
这回,在十月的武汉再次见到王欣时,他正和女儿于果站在一家酒店大堂。于果说,车停在地下车库了,没找着电梯,老爷子和她一起爬了两层楼梯。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王欣老人站着。以前,不管是在病房里,还是在视频上,他不是躺着,就是坐着。我没想到他能和女儿一起来和我重逢,更没想到这次他竟是站着。我的记忆还停留在早春时节。
王欣对我的记忆似乎也留在了几个月前,他说:“我看你穿防护服的样子,还以为你很高。”很高,也许是防护服产生的错觉,也许是他心里对所有医务人员形象的高大化(虽然我当时穿防护服,却并非医务人员)。
阔别半年多,一见面还是聊起跟疫情有关的事。王欣说,两天前受邀参加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展览”的开幕式。刚一进馆,就有记者认出了他,一大群人立刻在他身边围了好几圈。“话筒都堵到嘴跟前了,”他女儿一面比画一面说,“这阵仗从来没见过,我们都吓蒙了。”记者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抛过来,有些问题老爷子回答了十多遍。后来,我看了不少媒体在专题展上拍摄的视频,反复听到老爷子说一句话:“感谢党,感谢国家。”
“感谢党,感谢国家”的话,我听王欣老人说过多次,在病房里、视频通话里、媒体报道上。这天,在疫情过后的十月,我们坐在酒店的大堂里畅聊别来情由,他又说起这句话,眼圈又红了。女儿在一旁说:“又激动了。”反倒是说到自己病中苦痛时,他一直很淡然。
像王欣一样,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是经历了新冠疫情后很多人共同的认识。他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中国如何在短时间内控制疫情,政府如何不惜代价救治患者。他们也从新闻里看到,国外疫情如何蔓延,损失如何惨重。“此生有幸做中国人。”这是在武汉,另一位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对我说的一句话。说话时,他也流泪了。
我常常在想,是什么让一个人感动。首先当然是情,爱情、亲情、友情……那些柔软、温暖的情绪。此外,还有义——把个人追求置于伟大事业中,舍生取义、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
在这片发起过辛亥首义、见证过武汉会战的土地上,家国情怀根植已久。109年前,革命党人在武昌城外的中和门打响了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第一枪。82年前,面对日军进攻,这里唱响过“保卫大武汉”的歌声。
2020年,与新冠疫情的斗争再次激发了武汉人的这份家国情怀。那位康复后的武汉市民说:这次疫情我是病人,受到很多人的帮助,万一以后国家再遭遇这样的灾难,我会想尽办法去帮助别人。就像《查医生援鄂日记》中所说:“这世上可能确实没有超级英雄,不过是无数人都在发一分光,然后萤火汇成星河。”
如今,王欣老人又恢复了往日的作息:早晨八点起床,听五分钟手机新闻,出门吃早饭,回家练琴,下午在小区散步。偶尔,还出门会会我这样的远方来客。康复后,他不仅时时把“党”挂在嘴边,而且还挂在身上——和他对面坐了许久以后,我才发现,他的胸前别着一枚党员徽章。
前 路
我在武汉采访期间,唐建明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份荣誉证书:他在一项全国性演讲比赛武汉赛区中获得了一等奖。他演讲的内容是患病期间遇到的那些光辉榜样。做一个正能量的传播者,这是他愈后新的人生方向。
唐建明是武汉冠捷科技的一位供应链管理师,也曾是一名新冠肺炎患者。一月底,被初步诊断为疑似病例后,他在几家医院之间辗转了25个小时,最终在武汉第三人民医院找到一张病床。几天后,武汉第一批方舱医院开舱。因为他病症较轻,医生动员他转院到方舱,把病床留给还在医院门口等待的重症患者。
他说,道理当然懂,但是关系到个人生死存亡,谁不想多一线生存的希望?在医院病房里,生命就多一份保证。虽然是轻症,但他也听说过不少轻症患者病情突然恶化的案例。况且,方舱医院谁也没见过,到底怎样,谁也说不准。他记得对劝他转院的医生说:“我还年轻,活着还能为国家多做贡献。”
但当医生第二次来做他工作的时候,唐建明还是答应了。这就是武汉人,做起事说起话来,给人很聪明很强硬的感觉,而实际上大多数都颇厚道。
医生交代完转院事宜,离开病房,又转身折回来,对唐建明说:“谢谢你,32床。”离开三院是在二月五日深夜,那一晚下着小雨,他看着医院门口的高架路上空空荡荡,只有雨丝在路灯下反射着光,他想:武汉能挺过去吗?我能挺过去吗?
在转院的急救车上,一位年长的病友已经拿着行李在等候。相互通报了姓名,长者叫蔡龙跃。谈起为什么答应转到方舱,蔡龙跃说:“我是党员,应该把床位让出来。”蔡龙跃干脆的答复、自己对于转院的纠结,两相比较,唐建明有些羞愧。同时,对“党员”二字也有了第一手的认识。从此,唐建明一直称蔡龙跃为“党员大哥”。
唐建明和“党员大哥”是第一批入驻方舱医院的患者,也是第一批挺过来,从方舱医院出院的患者。康复半年多后,他开玩笑说:“那次差点进了鬼门关,等下次真进了,阎王爷要问,‘这中间你有什么收获吗?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吗?我应该怎么回答?”
其实,他早已有了答案,就是宣传身边的那些榜样:坚守岗位的武汉医护、逆行而来的外地医疗队员、主动让出床位的“党员大哥”……从方舱出院后不久,他就写了文章《致上海“逆行者”:拜谢你们,为我们拼过命》,向上观新闻投稿。九月他致信“湖北之声”广播电台。十月他参加了一项全国性演讲比赛。他说:“如果每个人都学榜样做榜样,何愁国家不能渡过难关?”
二三月间,我在武汉采访,曾一次次驾车跨越长江,往返于两岸的武汉三镇各家医院。那时候,江边黄鹤楼上,景观灯夜夜寂寞地亮着,却无人登临。当时我想,等疫情过了,黄鹤楼重开的时候,一定要登上楼顶,俯视大江两岸。
十月,重访江城,再渡长江,又想起了半年多前的愿望。但上網预约参观时,却发现,热情的游客早已把近几天的名额约满。热热闹闹的武汉又回来了,不再是“此地空余黄鹤楼”。
华自力摘自《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