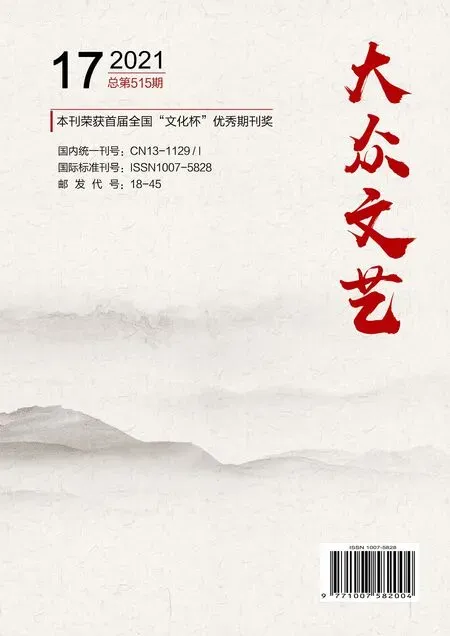从“时代三部曲”看顾长卫的个体写作与生存困境
张铭航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 100024)
一、创作环境的“两面夹击”
进入新世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使得中国的电影市场变得异常复杂。好莱坞大片迅速涌进了中国观众的视野,从而对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进行了改造。此种形势之下,张艺谋和陈凯歌迅速转型,开辟“中国式大片”道路。《英雄》以商业运作手段率先拉开了中国电影大片的序幕。《十面埋伏》紧随其后,以1.5亿的票房收入,创造了2004年国内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陈凯歌在拍摄影片《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和你在一起》时,就已经开始以特定的方式面向市场,而到了《无极》,市场几乎成为唯一的目标。
第六代电影人踏上影坛之际,就面临着特定的文化语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权威性强化,精英文化衰落而大众娱乐潮兴起,这一代导演“俨然成为被拒绝、被隔离于秩序边缘的独行者。”新世纪之后,他们依据自己的创作环境和生存状况,而表现出某种回归主流话语,和寻求观众认同的姿态。首先是进行了体制内制片,但他们的影片也大多秉持着一种相对独特的电影观和历史观,将第五代有关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宏大母题,演变为个体的成长独语。这些“边缘人”的生活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跟中国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相抵牾。
而顾长卫创作“时代三部曲”的语境与此也极为相似。从《孔雀》始,顾长卫的导演创作,就注定面临着政治压力,商业诱惑和大师笼罩的艰难。除进行体制内制片外,主流化也成为第六代导演皈依的策略之一。面对着“第五代”的大片时代与“第六代”的主流皈依,顾长卫曾坦言,处在缝隙中的状态并没有过多地影响到自身的创作。因为在导演看来,做值得做的事,创作一部打动人的作品更重要,所以他构筑的影片执着地表达着存在、个体与尘世关切,游走在主流和边缘之间。
二、时代性的主题导向
(一)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孔雀》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个偏僻小镇的五口之家。时代的大潮还尚未涌进这个封闭的小城,人们过的是匮乏且单调的日子。从最终展现的电影文本来看,姐姐的故事悲剧浓度最强。她将降落伞绑在自行车后,双手撒把,在人们的侧目下欢呼在街道上。这是一种颇具冲击力和感染力的画面,是真正源自艺术的,这一设计直接把人物的精神世界外化和具象化。艺术对现实最好的呈现方式,就是既取材于现实又跳脱于现实。导演对精神世界匮乏,现实理想无法满足的人物给予了关照,通过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帮助人物找到一个欲望亟待释放的缺口,影像的诗意也油然而生。《孔雀》中表现的是个体的困境,同时又是那一时代中国人整体命运的写照,电影刻画的是姐姐的勇气,和对理想所抱有的热情。但在降落伞被扑倒的那一刻开始,都在深刻揭露封闭思想的残酷,这些都是潜藏在个人命运之下的悲剧因素,是对时代与文化的反思。
和《孔雀》里的五口之家不同,《立春》讲述的是小城镇里的四个艺术青年。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这是一个充满着希望和未知的时期,以往强烈的意识形态话语对个人意识的控制在渐渐消退,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个体生命体验开始受到重视。顾长卫镜头下的人物,给予了人们努力实现自己理想的希望,同时又揭示出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鸿沟。《立春》中的王彩玲就像《孔雀》中的姐姐一样,有着殉道士般的执着。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孤独地坚持着。影片没有平面地展示人物悲剧,而是通过呈现一个王彩玲,折射出导演自己对理想与现实的思考,同时召唤着人们在无奈的现实背后找到一丝希望。从通俗意义上来说,王彩玲并不成功,但从某种高度来说,王彩玲获得了另一种成功。她的不成功,也许唤醒了更多人成功的可能。
如果说《孔雀》和《立春》是理想的幻灭与重生的话,那么相比较之下,《最爱》里的赵得意和商琴琴根本没有梦想可言。他们有的仅仅只是对生的渴望,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更加残酷。身体的病痛也时刻提醒着他们,哪一种结局都注定是悲剧的,但这段以违背伦理开始的情爱,有着向死而生的信念和勇气。与那些冷漠的同乡人相比,他们人性中散发的光辉正是导演要颂扬的,“商琴琴和赵得意是这个时代当中提炼出来的人物,有很强的时代气息和特点,是这个时代很典型的一种人物。”
(二)身体与文化的二元对立
顾长卫电影中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包含着多重范畴,它同时关联着个人与家庭、个人与时代的冲突与和解,而戏剧性效果最强的莫过于身体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孔雀》中,哥哥这类人物是20世纪七十年代的一道独特风景,无论是人流汇聚的大街小巷,还是任何一个热闹场所,都会看到这类的智力障碍者,所以他的形象本身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同时又有着娱乐大众的功能。他肥胖的身躯,总在与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发生着冲突并寻求着和解。
《立春》中王彩玲是不甘平庸,但胡金泉是与世俗生活水火不容。他不被法律所允许,也陷入了道德谴责的困境。叔本华的悲观哲学认为,痛苦是人的本质与根源。消除和否定意志才是摆脱痛苦的利器。“悲剧的真正意义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认识到悲剧主角所赎的不是他个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亦即生存本身之罪。”焦刚饰演的胡金泉正是这种生存之罪的鲜明体现。
《最爱》中健康的村民们对“热病”患者避之不及,这是知识的缺失也是人性的泯灭。在这样封闭落后的村庄,艾滋病患者难以实现身份的认同,只能被孤独地隔离在远处山顶的娘娘庙小学。顾长卫以审视,严肃的态度,对特殊境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性进行了拷问。可以看到,顾长卫镜头下的人物特质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是理想主义的,但都在现实面前惨败,回归世俗,但依旧心怀浪漫。这些个人背后所体现出的悲剧性是非常具有时代性的,这些人物在每一个时代都可以得见。因为无论何时,个体的困境是昨天、今天和明天都会存在的。
三、商业性的价值取向
《孔雀》获奖前,顾长卫毫不掩饰对市场的担心,“我对《孔雀》的质量是有自信的,《孔雀》是个好看的电影,按说应该有很好的票房,但是它又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影片模式,没有明星、没有动作、没有喜剧这些常规的商业元素。”幸运的是从柏林捧回的银熊奖成为电影打开市场的利器。《孔雀》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后,电影在北京的新东安戏院举办了6次超前点映,对观众进行了细分,主要以导演和部分艺术家为主。影片发行方获知了不少名导对于该片众口一词的高度评价,确定影片的上映日为2月18日。幸运的是,在电影上映的第二天就捧回了银熊奖。电影在国内市场人气高涨,票房开始走高,全国各地开始追加影片拷贝。柏林国际电影节原在每年6-7月间举行,从1978年起提前至2月举行,为期2周。可以说《孔雀》的上映日期经过了精准推算。除了在国际上夺奖之外,《孔雀》档期优势还在于当年的春节与情人节时间相距过近,导致春节档电影《喜马拉雅星》和全明星阵容的《韩城攻略》,稀释了一部分情人节档期的票房,而春节的节日气氛过后,《孔雀》独树一帜的风格恰恰带给观众差异化的观影体验。《孔雀》的宣发将国际电影节和国内电影市场进行了巧妙的互动,借着获奖的势头,和档期的巧妙安排,为艺术电影打开了市场。
相比《孔雀》的顺风顺水,电影《立春》的上映可谓一波三折。首先因为后期制作的原因,电影错过了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其次,电影原定于2008年2月4日立春上映,但因南方雪灾不得已延后,转战进入大片云集的清明档期。而当时《见龙卸甲》票房领跑,加之《黄金罗盘》《史前一万年》《国家宝藏2》三部大片已占有市场约80%的额度。同时,电影上映距离女主演蒋雯丽夺得罗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也有一段时日,最终135万的票房不尽如人意。但从影片人物的设定上可以窥见,导演想要对标的依旧是国际市场与国内的联动。
《立春》四个主角身上,最鲜明的共性就是都习得西方艺术结晶。而李樯特意为蒋雯丽所写的王彩玲,热爱意大利歌剧的背景设定,让导演的创作意图也可见一二。《立春》在市场上的惨败,让顾长卫在《最爱》的商业化追求上显得极为迫切。在宣发层面上,更是将电影定义为一部时尚爱情偶像剧。事实证明,这部由章子怡和郭富城领衔主演的“时尚爱情偶像剧”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成效。加之蒋雯丽,王宝强,濮存昕,陶泽如,蔡国庆等一众演员颠覆性出演,更有姜文,冯小刚,陆川前来客串,近6000万的票房成为顾长卫“时代三部曲”票房之最。
“时代三部曲”对个体的言说,让顾长卫面临着艰难的生存困境。《孔雀》1600万的投资,票房累计收入1000万;《立春》投资2000万,累计票房135万;《最爱》首周票房达4000万,累计票房近6000万,从商业角度可以看出“时代三部曲”在电影市场上的困境。从内容创作角度来说,电影在时代背景的处理上涉及敏感题材,所以顾长卫同样要不断与审查博弈,在坚守与冒犯中不断前行。
四、结语
“时代三部曲”怀旧伤感的基调和日常生活化的呈现,都体现出在大片时代下,导演对个人风格和作者特性的坚守。在“第五代”开启大片时代,“第六代”进行主流皈依的时代背景中,顾长卫以底层人物的视角,诉说着平凡生命的平凡传奇。电影将历史搁置,聚焦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出导演一贯以来的人文情怀。他以极具作者特性的个体言说,在新世纪之后为自己寻得一处艺术的高地。正如《最爱》里远离中心,位于山顶的娘娘庙小学,也似乎成了顾长卫创作身份的一种隐喻。顾长卫“时代三部曲”的突围是艰难的,打破“唯美”书写“残酷”,展现了其自身特性,虽票房不高,但艺术创作的水准和商业性思维却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①黄式宪.第六代来自边缘的"潮汛"[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23-24.
②张晓琦.顾长卫专访:每一个生命都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J].电影世界,2011(4):48.
③袁庆丰.新世纪中国电影读片报告[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02.
④(德)叔本华,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52.
⑤罗志芬.从《孔雀》获奖谈艺术电影营销[J].东南传播,2005(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