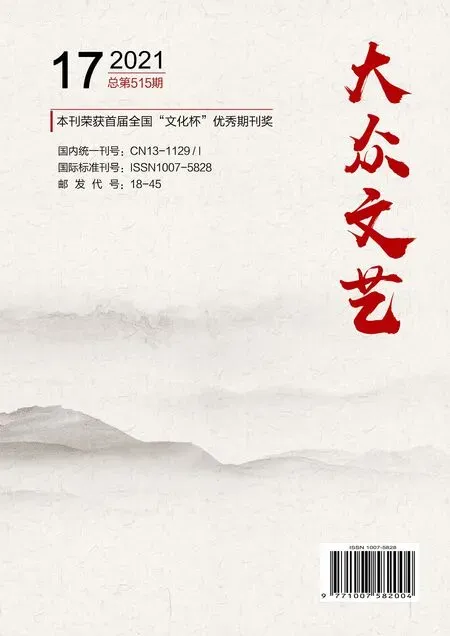迈克尔•博伊曼斯绘画表现语言的多样性
靖 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江苏南京 210023)
人类社会进入新媒体时代后,图像资源对当代绘画的变革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代艺术家不再局限在某一领域进行艺术活动,他们的创作开始涉足各种新艺术媒介或观念形式的表达,以及个体所处时代的价值与意义,比利时艺术家迈克尔•博伊曼斯就是其中的代表。迈克尔•博伊曼斯在继承传统艺术形式的同时,更注重对艺术形式进行观念性表达的探究。他创造出一种机械而符号化的人物形象,在看似无意义的状态下去呈现荒诞而富有深意的虚幻世界,其创作观念及绘画技巧在西方当代具象绘画领域具有非凡的影响力。
一、从传统绘画语言到新媒体的运用
作为欧洲油画诞生地的比利时,具象绘画在当代艺术发展中仍具有其可持续性,而肖像画的表现语言与技法在这一地区也不断被继承和发展。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当代艺术家迈克尔•博伊曼斯来说,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认为好的艺术家应该基于传统的基础而创造新的艺术。
在迈克尔•博伊曼斯的早期绘画中,可以看到印象派画家马奈的影子。例如他的作品《吹口哨的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马奈的《吹短笛的男孩》。马奈在这幅作品中改变了以往的作画习惯,他借鉴浮世绘的处理手法,以较为概括的用笔将《吹短笛的男孩》的画面背景平涂成明亮的灰色,一改往日追求立体空间的绘画习惯,向追求二维平面的画面表现迈出了一大步。同样,在迈克尔•博伊曼斯的《吹口哨的人》这幅作品中,处理背景的方式也采用单色平涂,即使有花纹背景,也被粗略带过,不做详细刻画,甚至用大笔触扫出了模糊的效果,只有投影又被细致的刻画,剔除掉了多余的细节。
此外,他还特意借鉴了马奈的《死去的斗牛士》,创作了《The Devil’s Dess》这幅画向马奈致敬。在作品《死去的斗牛士》中,画中的斗牛士斜躺在画面中央的地上,头倾斜向一边。背景是一个近乎黑颜色的色块,与人物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这样的人物动态,给迈克尔•博伊曼斯带来了启发。他在这幅作品中,安排了一个头面向右上角面部向上躺在地上的男人,身上穿着硬质材料制作的红色裙子。周围的背景被涂成了土黄色块,营造出类似老照片般的氛围,似乎暗示了特定时代的气息。迈克尔•博伊曼斯的安排似乎是在布置一场平静的、具有仪式感的行为艺术表演,他把人视为了没有特定含义的道具,我们无法看出画中人物面部的表情状态,他的脸似模糊似清晰,没有了可以在具体深入了解的特征。这或许是艺术家惯用的绘画形式,即取消人物的个性特征,只描绘肖像的共性,营造模糊不确定的气氛和感受。
从技法语言方面看,迈克尔•博伊曼斯的绘画在用笔及色彩表现上还借鉴了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他十分擅长运用土褐色的色块作为背景,将主体暗部与背景进行统一性处理,并在亮部用不透明色来提亮,使画面具有微妙而和谐的色彩关系 。他表现人物的服饰与头发等用笔轻盈而松动,摒弃琐碎的细节,在环境背景的融合中形成一定的空间感。从作品《索普》中不难看出博伊曼斯对古典油画技法的深入了解,他运用罩染法铺设画面,再对亮部使用不透明色进行提白,在加强塑造的同时保留用笔的灵活性,呈现出洗练而概括的画面效果。
由此可见,他对传统技法的继承和发扬似乎显得更加严谨,无论构图、色调还是笔法,都可以看得出并非一味地模仿,而是在对传统进行绘画精心研究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特点。
摄影和影像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当代绘画适应新科技的发展是现代社会科技发展、技术革新的必然结果。庞大的图像资源成了我们认知事物的快速方式,也成了艺术家拓展视角、表达更多艺术观念的重要途径。迈克尔•博伊曼斯的绘画对新媒介的借鉴和运用,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也呈现出虚无、荒诞和毫无倾向性的视觉特质。他时常在绘稿旁写下对影像创作的思考,对他而言,绘画更像是在做某种实验,他善于建造自己的二维空间,这个空间也具有一定的私密性。
在博伊曼斯的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组对于剧场模型的草稿。他设计了很多不同视角的场景,剧场里正在放映着他绘画中的巨大图像,譬如一个正在工作的、不具有明确特征辨识度的男性,他面无表情,机械地操作着,时间仿佛停止在那一刻。博伊曼斯还配合图像做了剧场模型的道具,模拟了剧场里的光线,如同做实验一般。自2004年开始,他的影像作品开始有了静谧的氛围,这一时期的绘画如同从影像中分离处理的图像一般,一并舍去了绘画中的叙事结构,绘画手法依旧来自传统,但带给观众的是另样的感受。借助这些本就无意义的形象,博伊曼斯将这些虚无、无意义的形象营造出一种静谧的氛围,这种视觉感知的荒诞和虚无恰恰是他成熟的艺术内核。博里曼斯带给观者以疏离感的代表作是《选择之屋》系列,他用油画、绘本和装置三种形式进行创作,这些屋子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窗户,夸张的比例与构造制造出多重假象。这个屋子不仅是一个模型,它还可以是臆想中的公寓、餐馆或是博物馆等,抑或是一间平静的庇护所。在此,每一扇窗户的排列似乎都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暗示着人生的各种可能性,给观众以遐想。
二、观念在绘画中的表达
在迈克尔•博伊曼斯的一些作品中,他喜欢运用具有多层次含义的元素进行创作,这些元素往往具有暗喻性,在艺术家对其进行巧妙的编排后,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作品《二十三个隐喻》中,他安排了二十三只燕子排列在墙上,而墙脚下聚集着一众人,从人群与燕子的比例可以看出,这不是单纯的描绘燕子飞过的景象,通过燕子的阵型,可以联想到战争时期战斗机在空中排列的队形。这是博伊曼斯在战争主题的作品中较为尖刻的一次尝试,他试图将观众带入一个毛骨悚然的军国主义世界,在动荡时期人的命运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在《野兔》这幅作品中,两个少年面无表情的低头看向其中一个少年手里抓住的野兔,而少年手中的野兔,四肢无力,身体瘫软,看似已经死去。野兔在欧洲经常出现在寓言故事和民间传说中,它们具有很强的隐喻性。野兔因为具有不能被驯化的属性,所以被看着自由的化身。画面光线被设置成了顶光,使得两个少年的面部处于暗部阴影,我们无法看清他们的真实表情,似乎他们在对野兔的遭遇进行思考,或是在野兔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画面强烈的光源对比制造些许的紧张氛围,潜在的含义被其象征性所复杂化了。象征物有时会被不同的艺术家赋予其特定的意义,但是这种手法带给作品以新鲜感和生命力。迈克尔•博伊曼斯对隐喻手法的运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在当代艺术家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
人物作为迈克尔•博伊曼斯的绘画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对象,经常带给人似近似远模糊不确定的感觉。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基本来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照片,这些画中人物的原型大多从他的一间工作室所设置的人造环境里拍摄而来的,其中也包括他的一些电影。他将作品中的人物视为容器一般,不具有任何的特殊含义,似乎在尽力避免与观众之间产生的关联,比如其中最明显的特点:画中的人物视线避开观众的视线,博伊曼斯不要求作品中产生任何叙事效果,只需要安排人物如果物体一般展示出来,取消其自主性。
三、神秘而静谧的调性
从对迈克尔•博伊曼斯的作品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他创作风格及手法的多样化,即向传统大师学习与借鉴的同时,又融入了当代艺术的观念元素,他还结合现代科技媒体,通过不同的手法对人性、人的生存环境等问题进行思辨和追问,具有鲜明的个人艺术特质。
迈克尔•博伊曼斯的作品不止局限于表面的形式,笔下的人物看似平常,却有着不平凡的举动,这些表面平静的人物,内心都隐含着某些痛苦和不安。他时常将人物形象置身于黑色基调的氛围中,冷静地专注于某种仪式,这些人物或喁喁私语,或无休止从事某种机械性活动,仿佛在日常中被注入了魔咒,营造出类似宗教的仪式感。如作品《假象之境中》,描绘了多人围观在微缩的三维景观之上,地上的模型让人联想到了战争与死亡,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艺术家对怪诞与神秘情节的偏爱。虽然画中我们看不到清晰的面部细节,但画面的氛围使得人物异常平静从容,透过他们的视线,我们感受到了博伊曼斯所要渲染的一种神秘氛围。
他在画面中创造了一个“神秘”而“静谧”的世界。神秘感往往源于题材与形式的相互作用,但主要还是体现艺术家的思想观念。他借用常人看似无意义的一些图像去描绘常人思维中无法理解的画面场景,这种无意义、不符合逻辑关系的视觉感受带给观者以强烈而深刻的印象。静谧感则来自他惯用的绘画表现手法,从他对画面元素的选用这一点来看,无论是静物还是人物,其动态与静态之间的界限都是模糊的。这就像一个无声的世界,即便安排了叙事性元素,也是让观者在默然中自体会其中的隐喻与讽刺。他在2013年的作品《天使》中,在三米高的画布中绘制了一位穿着粉色长裙笔直站立的青年女子,这位女子的脸上涂着看起来很厚重的黑色面膜。画中的形象灵感来源于同样是比利时人的模特儿克努茨。博伊曼斯有意将人物的面部特征用黑色覆盖,人物姿态处于静止的状态,在宁静中却尽显张力,时间仿佛在画面中停滞,人物与空间在如此矛盾的氛围中交相呼应。女子脸上的“面具”似乎也是一种人物摆脱个人情感的特征,这种手法使得画面欲言又止的静谧氛围得以显现。
四、结语
迈克尔•博伊曼斯对当代具象绘画有独特的理解,他利用传统绘画的技巧和韵味包裹着自己独有的观念内核,给观众创造出了虚无荒诞的场景氛围。他对主题的选择、对经典的借鉴,还有图像的挪用都恰到好处,其艺术表现语言丰富而多样。他的作品并非只有荒诞和无意义,神秘而静谧的调性背后是一种反叛精神,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入思考。同时,他对绘画表现语言多样性的探讨与实践,打破了人们对架上绘画日渐衰落的惯性思维和普遍性认知。他的观念性表达以及对荒诞而富有深意的虚幻世界的呈现,在西方当代具象绘画领域中独树一帜,也使其成为比利时最具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