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诗论》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设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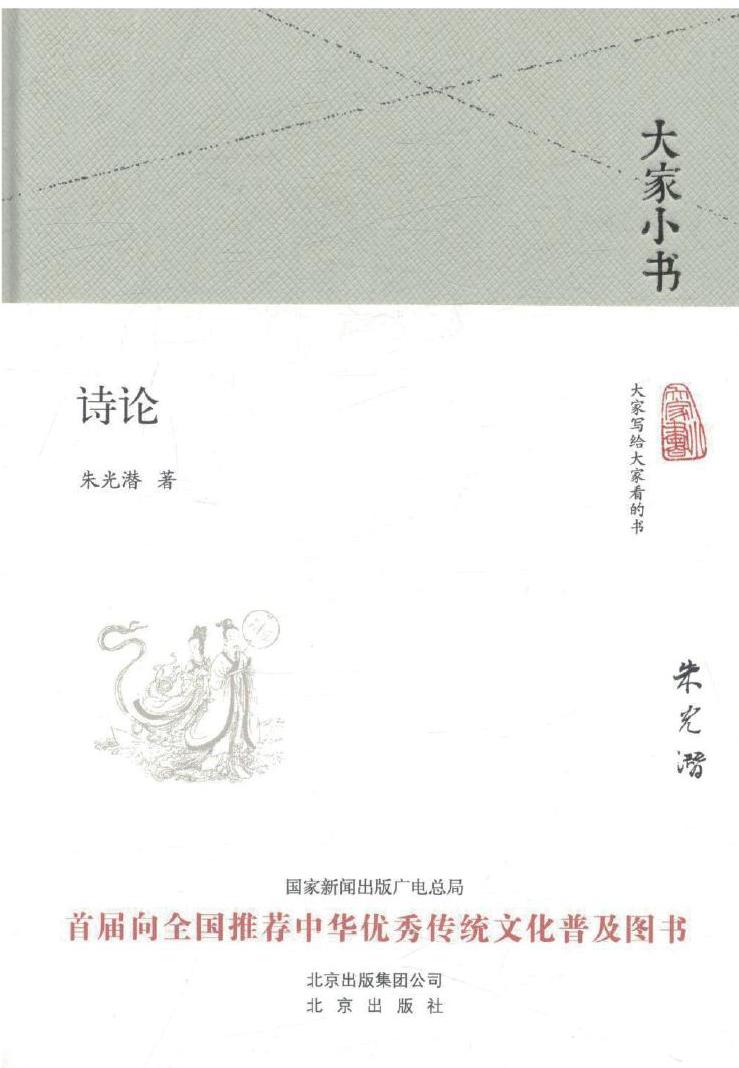
摘 要:朱光潜的《诗论》对创建中国比较文学学派有着重要的贡献。《诗论》中,朱光潜不仅以平行研究的方法,积极开展中西文学的比较,更是较早地运用西方理论阐释、分析中国文学作品,使中国文学作品获得别开生面的意义,揭示了“阐发研究”不同凡响的理论价值。同时,他在中西诗学、美学双向阐发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有力纠正了早期阐发研究单向阐发的偏颇,向西方学者彰显了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在阐释西方文学作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美学走向世界。
关键字:朱光潜;诗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研究成果。
朱光潜先生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创建有着重要贡献,然而他在美学、文艺学上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遮蔽了他在这方面的建树,因而除少数学者鲜有提及外,在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及比较文学史著作中更是不见朱光潜先生这方面的独特成就。
朱光潜先生自1925年至1933年留学海外期间先后完成了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写出了《文艺心理学》,出版了《变态心理学》等著作,这些书都是运用西方心理学理论,解释中西文学创作,剖析中西文学现象,令人信服地分析作品的主旨及人物形象的佳作,其对于促进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不亚于鲁迅、茅盾、吴宓等人。尤其是朱光潜先生1931年在国外写成,并于1941年由国内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的《诗论》,更是对创建中国比较文学学派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这一贡献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首先,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论述中西诗在情趣上的相同与不同,给人极大的启迪,打破了此前比较文学囿于西方地域内的局限,还让西方学者开始了解中国文学,让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须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正是一个新学派得以成立的依据之一。
他指出:“西方诗和中国诗的情趣都集中于几种普泛的题材,其中最重要者有(一)人伦(二)自然(三)宗教和哲学几种。”[1]85这是相似点也是不同点。诗的情趣集中于这三种题材,这是相同的,但诗的情趣在每一种题材内表现的内涵及偏向程度既有相同又有不同。拿诗表现人伦来说,朱光潜认为“朋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谊在西方诗中不甚重要,而在中国诗中则几与爱情占同等位置”[1]85-86。中国叙人伦的诗大半是君臣、朋友间赠答酬唱的作品。而恋爱诗远不如西方诗的重要。中国有的诗表面看是爱情诗实则却是表达理想的政治诗。如屈原的《离骚》,诗中倾诉着对美人的思念与爱慕,其实是作者忠君爱国思想的渲泄。即便是爱情诗,西方的爱情诗表现得是热烈奔放,而中国的爱情诗则是委婉含蓄。造成这样的原因,朱光潜从中西文化的根源上分析,十分到位。他指出:“第一,西方社会表面上虽以国家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个人主义。”[1]86“中国社会表面上虽以家庭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兼善主义。”[1]87“第二,西方……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在学问和情趣上往往可以与男子诉合。”[1]87“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女子地位较低。夫妇恩爱常起于伦理理观念,在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乐趣颇不易得。”[1]66第三,“西方人重视恋爱……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1]87虽然朱光潜没有从经济形态上分析社会风气、民族性格带给中西伦理诗的不同,但这种从诗作的差异深究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源,或者说从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揭示诗作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正是平行研究的命脉所在。它剔除了为比较而比较这一比较文学研究的垢病,直抵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在当时确为不易。同样,诗歌情趣在对自然的描写上,中西诗歌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朱光潜分析道,中西方歌颂自然的诗都产生较迟,但相较而言,中国的自然诗起于晋宋之交,远比西方产生浪漫主义运动的自然诗要早一千三百年的光景。而且就中西方自然诗的总体风格来说,“一个以委婉、微妙简隽胜,一个以直率、深刻铺陈胜”[1]89“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荒谷,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色,是月景。”[1]89这样的比较大体正确,西方主要是商业性的社会经济形态,海上贸易是其主要的经济活动,天人对立思想较为严重;中国古代是农业性的社会经济形态,先民们大都恪守“天地自然,孕成万物”的理念,“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小桥流水、月光疏影,造成中国先民对自然有一种亲切感、依附感,很早就产生“天人合一”的思想。由此形成中西方自然诗在题材和手法上的不同也就不奇了,朱光潜的分析无疑正确。但朱光潜对中西诗歌情趣深浅的结论却不能令人信服。他认为中国诗总体而言较为肤浅与不深刻,这是因为中国古人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操的淡薄。中国诗是否肤浅与不深刻,原因是否仅是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操的淡薄?朱光潜显然受黑格爾认为中国人缺少思辨性的影响,这大可商榷。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如朱光潜所说:中国人“处处都脚踏实地走,偏重实际而不务玄想,所以就哲学说,伦理的信条最发达,而有系统的玄学则寂然无闻”[1]92“中国民族性是最‘实用的,最‘人道的。它的长处在此,它的短处也在此。”[1]92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由此就判定中国诗为肤浅,我们却难以苟同。屈原、李贺、李商隐的诗就颇耐人寻味,而且中国古代哲人老子、墨子等也不缺思辨能力。不过朱光潜先生始终将中西文学的比较深入到中西文化传统的深层次中剖析原因,是值得称道的。
二
其次,朱光潜先生较早地运用西方科学的理论评析中国诗歌手法的意义,体现了“阐发研究”的实绩。
朱光潜先生早年留学欧洲,曾一度醉心于西方心理学。他先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过《变态心理学派别》《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书,同时用英文写出《悲剧心理学》博士论文,获得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博士学位,该书也于1933年由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他又痴迷于美学,尤其对黑格尔、克罗齐、维科的美学情有独种,有着很高的学术建树。这就使得朱光潜先生能较早地运用西方美学理论尤其是心理学理论分析中国诗歌的创作手法与价值。朱光潜对西方的“移情说”研究颇深,他常用西方的移情理论分析作品。他认为作者在创作中,只有将内在的情趣和外来的意象相互融合,才能创作出不朽之作。朱光潜说:“物我两忘的结果是物我同一。观赏者在兴高采烈之际,无暇区别物我,于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复交流,在无意之中,我以我的性格灌输到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比如观赏一棵古松,玩味到聚精会神的时候,我们常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心中的清风亮节的气慨移注到松,同时又把松的苍劲的姿态吸收于我,于是古松俨然变成一个人,人也俨然变成一棵古松。总而言之,在美感经验中,我和物的界限完全消灭,我没入大自然,大自然也没入我,我和大自然打成一气,在一块生展,在一块震颤。”[2]这种物我同一的现象即是德国美学家所说的“移情作用”。
“移情作用”就是主体在观照外物时,把自己的情感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但移情作用不只是一种情感的外射,外射作用由我及物,是单方面的;移情作用由我及物,也由物及我,是两方面的。在外射作用中,物我不必同一;在移情作用中,物我必须同一。所以,朱光潜说:“移情作用不单是由我及物的,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它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所谓美感经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3]这样产生的作品才是有意境的作品,才具有感染人的魅力。他举例说,陶潜的“悠然见南山”、李白的“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应如是”、姜夔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流芳百世,都是作者面对物象,产生了移情作用。朱光潜说:“每人所见到的世界都是他自已所创造的。”[1]62陶潜,李白、辛弃疾、姜夔所见到的都是山,“在实际上却因所贯注的情趣不同,各是一种境界”[1]62,所以,“物的意蕴深浅与人的性分情趣深浅成正比例,深入所见于物者亦深,浅入所见于物者亦浅。诗人与常人的分别就在于此”[1]62。这正是创作好诗的诀窍所在。好诗应是诗人的独特发现,应包蕴诗人的真挚情感。朱光潜的剖析在当时的确震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
朱光潜还用移情作用分析中国古代诗歌的欣赏。他举姜夔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为例,说明“欣赏与创造并无分别”。诗人写这句诗,先就在观赏自然中见到这种境界,感到这种情趣,然后用这九个字把它传达出来,读者在读这句诗时,同样要用心灵综合作用,领略出姜夔原来所见到的境界,每个人所能领略到这诗的境界,完全取决于读者各人“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1]63“各人在对象中取得多少,就看他在自我中能够付与多少,无所付与便不能有所取得。”[1]63也就是说,欣赏作品也需有移情过程。创作时,作者与所咏对象进行情感交流,达到物我同一;读者欣赏作品时,也只有与作品心心相印,黙契无间,产生情感交流,才能进入欣赏极致。朱光潜还指出,中国不少古诗有令读者常读常新的感觉,或者能百代流传、脍炙人口,就在于作品留下给读者再创造的空间,欣赏一首诗就是再造一首诗。“每次再造时,都要凭当时当境的整个的情趣和经验做基础,所以每时每境所再造的都必定是一首新鲜的诗”[1]63“真正的诗的境界是无限的,永远新鲜的。”[1]63朱光潜也就用西方心理学的理论解释了中国古代优秀诗作何以百读不厌、历久弥新的原因。这里,还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朱光潜的“欣赏也是在创造”的结论,实际上启发了后人开启接受美学的思想。
此外,《诗论》中,朱光潜先生还用西方的“游戏说”解释中国古代民歌的不朽价值,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朱光潜在《诗论》中说:“艺术和游戏都像斯宾塞所说的,有几分是余力的流露,是富裕生命的表现。”[1]48-49其实,文学艺术起源于游戏,是西方较为普遍的观点之一。康徳、弗洛伊德都曾谈论过文学艺术与游戏的关系。康徳在《实用观点的人类学》一书中提到心灵游戏的观点,曹俊峰在《康德美学引论》中指出:“康德论述心灵的游戏和幻象时,透露出一种思想:艺术和审美活动就是对心灵特别是感性的欺骗,就是人为了欺骗自已的感性而人为创造出来的。”[4]75“心灵需要游戏,也需要欺骗,这就是艺术和一般审美活动的根源。”[4]75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进一步提出了“自由游戏”的概念,认为审美活动的本质就是自由游戏。在人的认识活动和伦理活动中,想象力、知性和理性都不是自由的,都必须受到约束,而只有人的审美活动,想象力、知性和理性才能处于自由游戏之中,审美活动的每一过程、每一方面都是自由游戏的结果。弗洛伊德在揭示创作与梦的联系时,也认为作家在创作中就象儿童在游戏中一样,都是在充满激情地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并在幻想世界中得到满足的乐趣。这就说明西方的游戏说,都强调艺术创作是自由的、非功利的,仅仅是满足人的审美愉悦、发泄旺盛的生命力或为“力比多”寻找出路。朱光潜用这样的观点分析中国民间歌谣,不仅说明了歌谣中一些手法产生的必然,还正确评价了歌谣的社会价值。朱光潜说:“民间诗也有一种传统的技巧,最显而易见的是文字游戏。”[1]25民间诗的手法有三种:“第一种是用文字开玩笑,通常叫做‘谐;第二种用文字捉迷藏,通常叫做‘谜或‘隐;第三种……通常无适当名称,就干脆地叫做‘文字游戏亦无不可。”[1]25在艺术中他举三棒鼓、拉戏胡琴、相声、口技、拳术之类,诗歌中特别指出民俗歌谣。他从《北平歌谣》举两首民谣为例,说明歌谣的这种搬砖弄瓦式的文字游戏,重点不在歌谣的内容意义,而在声音的滑稽凑合,深得民众的喜爱,“他们仿佛觉得这样圆转自如的声音凑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巧妙”[1]50。这种巧妙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创造精神,显示了“限制中争得的自由”[1]49“规范中溢出的生气”[1]49的价值,这也是艺术使人留恋的所在。朱光潜先生用西方的理论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歌谣的艺术成就,有利于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也体现了比较文学的价值作用和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
三
最后,也是重要之点,在于朱光潜先生最早尝试中西诗学的相互阐释与印证,纠正了早期“阐发研究”单向阐发的偏颇。
中国和西方文化传统的回异及相对独立发展,以及各自民族偏爱的文学样式的差异,造成中西方文论有着显著不同。中国古代文论讲神韵、性灵、意境,重感悟,有着较多的直观性,不象西方重分析、重论辩,有着很强的系统性。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的特点,不如西方文论范畴的明晰与确定。中国古代的美学观点强调美与善的结合,而西方的美学观普遍认可美与真的一致。因而,中西诗学、美学的比较,可以互相印证,取长补短。由此建立更为科学、全面的诗学、美学理论。在这方面,朱光潜先生是有着重要贡献的。
朱光潜十分赞同王国维关于诗词的“境界说”,但他又折中了克罗齐的“直觉说”、立普斯的“移情说”、布洛的“距离说”及谷鲁斯的“内模仿说”,对王国维的境界说作了分析与发挥。朱光潜认为,“每首诗都自成一种境界”[1]54,正如王国维所说的“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5]。朱光潜对此作了进一歩阐述,他说:“诗是人生世相的反映”[1]54“诗对于人生世相必有取舍,有剪裁……必有作者的性格和情趣的浸润渗透。”[1]54境界就是情景合一的产物。朱光潜接着用西方的移情理论来说明“内在的情趣常和外来的意象相融合而互相影响”[1]60。他举例说,比如欣赏自然风景,一方面,心情随风景千变万化;另一方面,风景也随心情而变化生长。情景相生而且契合无间,“即景生情,因情生景”,这正是情景相融的好境界,也是移情产生的美好诗境。移情作用不仅仅是将主观的情感外射到物的身上,而且也由物及我,最后达到“一切景语皆情语”、物我同一的地步。好诗的境界就在于“在刹那间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以小见大,给人浮想连翩、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感受。朱光潜先生认为“诗的境界是用‘直觉见出来的”[1]57,是观者直接对形象的感性认识,而非运用概念的理性认识。当然,朱光潜先生并不否定思考和联想对于诗的重要,但“思索之后,一旦豁然贯通,全诗的境界于是像灵光一现似的突现在眼前,使人心旷神怡,忘怀一切”[1]58。朱光潜认为,这就是“想象”,也就是“直觉”。朱光潜先生就是这样,在中西理论的互参中,将王国维的“境界说”上升到理论层面,给人心悦诚服的阐释。朱光潜先生还用西方象征派理论,对王国维关于诗的“隔”與“不隔”的理论提出不同看法。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诗的境界分为“隔”与“不隔” 两种。“隔”与“不隔”的区别在于语言的运用,“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否则就是“隔”。他举例说“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便是“不隔”,而“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王国维是赞赏“不隔”的境界的。朱光潜不同意王国维的这一看法,他说:“王氏所说的‘语语都在目前的标准太偏重‘显”,而“象征派则以过于明显为忌,他们的诗有可能正如王氏所谓“隔雾看花”,迷离恍惚,如瓦格纳的音乐”[1]65。“不隔”的诗有可能太过于显,不见得是好诗;“隔”的诗也可能象瓦格纳的音乐,是好诗。朱光潜继续论道:“‘显易流于粗浅,‘隐易流于晦涩。……但是‘显也有不粗浅的,‘隐也有不晦涩的。”[1]65朱光潜先生还指出,由于人的生理与心理的不同,对诗的“显”与“隐”也各有偏爱。“有人接受诗偏重视觉器官,一切要能用眼睛看得见,所以要求诗须‘显,须如造型艺术。也有人接受诗偏重听觉与筋肉感觉,最易受音乐节奏的感动,所以要求诗须‘隐,须如音乐,才富于暗示性。”[1]66朱光潜先生用人的心理差异说明,不能简单地认为“不隔”的诗优于“隔”的诗,“隐”与“显”各有千秋,因人而异,不可一概而论。
朱光潜先生就是这样,立足于世界文学的高度,运用中西诗学比较的手法,一方面对王国维的“境界说”提供了西方相关理论的互参与阐释,使“境界说”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弥补了“境界说”囿于一国诗歌的理论缺憾,使这一理论更为科学与全面。朱光潜先生在中国比较文学理论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而令人称道的。
四
综上所述,朱光潜先生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功莫大焉。朱光潜先生不仅以平行研究的方法,积极开展中西文学的比较,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内涵,更是较早地运用西方理论阐释、分析中国文学作品,使中国文学作品获得别开生面的意义,给读者另辟蹊径的启迪,从而揭示了“阐发研究”不同凡响的理论价值,这就为“阐发研究”最终为中外学者接受,使之成为比较文学重要方法之一,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同时,他在中西诗学、美学的双向阐发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有力纠正了早期阐发研究单向阐发的偏颇,启动了中国古代诗学、美学的当代价值,向西方学者彰显了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在阐释西方文学作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美学走向世界。
正是由于朱光潜先生及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的共同努力,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才得以创立并为学界认可。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诗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2]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朱光潜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214.
[3]朱光潜.谈美[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8:23.
[4]曹俊峰.康德美学引论[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
[5]王国维.人间词话[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14.
作者简介:吴家荣,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师大皖江学院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