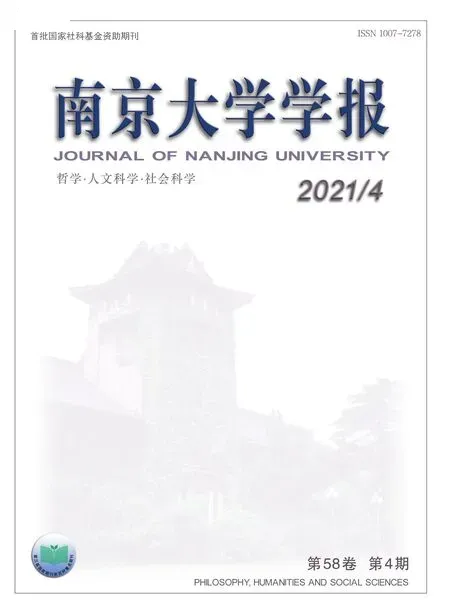国民革命与医学群体
——以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伤兵救护为中心的考察
张 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国民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后,当地各个社会阶层均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对于医学群体来说,亦是如此。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医学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国民政府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亟需医生、医学机构、医学社团的协助与支持。救护伤兵本是一个与医疗相关的问题,然而在国民革命的特殊历史情境下,此问题又与政治、中外关系、宗教、民众运动等因素纠缠在一起。到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出现伤兵救护的危机时,国民政府与医学群体之间复杂而多元的关系集中体现出来。
近年来,民国时期政府与医学群体间的关系问题已渐引起学界注意,但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及其对医学群体的影响,学界关注较少,或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存在时间较短,其相关政策未产生多少历史影响。学界对于北伐时期在华基督教会所受反帝运动及非基督教运动冲击问题已有诸多讨论,也有学者考察了在此背景下教会医疗事业所受影响。博格探讨了南京事件后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处境及其对国民革命、国民党,以及教会未来发展的看法;杨天宏对从五卅运动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期的非基督教运动做了研究,并对北伐期间教会的受损状况做了考察;李传斌探讨了南方与北方教会医院受北伐影响情况(1)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New York: America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7, pp.359-365;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7-373页;李传斌:《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时期的伤兵救护问题,学界缺乏较为充分的探讨(2)对此问题,一些相关人物的研究有所涉及,如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159-161页;钱益民、颜志渊:《颜福庆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8-99页,等等。张静考察了第二次北伐时期的救伤危机之由来,以及国民政府对救伤的应对及国民革命军卫生后勤机关的举措,重点探讨各民众团体在救护中所发挥的作用,张静:《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中的伤兵救护——以伤兵救护组织为中心》,《军事历史研究》2020年第5期。。本文以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时期的伤兵救护为中心,通过梳理自北伐军克复武汉至“七一五”事变前后,各地特别是武汉三镇的医生、医学机构、医学社团与国民政府的交往及其境遇,考察武汉国民政府与医学群体之间复杂而多元的互动关系。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是在医院、医学教育机构、医学团体、慈善组织中工作的医生,至于私人诊所医生和军医等,则不作为重点讨论的对象。
一、武汉克复后的国民政府与医学群体
“西医最初是通过英美传教士在我国设立医院传入中国的。这当然是传教士们的传教手段之一,客观上起到了引进和推广西医的作用。”(3)张孝骞:《湘雅医学院的缘起和变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页。由于现代医学在中国发端及发展的特殊路径依赖,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各地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医院及医学教育机构,多由欧美教会或慈善组织创办;许多接受了现代医学教育的中国医生,与来自欧美国家的传教士医生,皆在此类医学机构中服务。就武汉三镇而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英美教会循道会、伦敦会、圣公会先后在汉口、武昌设立普爱、仁济、同仁等医院(4)普爱医院(Hodge Memorial Hospital),前身为1864年由英国循道会创办的危斯理会医院,是武汉第一所西医医院。仁济医院(London Mission Men’s Hospital),1886年由伦敦会在汉口创办,1928年与普爱医院第二分院合并,成立汉口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其前身为圣公会医院(St.Peters Hospital),1876年由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创办,时为文华书院(Boone Memorial School)的校医院,辛亥革命后扩建为同仁医院(the Church General Hospital),并由文华独立。。至北伐军克复武汉时,这些教会医院在规模、设施、医护人员配置等方面,仍是当地条件最好的。
北伐军克复武汉前后,当地西医医院的大体状况为:至1926年末,武汉共有西医医院25所,病床989张,卫生技术人员255人。其中,教会医院10所,病床685张,卫生技术人员129人;日本同仁会医院2所,病床123张,卫生技术人员50人;社团医院1所,病床100张,卫生技术人员38人;公立企业医院1所,病床20张,卫生技术人员7人;私立医院11所,病床61张,卫生技术人员31人。此外,另有驻军医院3所,病床及卫生技术人员情况不详(5)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卫生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2页。。
总体来看,在此时期,武汉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于教会医院,市立医疗机构缺乏,各医院规模都不很大,医护人员人数和病床数量均属有限。
在护理教育方面,清末时普爱、仁济、同仁医院先后开办了汉口普爱男、女护校,汉口仁济男、女护校,武昌同仁高级护校(6)1888年,汉口普爱男、女护校成立。1905年,汉口仁济男、女护校成立。同年,武昌同仁高级护校成立。。武汉最早的高等医学教育机构是1902年伦敦会的纪立生(Thomas Gillison)在汉口创办的大同医科学校,1917年该校并入齐鲁大学医科(7)纪立生(1859-1937),英国人,毕业于爱丁堡大学。1882年受伦敦会之派来华,任汉口仁济医院院长。1902年兼任伦敦会医科学校校长,该校后更名为大同医科学校。1917年该校并入齐鲁大学医科,纪立生到济南工作。1923年回到汉口,任仁济医院院长。1928年,仁济医院与普爱医院合办的汉口协和医院成立,纪立生任院长,1929年退休,1937年病逝于汉口。。1922年,留德博士陈雨苍在武昌创办湖北省立医学专门学校,1924年该校改为省立医科大学(8)陈雨苍(1889-1947),字少峰,湖北荆门人,1911年毕业于湖北陆军军医学堂。武昌起义后参加阳夏战役。先后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德国柏林医科大学,1916年获得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内务部卫生司行走。1921年回湖北,1922年创办湖北省立医学专门学校,任校长,1924年该校改为省立医科大学。1927年在汉口开诊所,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被捕,出狱后任上海国立同济大学秘书长兼医学院院长,1942年任国民政府司法院法规委员会名誉秘书,1947年病逝。。直至1926年,武汉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仍处于较为初步的阶段。
1.北伐战争对于医学群体的影响
随着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各地反帝运动及非基督教运动空前高涨,各教会及其下属医院、学校等机构受到战事与民众运动的双重冲击。1926年底至1927年初的收回汉口英租界事件以及1927年3月的南京事件,对这些机构造成的冲击尤大。
就教会医院及医学教育机构而言,一些机构中的大多数外籍医护人撤往上海,部分人进而离开中国,这些机构由中国医生暂时管理及维持;还有一些机构被迫关闭。北伐时期,设于上海的博医会(9)博医会最初由医学传教士发起,历经数十年发展,在当时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医学专业团体之一。其前身是1838年由医学传教士建立的“在华医务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1886年改名为“中华基督教博医会”(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1923年,为淡化教会色彩更名为“中华博医会”(the 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定期召集年会,出版《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1932年,博医会并入中国医生发起的中华医学会。出版的《博医会报》密切关注教会医学机构的命运。据博医会执行干事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 Jr.)所做的一项调查,截至1927年5月底,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福建、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上海、安徽等省市的170所教会医院中,除云南的5所医院情况未明外,有35所大体正常运转,由外国或中国常额人员管理,或处于外方的经常性监督之下;71所根据临时性安排由中国职员管理;4所被军队占用由军医管理;55所关闭(10)James L.Maxwell,“Present Position of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5), 1927.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 Jr.,1876-1951),亦译作“马雅各二世”,英国人,麻风病专家,是传教士医生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 Sr.,1836-1921)之子,隶英国长老会,1900年在台南新楼医院任职,1923年任博医会执行干事。。
就两湖地区的情况而言,湖南的反帝、非基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教会医学机构受影响的程度最为严重。至1927年春,全省教会医院除一两所外均已关闭(11)James L.Maxwell,“Present Position of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5), 1927.。此时期,著名的湘雅医科大学是受损失最严重的医学教育机构之一。湘雅医科大学原名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14年由美国雅礼会与湖南育群学会合作创办,颜福庆任校长(12)颜福庆(1882-1970),祖籍福建厦门,祖父一代移居上海。颜福庆先后毕业于圣约翰书院医学院、耶鲁大学,获医学博士。1910年应雅礼会之聘任职于长沙雅礼医院。同年,加入博医会,成为该会首位华人会员。1914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成立,颜福庆任校长,胡美(Edward H.Hume)任教务长,雅礼医院更名为湘雅医院,胡美兼任院长。1915年,颜福庆与伍连德等发起中华医学会,任会长。1925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更名湘雅医科大学。1926年底,颜福庆离开湘雅,到汉口。1927年5月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校长。10月在上海创办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28年,任校长。同年,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院长。1938-1940年,任内政部卫生署署长。1949年后,任上海医学院副院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上海分社主任委员等职。1970年,病逝于上海。。1925年5月,受收回教育权运动推动,湘雅医科大学改由育群学会组织的中国校董会管理,湘雅医院仍由雅礼会与育群学会合办。1926年秋,受北伐军进军湖南的鼓舞,湘雅医科大学学生积极参加长沙各项游行、示威、宣传等革命活动。11月,该校学生为反帝、反基督教、收回教育权,发动学潮;湘雅医院的护士、工役亦发动工潮。12月,外籍教师、校长颜福庆及大部分中国教师相继离开长沙,次年春,该校停办(13)张孝骞:《湘雅医学院的缘起和变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11页;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35-238页;钱益民、颜志渊:《颜福庆传》,第35-42、65-71页。。在此前后,一些湘雅学生,特别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担任军医或从事政治宣传工作(14)敏猷:《从湘雅到湖南医学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2-24页。。湘雅医院由省政府接办,因经费支绌、人员缺乏,暂时关门停业。
湖北的情形略有不同。在此时期,武汉三镇由英美教会所办的八所教会医院(含循道会所办三所、伦敦会所办三所、美国圣公会所办两所),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反帝运动的影响,但至1927年5月各医院皆在继续运转,大多临时由中国医生管理。以当地最大的教会医院——普爱医院为例,北伐军攻克武汉后,1926年11月初,该院护士与护士生在工会领导下,为争取自身权益、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而举行罢工,医院暂时关闭一个月。12月底,汉口各界群众举行反英大会。普爱医院及其护校的护士、护士生也在医院、学校进行反英、反基宣传。英籍院长贝福臻(John E.Pell)及护士长离开武汉。江虎臣接任院长,率中国职员维持医院工作(15)江虎臣(1883-1962),湖北黄陂人,毕业于武昌博文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1913年,受循道会之派,任大冶普爱医院院长,1921年,任汉口普爱医院副院长,1926年底,任院长。1941年至1945年,兼任汉口普仁护校校长。。江虎臣上任后,鉴于医护人员已大为减少,将院中原有84张病床减少到57张。1927年3月,为避免病房被军队或政治组织占用,又将病床恢复至84张。在工会的组织下,普爱的护士、工役又曾数次发起争取自身权益的运动,院方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经江虎臣等的努力,该院工作逐渐恢复正常。从1927年初至4月底,该院的28名护士中先后有8人离开医院,加入国民革命军,成为军医。南京事件发生后,美、英两国领事馆要求各自的侨民由武汉撤离,普爱医院女医院(Jubilee Women’s Hospital)的院长撤往上海,也有一些外籍医护人员未撤离。4月,施德芬(Gladys Stephenson)到普爱医院担任护士长,数名资深护士亦回归,该院护理工作渐回正轨(16)J.E.Pell,“The Hodge Hospital Hankow,”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2), 1927; H.Owen Chapman,“Hodge Memorial Hospital(W.M.M.S.), Hankow:Progress Report,”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5), 1927.施德芬(1889-1981),英国人,1915年受英国循道会之派来华,先后在汉口普爱医院、安陆普爱医院等地任职,1924年任中华护士会会长。。除武汉以外,湖北各地尚有七所教会医院,其中有五所临时由中国职员管理,两所关闭(17)James L.Maxwell,“Present Position of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5), 1927.。
国民政府对于外国教会所办医院、学校等机构的态度十分复杂。一方面,国民革命以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号召,支持反帝运动、非基运动,支持工会组织、学生组织的相关活动。在战争中,教会的医院、学校等建筑,也容易成为军队、党部进驻的目标。另一方面,武汉政府也害怕反帝运动过于激进或盲目排外,以致影响到其与列强间的外交谈判,甚至引起列强的武装干涉,因此武汉国民政府曾多次下令保护外国人私产及教产。特别是南京事件发生后,美、日、英等国一面在外交上对武汉国民政府施压,一面增派军舰在长江逡巡。1927年4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多次讨论工人抵制外商、军队骚扰外国人私宅、教会房产被占等问题(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35-1061、1065-1078页。。4月20日,中政会决议:“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域之内,外人所办学校校舍、教堂及其他房屋,如愿租借者,悉听自由;其不愿租借者,均在受国民政府保护私人财产法令保护之下,无论何人不得强行占据。”(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第1073页。此外,在医疗卫生领域,国民政府亦需要利用教会医学机构的相关资源,与其进行合作。
武汉克复前后,一些国人自办的医学机构亦受到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武昌围城期间,湖北省立医科大学关闭。1926年12月底,国民政府将省立医科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私立中华大学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次年2月正式开学。1926年底,汉口慈善会中西医院因资金困难,改为汉口卫戍区医院,收治北伐军伤兵。
2.国民政府与医学群体在卫生领域的合作
1902年,袁世凯于天津巡警所设卫生科,是为中国自办公共卫生事业之始。清末新政时期,清廷在巡警部警保司设卫生科。辛亥革命后,各地公共卫生管理承袭旧制,归于警政之下,卫生事权不统一,缺乏专业技术与人才。1920年,广州市设立卫生局,因广东省内无其他卫生行政机关,该局实际办理全省卫生事务。1925年,在兰安生(John B.Grant)的倡导下,北京协和医学院与京师警察厅合作,在内左二区设立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20)兰安生(1890-1962),生于宁波一个加拿大医学传教士家庭,毕业于密歇根大学、霍普金斯大学。1918年任职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1921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驻华代表、北京协和医学院副教授,1923年创办该校公共卫科,任主任。。因成效良好,于次年将名称中“试办”二字删去,其公共卫生实践渐引起各地的关注与效法(21)1928年,更名为“北平特别市第一特别卫生区事务所”。。1926年8月,上海设立淞沪商埠卫生局,专管卫生事务。
北伐军克复武汉后,1926年9月,湖北政务委员会成立。湖北政务委员会先后在汉口、武昌设立市政委员会、市政厅,以改良市政,建设新都市。在卫生领域,两市均设立专门的卫生行政机关,任用专业人才,展现出一种重视发展卫生事业的姿态,由此也吸引了一批中外公共卫生专家来到武汉,协助政府规划卫生事业。
1926年10月,汉口市政委员会设立,下设财政、公安、教育、工务、卫生、统计各局,并统辖第一特区管理局、第二特区管理局,由汉口市长刘文岛及上述八局局长任委员。汉口市卫生局是武汉第一个专管卫生的行政机关,陶冶公任局长(22)陶冶公(1886-1962),名铸,字冶公,号望潮,浙江绍兴人,早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1905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明治大学附设经纬学堂、国立长崎医学专门学校。1907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回国,任沪军第五先锋队第五队指挥官,参加光复南京之役。民国成立后,回长崎医学专门学校读书,1913年毕业回国,同年,参加二次革命,1918年入北京陆军讲武堂进修。1926年7月南下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10月,任汉口市卫生局长。。1927年初,公共卫生专家,曾在中央防疫处、京师警察厅公共卫生事务所、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处任职的黄子方放弃协和医学院的教职,来到武汉,在汉口市卫生局担任科长(23)黄子方(1899-1940),生于厦门,先后毕业于香港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等,1924年任中央防疫处技正,1925年任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卫生科主任,后兼保健科、统计科主任,1927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名誉讲师,后赴汉口,任汉口市政委员会卫生局局长。1928年,任北平特别市卫生局局长。。3月初,陶冶公辞职,黄子方代理卫生局长(24)《汉口市两局长辞职》,《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7日,第3张第2页。。在此时期,黄子方为中国未来五年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构想了计划,共分三层:“国家公共卫生总机关计划”“中央卫生模范城计划”“卫生模范区计划”(25)黄子方:《中国卫生刍议》,《中华医学杂志》第13卷第5期,1927年10月,第338-354页。。
1926年12月,武昌市政厅成立,下设秘书处、财政局、工务局、公安局、教育局、卫生局、土地局,黄昌谷任市长。在黄昌谷的就职典礼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徐谦致训词,提醒其要特别注意卫生事务,“而此项经费,所需无几,如能即时办到,可免人民瘟疫等症”(26)《武昌市长昨日就职情形》,《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3日,第3张第2页。1月21日,武昌市政厅方正式成立。徐谦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兼司法部部长。。
其时,武汉缺乏公立医院,贫苦市民的看病问题难以解决。为尽快建立市立医院,1927年2月,汉口市卫生局向普爱医院和仁济医院提议:将两医院及其所属女医院置于卫生局管理下,以市立医院的形式,运转二至三年;四家医院现有全部职员留任,工作如前,并协助政府做一些公共卫生工作;双方成立联合委员会,共同管理。此提议令这些处在反帝运动压力下的教会医院感到意外与振奋。在他们看来,在四下教会机构纷纷关闭的浪潮中,这是解决目前问题难得的一个现实途径。成为市立医院可以淡化这些医院自身的外国色彩,减轻其所受反帝运动的压力;新承担的职责所导致的额外支出则将由市政当局负担。面对这样一个建设性方案,各教会医院迫切希望与国民政府达成合作。各医院与汉口卫生局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协商,特别是在黄子方主持卫生局期间,协商进展颇为顺利,协议几近达成(27)H.Owen Chapman,“Hodge Memorial Hospital(W.M.M.S.), Hankow:Progress Report,”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5),1927; H.Owen Chapman,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6-27: A Record of the Period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as Seen from the Nationalist Capital, Hankow,London: Constable & Company Limited, 1928, pp.178-180.。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在一些公共卫生专家的推动下,也开始筹建中央卫生行政机关。或许是受到汉口卫生行政进展消息的鼓舞,1926年底,兰安生联系暂居于武汉的颜福庆,要其设法推动中央卫生行政机关之设立(28)钱益民、颜志渊:《颜福庆传》,第69-92页。。颜福庆与宋子文、孙科等进行联络,建议国民政府立即设立全国系统性的卫生行政机关,及早建立中央卫生部,以主理全国卫生行政(29)宋子文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财政部长;孙科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交通部长。。1927年初,兰安生也来到武汉,随即被国民政府聘为卫生顾问,成为其第一个美籍顾问(30)《孙科委美人为河工顾问》,《大公报》1927年2月9日,第2版。。受国民政府方面的委托,颜福庆为中央卫生部拟订了一个较为详尽的方案(31)此方案还附有卫生部经常费预算书、卫生部编制表、卫生行政机关系统表各一份,数月后,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颜福庆:《国民政府应设中央卫生部之建议》,《中华医学杂志》第13卷第4期,1927年8月,第229-240页。。
在武汉期间,颜福庆还被博医会指派为代表。国民政府外交部则通过他,向博医会转达了请该会派代表出席有关汉口卫生问题会议的邀请。对于外交部的邀请,博医会的执行委员会于4月11日讨论决定:先与中华医学会及中华护士会商议;若该代表选定,他须坚持汉口各医院免受工会、罢工及工人纠察队干预的原则。随后,博医会、中华医学会、中华护士会分别推选马雅各、颜福庆、伍哲英作为各自出席会议的代表(32)“Minute of Executive Committee,”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4),1927.。
然而,上述医疗卫生计划的实施也面临种种障碍。在地方层面,汉口、武昌两市政府财政支绌的现状,使各项市政计划一时难以实行。1927年初,孙科曾引述汉口市长刘文岛的报告称,“汉口市政府收入除公安局外,每月不过二万元”,“除公安不计外,其余五局行政费,总在二万元以上,即市政府之收入,不敷五局行政费之用。因财政无着,致各种市政计划,均不能实行”。武昌市的财政收入,则“完全无着”(33)《筹议中之武汉市政》,《大公报》1927年1月9日,第 6版。。卫生事务亦深受财政状况之影响,1月中旬,汉口市卫生局洁净科因无款,数度向局长请款而不得,以致道路清洁工作停顿,引起市民疑虑(34)《汉口洁净工作停顿原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7日,第3张第2页。。此外,国民党内的政治纷争、人事更迭以及武汉行政机构的调整,也导致卫生行政计划难以推行。宁汉分裂之际,3月上旬,汉口市长刘文岛辞职,随即经九江潜往上海,投靠蒋介石。武昌市长黄昌谷则于3月上旬改任汉口第三特区管理局局长。不久,黄子方在担任汉口市卫生局长数周之后,因政治形势变迁而辞职,离开武汉。其继任者是曾任职于湘雅医院的王子玕,但他就任仅三日,武汉行政机构就又进行了调整。4月16日,武汉市政府成立,汉口市政委员会及武昌市政厅裁撤。武汉市政府未设置卫生局,卫生事务复归公安局执掌。在这一系列变动后,前汉口市卫生局与几家教会医院间的合作协商亦不了了之,这令后者大为失望(35)H.Owen Chapman,“Hodge Memorial Hospital(W.M.M.S.), Hankow:Progress Report,”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5),1927; H.Owen Chapman,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6-27: A Record of the Period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as Seen from the Nationalist Capital, Hankow,pp.178-180.。
在中央卫生部筹划方面,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了增设劳工、农政、教育、实业四部的提案,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临时提议,卫生问题极为紧要,应增设卫生部。孙科表示,卫生关系人民健康,至为重要,各国对此问题皆十分重视。目前的确有设立卫生部以规划一切卫生事务之需要,且设立一部,也不需很多经费。宋子文亦表示,长江各省即将统一,国民政府各部应有一定准备,有增设上述五部的必要。经表决,此提案获得通过(3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830-831页。。然而会后卫生部未能真正成立。不久,因卫生部人事任命问题,颜福庆感觉受到排挤,于失望中离开武汉。5月底,他被北京协和医学院任命为副校长(37)钱益民、颜志渊:《颜福庆传》,第92-98页。。9月,颜福庆到协和就任。
二、救护第二次北伐伤兵的吁请及其所引发的反应
1927年4月19日,国民革命军在武昌南湖举行誓师,开始第二次北伐。由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独立第十五师等组成的第一集团军沿京汉路北上,与占据河南的奉军作战。第一集团军攻城拔寨,6月1日,与东出潼关的冯玉祥所率第二集团军会师郑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北伐虽然取得胜利,但也付出沉重的伤亡代价,特别是第四、第十一、第三十六各军(38)在6月13日的中政会会议上,汪精卫提及,上述各军的伤亡人数达14 000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第1229页。。由于国民革命军出兵前准备不足,伤员在河南前线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自5月中旬起,北伐伤兵陆续由京汉线运回武汉,每天大约有500名伤兵运抵汉口大智门车站,至6月下旬共有12 000余名伤兵运回(39)《武汉伤兵调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4日,第2张第3页。。
由于伤兵人数多,主管军事医疗卫生的军事委员会陆军处第六局在出兵前建立的两所伤兵医院远不能应对所需,普爱医院、同仁医院、仁济医院、原慈善会中西医院等尽力协助收治伤兵,但各医院医护人员及床位有限,致使大量伤员滞留于大智门一带,亟待救治。由于运送时间较长,天气炎热,许多伤员已患坏疽(40)“Why the Fund Was Inaugurated: Indescribable Condition of the Wounded,”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 8, 1927,p.7.。武汉各团体纷纷发起救护伤兵活动,捐款捐物,到大智门和各医院护理伤员。然而专业性医疗支持的缺乏,特别是医院、医生、护士的急缺,是救护面临的最大问题。为增设军医院,军方曾试图征用普爱医院,院方则求助于外交部,由后者处获得不被征用的承诺(41)H.Owen Chapman,“Hodge Memorial Hospital(W.M.M.S.), Hankow:Progress Report,”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5),1927.。
1.伤兵救护会的吁请
对于缺乏医疗资源,又处于经济封锁、财政困顿中的武汉国民政府来说,如何救护成千上万麇集于武汉的伤兵是一大难题。5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决定,向各地团体及武汉当地民众团体寻求帮助,“除交军事委员会通盘筹办外,一面由汉口红十字会、总商会及中国济难会电上海红十字会及人民团体,速请医生及运送医药来救护,同时并由人民团体组织一革命军人救护会,受军委会指挥”(42)《中执会致军委会等函稿》(1927年5月24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档案号:汉1073。。
为联系各界救护伤兵,宋庆龄、何香凝、陈璧君、韦增英、沈仪彬等人发起成立红十字救护组织,5月27日,邀集党政要员和各界代表300余人,在中央党部举行谈话会(43)韦增英(1885-1975),顾孟余夫人,广州人,1904年赴德国留学,1912年与顾孟余结婚。1927年3月,顾孟余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沈仪彬,徐谦夫人。。会议宣告成立“伤兵救护会”,宋庆龄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批当地知名的中外医学界人士以及与医疗、慈善有关的宗教界人士出席了此次会议,包括:文德(Fred Wendt)、马榖良(John MacWillie)、舒厚仁、江虎臣、吴德施(Logan H.Roots)、饶永泰(Harold B.Rattenbury)等(44)文德(Fred Wendt,1878-1937),生于德国柏林,一战期间任德国海军军医,1921年,在汉口开设诊所。马榖良(John MacWillie,1880-1947),加拿大人,医学传教士,1902年来华。1905年,任武昌圣公会医院院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马榖良等组织红十字会,从事救护,获黎元洪嘉许。同年,经黎氏拨地,马榖良等将圣公会男、女医院合并扩建为同仁医院。1918年,马榖良离开同仁医院,在汉口开设私人诊所。舒厚仁(1876-1951),字栋臣,浙江慈溪人,1900年毕业于英国阿伯丁大学,1920年任汉口慈善会中西医院副院长兼西医院院长。其妻颜庆莲,是颜永京之女。吴德施(1870-1945),生于美国伊利诺伊,189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896年毕业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圣公会神学院。同年,受圣公会之派到武汉。1904年,任圣公会鄂湘皖赣教区主教。1906年,营救被捕的日知会成员刘静庵。1910年任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武昌起义后,在汉口参加红十字救伤活动。1924年兼任华中大学理事会主席。1938年退休回国。饶永泰(1878-1962),英国人,1902年受循道会之派来华,1921年任武昌教区负责人,1934年回国。。吴德施主教在会上表示,各教会医院愿意在救护伤兵方面予以协作。他提到,武汉各教会医院已在尽量收治伤兵,但各医院住院病患已满员,无法进一步收容(45)《北伐伤兵救护大会成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8日,第1张第1、2页;《汉口伤兵逾五千人》,《大公报》1927年5月30日,第2版。。会后,伤兵救护会进一步建立组织,筹划工作。由全体发起人、数位知名医生及热心救护人士组成执行委员会,韦增英、连声海、刘骥、文德、马榖良担任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46)《伤兵救护会之积极进行》,《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1日,第1张第1页。连声海(1885-1947),广东顺德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6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23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秘书,1926年任国民政府交通部秘书长,1927年3月任武汉国民政府秘书长。刘骥(1887-1964),湖北钟祥人,清末入新军,与冯玉祥同伍。1924年参与北京政变,1925年任国民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京兆尹等职,1926年9月底,到汉口,被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任命为河南招抚使。1927年1月,任湖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委员,3月,任军事委员会陆军处处长。。执行委员会下设财政、医药委员会。伤兵救护会虽是一个社会团体,但因其成员的特殊身份,又具有一定的半官方色彩,扮演率领各团体、协调各机关、联络各方、统筹救护伤兵工作的角色。其最初的工作之一,即对外展开联络,寻求援助。
伤兵救护会谈话会召开后,一些中外医生及圣公会、伦敦会、循道会、基督教青年会代表在汉口成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吴德施任主席。该委员会决定与伤兵救护会合作,并计划将各教会医院充作后方医院,增加各医院医护人员,利用医院周边建筑,增设病床。至于所需资金,鉴于武汉本地工商业萧条,他们决定向英美基督教团体求助(47)《武汉救济伤兵之团体》,《申报》1927年6月7日,第6版;H.Owen Chapman,“The Hankow Red Cross,”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 10, 1927, p.4.。6月初,圣公会的吴德施、侯礼敦(John Holden),基督教青年会的高德瑞(Arthur M.Guttery),循道会的饶永泰,仁济医院的纪立生,以此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名义,分别致电纽约的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伦敦的国际宣教协会(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 Council),请其捐助鹰洋10万元,以救助武汉伤兵(48)《教士请募捐款救伤兵》,《申报》1927年6月6日,第5版。侯礼敦(1882-1949),英国人,1907年受英国圣公会之派来华,1923年任圣公会桂湘教区主教,1933年任华西教区主教,1938年回国。高德瑞(1885-1981),美国人,1913年来华,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1914年后,任汉口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等职,1928年回国。。
2.红十字救护队的组建
5月底,伤兵救护会、汉口红十字会、吴德施等分头致电北京、上海等地的医学、慈善机构,请其尽快派医生、护士,到武汉协助救护伤兵。
5月31日,洛克菲勒基金会驻远东副主席顾临(Roger S.Greene)在收到伤兵救护会的电报后,即与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胡恒德(Henry S.Houghton)等人开会讨论,决定响应该会的吁请(49)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for 1927,New York: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927, p.252.顾临(1881-1947),出身于美国传教士家庭。1902年由哈佛大学毕业。此后,在巴西、日本、俄国、中国等地从事外交工作,1911至1914年,任驻汉口总领事。1914年,入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属中华医学基金会工作,1921年任主任,1922年至1927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秘书,1927至1929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驻远东副主席,1928年1月,任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校长,1935年7月辞职回国。。为尽快组织救护队赴武汉,6月1日,顾临由北京出发,4日抵达上海。6月4日,北京协和医学院派出一名中国医生、七名护士(含两名外国女护士、一名中国女护士、四名中国男护士),携带药品与器械前往上海。
在上海,经颜福庆的策划推动,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组织了一支由颜福庆、王昌来、张剑雄三名医生,以及四名护士、两名工役组成的救护队(50)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for 1927,p.252.1911年,颜福庆任红十字会湖南分会会长。自1924年起,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由颜惠庆担任。。顾临与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负责人举行会议,讨论与武汉的伤兵救护会合作的各项问题,决定让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组织的救护队,并决定广泛征募志愿去武汉的医护人员(51)F.C.Yen,“Report of the Work of the Red Cross Unit in Wuhan,”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8), 1927;“Relief for Hankow Wounded,”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 7, 1927, p.12.。与此同时,博医会在收到以吴德施为首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征求医生的呼吁后,决定由该会执行干事马雅各负责医生的报名登记工作(52)“Appeal for Doctors for Hankow,”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June 11, 1927.。
苏州博习医院院长苏迈尔(John A.Snell)、安庆同仁医院院长戴世璜(Harry B.Taylor)、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高文明(Wallace Crawford)、安庆同仁医院的梅庚生(Blanche E.Myers)等报名参加救护队(53)苏迈尔(1880-1936),美国人,1908年毕业于范德比尔特医学院,1909年,受循道会之派来华,在苏州博习医院(Soochow Hospital)工作,1917年任院长,1936年病逝于苏州。戴世璜(1882-1971),美国人,1902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05年受美国圣公会之派来华,在安庆同仁医院(St.James Hospital)工作,1908年任院长。高文明(1883-1971),加拿大人,毕业于西安大略大学医学院。1907年,受循道会之派来华,在四川彭州、乐山、涪陵等地教会医院任职。1923年任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访问教师,教授公共卫生学。1930年正式在该校任教,后任公共卫生系主任。1939年创办华西协和大学麻风病医院。。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向红十字救护队捐助了一些药品、外科用品及外科器械,苏州博习医院借出了一些外科器械及一台X光设备(54)F.C.Yen,“Report of the Work of the Red Cross Unit in Wuhan,”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8), 1927,pp.728-729.。
6月11日,颜福庆率中外医护人员一行23人,作为红十字救护队的第一小分队,携带药品、器械,乘坐日清汽船会社“南洋丸”号,由上海出发,前往武汉。23人中,包括中国医生6人、外国医生2人、外国护士2人、中国护士和药剂师13人(55)《救护队出发赴汉》,《申报》1927年6月12日,第15版;“Red Cross Workers For Hankow,”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 11, 1927, p.12.。13日,顾临率第二支小分队乘坐怡和洋行“江和”号轮出发。另有一名女医生卢华棣(Lucy E.Harris)和一名外国女护士,由于从英国领事馆获得出行许可方面的问题,推迟至16日出发(56)James L.Maxwell,“Red Cross Work in China,”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 13, 1927, p.4; W.Rowley,“Caring for Hankow Wounded,”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 20, 1927, p.4; James L.Maxwell,“Caring for Hankow Wounded,”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 23, 1927, p.4.。
在顾临看来,这些医护人员的人数,仍不能满足救护之需。但时间紧迫,武汉方面的救伤形势不明,他在离开上海前安排马雅各继续征募医生,待他与颜福庆到武汉调查情形后,再确定进一步的计划(57)James L.Maxwell,“Red Cross Work in China,”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 13, 1927, p.4; James L.Maxwell,“Caring for Hankow Wounded,”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 23, 1927, p.4.。
3.围绕救护武汉伤兵问题的分歧
6月初,吴德施等人向美、英两国国内发出援助武汉伤兵的呼吁,顾临抵达上海组织救护队,正当此时,以《字林西报》为代表的上海英文报刊及美国的《纽约时报》上出现了一股反对救助武汉伤兵的舆论。自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后,特别是在南京事件发生后,在华外国侨民(包括传教士、医生、教师等)对于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原本存在意见分歧;而围绕是否救护武汉伤兵这一具体问题,这种分歧更为明晰地展现出来(58)曾任《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的鲍威尔(John B.Powell)在回忆录中谈及南京事件后上海外国侨民中的意见分歧。鲍氏反对列强对华武装干涉,并与一些持武装干涉论的英美侨民展开了论争,鲍威尔:《鲍威尔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29-163页。博格也分析了南京事件后,围绕对国民革命的看法,《北华捷报》与基督教团体之间,以及美国传教士内部的意见分歧,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New York: America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7, pp.355-365.。几名由武汉撤到上海的传教士找到《纽约时报》驻华特派记者,针对吴德施等的呼吁,表达反对援助武汉伤兵的意见。他们希望通过该报提醒美国人民,援助背后的“真相”是什么。这一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因仍希望日后回武汉工作而要求匿名;唯有在华中大学担任校医的韦克菲尔德(A.Paul Wakefield)自愿公开发表意见,并表示即使为此丢掉工作,也要说出“真相”(59)1871年,圣公会在武昌创办文华书院,1909年更名文华大学。1924年,武昌文华大学与雅礼会所办长沙雅礼大学、循道会所办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伦敦会所办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合并为华中大学,孟良佐(Alfred A.Gilman)任校长。。
韦克菲尔德是美国人,大约从1918年起在文华大学负责学生健康工作,时任华中大学校医和生理学教师,兼文华中学校医。在北伐军围攻武昌期间,他曾与校长孟良佐一道救济难民。南京事件发生后,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通知美国侨民撤离武汉。华中大学的大多数外籍教师在此时离开,而由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韦卓民率中国教师维持校务。吴德施主教没有做离开武汉的打算,5月初,圣公会内只剩下吴德施、韦克菲尔德等四个外国人继续工作(60)“Hankow is Quieter, but Digs Trenches,”New York Times,May 6, 1927.。不久,华中大学和文华中学均爆发学生运动,学生组织委员会接管了两校,韦卓民被迫离开武汉。吴德施等与国民政府外交部数度讨论两校问题,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劝其继续维持,但两校最终决定于5月中旬关闭(61)“Closing of Boone Middle School and Central China University,”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June 4, 1927.。不数日,第二次北伐伤兵的救护问题出现,吴德施劝说韦克菲尔德留下参加救护伤兵工作,然而后者不为所动,决意离开武汉。临行前,他分别向吴德施、洛克哈特及汉口美国商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6月8日,即韦克菲尔德抵达上海的次日,《字林西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救助汉口伤兵的呼吁》的文章,援引一名据称熟谙事实真相的、居住在汉口的传教士的备忘录,其主旨是反对援助武汉伤兵(62)“The Appeal for the Hankow Wounded: Real Facts of the Case as Intimately Know by Missionaries and Others in China,”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 8, 1927, p.7.从内容来看,此文与《纽约时报》10日的报道相似,显然出自韦克菲尔德之手。。同日,韦氏联合几名传教士,与《纽约时报》记者会面,该报随后刊发的报道内容与《字林西报》的文章相近,亦应源自韦氏的备忘录(63)Frederick Moore,“Opposes Aid from America: Missionary Suggests Money for the Wounded Would Go to Propaganda,”New York Times,June 10, 1927.。9日,韦氏再次应《纽约时报》记者之邀,详谈对传教士、民族主义、教会学校学生等问题的看法,此谈话先后刊登在《字林西报》《纽约时报》上(64)“Missionaries in China and the Cult of ‘Nationalism’: The Role of Students in Miss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Use Made of Them,”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ly 9, 1927, pp.11,16; Frederick Moore,“Fear Missionaries Deluded by Chinese,”New York Times,July 24, 1927.。在上述一系列报道中,韦克菲尔德表示,尽管职责所在,他们无法坐视数以千计的伤者因得不到救治而死去,然而不能让同情迷惑了双眼,不能让美国人民继续受到蒙蔽。他表达了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怨恨,历数其内外政策的各种罪恶,如:“欺骗”“破坏条约”“抢劫”“谋杀”“横征暴敛”“强占农民和商人财产”“宣扬仇恨和劫掠”等。他指责在武汉普通士兵领不到薪饷而官员生活奢华,并提出应由宋子文、孔祥熙等财阀自掏腰包救助伤兵。他视苏俄为中国近来一系列动荡背后的力量,并曾就苏俄的“危害性”问题与文华学生展开争论。他指责苏联在武汉赞助宣传民族仇恨和劫掠,提出应由其资助武汉伤兵。他认为伤兵问题是国民政府自身造成的,政府煽动排外,破坏商业;未设置后方医院,毁坏教会医院,造成湘雅医院关门,在普爱医院鼓动罢工,赶走贝福臻医生。在他看来,武汉政府救护伤兵只是为维护自身颜面。关于对武汉伤兵的捐助,他提醒防止捐款被国民政府用于军事或宣传目的。韦氏还披露了圣公会内部围绕国民革命而产生的分歧。他提及吴德施主教长期以来同情国民党的立场,还有他本人与吴德施之间的意见分歧。在他看来,国民党宣扬的是仇恨、谬误、非基督教的东西;不论将来中国政局走向如何,传教士都应坚守基督教原则,坚持“正义”。韦氏的言论,反映了部分传教士对于救护武汉伤兵问题及整个国民革命的看法,此观点在《字林西报》《纽约时报》等报刊上连续发表,形成了一种对救护武汉伤兵的负面舆论。
上海的英文报界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密勒氏评论报》曾转载日本的英文报纸《日本纪事报》(TheJapanChronicle)上的一篇文章,对另一家日本英文报纸所载韦克菲尔德有关中国南北政局及中日、中苏关系等问题的言论提出批评。文章称其为“极端保守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并认为不应将这种欠考量的言论刊登出来(65)“The Views of a Senator and a Missionary,”The China Weekly Review,July 30, 1927.。《密勒氏评论报》对文章的转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报自身的看法(66)北伐时期,在主编鲍威尔的主持下,《密勒氏评论报》倾向于主张外国人对国民革命应采取让步和承认的态度。鲍威尔:《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29-163页。。
在是否救助武汉伤兵问题上,医学界、慈善界人士的态度至为关键。其中一些人对于国民革命的态度与韦克菲尔德不同,值得一提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顾临。南京事件发生后,顾临曾致函《纽约时报》,表达对国民革命及列强对华政策的见解。他不赞成美国及其他列强以保护在华外侨、维护条约权利为由,对华实施武装干涉。他认为眼光应放长远,中国重建和平与秩序符合中外各方的利益。在他看来,外国政府及在华外国人长久以来已惯于将自身利益视为最重要的,而忽视了努力重建国家的中国人民的利益。治外法权等特权已不适合当下,继续维持这些特权无益(67)Roger S.Greene,“China’s Future Not Gloomy for Those Who Look Ahead,”New York Times,May 8, 1927.。基于这种见解,在收到武汉国民政府方面的援助请求后,顾临立即响应并策划组织红十字救护队前往武汉。
大约与韦克菲尔德同时由武汉到上海的贾溥泉(H.Owen Chapman),对于救护武汉伤兵问题的见解也与韦氏不同(68)贾溥泉,澳大利亚人,隶属循道会,1920年来华。1929年后,任汉口协和医院代理外科主任、副院长等职。。贾溥泉于1927年1月到武汉,在普爱医院女院任代理医生,并在该院院长离开后代为管理院务。在此期间,贾溥泉关注教会医院的命运,参与了普爱医院与汉口卫生局的合作磋商,还撰文向博医会介绍相关情况。第二次北伐伤兵运回武汉后,普爱医院参加救护,贾溥泉是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又在伤兵救护会的医药委员会工作。6月3日,他离开武汉,经上海回国。在上海期间,他投书《字林西报》编辑,对该报关于武汉伤兵问题的报道,特别是对《救助汉口伤兵的呼吁》一文中的错误及误导之处提出更正和补充。贾溥泉介绍了武汉伤兵近况以及伤兵救护会、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工作。对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援助武汉伤兵吁请,他解释道,他们在武汉救治伤兵,不问救护对象是谁,也不问其为哪一个政府效力;上海的外侨应在援助武汉伤兵问题上持更为慷慨及无偏见的态度。他还指出,对于捐款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担心并无根据,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完全掌控本会的运转(69)H.Owen Chapman,“The Hankow Red Cross,”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 10, 1927, p.4.。1928年,贾溥泉所著《中国革命,1926—1927》出版(70)H.Owen Chapman,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6-27: A Record of the Period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as Seen from the Nationalist Capital, Hankow.,该书记述从出师北伐到1927年8月间国民政府的历史,书中提及,关于英国对华政策问题,在华英国人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是一些老一代“中国通”的黩武主义主张,即希望英国继续采取昔日强硬的外交政策,维持旧秩序,他认为,这种观念是陈旧过时、不现实的;另一种是一小部分传教士的和平主义主张,在他看来,其时机尚未成熟(71)H.Owen Chapman,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6-27: A Record of the Period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as Seen from the Nationalist Capital, Hankow,pp.139-147.。
在驰援武汉救护伤兵的中外医护人员中,有不少人来自受到北伐战争及反帝运动影响的教会医学机构。如前所述,颜福庆原是湘雅的校长,后来曾协助国民政府筹设卫生部,当武汉方面发出救护伤兵吁请后,他在上海积极策划组织救护队。在外国医生中,苏迈尔是知名外科医生,时任美国监理会所办苏州博习医院院长。1927年3月,北伐军进军苏州,不久后南京事件发生,该院外籍医护人员撤往上海,由中国职员维持院务。戴世璜亦是知名外科医生,在圣公会所办安庆同仁医院任院长。梅庚生在同一医院任秘书兼会计。1927年3月,该院被北伐军征用。南京事件后,戴世璜等撤到上海。高文明是公共卫生专家,曾在英、加、美各差会在成都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教授公共卫生课程。1926年9月,万县惨案发生后,成都的反英民众运动高涨,受此影响,华西协和大学的大多数外籍工作人员于1927年1月离开成都(72)莫尔思:《紫色云雾中的华西》,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年,第172-186页。。6月初,当顾临等为救护武汉伤兵征募医护人员时,这些人又溯江而上。戴世璜在其回忆录中提及,他在上海得知武汉伤兵亟需救治的消息,当顾临来组织救护队时,鉴于到上海后医事不多,他便申请参加(73)戴世璜:《戴世璜自传》,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6页。。上海英文报纸对于武汉伤兵救护问题的负面报道,也使这些医护人员面临一定压力。女记者米利·贝内特(Milly Bennett)注意到这类报道对苏迈尔、戴世璜造成的困扰,但苏迈尔对她表示,他们到武汉是为救助急难,为从事医学工作,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上海英文报界的批评是目光短浅的(74)Milly Bennett,On Her Own: Journalistic Adventures from San Francisco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27,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4, pp.359-360.。
三、红十字救护队的工作
1927年6月16日及18日,红十字救护队的大部分成员抵达武汉。这支国际红十字救护队由中国、美国、英国、挪威、瑞典医护人员组成,共44人,包括:12名医生(含5名外国医生)、22名护士(含7名外国护士)、2名药剂师、1名技师、3名管理人员(含2名外国管理人员),及4名工役(75)F.C.Yen,“Report of the Work of the Red Cross Unit in Wuhan,”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8), 1927.。颜福庆担任红十字救护队队长。颜福庆的医学资历、对于武汉情况的熟稔程度,更重要的是他与救护相关各方——武汉国民政府、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红十字会、英美教会、博医会、武汉医学界等——之间的联系,使其成为此担任此职的不二人选。
红十字救护队的44名队员来自不同的背景,其人事费用由数家机构分担。其中,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派出的9名医护人员的工资、生活费和路费由该会支付;北京协和医学院除支付该校派出的医护人员的工资、生活费、路费外,还担负志愿工作人员的生活费、路费,以及由上海聘用的外国护士的工资;各教会医院医生的工资由其所在差会支付;除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员之外的人员,其生活费由伤兵救护会、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分担(76)F.C.Yen,“Report of the Work of the Red Cross Unit in Wuhan,”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8), 1927.。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此次救护工作支出分担了5 245.85美元(77)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for 1927,p.256.。
红十字救护队抵达武汉时,当地伤兵总数已达11 000人左右(78)F.C.Yen,“Report of the Work of the Red Cross Unit in Wuhan,”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8), 1927.。为收容伤兵,自5月底以来,陆军处第六局及各军已新开办了数所伤兵医院。其中一些医院的开设,得到了武汉医学界、宗教界的协助,例如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军医院脱胎于原慈善会中西医院;循道会将所办训盲书院腾出,作为陆军处第五分院的病房。不过,这些仓促设立的临时医院均面临经费困难、医护人员不足、药物缺乏、条件简陋、重伤员与轻伤员混居于同一病室等问题。
自成立伤兵救护会以来,宋庆龄等通过多种方式筹募资金,在武汉、上海等地采购药品、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并新近在汉口第一特别区四维路五号开办了一所伤兵医院,收有伤员100人左右。伤兵救护会对红十字救护队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予之充分信任,随即请救护队接管该会伤兵医院。红十字救护队发现这所医院同样存在伤员缺乏医治和护理的问题。不数日,伤兵救护会又在第一特别区福兴里开办了第二所伤兵医院,设有病床80张左右,同样交给红十字救护队负责(79)《慰劳负伤同志》,《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8日,第2张第3页。一说该医院设在华清街三多里,《慰劳伤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4日,第2张第3页。两地隔后街相望。。伤兵救护会所办第一医院、第二医院分别由戴世璜、苏迈尔担任院长,各院医生、护士均来自于红十字救护队,管理、后勤等事务性工作则由伤兵救护会负责。
红十字救护队由北京、上海等地带来了一些药品、敷料、手术器械及设备;伤兵救护会也已筹备了一定数量的药品、医疗器械、卫生材料;戴世璜等在伤兵救护会成员的陪同下,又在汉口置备了手术台、外科器械及其他医用必需品(80)戴世璜:《戴世璜自传》,第177页。。因此,两医院“设备完全,药材丰足”(81)《慰劳负伤同志》,《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8日,第2张第3页。。
红十字救护队对伤兵救护会的两所医院的功能做了界定——专门收治急需手术治疗的重伤员。红十字救护队与伤兵救护会、陆军处及各军医院商定,将各伤兵医院中的此类重伤员转送到伤兵救护会的两所医院。随后,两医院接收了由第四兵站第二分院送至的100余名重伤员,及由陆军处从武汉各医院转来的150余名重伤员(82)《慰劳负伤同志》,《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8日,第2张第3页。。此外,颜福庆等人每日在伤兵救护会成员陪同下到武汉三镇各伤兵医院巡查,一方面,筛选出重伤员,以转送到伤兵救护会医院;另一方面,对各医院的卫生状况提出改进意见,以避免传染病的发生(83)F.C.Yen,“Report of the Work of the Red Cross Unit in Wuhan,”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8), 1927.。
红十字救护队、伤兵救护会又与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同仁医院和普爱医院商定,两所医院同样担负治疗重伤员之责。鉴于普爱医院的重伤员人数较多,红十字救护队派高文明医生及三名外国护士前往支援。上述举措有利于使当地现有医疗资源获得更合理的配置,并使各医院存在的重伤员与轻伤员混居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6月下旬,顾临电告马雅各,红十字救护队工作进展顺利,并表示目前无须向武汉增派医护人员(84)“Hankow Red Cross Organization:No Further Workers Needed Just Now,”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July 2, 1927.。
由红十字救护队治疗的伤者中,大部分人为机枪子弹所伤(85)“News and Comments: Red Cross Unit, Hankow,”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7), 1927.。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有医生注意到,运回武汉的伤兵中以四肢中弹者居多,而头部、胸腹部受伤的重伤员在伤兵总数中所占比例偏低(86)“Heavy Casualties in Honan: Ghastly Story of Nationalist Wounded Troops,”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June 18, 1927; H.Owen Chapman,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6-27: A Record of the Period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as Seen from the Nationalist Capital, Hankow,pp.194-196.。这至少是6月中旬之前伤兵伤情的一种现象。
截至7月底,伤兵救护会第一医院和第二医院共收治伤员351人次。两医院在1927年6月18日至7月30日(87)伤兵救护会第一医院在此后又运转了1个月左右,其数据阙如。收治病例的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1927年6月18日至7月30日伤兵救护会伤兵医院出入院统计
截至7月底,两所医院共施行外科手术238台,其中,第一医院施行184台,第二医院施行54台。238台手术中,按麻醉方式划分,包括:全麻手术35台,局部麻醉手术75台,无麻醉手术128台。由红十字救护队治疗的重伤员人数,约占武汉重伤员总数的30%(88)F.C.Yen,“Report of the Work of the Red Cross Unit in Wuhan,”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8), 1927.。
除办理伤兵医院、救治重伤员外,红十字救护队还配合伤兵救护会,在武汉及郑州、九江等地进行了如下救护工作:
伤兵救护会自成立后,尽力购置药品与医药材料,起初主要为满足该会所办医院之需要,自7月初起,亦尽己所能,向其他伤兵医院提供一定的补助(89)《伤兵医院领取药品材料须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4日,第2张广告第4页。。在红十字救护队的协助下,伤兵救护会设立医药购料处,以监督药品、医疗器械、卫生材料的采购,及核准各医院对医药用品的申领。红十字会救护队派一名药剂师到该部门工作。鉴于伤兵救护会筹措的医药用品已足够供红十字救护队开展工作,于是红十字救护队将由北京、上海等地带来医药用品中的大部分送往郑州冯玉祥部(90)F.C.Yen,“Report of the Work of the Red Cross Unit in Wuhan,”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8), 1927.。
应冯玉祥之请,7月5日,红十字救护队派出一支全部由中国队员组成的小分队,包括四名医生、四名护士、一名管理人员及三名工役,由武汉赴郑州,从事救护工作(91)《慰劳负伤同志》,《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0日,第2张第3页。。
7月初,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东征讨蒋。中旬,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各军集结九江。伤兵救护会计划在九江建立一所后方医院。应该会之请,25日,红十字救护队派出一名医生、五名护士、一名药剂师及一名业务经理赴九江,协助该院的筹备工作。
红十字救护队还进行了一些卫生教育工作。他们印制了两种共20万张关于霍乱、痢疾、伤寒等传染病预防的宣传海报,在武汉的士兵及住院病人中分发,并携往郑州、九江,向士兵散发。
由于伤兵救护会的支持与合作,红十字救护队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后来,戴世璜在其自传中称赞伤兵救护会女性成员的干练,她们努力工作,处理医院食品供应等问题,使医生们得以专注于医疗工作(92)戴世璜:《戴世璜自传》,第177页。。颜福庆在其刊载于《博医会报》的救护报告中指出,管理医院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尽管伤兵救护会成员大多非医学专业人士,但他们全心全意地为伤兵解除痛苦,通过与红十字救护队一同工作,他们也学到管理医院的方法。伤兵救护会负责人的全力协作,使救护队的工作得以取得成效(93)F.C.Yen,“Report of the Work of the Red Cross Unit in Wuhan,”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8), 1927.。
7月中旬后,武汉的伤兵救护工作渐入收尾阶段。第二次北伐已结束一个多月,伤兵均已运回武汉,并在军事委员会陆军处、各军、伤兵救护会及其他团体的努力下由各伤兵医院收治,部分轻伤员经治疗已陆续出院。此时,红十字救护队鉴于治疗重伤员的工作已大体完成,准备离开武汉。《博医会报》刊登消息称,武汉伤兵人数虽多,但总体而言,其伤情并没有人们最初预计的那样严重,由红十字救护队治疗的伤者现已获得较好的康复(94)“News and Comments: Red Cross Unit, Hankow,”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7), 1927.。7月12日,宋庆龄在寓所花园与远道而来的中外医护人员合影留念。不数日,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政治局势的变故对于武汉的救护伤兵活动亦造成很大的冲击。14日,宋庆龄撰就《为抗议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3天后她离开武汉。20日,苏迈尔、戴世璜、高文明离开武汉,返回上海。伤兵救护会第二医院将处于康复期的伤员转往第一医院,随即于27日关闭。伤兵救护会第一医院尚有88名伤员继续留院治疗,该院由伤兵救护会接办,韦增英任代理院长,舒厚仁任副院长,红十字救护队中的两名外国医生、四名外国护士,及数名中国医生、护士,继续在该院工作。红十字救护队在普爱医院工作的三名外国护士分别于25日、30日结束工作。30日,救护队中的大部分成员离开武汉(95)F.C.Yen,“Report of the Work of the Red Cross Unit in Wuhan,”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41(8), 1927.。除在伤兵救护会第一医院、郑州、九江的数名成员外,这支红十字救护队的工作基本结束。7月中旬后,作为武汉救护伤兵活动重要领导机构的伤兵救护会将工作重心转向对东征的准备。至8月初,伤兵救护会已将所购药品及卫生材料运往前方,并停止对武汉各伤兵医院的补助(96)《伤兵救护会启事一》,《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第2张广告第4页。。8月底,伤兵救护会通告全体迁往九江(97)《伤兵救护会迁浔通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31日,第1张第2页。,该会在武汉的救护工作告一段落。
四、结 语
由于现代医学在中国发端及发展的特殊路径依赖,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各地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医院及医学教育机构,多与西方教会或慈善组织有关。与医学发展的这一现状相关,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后,战争与民众运动对医学群体的医事活动及医生的个人生活造成了空前的冲击。一些国人自办的医学机构受到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而众多教会医院、医学教育机构则受到战争、反帝运动、非基运动,以及工会组织、学生组织等其他诉求的活动的冲击。在南方各省教会医学机构中工作的大部分外籍医生、护士以及部分中国医生被迫离开职守,外籍医护人员先撤到上海,部分人离开中国,近三分之一的教会医院关闭,数所教会医院被军队占用改作军医院,仍在运转的医院大多暂时交由中国医生管理。各地教会医学机构受影响的程度不同,在湖南,此类机构受民众运动冲击非常严重;在武汉,各医院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大部分外籍医护人员离去,但在中国医生的主持下仍继续运转。此时,由于国民革命的影响以及北伐军对军医人才的需求,一些教会医学机构的医学生、护士加入北伐军,成为军医。国民革命也给教会医疗机构带来其他方面的影响,由于外籍管理人员的撤离,一些教会医疗机构交由中国医生管理,这原是一种临时性的应对措施,但在民族革命运动大潮的影响下,这些机构的行政权力加速向中国医生转移。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教会医疗机构的本土化进程。
北伐军克复武汉后,国民政府在汉口、武昌等地积极改良市政。在卫生领域,呼应1920年以来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卫生事业的发展,设立专门的卫生行政机关,任用专业人才,办理地方公共卫生事务。由此也吸引了一批公共卫生专家,特别是出身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的专家,他们或加入国民政府负责卫生行政工作,或充当顾问协助筹划卫生事业。在这些卫生专家的建议下,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卫生部,将卫生事权集中在一个机关内,主理全国卫生行政,为将来的统一管理做准备。汉口市卫生局为建立市立医院,与正处于反帝、非基运动压力下的普爱医院等教会医院协商合作。总的来说,国民政府与卫生专家、医学机构、医学团体之间在卫生领域的各项合作虽然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但最终未获得多少实际的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内的政治纷争、财政困顿。汉口市卫生局与各教会医院之间的合作磋商,在一系列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卫生局内部的人事与机构的变动之后,不了了之。至于卫生部的筹划,虽然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卫生部,但该部未能真正成立。直到“宁汉合流”后,在蒋介石完成二次北伐之际,192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才宣布设立卫生部。
自北伐以来,国民政府与医学群体之间的冲突与合作交织的关系,在救助第二次北伐伤兵问题上集中展现出来。在武汉,当北伐伤兵由河南战场运回后,中外医学界人士与其他各界人士一道,积极协助救护伤兵。而在上海,一些撤到此地的传教士医生,因国民政府对教会机构的政策而坚决主张反对救护,其观点在《字林西报》《纽约时报》等发表,甚至成为主流舆论。在这种反对声音中,仍有一批中外医护人员组成国际性的红十字救护队,赶往武汉,与伤兵救护会合作救助伤兵。这些医护人员不但为重伤员的救治带来了急缺的专业医护人员和技术支持,而且在医院的管理、救伤的流程、药品的分配、传染病的预防等方面,为武汉伤兵救护工作提供了专业经验,使之渐上正轨。
协助武汉国民政府救护伤兵的几个主要医学群体——顾临及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颜福庆、王昌来、张剑雄所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的医护人员,普爱医院等武汉当地医院医护人员,苏迈尔、戴世璜等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传教士医生,马雅各等博医会成员——他们自北伐开始以来有不同的经历,在救护第二次北伐伤兵中也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红十字救护队的两位组织者顾临、颜福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身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领导层成员的顾临,在教会医学人士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他是此红十字救护队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在北京、上海等地积极进行联络,协和医学院亦为救护队承担了大部分开销。颜福庆则因其在医学专业领域的资深经历,及其与医学团体、教会医学机构、武汉国民政府等各方的关系,而担任红十字救护队的负责人。值得注意的是,颜福庆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系统的多位医生,皆曾与武汉国民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进行过合作。
在一个中外冲突,武汉、南京、北京各政权对峙的时期,这支红十字救护队能够超越民族、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分野,组建起来并顺利完成工作,实非易事。此次救护活动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首先,是各位中外医生、护士救死扶伤的职业本能与人道主义精神;其次,是顾临、吴德施等部分医学界、慈善界、宗教界较有影响的人士,对于国民革命持一定的同情态度,并期望借此改善带有外国色彩的医学机构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以宋庆龄为首的伤兵救护会的大力呼吁及与各界的联络,他们一面筹措救护资金和医药用品,一面联络各地中外医学、慈善团体,他们大多并非医学专业人士,但他们对于这些前来救护的医护人员给予充分的信赖,并积极配合,使其工作能顺利进行。
-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其它文章
-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组织变革
——基于系统观的诊断与设计 - 请求权基础视角下《民法典》的规范类型
- 辛亥《时事新报》征文的政治旨趣与舆论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