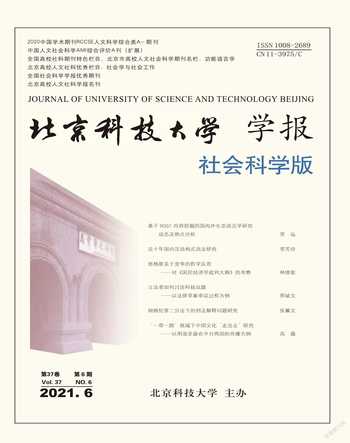立法者如何讨论科技议题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与科技的飞速发展,如何对相关科技议题做出妥善的立法回应,是现代社会立法机关面临的一大挑战。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统一审议法律草案过程中,会充分考虑相关专家、团体和机关的意见,调整相关科技概念和专业术语的定义,维持或变更基于特定概念/标准的法律措施,或者对特定科技议题进行研究和说明。由于立法与科技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应对科技议题时也存在着多种策略,推动科技议题向法律议题的转化。应当坚持立法过程的开放性、民主性,加强立法的公众参与,消解现代科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关键词〕立法;科学技术;法律草案;审议
〔中图分类号〕 D971.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21)06?0670?09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法律与科技的关系日益密切。从医疗、生殖技术、工业生产、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到安乐死、同性婚姻、基因编辑、气候变化应对等,或新鲜或老套的法律议题背后总是交织着科学与道德问题。法律如何应对科技议题(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Issues ),关系到立法是否能够顺应和满足社会与科技发展的需要。正如有学者[1]所言:“法律是一个伟大的借方( agreat borrower),从科学发现中借取资源。……对于科学提供的知识,法律应当像一位见多识广的顾客……这意味着,法律既要理解权力,也要理解科学的界限。”法律作为社会科学,与位于科技背后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的差异和碰撞,无形中催生出了科学与民主、专家主导与公众参与、风险评估与风险防控等诸多问题,这在现代乃至后现代语境中都是非常复杂的关系。这些问题既关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关乎民主的实现与权利的保障。科学家希望“将真理置于一个民主的框架之中”,以确保科学处于“良序科学”( Well-ordered Science)的理想状态[2]241;立法者也提出了“科学立法”的理念与原则,以确保“法律准确反映和体现所调整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进而“真正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3]。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相关科技争议涉及到的理、工、农、医类知识,已经超出了法学知识的范畴。立法者如何在立法實践中融合法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从而妥善应对相关重大的科技议题,就成为了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探讨的问题是:在我国的立法体制下,作为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职责的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①,如何在立法过程中讨论相关科技议题,妥善处理社会广泛关注的科技争议。在我国立法实践中,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交的相关法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法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统一刊载于《全国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其中包含了大量立法过程中立法者讨论具体问题的记录。本文将从中筛选出立法者运用自然科学知识讨论相关立法问题的事例,分析立法过程中、特别是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立法者应对科技议题的方案与逻辑。总体而言,本文将按照以下步骤展开:第一,阐述在法律文本之外的立法过程,探讨其对于立法者讨论和应对科技议题,寻求社会共识的重要意义;第二,对我国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应对科技议题的实践进行梳理和类型化分析;第三,提炼立法者应对科技议题的策略和思路。
二、关注法律文本背后的讨论:重大科技议题应当在立法过程中寻求共识
本文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关注科技议题背后的立法过程?从静态的法律文本来看,法律会对某些科技议题做出规定,但对于不断产生的新兴科技风险问题,现有的法律体系往往面临“立法分散”“立法层次较低”“缺乏衔接”“存在立法空白”[4]96等质疑。而在法律文本之外,动态的立法过程则展示了立法者是如何在立法过程中讨论相关科技议题,自然科学知识是如何影响立法者决策的。而且从立法过程,能够更加清晰地探析立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应用自然科学知识,既是其对相关科技议题的应对,也深刻影响了相关法律的解释与适用。有学者也指出,通过“科技界建制化参与立法”,解决“立法过程的科技论证与支撑不足”,是提高我国立法科学性的有效方法[5]。从立法者的角度来看,法律面对的科技争议,实质上是由科技引发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在于在立法过程中妥当地使用相关科技概念及相关知识体系,并厘清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职责的关系。由于立法的滞后性,执法和司法活动往往能够最先接触到法律领域中的相关科技争议,并从法律角度做出回应。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典型案例,如2014年审结的江苏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2019年审结的“基因编辑婴儿案”和2020年底一审宣判的杭州动物园人脸识别纠纷案等,就是这样。但是,对于重大的科技议题,个案执法或者裁判往往无法充分消弭其中存在的争议,因而需要在立法层面做出回应。笔者认为,现代社会中重大科技议题背后的争议,应当在立法过程中逐步寻求共识。
首先,立法机关在法律事实的认定上具有更大的优势。所谓立法事实,是指作为法律规范的制定和修改、法律制度的设计和改革根据的事实,又称为制度事实[6]32-33。科学技术的理念、概念和标准会深刻影响到立法事实的确定,进而构成法律规范制定之前提。科技议题在法律上引起争议的前提是,科学上的概念、认知经由法律规范的转介,可能会引起公民权利义务在法律上变化,以及法律的解释和适用。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规则时会借用相关科技概念,进而影响到法律文本的理解与解释。一方面,立法者在法律文本中会直接借用理、工、农、医等学科的术语及相关概念体系,如“化石”(《刑法》《文物保护法》等)、“生物识别信息”(《民法典》《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等)、“传染病”(《传染病防治法》、“沙化”(《防沙治沙法》)、“放射性污染”(《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法》)等,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权力与职责、权利与义务之间的法律规则建构。相关法律争议的解决,实际上是以某些专业概念的理解与解释为基础。譬如:太阳能是否应当被认定为《宪法》第九条所说的“自然资源”而归为国家所有,首先应当准确定义“太阳能”“自然资源”及两者的关系[7]。另一方面,立法者会以相关科学技术的常识/结论为基础构建法律规则。例如对“醉酒驾车”刑事责任和“酒后驾车”行政责任的区分是建立在相关医学标准之上的①,《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关于机动车限行的措施是以“机动车尾气排放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的科学论断为前提的。如何将科学概念转化为法律语言,是否将相关科学结论作为法律规则建构之前提,需要慎重考量。有学者指出,立法机关在立法事实的认定上具有“更胜一筹”的能力,如信息来源广泛、充足的资金来源和人才配备、不受先例拘束、专业经验积累丰富等[8]。这意味着,在重大的科技争议问题上,立法机关更适合对法律规则的前提事实进行讨论和做出认定,进而打通科学技术争议向法律问题转变的通道,为正确、妥善解释和适用法律创造条件。
第二,是否为科技议题设置法律规则、如何对科技议题立法,这些判断权都在立法机关。法律问题与科技问题都有其自身的界限,并不是所有涉及科技的争议都需要由法律来干预。立法机关并不直接处理科技争议,也不能代替科学家就特定科技争议得出科学的结论,而是根据已有的结论和知识来调整科技议题背后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职责关系。只有在科技议题已经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并可能会对公民的权利义务实现和国家机关的职责履行产生重大影响时,立法者才有可能对特定的科技议题做出回应。也就是说,立法机关所要解决的是由科技议题转化而来的为社会普遍关注的权利义务问题,具有高度的抽象性。面对新出现的科技手段引发的具体法律争议,作为最高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会直接采取立法措施进行回应,而是先由行政主管部门针对较为具体的科技问题制定位阶较低的法律规范,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①,以便“摸着石头过河”,积累经验,凝聚社会共识,再判断是否有必要在法律中对相关问题做出统一的抽象规定。可见,在立法时机是否成熟、立法策略是否可行等关键问题上,立法者拥有更为主动的判断权和决定权。所以立法过程中各部门之间的的充分讨论与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科技议题所包含的重大道德伦理争议、利益纠葛和不确定风险,需要通过立法过程中的充分讨论和协商,才能凝聚共识,统一意见。科学技术与法律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投入?产出”关系,立法者并不是简单地在法律文本中照搬科学技术的相关概念或术语。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涉及相关科学问题的立法工作中,立法者对相关问题设置程序、规则和限制,需要依赖科学研究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并借用相关科学术语( Scientific Termino- logy)。但科学与法律之间对于特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立法者会在一些重要概念的使用上与科学界产生差异,而在有些场合中,道德和正当性问题的争论已经超出了纯粹的法律问题范围[9]。也有学者指出,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不再是能够自我证明的真理,而直接成为立法者能够运用的原料。而且科学严重依赖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充满了内在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这使得立法机关在处理立法中存在的科学问题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10]。一方面,某些重大的法律争议已经不仅仅源于科学技术本身的争议,而是涉及到科学技术背后的道德伦理问题和利益平衡问题。例如,性别的科学标准与不可变性( Immutability)在科学上的认定结果,对于法律是否认可同性婚姻的辩论已经无关紧要,支持和反对同性婚姻的群体似乎都不在意上述问题的科学答案[11]。又如,即便“吸烟有害健康”当下已经在医学上得到了充分的论证,但控烟立法依旧受到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历尽坎坷[12]75。可见,相关科学上的结论并不能简单地决定立法的结果。另一方面,诸多科学技术问题(如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等)在当下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或者取得广泛的共识,因而具有不确定的风险性。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的是人类对科学认知的有限性,从而导致“技术风险的合法性规制困境没有完美答案”[13]358。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科学早已不纯真,已经变得很积极地谋求自己的利益”[14]206,因此只有在民主的立法过程中加强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才能够在充分讨论协商的基础上凝聚社会共识,并有效应对和降低技术风险不确定性的威胁。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立法者在理想的立法过程中充分讨论,也不能保证所有的科学技术议题都得到合理的解决和应对。当代学者对于议会立法的专业性、独立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质疑。即便美国国会有着成熟的委员会立法模式,仍然有美国学者质疑美国国会专门委员会在立法过程中无法妥善地处理科学问题。理由包括国会缺乏独立、超脱的评估机制,委员会对科学问题缺乏理解,以及公众无法有效参与到相关法案的讨论中等等,并建议另起炉灶设立独立的科学问题评估机构[15]。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立法过程中充分讨论、研究,就科技议题存在的争议达成共识,较之于通过行政和司法手段处理科技争议,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
三、我国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应对科技议题的实践
从我国的立法体制与实践出发,法律草案的审议阶段是决定法律质量与確保“人大主导立法”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在我国法律草案多数由政府部门牵头起草的状况下,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法律草案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使行政机关起草法律的业务优势与人大对立法工作的主导权得以平衡,能够保证人大、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意见交流。另一方面,在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充分发挥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人才荟萃,知识密集”[16]的优势,能够进一步确保立法活动中多学科知识运用的妥当性。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以对法律草案的内容进行实质性修改,纠正法律草案中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内容或者不当之处,防范立法中可能出现的风险[17]。从抽象的层面来看,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能在审议中表现出规避科技风险的立场。例如,在审议《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就采纳了相关地方、法学教学研究机构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在草案中增加了“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18]。再次审议《民法典人格权编》时,又在草案中针对相关医学和科研活动增加了“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的规定[18]。而从具体层面来看,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相关科学的概念、标准及可行性进行了大量的审查和讨论,并对相关科技议题做出了处理,大体而言可以包括以下三类:
(一) 调整相关概念和专业术语的定义
科学技术问题对立法的影响就是通过概念影响法律文本。理、工、农、医类的专业术语在被写入法律文本后会对立法目的、法律调整的对象乃至具体法律措施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法律草案的审议过程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需要结合其他代表、专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对重要的术语进行审查,确保立法用语和概念的严肃性、周延性与科学性,纠正相关概念定义错误或不当之处。法律草案中科技术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草案文本中专业术语概念不准确或不明确。例如,在审议《民用航空法》草案时,草案中规定航空器“是指能够凭借空气的反作用而不是凭借空气对地面的反作用在大气中获得支撑的任何器械”。有些委员提出,这一款对航空器定义的规定是否准确,应再作研究,本法对航空器定义也可以不作规定。基于此,原法律委员会就删除了草案中对“航空器”的定义[19]。因而《民用航空法》直接回避了对“航空器”这一专业术语做出定义。又如,在审议《生物安全法》草案时,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地方和社会公众提出,草案中对“生物安全”的定义比较抽象和学术化,内涵要求不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研究后,对草案中“生物安全”的定义进行了修改。原草案对“生物安全”的定义是:“国家有效应对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在生物领域能够保持稳定健康发展,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具备保障持续发展和持续安全的能力。”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将这一概念修改为“国家有效防范和应对危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生物技术能够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系统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生物领域具备维护国家安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20]。经过修改后,“生物安全”的概念更加周延和直白。
第二,草案中使用的科技概念与术语不符合或者不足以凸显立法目的。对于草案中使用不当的术语,可能会影响立法目的的实现或者影响法律实施效果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审议时也会进行调整。《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二审稿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生物制品实施重点监督检查。”有些常委委员和部门建议将“生物制品”修改为“高风险的药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21]。这一修改显然使扩大了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重点监督检查的范围。又如,《防沙治沙法》草案原规定:“本法所称沙化,是指因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天然沙漠扩张和沙质土壤上植被破坏、沙土裸露的过程。”有些常委会委员和地方、部门、专家提出,造成土地沙化,有气候变化等自然原因,也与人类不合理活动密切相关,对完全由自然原因造成的土地沙化,还难以预防和治理。为了使立法更有针对性,本法应着重规范主要因人类不合理活动所引起的土地沙化的预防和治理活动。原法律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将“沙化”定义为“主要因人类不合理活动所导致的天然沙漠扩张和沙质土壤上植被及覆盖物被破坏,形成流沙及沙土裸露的过程”[22],以强调对人类不合理活动的预防、治理的立法目的。
第三,法律草案中有关专业术语使用错误。例如,《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草案对“放射性污染”原有定义是“人类通过不同途径排放的放射性污染物,使环境的放射性水平高于天然本底或者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对大气、水体、土壤和人体等造成的污染。”有的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和有些专家提出,自然界的放射性水平天然本底因多种因素而有所不同,甚至存在较大差别,草案上述规定在实践中会产生许多问题[23]。因此,原法律委员会删去了定义中“高于天然本底”,限缩了“放射性污染”的范围,确保了法律定义的妥当性。又如,在《核安全法》起草过程中,有关方面曾围绕“核材料”的范围产生争议。草案原本将氚、氘和锂-6明确列举为核材料。但有的部门、企业和专家认为“氚、氘和锂-6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应用很广,有关国际公约和各国没有将这些材料纳入核材料的范围,不宜纳入本法调整”,且“经过专家论证,认为氘和锂-6没有放射性,氚的放射性不强,氚、氘和锂-6属于聚变材料,需要在裂变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核反应,在严格管制铀、钚等裂变材料的情况下,不会造成核事故,可以不将这些材料纳入核材料的范围”[24]。原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在法律文本中对上述材料不作具体列举,为实践需要预留空间。从上面的例子看,经过对特定专业术语的修正,立法者有效避免了在科技专业知识上的错误,并科学地确定了法律调整的范围。
(二)维持或变更基于特定概念/标准的法律措施
立法者可能会基于特定的概念或者标准设置相应的法律措施,进而可能影响到公民的法律权利,甚至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在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对相关条款采用比例原则的审查方式,即有可能在妥当性审查和必要性审查环节涉及对相关概念和标准的评价问题。坚持科学的标准与立场,对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在制定《传染病防治法》的过程中,有些委员和有的地方、部门建议将艾滋病从乙类传染病改为甲类传染病,严加管理。而甲类传染病则可以适用“设立和封锁疫区”这一严重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措施。原法律委员会根据一些医学专家的意见,认定艾滋病在传播途径、传播速度和潜伏期长短等方面明显不同于鼠疫、霍乱,在医学上不应将其与鼠疫、霍乱共同划定为甲类传染病,维持了草案原有的传染病分类[25],进而限定了设立疫区与封锁疫区的适用范围,避免了对公民权利的不当干预以及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变相歧视。
又如,原《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草案中规定了“机动车船排污超标的应限期改造更新,超期仍不达标的应责令停止使用”的措施。但有些部门、地方“提出缺乏监管经验”,有些机动车船的排放标准“尚未制定”,“缺乏必要的监测手段”,“即使存在汽车排放标准,但有些地方汽车超标太多”因而“不可行”,原法律委员会采纳相关意见而将上述条款删除[26]。限期报废超标机动车传涉及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原法律委员会首先确认了相关立法事实,即现实中缺乏全面的机动车传排放标准,以及必要的监测手段,进而认定“责令停止使用超标排放的机动车船”无法实现防治大气污染的立法目的,进而放弃了将这一措施写入法律文本,避免了对公民财产权的不当限制。
(三)对特定科技议题进行研究后做出进一步说明
在立法过程中,当不同群体对某个科技议题存在重大分歧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的主体,可以协调对特定问题的研究。之后对特定问题做出说明,或者督促法律起草单位对特定问题做出进一步说明,以便使各方能够统一意见,取得共识。这种调查研究与说明对于普及法律文本背后的科技知识,论证相关法律条款的科学性与必要性,促进专家、立法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深度对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例如,在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后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的过程中,由卫生部牵头起草的修订草案中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两个新病种列入“可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的乙类传染病范围。有些常委委员和地方、专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不宜列入法定傳染病,因为我国尚未发生过这种病例,人与禽之间能否传播,现在还没有科学根据,尚不能下结论,将其列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甲类传染病管理,值得商榷。原法律委员会同教科文卫委员会、原国务院法制办、卫生部研究后认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传染力强、病死率高、危害性大,宜列入法定传染病范围,以加强对它的预防与控制[27]。最终,法律修订草案的内容获得了维持和通过。
又如,2003年在审议《居民身份证法》草案时,有的常委委员建议增列指纹为身份证信息登记项目,但原法律委员会认为“各方面意见还不一致,条件尚不具备”因而“暂不规定”[28]。到了2011年修改《居民身份证法》时,公安部牵头起草的修订草案将指纹信息列入登记范围,公安部专门对此进行了说明,特别指出:“在居民身份证中登记的指纹信息,是数字化的指纹特征点,不能被还原成指纹图像,能够有效保护公民的指纹信息安全”[29]。这一说明能够有效缓解社会公众对于身份证加入指纹信息后可能导致隐私泄露的忧虑,在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相关立法参与者也未对此事提出质疑,因而修订草案顺利通过。虽然立法者在2003年暂时搁置了“身份证收录公民指纹信息”的措施,但也促使相关部门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方面做出更为周到的安排,社会公众对相关技术措施的忧虑也得以解除。
总体来看,在法律草案审议的过程中,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面对相关科技争议时,能够结合相关专家和有关部门的意见,从专业术语表述的准确性、法律措施的可行性和法律规定的科学稳妥性等多个角度出发,积极应对相关科技议题。这在某些场合下甚至确保了法律的合宪性,避免了因对科学技术的误解而导致不当限制或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社会公众对技术风险的担忧,为新技术的应用开辟了法律渠道。
四、法律草案统一审议过程中立法者应对科技议题的策略与思路
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应对科技议题的特殊挑战有两点:一方面,立法者需要在立法过程中需要准确运用大量自然科学知识和相关科学结论,而立法者可能无法独立做出专业性判断;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国家权力具有了更广泛的覆盖面、更深入的渗透性和更强的隐蔽性,立法者需要更加慎重地处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规范科学技术加持下的公权力,避免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不当限制甚至侵犯。相关科技争议的存在本身并不会导致社会公众的担忧,社会公众对科技议题的忧虑源于对科学技术的不确定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公权力滥用风险,专业知识的欠缺和信息不对称可能加剧社会公众对新科技应用的怀疑甚至抵触情绪。
立法介入重大科技议题,既是一个科普的过程,也是一个公共政策的讨论过程。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需要将科技议题转化为法律议题,用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缓解现代科技具备的不确定性风险。更为重要的是,立法过程中的辩论使社会大众相信:相关科技背后隐藏的技术风险和伦理危机能够有效控制,公权力使用相关技术手段和措施将会受到法律的有效规范。公民的合法权益能够受到有力保护,相关的科技会为生活带来便利,而非带来损失和风险。从实践来看,在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处理科技议题时展现出了如下策略:
第一,借助乃至依赖专家和其他机关的说明或专家论证理解、审查法律草案中的科技议题。部分理、工、农、医类的专业术语、概念与标准判断,已经超出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知识范围。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的机构,可能无法对草案中关键科技概念与术语独立提出针对性意见。在此情况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专家和其他机关的意见具有相当的依赖性。从上文梳理的实践来看,有关专家学者、高校、常委会委员、其他专门委员会、相关地方和部门的意见,都得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积极回应。当相关议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能够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处理。这意味着立法过程必须保持公开性,立法过程中的多方参与是妥善处理科技议题、回应社会关注的重要前提,也是确保立法专业性与妥当性的重要手段。
第二,根据立法的需要,对不同的理、工、农、医类术语的定义与内涵进行选择性改造。当科技概念和术语转化为法律文本语言,其内涵需要满足立法目的。立法者对相关科技术语的概念当然建立在相关专业的理解基础之上,不能出现违背科学常识的理解。比如不能将艾滋病与霍乱、鼠疫视为危害性相同的同一类传染病。但在法律文本中的科技术语经立法过程的改造和“裁剪”,与纯粹的学术概念已经出现了差异。比如对“沙化”的定义突出人为因素而有意省去自然因素,以强调《防沙治沙法》的立法目的。这也意味着,立法机关在特定科技术语的定义上,存在着立法自由形成的空间,而不必然受原有理、工、农、医类定义的绝对拘束。如果立法机关认为有必要,甚至可以忽略对特定术语的正面定义,如《民用航空法》中有意回避了对“航空器”的专业定义。在立法过程中,需要对法律草案中专业术语的定义格外慎重,特别是对特定行政机关和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中相关术语的应用要进行充分讨论,防止因部门利益或其他不当利益对相关科技术语的定义产生不良影响,进而影响整部法律的质量。例如,在起草《草原法》时,对“草原”范围的界定事关草原管理部门、林业管理部门与土地管理部门的职权划分。围绕着“树木郁闭度0.2以下”和“树木郁闭度0.1以下”两个界定草原的标准,有关部门在立法过程中曾展开激烈的博弈[30]52-59。只有充分的讨论、沟通、论证,才能够确保法律背后相关科学标准的妥当性。
第三,在立法决策时不必确定科学意义上绝对因果关系。在存在某种可能性或者风险的情况下,立法者即可以根据相关盖然性判断进行立法决策,以达到法律政策层面的特定目的。例如上文所述,即便有关医学专家认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在人与禽之间能否传播尚无科学根据,在我国也没有实际病例作证,但为了满足公共卫生管理的需要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立法者仍然可以将“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列入“可以采取甲类传染病防控措施的乙类传染病”范围。这意味着,当公共利益面对重大风险时,科学上的盖然性足以引发立法政策的变化,以应对不确定的风险,这也会直接影响到合宪性审查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特定立法事实的审查强度。
第四,当特定技术可能影响到公民基本权利而存在争议时,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需要根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对有关技术手段的应用进行规范。诸如“电子定位”(《社区矫正法》)、“技术侦察”(《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规定的对公民权利产生重大影响的技術手段,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统一审议法律草案时,对法律草案进行审查,在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上对相关措施进行合理限制。在审议《社区矫正法》草案时,针对草案中规定的“电子定位”措施,有的常委委员、部门、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提出,使用电子定位应当慎重,建议进一步明确使用的条件、批准程序和期限。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经过批准”明确为“经县级司法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增加规定“使用电子定位方法的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不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及时解除;对于期限届满后,经评估仍有必要继续使用的,经过批准,期限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同时,根据监督管理需要,增加两种可以使用电子定位的情形:一是,“拒不按照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被给予警告的”;二是,“拟提请撤销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收监执行的”[31]。当科技议题转化为法律措施的正当性问题,就为比例原则的适用与法解释学的展开提供了条件。
当科学技术成为国家治理与公权力运行的重要工具时,“科技+国家权力”的组合既扩大了科学技术对整个社会日常生活的实质影响,也深刻影响到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和效率。在“科技议题”转化为“法律议题”的过程中,专业知识、科学常识与公共决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需要通过代议机关的民主确认予以正当化。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应对科技议题所采取的策略,体现出我国立法机关的基本思路如下:
首先,立法者对相关科技议题保持“有限介入”的态度。立法者应对科技议题的重点,不在于从科学技术层面得出正确的科学结论,而在于根据可靠的科学结论进行权力职责与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对于理、工、农、医类的“法外知识”( ExternalKnowledge)的应用和判断,立法者必须谨慎克制。一方面,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会有限地使用相关自然科学的概念及知识体系。只有在有关知识能够构成法律关系或影响法律关系时,立法者对相关“法外知识”才有借鉴的可能性。立法者不需要熟悉和了解所有的自然科学知识,只需要在开放的立法过程中借助专业团体确认作为法律与科技“连接点”的特定科技概念、专业结论的妥当性即可。另一方面,立法机关无法通过立法解决相关科技争议,只是利用已经成为共识的科技知识作为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建构之前提。因此,立法对科技发展的回应,体现出一种“渐进”的趋势。在相关知识存在争议或有关技术措施应用不成熟的情况下,立法机关不会轻易将其纳入法律体系之中。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和技术上的成熟,立法者才有可能考虑通过立法的方式回应具体的科技议题。
其次,立法者应对科技议题的基本方法是在立法中使用、借鉴和改造相关概念和专业术语。立法者无需对相关科技议题中的争议做出科学上的论证,而只需要将已经程序的科技概念或术语嵌入具体的法律规范。立法者借助相关科学知识,将相关科学技术概念纳入法律文本,或者作为相关立法事实之前提,即实现了科学技术概念向法律概念的转化。这就意味着,相关科技知识和概念能够影响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与消灭。经过立法者的使用、借鉴和改造,相关法律规范能够成为执法和司法机关行使职权的法律依据,而其中的科技概念与术语可以作为法律推理的重要前提。立法机关也可以在必要时对相关概念做出法律解释,或者及时修改法律,满足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法律实施的需要。
最后,立法者对科技议题的处理是在民主框架下的一个协商对话的过程,并最终达成法律上的共识。一方面,立法者需要借助立法机关之外的相关部门和专业团体为立法工作中涉及的科技议题提供智力支持,特别是确认立法事实的存在和专业术语表述的科学性,保证立法的严肃性与可行性。相关部门和专业团体借助特定的专业优势,通过向立法机关提出专业意见,影响到法律文本具体内容的形成。立法学和需要确保立法过程的公开性和广泛参与性。另一方面,在立法过程中,有关的概念使用和专业判断需要得到民主的确认,则需要有关部门和专业团体对特定知识进行组织,协助立法者和社会公众了解相关内容,并根据对话和协商进程不断地对相关争议进行说明,为相关议题在法律上达成共识创造条件。而这一对话协商过程所产生的立法背景资料,则可能成为法律通过后执法、司法、法律解释与合宪性审查的重要参考。
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围绕科技议题展开的讨论,直接目的都是为了推动“科技议题”向“法律议题”的转化。而“科技议题”向“法律议题”的转化,本质就是将自然科学知识背后的事物、个人与机关团体纳入到法律关系的框架中。立法过程的公众参与克服了立法机关专业知识上的不足,立法过程的公开和有效协商能够消解社会大众对特定科技议题的质疑,而在立法过程中遵循宪法精神,能够确保国家权力的规范行使。在一个公开的、开放的、民主的、专业的立法过程充分讨论相关议题,既提升了立法的专业性和准确性,更推动了整个社会理性地看待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克服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恐惧,为法律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良性互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也为国家通过立法应对科技风险、特别是规范现代科学技术加持下的国家权力奠定了制度基础。
五、结论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开放、民主的立法过程为立法机关应对科技议题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原则,加强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参与,能够有效确保立法者准确使用科技术语和概念,进而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职责的法律关系。立法者对科技议题的处理,既依赖于其他机关、团体和公众的参与,也具有独立的立法决策考量。应当充分发挥现有立法制度的潜力,运用《立法法》上规定的立法辩论、单独表决等机制,处理立法中遇到的重大科技争议,用妥善的立法消解科技风险带来的社会忧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对国家事务与公民生活的渗透日益深入,而公民权利意识也在不断提升,因此特定领域针对相关科技议题的争议也会不断发生。,但是社会公众对特定议题达成共识的难度可能会越来越大,这就为当代的立法工作的专业性、公众参与的程度和立法过程的公开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立法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在重大的科技议题上,“有限介入”基础上的渐进式探索依旧是立法机关应有的立场。
〔参考文献〕
[1 ]FAIGMAN D L. Where law and science (and religion?)meet[J]. Texas Law Review, 2015(7): 1659-1679.
[2]菲利浦·基切尔.科学、真理与民主[M].胡志强, 高懿,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3 ]张德江.提高立法质量落实立法规划?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中国人大,2013(21):8-13.
[4]沈秀芹.人体基因科技医学运用立法规制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5.
[5 ]罗先觉.我国科技界建制化参与立法的问题及对策[J].科学学研究,2019,37(2): 193-195.
[6 ]高家伟:证据法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8.
[7 ]殷啸虎.论宪法援引过程中的宪法解读:从对黑龙江规定风能太阳能属国有涉嫌“违宪”的质疑谈起[J].社会科学,2012(12):92-100.
[8 ]陈鹏.合宪性审查中的立法事实认定[J].法学家,2016(6): 1-12.
[9 ]GARZONEGE. Scientificknowledgeandlegislativedrafting: focusonsurrogacylaws[J]. Languages Cultures Mediation, 2018(1):9-36.
[10] GARYK. Publicdebateonscienceandtechnology:issuesforlegislators[J]. ScienceandPublicPolicy, 2000, 27(5):321-326.
[11] MUVVIARONIG & KILLIANML. Immutability,science,andlegislativedebateovergay,lesbianand bisexualrights[J]. Journalof Homosexuality, 2004,47(1):53-77.
[12]刘艳丽.社会组织参与立法过程研究?以《广告法》烟草广告条款修订为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13]伊丽莎白·费雪.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M].沈岿,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
[14]江晓源, 方益昉.科学中的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15]GREGORY D. Speaking of science: introducing noticeand comment into the legislative process[J]. Utah Law Review, 2014(2):243-279.
[16]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J].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9(3):333-347.
[17]邢斌文.论立法过程中法律草案合宪性的判断标准[J].政治与法律,2018(11):61-72.
[1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C]//《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38, 53.
[19]薛驹.关于民用航空法(草案修改稿)、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草案修改稿)、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草案修改稿)和食品卫生法(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汇报[J].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5(7):48-54.
[20]从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J].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5):751-753.
[2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J].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9(5):796-798.
[22]李伯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J].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1(6):459-463.
[23]杨景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J].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3(4):392-394.
[24]苏泽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J].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7(5):648-650.
[25]项淳一.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J].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9(1):29-30.
[26]宋汝棼.全國人大法律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J].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7(5): 12-14.
[27]胡光宝.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J].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6):439-444.
[28]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草案)》主要问题修改意见的书面报告[J].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03(4):364-365.
[29]楊焕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J].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1(7):654-656.
[30]布小林.立法的社会过程?对草原法案例的分析与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31]江必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J].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20(1):101-102.
How Legislators Deal with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Issues ?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Law Draft Deliberation
XING Bin-wen
( Law School, Jilin University,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How to make proper responses to releva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ssues by legislation becomes a challenge in modern society. We should try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NPC and NPCSC,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 Committee may fully consider the opinions of experts,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nd agencies during the unified deliberation of law drafts, then decide to adjust the definitions of related concepts, maintain or change the definitions based on specific concepts/standard legal measures, or sup- ply special explanations abou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opics. There is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le- gislation and science.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 Committee uses a variety of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ssues based on the legal methods. We should keep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more transparent and democratic, and strengthe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legislation, to eliminate the risk of uncertainty caused by mod- ern technology.
Key words:legisla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law draft;delib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