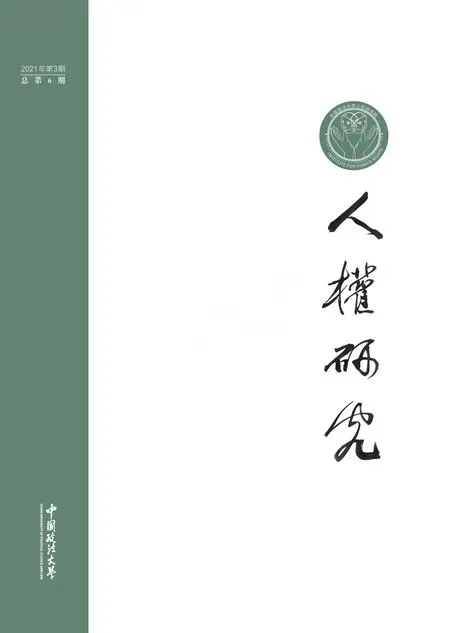中国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法律问题研析
刘小楠 杨一帆
2018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法〔2018〕344号),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一部分“人格权纠纷”的第三级案由“9、一般人格权纠纷”项下,增加一类第四级案由“1、平等就业权纠纷”。这是我国首次专门针对就业歧视发布的案由。“平等就业权纠纷”这一新案由自2019年1月1日起适用。本文通过对2019—2020年间以“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起诉的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考察,揭示法院对“平等就业权纠纷”这一新案由的认识和适用情况,探寻“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对就业歧视司法救济的积极意义和不足,以及折射出的我国在消除就业歧视、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方面的立法和司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平等就业权纠纷诉讼概况
截至2021年8月1日,笔者通过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1截至2021年8月1日,用“平等就业权”作为关键字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检索到12起案件。其中5起案件公布了法院的判决书,这5起案件分别为:杜某诉广东粤海丽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上诉案,案号为(2020)粤01民终219号;韩某某诉北京市大兴区弘福达养老服务中心平等就业权纠纷案,案号为(2020)京0115民初865号;闫某某诉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一审、二审判决书均公布),案号分别为(2019)浙0192民初6405号、(2020)浙01民终736号;杨某某诉杭州次元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上诉案,案号为(2020)浙01民终2725号;关某诉北京减脂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上诉案,案号为(2021)京03民终6702号。其余7起案件有案号和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但因程序性事项或其他原因,没有公布案件相关的法律文书,或公布的法律文书中没有案件的实体性内容。这7起案件分别为:1起以“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进行上诉的案件,但法院以上诉人构成重复起诉为由驳回上诉,该案案号为(2020)皖06民终1313号;2起民间调解结案的案件,法院作出了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裁定书,其中没有说明案件的具体情况,这2起案件的案号分别为(2021)京0115民特27号、(2021)京0115民特26号;1起法院调解结案的案件,法院作出了民事调解书,其中没有说明案件的具体情况,该案案号为(2020)陕0502民初1004号;1起因当事人双方和解而向法院提出撤诉的案件,法院作出了准许撤回起诉的裁定书,其中没有说明案件的具体情况,该案案号为(2019)川0104民初13358号;还有2起只检索到案号的案件,法院没有公布其法律文书,只以“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作为说明,这2起案件的案号分别为(2021)京0108民初5711号、(2020)渝0111财保42号。、媒体报道等公开渠道,检索、收集到我国从2019年1月1日到2020年12月31日的两年间适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的案件15起,其中有8起案件的案情相对清晰,可用于分析。在这8起案件中,7起已经审结(至少已有一审判决)2其中,樊某某诉珠海英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案,被告已提起上诉,二审尚未审结。,其中调解结案的1起,审判结案的6起。这8起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3 关某诉北京减脂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3民终6702号民事判决书。4 案件相关信息参见《验出怀孕当天被辞退,广东“平等就业权纠纷”首案一审胜诉》,载搜狐网2019年11月6日,https://www.sohu.com/a/351974595_260616。

1 杜某诉广东粤海丽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1民终219号民事判决书;未检索到该案的一审判决书。2 韩某某诉北京市大兴区弘福达养老服务中心平等就业权纠纷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865号民事判决书。3 杨某某诉杭州次元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一审详情参见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574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文书中没有实质性内容,只以“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作为说明),二审详情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终2725号民事判决书。4 已立案,未开庭。5 案件相关信息参见周世玲:《青岛一幼儿教师自称因同性恋被解雇 起诉幼儿园获受理》,载新京报网2019年1月15日,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9/01/15/539768.html。6 案件相关信息参见郭帅:《茅台遭派遣员工起诉:擅自检测艾滋指标、拒录艾滋病毒感染者违法 此前已在茅台工作两年》,载中国网财经2019年10月24日,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191024/5104626.shtml。

1 闫某某诉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一审详情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0192民初6405号民事判决书,二审详情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终736号民事判决书。
上述8起案件的原告都是主张自己的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的劳动者(包括求职者),其中2起是求职者被拒绝录用,其余6起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已经形成劳动关系的案件均与劳动关系解除有关。从就业歧视的事由来看,性别歧视诉讼最多,有4起;其余4起案件涉及的歧视事由分别为性别认同、性倾向、健康状况(艾滋病毒感染)和地域。从审理结果来看,在法院已经作出判决的6起案件中,劳动者胜诉的案件只有2起,其余4起案件都是用人单位一方胜诉。劳动者胜诉的2起案件中,法院都判决了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支持了劳动者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在珠海樊某某怀孕歧视案中,用人单位被判决支付劳动者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并被要求向劳动者书面赔礼道歉;在杭州闫某某地域歧视案中,被告喜来登公司被判决支付劳动者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元,并向劳动者进行口头道歉、在国家级媒体《法制日报》登报道歉。
二、我国法院对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中就业歧视的认定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就业歧视作出界定。根据国际公约对歧视的定义,一般认为,歧视的构成要件包括法律禁止的事由、法律禁止的领域、区别对待、不利后果和因果关系。2参见刘小楠主编:《反歧视法讲义——文本与案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本文将从这些歧视构成要件出发对上述案件进行考察,以了解我国法院在审理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时对就业歧视的认定和处理情况。
(一)禁止歧视的事由
禁止歧视的事由(grounds),也即受保护的特征。基于这些法律所保护的特征对人进行区别对待则可能构成歧视。我国《劳动法》明确列举禁止基于“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4种事由的就业歧视。《就业促进法》总则中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第三章“公平就业”中也禁止对残疾人、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农村进城务工的劳动者等人群实施就业歧视。《传染病防治法》第16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中也都有禁止基于民族、性别、残障的就业歧视的规定。因此,我国法律法规中明确禁止的就业歧视事由有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残障、健康状况(主要针对传染病病原携带者)、身份(主要针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7种。
前文表格中的8起平等就业权纠纷诉讼涉及性别歧视、性别认同歧视、性倾向歧视、健康歧视(艾滋歧视)和地域歧视5种就业歧视类型1在最高人民法院增加“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之前,用“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提起的就业歧视案件也涉及到乙肝病毒携带、户籍、年龄、容貌等事由。。其中性别歧视和艾滋歧视是我国法律所明确列举禁止的就业歧视,而性别认同歧视、性倾向歧视和地域歧视则未被我国法律明文禁止。那么这些法律中没有明确列举的事由是否属于法律所禁止歧视的事由,或者说不同性倾向、性别认同、地域的人是否属于反歧视法保护的群体?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未被法律明确禁止的歧视?
在杭州闫某某地域歧视案2大学毕业的闫某某于2019年7月应聘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的“法务”和“董事长助理”两个职位。然而,闫某某很快收到了该公司拒绝录用的回复,原因一栏只写了“河南人”三个字。闫某某认为,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招聘人员存在地域歧视行为,遂提出诉讼。一审法院判决喜来登赔偿闫某某1万元,并在媒体道歉。原被告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0年5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闫某某及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上诉,维持杭州互联网法院一审作出的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赔偿闫某某1万元并在《法制日报》书面向闫某某赔礼道歉的判决。中,法院在一审判决中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条在明确规定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四种法定禁止区分事由时使用‘等’字结尾,表明该条款是一个不完全列举的开放性条款,即法律除认为前述四种事由构成不合理差别对待的禁止性事由外,还存在与前述事由性质一致的其他不合理事由,亦为法律所禁止。”3杭州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192民初6405号。对于司法中应如何处理法律中“等”的范围,该案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也做了详细的阐释:“何种事由属于前述条款4此处指《就业促进法》第3条第2款。中‘等’的范畴,现阶段在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是,用人单位是根据劳动者的专业、学历、工作经验、工作技能以及职业资格等与‘工作内在要求’密切相关的‘自获因素’进行选择,还是基于劳动者的性别、户籍、身份、地域、年龄、外貌、民族、种族、宗教等与‘工作内在要求’没有必然联系的‘先赋因素’进行选择,后者构成为法律禁止的不合理就业歧视。劳动者的‘先赋因素’,是指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人力难以选择和控制的因素,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和调节机制,不应该基于人力难以选择和控制的因素给劳动者设置不平等;反之,应消除这些因素给劳动者带来的现实上的不平等,将与‘工作内在要求’没有任何关联性的‘先赋因素’作为就业区别对待的标准,根本违背了公平正义的一般原则,不具有正当性。”5杭州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192民初6405号。从判决书的这段阐述中可以看出,法官把“先赋因素”和“自获因素”作为确定禁止歧视事由的标准。
在杭州杨某某性别认同(跨性别身份)歧视案6杨某某于2015年入职次元公司,2018年10月,杨某某在经次元公司同意、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后,进行了男跨女性别重置手术。而在其返回次元公司上班一个月后,公司以杨某某迟到早退行为已构成公司“员工手册”中规定的“严重过失”为由作出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杨某某认为,次元公司解除其劳动合同的行为存在差别对待,是基于其跨性别身份的歧视行为,遂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杨某某主张次元公司强行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真实原因是其跨性别身份,依据尚嫌不足”,驳回杨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杨某某不服并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的一审判决中,虽然原告方主张用人单位是基于杨某某跨性别身份而对其进行了差别对待,但是法院在判决中并没有用“等”字来解释跨性别身份歧视也同样被法律所禁止,而是在引用《就业促进法》第3条1《就业促进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 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的规定之后,忽略原告方遭受跨性别身份歧视的主张,直接把跨性别身份歧视纳入性别歧视之中:“本院审理的对象是次元公司是否实施性别歧视从而侵害杨某某的平等就业权。”“基于对本案证据的综合分析评判,本院认为,次元公司并未基于性别歧视原因解除与杨某某的劳动合同,即次元公司未侵害杨某某的平等就业权,对杨某某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108民初5749号。(该判决书由代理律师提供)
可见,法院并没有因为性别认同、性倾向3青岛明珏性倾向就业歧视案尚未开庭审理,但是已经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立案。、地域未被法律明确列举为禁止歧视的事由就拒绝立案,或者以此为由判决劳动者败诉。在杭州闫某某地域歧视案和杭州杨某某性别认同歧视案中,审理法院虽然把地域歧视和性别认同歧视纳入到司法救济之中,但是采用了不同的进路和态度。杭州闫某某地域歧视案一审法院对于利用《就业促进法》第3条的开放性条款禁止各种就业歧视的意义做了阐述:“平等的劳动就业权是公民最重要、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是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依法应受到法律保护。人的特征几乎是无限的,今天闫某某因‘河南人’的地域标签受到歧视,明天其他劳动者也可能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年龄、容貌、方言、血型、甚至是姓氏、星座等等形形色色、举不胜举的事由受到不公平对待,而前述特征中只有极少数特征与工作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相关,故对于侵害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歧视行为,应旗帜鲜明的给予否定,对遭受侵害的权利依法给予及时、适当救济,以维护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秩序及公民合法权益。”4杭州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192民初6405号。杭州杨某某性别认同歧视案审理法院对于性别歧视与性别认同歧视之间的关系仍然持回避和模糊态度,并未明确就性别认同歧视(跨性别身份歧视)是否属于以及为何属于性别歧视进行论证和说明,而且由于两审法院最终都没有认定用人单位的行为构成就业歧视,使得法院对待未明文禁止的歧视事由的态度更显扑朔迷离。
(二)禁止歧视的领域
“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适用于就业领域的歧视案件,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但是在前文表格中的6起已经作出判决的案件中,有4起案件5分别是北京关某怀孕歧视案、珠海樊某某怀孕歧视案、广州杜某怀孕歧视案、北京韩某某退休歧视案。的争论焦点之一都是案件“是否属于平等就业权纠纷”,法院对此的判决意见也并不相同。
在北京韩某某退休歧视案6韩某某在北京市大兴区弘福达养老中心工作。由于其为女性且档案记载身份为工人,因此其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2018年3月11日,韩某某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弘福达养老中心于该日终止了与其的劳动合同,之后双方仅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为此,韩某某认为仅因其是女性,其退休年龄就与男性不同,使得其职业生涯被割断,这是一种就业性别歧视,侵犯了其平等就业权,遂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韩某某法定退休年龄为50岁,被告据此与其终止劳动关系并于之后签订劳务合同并无不当,驳回韩某某关于平等就业权等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韩某某不服并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韩某某全部诉讼请求。中,被告主张:“本案中原告不是入职时遭受歧视性对待,也不存在原告系女性而直接将其辞退,根本不存在其提到的歧视性对待,也不构成对原告平等就业权的侵害,……我单位没有对原告进行不平等对待、歧视妇女,录用时候也没有对原告进行歧视、排挤,或者拒绝录用,不存在侵犯平等就业权的前提。”1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115民初865号。因此,被告方认为双方纠纷是劳动争议,是终止与原告的劳动关系而引起的,不是人格权、平等就业权纠纷。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平等就业权旨在保障求职者与具有相同条件的人在求职过程中,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的不同而被区别对待。但劳动者是否符合退休条件以及办理退休手续等涉及退休问题而引发的争议,并非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亦不属于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项下应当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2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115民初865号。也就是说,审理法院支持了被告的主张,认为平等就业权纠纷旨在保障求职过程中不受歧视,退休等终止劳动关系的案件不应适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
在北京关某怀孕歧视案3关某与被告签订了期限为2015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的劳动合同。关某主张在其孕期及产后,被告对其实施了一系列排挤和报复行为,致使其生理、心理都处于不安状态,故其于2018年6月8日提请辞职。关某认为被告这种持续性的行为均基于其作为女性特有的生育事由,构成对女性的就业性别歧视,遂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结合证据进行了事实认定和法律分析,认为关某主张的被告安排其出差、成立“品牌营销部”、调整办公座位、发放工资及生育津贴等行为中均不存在就业歧视,在该案中不足以认定被告侵犯了关某的平等就业权,关某诉讼请求依据不足,驳回了原告关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中,一审法院对于已经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纠纷是否属于“就业”歧视,是否可以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起诉,也颇为疑惑和犹豫。为此,2020年6月,四川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3所大学的教授签名提交了《关于怀孕排挤与“平等就业权纠纷”的专家意见》,该意见指出,“《就业促进法》的适用范围涵盖招聘及就业全程。立法初衷旨在保护劳动者求职及整个职业生涯的平等就业权,司法宜采取广义‘就业’概念”4《关于怀孕排挤与“平等就业权纠纷”的专家意见》的上述内容可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349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由代理律师提供)。一审法院最后在判决中认定,根据《就业促进法》的规定,“原、被告曾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其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受到就业歧视,故原告以平等就业权纠纷为案由起诉被告并无不当”5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105民初3496号。(该判决书由代理律师提供)。由于缺少法律上的定义,一审法官根据相关文件和词典,对平等就业权作出释义:“对于平等就业权,劳动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中指出,‘就业’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在法定劳动年龄内,依法从事某种有报酬或者劳动收入的社会活动。根据《现代汉语词典》释义,‘平等’是形容词,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相等待遇或泛指地位相等。平等就业权是求职者在招聘阶段及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6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105民初3496号。(该判决书由代理律师提供)二审法院在判决中再次确认了“平等就业权是求职者在招聘阶段及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7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3民终6702号。。
在珠海樊某某怀孕歧视案1樊某某于2019年1月入职英利物业公司,在2月20日发现自己怀孕,便告知其领导。次日,樊某某被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樊某某认为这种非基于岗位需要、无理由解雇怀孕妇女的行为,侵犯了其平等就业权,遂提起诉讼。被告主张其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是因为樊某某迟到、早退等不良行为,而非因其怀孕。法院就被告辞退樊某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樊某某在怀孕前虽有迟到行为和提出过辞职,但英利公司未同意辞职,且未对其迟到行为进行任何处罚;但在知道樊某某怀孕后将其立即辞退,足以证明其辞退樊某某的原因是因为怀孕”,因而判决被告向樊某某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孕期工资损失2,064元、未休产假损失1,87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中,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引用《就业促进法》第3条、第27条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6条、第27条的规定,主张“平等就业权保护的范围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招录过程中劳动者被平等录用的权利,二是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劳动者被平等对待的权利。本案中,樊某某虽然不是在入职时遭受歧视性对待,但英利物业公司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因为樊某某怀孕而将其辞退,使其失去原本已经获得的工作,属于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对樊某某的歧视性对待,仍然构成对樊某某平等就业权的侵害”2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402民初6356号。(该判决书由代理律师提供)。
在广州杜某怀孕歧视案3杜某与被告粤海公司签订了2018年12月3日至2021年12月2日的劳动合同,试用期到2019年6月2日止。杜某于2019年3月发现其已怀孕,并于4月将怀孕事宜告知粤海公司。5月20日,粤海公司以杜某未通过试用期考核、不符合职位录用条件为由将其辞退。杜某认为其入职后工作表现优异,但自告知公司其怀孕事宜后,其工作表现开始被诋毁和恶意降低,导致其在试用期届满前被辞退,被告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其平等就业权,遂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方“无论是分管领导的考核意见,还是人力资源部的调查结果,均认为杜某工作能力没有达到本职岗位工作要求,并未以杜某怀孕等歧视性理由将其辞退”,故驳回杜某诉讼请求。宣判后,杜某不服并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现有事实“未反映出粤海公司因杜某怀孕的事实而对其区别对待的情况”,“杜某在与粤海公司的沟通中也未强调因为怀孕而被区别对待的问题”。“鉴于杜某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粤海公司存在性别歧视行为,故本院对杜某请求,不予支持。”中,法院确认“本案为平等就业权纠纷。就业性别歧视系指用人单位在招聘录用、晋职、晋级、考核评定、报酬、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方面,仅因劳动者的性别而作出的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损害了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和人格尊严”4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1民终219号。。
可见,我国法院对于就业歧视的含义以及“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的适用范围仍然存在争议。目前已判决的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中,有法院对就业歧视采用狭义的理解,认为只有求职阶段遭到歧视才可以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起诉,但是大多数法院对平等就业权做了广义理解,认定形成劳动关系之后遭受就业歧视也可以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起诉。
(三)区别对待的行为
前文表格中的8起诉讼都是涉及直接歧视的案件。“直接歧视即处于同样情况下的一个人因为一种禁止的理由所受待遇不如另一个人”5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第20号一般性意见: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不歧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2款)》,E/C.12/GC/20,2009年,第10段(a)。,其本质是不合理的区别对待,具体而言,这种区别对待可能是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中,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区别对待也是原被告双方的争论焦点之一。比如,杭州杨某某性别认同歧视案中,原告杨某某力图证明其在完成性别置换手术后,与自己实施性别置换手术前相比,以及手术后和其他员工相比,都受到了不利的区别对待。北京韩某某退休歧视案中,原告韩某某主张因其为女性,以及其档案记载为工人身份,因而与男性以及女性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人员相比,在退休年龄上都受到了不利的区别对待。杭州闫某某地域歧视案中,原告也主张被告的行为是因主观上存在对“河南人”这一群体歧视的故意,进而在客观上侵害了原告的平等就业权,这是与其他地域人员相比受到的不利的区别对待。
在几起案件的判决中,法院对于劳动者是否受到不合理的区别对待进行了审视和判断。其中,杭州闫某某地域歧视案的一审判决完美体现了法官对直接歧视概念的运用,判决指出:“就业歧视的本质特征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差别对待,其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要素:第一,存在差别对待的行为;第二,这种差别对待缺乏合理性基础,为法律所禁止”;同时,法院对合理的差别对待、用人单位用人自主权与就业歧视的边界进行了讨论:“用人单位合理、合法的自主用人权应当受到尊重,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过程中的决定性、基础性作用不容否定,但用人单位的自主权应受到法律的规制。就业意味着职业作为一种资源或财富的分配,有分配就会产生竞争,进而不可避免会产生差别,竞争促进发展,并非所有的差别对待都构成歧视,但对资源的分配应符合正义标准——相同者予以相同处理,不同者予以区别对待,歧视的本质不是差别,而是不正当的差别对待,故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不应突破法律禁止的红线,有必要通过司法的评价和确认来厘清权利的边界,引导建立兼具公平、效率的用工秩序和市场环境”;进而法院认定闫某某遭受地域歧视是基于“喜来登公司使用了主体来源的地域空间这一标准对人群进行了归类,并根据这一归类标准而给予闫某某低于正常情况下应当给予其他人的待遇,即拒绝录用,可以认定喜来登公司因‘河南人’这一地域事由要素对闫某某进行了差别对待”。1杭州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192民初6405号。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直接歧视作为一种区别对待,一般都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对象,来说明同样情况下受到不利对待。前述8起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中,有3起怀孕歧视案,怀孕歧视在选取区别对待比较对象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长期以来,我国因怀孕解雇的案件都是通过劳动争议纠纷诉讼来解决的,并没有将怀孕歧视当作“性别歧视”问题来看待和处理,因为立法和司法上并没有对于怀孕歧视比较对象的关注和讨论。“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的适用,使法院更加关注是否存在差别对待的讨论和认定,这在怀孕歧视案中也有体现。比如广州杜某怀孕歧视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杜某以粤海公司侵犯其平等就业权起诉要求粤海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等,根据举证规则,需要由杜某在诉讼中提供证据证明粤海公司在招聘、工作过程中有差别待遇、歧视待遇的情形,比如用人单位没有为怀孕女员工提供适合其身体状况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在晋职、晋级、考核评定、报酬、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方面存在歧视性差别。”2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1民终219号。
北京关某怀孕歧视案中,诉讼各方更是着力分析是否存在差别对待问题。由于该案并不存在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这给怀孕歧视的认定带来更多困难。原告方主张,用人单位对其实施了一系列排挤行为,包括在早孕期被安排连续出差、架空岗位、提高请假审批标准、拖欠工资和生育津贴、跟踪骚扰、拒绝及时出具离职证明等等,排挤孕妇迫其辞职,侵犯了生育女职工的平等就业权,并主张怀孕排挤行为构成“推定解雇”1我国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推定解雇制度,但是2016年樊某某诉苏州某房地产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中,审理法院认为,原告樊某某怀孕后,用人单位免去其企划主管职务(且该通知上未明确原告之后的工作安排),此后,更是将原告调整为行政岗位,负责统计员工宿舍的房租、水电费以及信件收发等事务性工作,该岗位调整明显违反合理性原则,损害原告的职业规划及职业前景,因该调整造成原告辞职的表象,应视为“推定解雇”,即劳动者被迫辞职,故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一审判决参见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6)苏0507民初236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7 年11 月15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5 民终7893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通过对安排出差、成立新部门与调整办公座位、请假、发放工资与生育津贴、邮箱密码、移除部分微信群等行为进行逐条比较的方式,认为“不足以认定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就业权”。比如在“安排出差不属于就业歧视”的分析认定部分,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被告安排原告出差违反了法律规定或者双方合同约定,亦未举证证明被告存在从未安排其他怀孕员工出差的差别对待行为……。”2一审判决书内容由代理律师提供。一审法院把“其他怀孕员工”作为用人单位是否存在怀孕歧视的比较对象并不恰当,因为就业歧视行为本身就是针对某个人群的,并非针对个人,用人单位可能对所有怀孕职工都给予不利待遇,把该案的原告与“其他怀孕员工”比较没有意义。此外,在怀孕歧视案件中,无论是认定“推定解雇”还是“就业歧视”,将每个具体行为孤立起来、单一比较、“就事论事”,很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尤其对于隐性歧视,往往需要法官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来审视一系列间接证据,综合衡量各方面因素来考虑,如果员工不是因为怀孕,是否会遭受这样的不利待遇。
(四)不利后果及因果关系
歧视的构成还需差别对待行为给受害者造成不利后果以及歧视行为与不利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1.不利后果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Discrimination Convention,No. 111)的规定,差别对待的效果为“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则涉嫌就业歧视。“反就业歧视法属于以保护他人利益为目的的行为法,平等就业权的法益结构是人格尊严与就业机会两位一体的利益集合。”3王显勇:《论平等就业权的司法救济》,载《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2期,第88页。但是由于我国“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在“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之下,因此,法院在审判时,会主要关注歧视行为是否对人格权和人格尊严造成侵犯,以及由此造成的精神损害,而不是平等就业机会和平等待遇自身的丧失。比如在北京关某怀孕歧视案中,二审法院指出:“就民事侵权责任而言,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应属于一般人格权的范畴,侵害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行为应以是否侵害自然人人格尊严为主要考量和评判依据……。”1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3民终6702号。根据《民法典》第1183条和《侵权责任法》第22条2《侵权责任法》现已被《民法典》废止。但本研究中几起案例的判决发生在《民法典》生效前,故审理法院在认定劳动者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时仍有以该条作为法律依据的情况。如杭州闫某某地域歧视案,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0192民初6405号民事判决书。的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此原告方不得不在诉讼中着力强调歧视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的严重性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尽管根据2020年12月23日重新修订的该《解释》,原第8条实际已不适用,但本研究中几起案例的判决发生在该《解释》重新修订前,故审理法院在认定劳动者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时仍有以该条作为法律依据的情况。如珠海樊某某怀孕歧视案,参见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6356号民事判决书。。比如珠海樊某某怀孕歧视案中,原告主张“英利物业公司获知樊某某怀孕后,非基于工作岗位需要,无理由解雇樊某某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樊某某的平等就业权利,导致樊某某精神沮丧、失眠、情绪低落、痛苦难当,以至流产,给樊某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害”4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402民初6356号。(该判决书由代理律师提供)。同时,法官也必须在判决中认定歧视行为是否对劳动者造成精神损害。比如,在杭州闫某某地域歧视案中,一审判决中指出:“对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侵害,不仅会使劳动者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不能公平参与社会资源分配,难以通过提供劳动获取基本生活来源,更会阻碍劳动者的人格发展,使劳动者在就业活动中受到排斥、归于异类,会感到自己的人格、自尊被无端地伤害,产生一种严重的受侮辱感,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劳动者精神造成损害,故本案被告喜来登公司侵害原告闫某某平等就业权,原告闫某某主张受到精神损害,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依法应予支持。”5杭州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192民初6405号。
在珠海樊某某怀孕歧视案中,除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赔礼道歉,法院也支持了原告关于孕期工资和产假期工资损失的诉求:“原告在本案主张的孕期、产假期工资损失、生育医疗费,是其平等就业权被侵害后发生的经济损失,可以不经过劳动仲裁程序,在侵权诉讼案件中进行处理。”6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402民初6356号。(该判决书由代理律师提供)
可见,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下,对于求职过程中遭遇的就业歧视,平等就业机会受到的损害并未得到赔偿,只能通过证明自己因歧视行为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从而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或)赔礼道歉。已经形成劳动关系的怀孕歧视案件中,法官对由于怀孕歧视导致的孕产期工资也判决给予赔偿。
2.歧视行为与不利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就业歧视的后果要件也包括不利后果与歧视行为之间要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指损害事实是由区别对待的行为所导致,查找因果关系的目的在于确定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前述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判决中也可见对因果关系的讨论。比如,杭州闫某某地域歧视案一审判决中指出,“被告喜来登公司直接以原告闫某某系‘河南人’为由,两次拒绝闫某某的求职请求,该公司拒绝理由本身就包含明显的不合理的差别对待,属于直接就业歧视,直接剥夺了闫某某平等参与和平等被对待的就业机会,对其人格尊严和意志自由构成侵害,故闫某某在求职中遭受的损害与喜来登公司歧视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1杭州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192民初6405号。。而珠海樊某某怀孕歧视案中,法院则认为“樊某某作为孕妇受到就业歧视,人格权遭受侵害,其主张感受到相当程度的精神痛苦符合常理,予以采信。但是,樊某某在被辞退1个月余后自然流产,难以认定流产与英利物业公司的侵权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此节不作为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因素予以考虑”2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402民初6356号。(该判决书由代理律师提供)。
从上述判决可见,我国对就业歧视的司法认定要求损害后果与歧视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在“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之下,法院强调的损害后果主要是遭遇歧视给当事人造成的精神损害。由于这种精神损害是无形的,甚至间接的,因此证明歧视行为带来的精神损害与证明歧视行为造成的工作机会和平等待遇取消或损害相比较,在直接因果关系的论证上更为困难。
三、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审理就业歧视案件的不足
新增的“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就业歧视案件的“名分”问题,令就业歧视案件“名副其实”,无须再“借名诉讼”,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新案由的增加体现了法院对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重视,鼓励并提醒法院用平等就业权纠纷的视角更清晰地去认定和裁量案件是否构成就业歧视。从前述案件,尤其是杭州闫某某地域歧视案可以看出,法院在是否存在区别对待等就业歧视认定方面做了相当完善和充分的讨论。此外,“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的使用也方便就业歧视案件的统计、研究,有助于反歧视法律和理念的宣传、倡导,从长远看也是推动反歧视立法以及专门的就业歧视类诉讼体系形成的基础。但是,通过前文对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仅仅依靠增加“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仍然无法完全解决就业歧视的司法救济问题。
(一)就业歧视与一般民事侵权构成要件不完全一致
“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在“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之下,因而平等就业权纠纷中所产生的责任往往会参照一般人格权纠纷处理,被归属于一般侵权责任。通说认为,一般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由四个要件构成:(1)损害行为的违法性;(2)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3)行为人的过错;(4)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3参见中央政法干校民法教研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324—338页。前述就业歧视案件的审理法院在判决中一般结合劳动者所主张存在的就业歧视行为,根据一般侵权责任的四个要件来认定用人单位是否侵犯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以及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比如北京关某怀孕歧视案的二审法院明确指出:“本院从减脂时代公司是否存在就业歧视行为、关某的人格尊严是否受到侵害、减脂时代公司的行为与关某主张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减脂时代公司主观上是否有过错等方面进行分析。”4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3民终6702号。这与前文提到的就业歧视通常要考查的禁止歧视的事由和领域、区别对待、不利后果和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并不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特别是就业歧视与一般侵权在过错要件方面的不同,催生了对实践中参照一般侵权案件处理就业歧视案件的做法的反思。
一般侵权责任强调唯有个人过错才是承担责任的合法依据,其中的过错指行为人决定其行为的心理状态,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基本形态。在目前根据一般侵权责任四要件处理就业歧视的实践中,法官不仅需要认定原告因就业歧视遭受的损害事实客观存在,还需要认定被告存在主观过错才可能确定其侵犯劳动者平等就业权。比如,在杭州闫某某地域歧视案中,法院在判决中指出:“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可以推定被告喜来登公司对于其实施的歧视行为至少存在有主观上明知或应知而放纵损害发生的主观过错,具有可责难性。”1杭州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192民初6405号。然而,歧视远不只是个体的偏见问题,往往深受社会制度的影响,而这无法明确归咎于任何个体。2参见[南非]桑德拉·弗里德曼:《反歧视法》,杨雅云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
相关国际公约中强调歧视构成中的消极影响或不利后果要件,但并不要求必须具备歧视的主观要件。比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所载关于歧视的定义明确表明,《公约》适用于基于性别的歧视。该定义指出,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行为,如果其影响或目的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认识、享有或行使其人权和基本自由,这类行为都是歧视,即使这类歧视并非有意。这可能意味着,即使对妇女和男子给予相同或中性的待遇,如果不承认妇女在性别方面本来已处于弱势地位且面临不平等,上述待遇的后果或影响导致妇女被拒绝行使其权利,则仍可能构成对妇女的歧视”3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缔约国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二条之下的核心义务第28号一般性建议》,CEDAW/C/GC/28,2010年,第5段。。
在国外的司法实践中,“(因此)一般都认为在间接歧视中无须证明歧视的故意,在直接歧视案件中也正在逐渐朝这一方向发展。现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南非以及欧盟25个成员国在直接歧视案件中都不要求歧视的故意”4[挪威]Ronald Craig、Lisa Stearns:《歧视概念的演变和发展》,李薇薇译,载李薇薇、Lisa Stearns主编:《禁止就业歧视:国际标准和国内实践》,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0页。。美国对于直接歧视,虽然要求具有歧视的意图(intent)或动机(motive),但是,有区别对待的意图并不等同于有区别对待的恶意。从国外的司法实践来看,即使是出于保护目的而实施的区别对待,只要造成消极的影响或者后果,影响了就业机会均等或者待遇平等,仍然可能构成歧视。例如,某个岗位出差较多,用人单位认为出差会对肢体障碍者造成较大负担而“善意”地拒绝录用。该区别对待虽出于“善意”,但也可能对残障者或与其有密切联系的第三人在平等基础之上认可、享有或行使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造成过度妨碍,故也可能构成残障歧视。5参见刘小楠主编:《反歧视法讲义——文本与案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页。
综上,一般侵权责任所强调的过错主观要件并非就业歧视认定过程中的关注重点。参照一般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来认定就业歧视,无形中提升了就业歧视的认定门槛,使部分实际遭受就业歧视的劳动者无法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
(二)诉讼竞合问题仍无法解决
虽然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就已经确立了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但是直到2008年《就业促进法》实施,招录环节遭遇歧视的劳动者才获得诉权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1条的规定,法院仅受理劳动关系成立后发生的相关纠纷。因此,若劳动者在招录阶段受到用人单位的差别对待,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审查范围。。自此,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招录环节的就业歧视用“一般人格权纠纷”提起诉讼,已经形成劳动关系的就业歧视案件则可以选择使用“劳动纠纷”或“一般人格权纠纷”两个案由起诉2如果用人单位是行政机关,也可能提起行政诉讼。。自2019年1月1日起,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案件可以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立案,但是“平等就业权纠纷”仍属于“一般人格权纠纷”的一种,并没有打破之前就业歧视诉讼的司法救济途径框架。
目前,对于招录环节的就业歧视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起诉在司法实践中尚无争议。但是由于《劳动法》的规定3《劳动法》第79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长期的司法实践及由此产生的思维惯性,再加上对“就业”概念狭义还是广义的理解不同,对已经形成劳动关系的就业歧视案件是否可以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起诉仍然存在争议。虽然大多数审理法院确认了即使是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争议案件,也可以另行提起平等就业权纠纷诉讼寻求损害赔偿,给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救济途径和选择,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争议双方不得不面临多次诉讼。因为在目前我国对就业歧视的司法救济体系下,无论单独提起平等就业权纠纷诉讼还是劳动争议纠纷诉讼,劳动者都无法得到全面的救济和补偿。“平等就业权纠纷是一个综合性的纠纷类型,既包含精神损害又包含物质损害,现行的人格侵权和劳动争议都侧重于保护其中某一方面的法益:人格侵权侧重于保护劳动者的人身利益,劳动争议侧重于保护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如果单纯提起人格侵权之诉,则工资损失、要求录用或复职等因属于劳动争议而需要另行起诉;如果单纯提起劳动争议,则精神损害赔偿因属于侵权请求而不予审查。”4王显勇:《论平等就业权的司法救济》,载《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2期,第90页。前述已经形成劳动关系的6起平等就业权纠纷诉讼中,遭受就业歧视的劳动者也都提起了劳动仲裁,有的甚至经过了劳动争议纠纷两审判决。对于同一个事实提起多个诉讼,不仅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浪费司法资源。
此外,劳动争议的审理依托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劳动法律制度,侵权纠纷的审理依托于《民法典》《民事诉讼法》等民事法律制度。由于立法目的、法律性质等因素的差异,劳动争议与侵权纠纷在审查范围、法律责任、举证责任分配、司法救济途径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起诉的劳动者仍需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法院通常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要求劳动者按照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对违法行为、损害事实、过错、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比如,广州杜某怀孕歧视案的审理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因平等就业权纠纷系人格权纠纷,属于一般侵权案件,故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证明原则。杜某主张粤海公司存在性别歧视行为,应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5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1民终219号。由于就业歧视通常是隐性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相比常常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信息掌握上具有极大的不对称性。前述案件中,杜某最终因无法证明用人单位基于性别歧视解除劳动合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败诉。而在我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用人单位则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劳动争议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倒置,体现了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的倾斜保护。相较于劳动争议案件,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中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举证能力并无不同,基于同类型权利受损的事实,却不能受到同等的救济,存在逻辑上的不自洽。
四、加强平等就业权保障的法律对策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的增加,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就业歧视诉讼的“名分”问题,但就业歧视诉讼面临的其他一些障碍诸如举证难、胜诉难、诉讼成本高等问题仍然存在,而且也产生了用“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处理歧视案件时没有突显的新问题。因此,出台专门的反歧视法,对就业歧视的概念、分类、构成要件等进行界定,把平等就业权纠纷诉讼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诉讼进行确认,并设置相应的认定标准、举证责任和法律责任,是立法和司法仍需解决的问题。
(一)适当增加禁止歧视的事由,明确歧视事由的范围和边界
“(禁止歧视的)基础价值会引导法律在诸多具体事由中有所取舍,选择需要重点保护的类别予以‘明令禁止’。‘法律禁止的事由’的实质是从不同角度将人群进行归类、区分的标准。”1刘小楠主编:《反歧视法讲义——文本与案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6页。对人群归类、区分的标准可以有很多,哪些人群应该纳入法律的保护,哪些对人群归类和区分的事由应该被法律禁止,是我国反歧视立法首先面临的问题。
1.保留开放式列举方式,适当增加禁止歧视的事由
国际人权公约一般采用开放式的规定,通过列举普遍性的禁止歧视事由,设置各国在消除歧视、促进平等方面努力的方向和目标。2比如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2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不得有例如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分”。“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分”这一兜底条款,使禁止歧视的事由具有开放性。国际劳工组织《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禁止“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等原因”(第1条)的就业歧视。除了用“等”字来延展禁止就业歧视的事由范围,“有关会员国经与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如存在此种组织)以及其他适当机构协商后可能确定的、具有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作用的其他此种区别、排斥或优惠”(第1条)也是公约中“歧视”所包括的内容。而各国国内立法和司法中禁止的就业歧视事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歧视法赖以发展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对于禁止歧视的事由各国法律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一些国家采用封闭式的列举方式,将法律保护限定于特定的受保护特征:法律对歧视理由进行穷尽式列举,只有通过立法或者修法才能增加或删除相应的歧视理由,法官不享有自由裁量权。英美和一些欧盟国家的反歧视立法都采用了这种“固定类别”模式。比如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第七章禁止基于个人的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者民族本源(national origin)的歧视;英国2010年《平等法》(Equality Act)禁止基于年龄、残障、性别重置(gender reassignment)、婚姻与民事伴侣、种族、宗教和信仰、性别、性倾向的歧视;德国《一般平等待遇法》(General Act on Equal Treatment,AGG)禁止基于种族或民族、性别、宗教或者世界观、信仰、残障、年龄和性倾向的歧视;瑞典《反歧视法》(Discrimination Act)禁止基于性别、跨性别认同或表达、民族、残障、性倾向和年龄的歧视。1参见刘小楠主编:《反歧视法讲义——文本与案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6—80页。在采用封闭式列举方式的国家,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在实践中拓展禁止歧视事由的空间非常有限,如果劳动者基于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歧视事由受到差别对待,很难获得法律救济。在美国这样的判例法国家也可能通过判例来对法律明确列举的歧视事由的含义进行扩大解释,从而把更多的人群纳入法律的保护。
在另外一些国家,法律对禁止歧视的事由采取开放式的列举方式,既明确列举具体的歧视理由,又使用了诸如“……等”或者“其他情形”等措辞。我国《就业促进法》规定了“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这样原则性的平等权利宣告,之后在列举禁止“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歧视的同时以“等”结尾,就属于开放式的列举方式。与采用封闭式列举方式的国家相比,在采用开放式列举方式的国家,行政部门、执法部门和法院在实践中有更大、更灵活的空间去拓展禁止歧视事由,比如我国教育部通知中禁止的关于毕业院校(985高校、211高校)、户籍、学历、学习方式(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等方面的歧视性要求,其实都是对法律未明确规定的禁止歧视事由的扩展。2如2013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出《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3〕5号),要求各地、各高校在组织校园招聘活动时,要加强对用人单位资质、招聘信息的核查,营造公平就业环境。“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严禁发布违反国家规定的有关性别、户籍、学历等歧视性条款的需求信息,严禁发布虚假和欺诈等非法就业信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2018年,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做好2019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学〔2018〕8号),再次要求各地各高校“加强校园内招聘活动管理,严禁发布性别、民族、院校、学习方式(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等歧视性信息”。2019年,教育部发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6027号建议的答复》(教建议字〔2019〕196号),重申了2013年和2018年两份文件关于严禁发布歧视性信息的要求,同时强调“不得设置与岗位要求无关的条件,不得将院校作为限制性条件”,提高毕业生维权意识。2020年2月4日,教育部办公厅在其印发的《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全日制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研厅函〔2019〕1 号)中要求“对不同教育形式的研究生提供平等就业机会”。2020年11月26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做好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学〔2020〕5号),要求“各省级教育部门要协调和配合有关部门,推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在招聘公告和实际操作中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作为限制性条件,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改变人才‘高消费’状况,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氛围”等。
虽然禁止就业歧视的事由并非越多越好1如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法》(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ct)禁止“基于性别,宗教信仰,残障,年龄,社会身份,出生地域(包括出生地、原籍、未成年之前所在主要居住区),国籍,民族,容貌等身体条件,已婚、未婚、分居、离异、丧偶和事实婚姻等婚姻状况,怀孕或是生育,家庭形态或者是家族状况,种族,肤色,思想或是政见,有效刑期已满的犯罪记录,性倾向,学历,病史等”(第2条)19种事由的歧视,详情参见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网站,https://www.humanrights.go.kr/site/homepage/menu/viewMenu?menuid=002003001002。我国台湾地区的“就业服务法”禁止基于“种族、阶级、语言、思想、宗教、党派、籍贯、出生地、性别、性倾向、年龄、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碍、星座、血型或以往工会会员身分”(第5条)18种事由的就业歧视,详情参见月旦知识库,https://www.lawdata01.com.cn/anglekmc/lawkm?@@984376652。,但是与国际公约的要求以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经验相比,我国目前法律明确禁止的就业歧视事由仍不充分。尽管开放式的列举可以允许法院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道德观念对反歧视事由进行调整跟进,适时拓展受保护的特征范围,2参见[英]鲍勃·赫普尔:《平等法》,李满奎译,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62页。但是对于法律列举之外的歧视事由的认定更依赖于法官对歧视的态度和认知。我国批准的国际公约中所禁止的歧视事由以及我国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歧视现象,尤其是基于“先赋因素”的歧视,如户籍、地域、年龄等,应该由国内立法加以明确禁止。法律明确禁止本身就有强调、倡导和威慑作用。当然在司法中,即使是法律所明确禁止歧视的事由,也需要法官来具体判断这些事由是否与“工作的内在要求”有关。确是基于“工作的内在要求”,即使是针对性别、民族等“先赋因素”进行差别对待,也可能是合理的差别对待,可以构成雇主有效的抗辩事由。
2.明确性别歧视、性别认同歧视和性倾向歧视的关系
“性别”是国际公约以及许多国家和地区有关规定普遍禁止的一种歧视事由。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其涉及平等(反歧视)的相关规定中把性别、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倾向等并列作为禁止歧视的事由。比如,瑞典2008年通过的《反歧视法》在原有立法已经禁止基于性别和性倾向的歧视之外,又新增了“跨性别的身份认同或表达”这一禁止歧视的事由。挪威《平等与反歧视法》(Equality and Anti-Discrimination Act)也明确禁止基于性别、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倾向的歧视。英国《平等法》禁止基于性别、性倾向和性别重置的歧视。我国台湾地区的“性别平等教育法”也要求在学习环境与资源方面,学校不得有基于性别、性别特质、性别认同或性倾向的差别待遇。3详情参见月旦知识库,https://www.lawdata01.com.cn/anglekmc/lawkm?@@1763666303。在性别歧视与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倾向等歧视事由并列的时候,“性别歧视”一般是相对狭义的概念,仅指对男女两性的区别对待。比如,在英国《平等法》中,性别(sex)被界定为“对男性或者女性的指称”;“‘性倾向’被定义为一个人对相同性别的人、另一性别的人以及两个性别的人在性问题上的取向”,亦即“受保护的群体包括同性恋、异性恋和双性恋”;“跨性别的人(transsexual or transgender or gender variant, trans)是指那些不完全认同自己出生时性别的人,或者不遵从与这一性别相关的外表或者行为方式预期的人”。4[英]鲍勃·赫普尔:《平等法》,李满奎译,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99、112、101页。
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禁止性别认同和性倾向歧视,但不论是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起诉的杭州杨某某性别认同歧视案,还是之前用“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起诉的深圳穆易(化名)性倾向就业歧视案1一审详情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粤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二审详情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789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一审、二审判决书均由代理律师提供)、贵阳C先生跨性别身份就业歧视案2一审详情参见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6)黔0103民初217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由代理律师提供);二审判决书内容亦由代理律师提供,文书案号已做隐去处理。等诉讼,审理过程中法院和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讨论性别歧视与性倾向歧视或者性别认同歧视之间的关系。如在贵阳C先生以“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提起的就业歧视诉讼中,虽然原告主张了被告公司是基于其跨性别身份进行歧视,但是法院在判决中并没有作出被告公司对原告的歧视行为是基于何种事由的认定,只是指出被告公司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就业权和人格权,未明确判定被告公司的行为对原告构成性别歧视或者性别认同歧视。C先生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确认就业性别歧视”以便“提高判决质量”,主张《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禁止就业性别歧视,“其中‘性别’涵盖性别、性别认同、性别表达,这已经成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共识”。二审法院判定个人的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属于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本案中,某某对自己性别的认同与表达应当依法受到保护和尊重,但其认为某某公司的行为对其构成性别歧视的主张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3二审判决书内容由代理律师提供,文书案号已被隐去。也就是说,二审法院并没有明确支持或者否认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属于性别歧视,而是以证据不足为由,未判定被告公司的行为构成性别歧视。而在2019年杭州杨某某以“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提起的就业歧视诉讼中,虽然原告方声称其是因跨性别身份而遭遇用人单位歧视,法院却没有讨论性别认同(跨性别身份)歧视与性别歧视之间的关系,直接把性别认同(跨性别身份)歧视纳入到性别歧视中。
虽然我国目前基于性别认同、性倾向歧视的诉讼并没有因为法律未明文禁止而无法得到司法救济,但是法律若能对性别认同、性倾向歧视明确加以禁止才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一方面,这些禁止歧视的事由在法律中列举,可以明确和强调具有这些特征的人群受到法律保护,4比如C先生一案二审中,被上诉公司就提出:“某某自称是‘跨性别者’身份,该身份是其自身主观判断,并没有任何权威机构或者司法鉴定部门对其特殊身份进行认定,其自认的身份也不属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身份,现行法律并未对该种身份人群的权利义务进行规定。”从而减少法官个人观念认识等方面的制约,避免法官以证据或者程序为由回避对歧视的认定。另一方面,尽管性别与性别认同、性倾向关系密切,但是并不能相互替代:“首先,受到性倾向歧视不利对待男、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而司法上认定的性别歧视不利对待的往往是女性;其次,性倾向歧视背后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恐同(Homophobia)或者叫异性恋霸权,而不是性别歧视主义(sexism)。最后,更重要的是,性别歧视进路的运用,使得法院失去了批判性倾向歧视的机会。而最后这个方面可能也是最重要的,看起来性别歧视比性倾向歧视受到主流更多的重视,可以让性倾向歧视的受害者‘搭一下便车’,但是这又把反对性倾向歧视的话语关在了‘柜子’(closet)里。如果联想到,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性倾向歧视,大量的同性恋者掩藏自己的身份,成为不可见的群体,我们会知道用性别歧视处理性倾向问题更加强化了同性恋‘不被看见’的现实。质言之,如果用性别歧视进路来禁止性倾向歧视,那么关于同性恋的核心道德争论被架空了。”1刘小楠主编:《反歧视法讲义——文本与案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55—256页。而与性别歧视关系更加密切的基于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歧视也存在类似情况。将性倾向和性别认同作为禁止歧视的事由予以明文列举,才能更好地保护同性恋及跨性别者的权利。
3.明确怀孕歧视与性别歧视的关系及其比较对象
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起诉的3起怀孕歧视案,本文都归类为性别歧视。但是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并未出现怀孕歧视的提法,也未明确规定基于怀孕生育的歧视是一种性别歧视。在前述3起怀孕歧视案中,除了广州杜某怀孕歧视案2“本院认为,本案为平等就业权纠纷。就业性别歧视系指用人单位在招聘录用、晋职、晋级、考核评定、报酬、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方面,仅因劳动者的性别而作出的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损害了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和人格尊严。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应该是:粤海公司在用工的过程中是否对杜某存在性别歧视行为,即粤海公司在试用期解除杜某劳动关系的原因是否系因杜某的女性身份以及怀孕事实。”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1民终219号。,另外两起案件的审理法院并未讨论怀孕女员工是否遭受性别歧视,而只是审查她们是否遭受就业歧视、她们的平等就业权是否受到侵犯。而且在北京关某怀孕歧视案中,一审法院把原告与“其他怀孕员工”的待遇相比较作为用人单位是否存在怀孕歧视的依据。
在国际上,对怀孕歧视与性别歧视的关系以及对怀孕歧视比较对象的认识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一些国家早期的法律其实并不认为对怀孕女性予以解雇或施以不平等的对待构成性别歧视。比如,英国法律曾认为性别歧视需要以男性为比较对象,但不可能有怀孕的男性与怀孕女性进行比较。因此,女性因怀孕而遭受差别对待不属于性别歧视。后来英国有判例3Hayes v. Malleable Working Men’s Club & Institute, [1985] IRLR.将女性怀孕与男性患慢性病类比,如果男性因患慢性病长时间无法正常工作而被解雇不构成歧视,那么雇主解雇孕期妇女也不构成歧视。美国1978年《反怀孕歧视法案》(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ct)也做了类似的规定,雇主们只被要求对怀孕员工给予与其他暂时性失去工作能力的员工相同的对待。这导致许多雇主,尤其是那些女员工占很大比例的行业的雇主,倾向于给所有的员工较少的福利待遇,以规避在女员工怀孕生育方面的成本。
在女权运动的推动下,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相关规定和判例中逐渐确认了怀孕歧视是一种性别歧视,而且不需要与男性相比受到较差待遇才能认定。比如,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性别歧视条例》第8条“对怀孕女性的歧视”规定:“任何人如——(a)基于一名女性的怀孕而给予她差于他给予或会给予非怀孕者的待遇;……即属在就第3或4部任何条文而言是有关的情况下,歧视该女性。”4参见电子版香港法例网站,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480!sc?INDEX_CS=N。本条援引的“第3部或4部任何条文”指的是《性别歧视条例》第3章(“在雇佣范畴的歧视及骚扰”,第11—24条)和第4章(“在其他范畴的歧视及骚扰”,第25—41条)所包括的条文。也就是说,一般的性别歧视,比较对象应该是另一个性别的人;而在怀孕歧视案件中,比较对象不应该是男性,也不应是其他怀孕员工,而应该是未怀孕员工。
目前一些国际公约和文件、国外立法和判例中也确立了怀孕歧视可以没有比较对象的规则。比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在第20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直接歧视还包括在没有可比较的类似情况下出于禁止的理由所采取的有害行为或不作为(例如,在妇女怀孕的情况下)”1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第20号一般性意见: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不歧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2款)》,E/C.12/GC/20,2009年,第10段(a)。。欧盟发布的关于保护怀孕受雇者的指令(Council Directive 92/85/EEC)2Council Directive 92/85/EEC of 19 October 1992, on the introduction of measures to encourage improvements in the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of pregnant workers and workers who have recently given birth or are breastfeeding,[1992] OJ L 348/1, Article 11(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1992L0085&from=EN.也确认怀孕歧视的认定不需要参照对象。英国2010年《平等法》不仅明确把怀孕和生育列为禁止歧视的事由,而且规定如果某人仅仅因为女性怀孕的事实而亏待她(unfavourably),即可以认定该人的行为构成性别歧视。3[南非]桑德拉·弗里德曼:《反歧视法》,杨雅云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160页。
近年来,随着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怀孕解雇和怀孕排挤现象日益严重且具有普遍性4“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对城镇女性就业影响机理研究”的专项调查数据显示:“生育二孩的女性所遭受的就业歧视是生育一孩女性的2.033倍。……其中私企表现最为明显,歧视程度较国有事业单位增加了61.4%。”蒋思睿、杨欢、刘军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歧视的影响研究》,载《劳动保障世界》2020年第3期,第18、19页。,“全面三孩”政策的推广更可能成为育龄女性就业的阻碍因素。在法律中明确怀孕歧视是一种性别歧视以及针对怀孕的推定解雇制度有助于遏制怀孕歧视的发生。另外,“只有法院和立法机关在认定直接歧视时不再机械地要求参考对象,才能真正保护因怀孕和生育而遭受歧视的妇女”5[南非]桑德拉·弗里德曼:《反歧视法》,杨雅云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160页。。
(二)明确就业歧视和平等就业权的含义
“就业”歧视是否仅指劳动关系形成前的招录环节中的不合理差别对待?形成劳动关系后,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不平等对待是否属于侵犯其平等就业权、是否可以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起诉?上述两个问题涉及对就业歧视和平等就业权含义的认定,是法院在审理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中的争议焦点之一,我国应尽快通过立法加以明确。
1.相关国际公约以及部分国家和地区有关规定中就业歧视的适用范围
在相关国际公约以及部分国家和地区有关规定中,就业歧视(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是一个广义概念,包括整个工作环节中不合理的差别对待。国际劳工组织《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1条规定:“就本公约而言,‘就业’和‘职业’二词所指包括获得职业培训、获得就业和特定职业,以及就业条款和条件。” 这里,“就业”(employment)指“与用人单位处于雇用关系的条件下从事的工作”;“职业”(occupation)指“不论经济活动类型、不论就业地位,个人所从事的行业、专业或工作种类”。也就是说,该公约不仅为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提供保护,也为从事所有类型工作的人提供保护,使他们不受歧视。“‘就业和职业’这一术语也包括公务员(包括军队和警察)、农业工人、无薪家庭工人、企业主和家政工人,以及街头小贩、出租车司机和三轮车夫等非正规就业中的自雇就业人员所从事的劳动”。1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国际劳工组织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体面劳动技术支持小组:《工作中的平等和无歧视(中国):工作手册》,第10页,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57232.pdf。国际劳工组织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建议书》(第111号)要求“各会员国应制订一项国家政策以防止就业和职业歧视”,并应考虑一系列原则,其中包括“所有人员都应在下列各方面无歧视地享有机会均等和待遇平等:(1)获得职业指导和安置服务;或(2)在个人适合该种培训或就业的基础上获得自己选择的培训和就业;(3)根据个人特点、经验、能力和勤勉程度的提升;(4)享有就业保障;(5)等值工作等值报酬;(6)工作条件,包括工时、休息时间、有酬年假、职业安全和卫生措施,以及与就业有关的社会保障措施、福利设施和津贴”。2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国际劳工组织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体面劳动技术支持小组:《工作中的平等和无歧视(中国):工作手册》,第57页,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57232.pdf。
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规定中,就业歧视的适用范围也包括了整个工作过程。比如,德国《一般平等待遇法》禁止在选拔标准和录用条件、雇佣条件和工作条件、职业晋升、职业咨询、职业培训、职业协会的成员资格与参与权、劳动保护等各个方面基于种族、民族、性别、宗教或者世界观、信仰、残障、年龄和性倾向8种事由的歧视,并且雇主有责任防止或消除在这些领域中的不平等待遇。英国《平等法》禁止雇主在劳动就业中对雇员或者求职者进行歧视或者欺凌,这一规定适用于招聘、获得劳动条件、晋升、培训或者其他待遇的机会、解雇或者其他损害。韩国《促进男女就业机会平等和支持工作与家庭平衡法案》第二章对法律适用的雇佣范围进行了列举,禁止包括招聘、录用、工作分配、工资、津贴、岗位培训、岗位调动、晋升、退休和解聘在内的各个工作环节的歧视。此外,该法案还禁止在工作场所实施性骚扰,并提供预防性补救措施。我国台湾地区“性别工作平等法”通过列举的方式对不得进行性别歧视的情况进行了规定,要求雇主对于求职者或受雇者的招聘、面试、录用、工作分配、业务考核或职务晋升、为员工提供或举办的再教育、培训或其他类似活动以及薪资给付、福利措施、退休、资谴、离职或者解雇都不得因为性别或性倾向而有差别待遇。3详情参见月旦知识库,https://www.lawdata01.com.cn/anglekmc/lawkm?@@1405098335。
2.在法律中明确平等就业权的含义和就业歧视的适用范围
“平等就业权是反就业歧视的基础和‘权利支点’,反就业歧视是平等就业权的保障,两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基本关系。”4李雄:《平等就业权法律保障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4页。关于平等就业权和就业歧视,国内学者存在狭义与广义的理解。有学者认为,狭义的就业权仅为劳动用工即建立劳动关系前的权利,亦即就业权一般意义中的工作自由权与平等就业权,且该平等就业权仅限于求职或找工作阶段的权利,相应地,就业歧视就仅限于求职和招工阶段的歧视。5参见李雄:《平等就业权法律保障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129页。也有学者认为,平等就业权应广义理解,指“平等地获得就业机会、就业待遇、就业保障和就业服务等方面的权利”6郝红梅:《平等就业权研究》,山东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4页。;相应地,“就业歧视是指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基于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对劳动者进行差别对待,损害其均等就业机会或平等待遇的行为”1王显勇:《论平等就业权的司法救济》,载《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2期,第93页。。学术上的不同理解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已经形成劳动关系的案件是否可以适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的争议,主要是因为法律规定不明确。
虽然平等就业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在《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中得到确立,但是我国法律中没有关于平等就业权或者就业歧视的界定。“就业”一词在《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中经常在“择业”“招用”等语境下使用。比如,《劳动法》总则中第3条把“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作为一项劳动权利与“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并列列举。第二章“促进就业”中,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第13条第1款在规定了“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后,第2款仅强调“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而没有关于其他工作环节中禁止歧视的规定。另外,我国《劳动法》只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也就是说《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范围不包括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而且对于尚未形成劳动关系的求职者,若在招聘环节遭遇歧视,也无法依据《劳动法》进行救济。2《劳动法》第79条。而《就业促进法》虽然可以适用于求职者,也给遭遇就业歧视的求职者提供了诉权3《就业促进法》第62条。,但是《就业促进法》是“为了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它在多处提到“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4如《就业促进法》第2、12条。。其中的“就业”似乎仅指狭义上工作岗位的获取,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找工作”;那么“就业歧视”则仅指招用环节中的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比如第3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第三章“公平就业”中强调的都是“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实施就业歧视”5参见《就业促进法》第26—31条。。综上,根据文义解释,对我国立法中“平等就业权”采取狭义解释似乎更为恰当。
尽管《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对“就业”一词含义的使用相对狭窄,但两部法律都强调对劳动者全面的劳动权利提供平等的保护。比如,《劳动法》总则中第3条保障劳动者各方面的劳动权利,各章也对这些权利做了具体规定。《就业促进法》第27条第1款也强调“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第28条第1款强调“各民族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同时,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传染病防治法》等多部法律对此也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以残障人士的平等就业权为例。《就业促进法》第29条第3款仅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歧视残疾人”;而《残疾人保障法》第38条第2款则要求在整个工作环节——“职工的招用、转正、晋级、职称评定、劳动报酬、生活福利、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都不得歧视残疾人。可见,我国多部立法都要求对劳动者入职期间及其整个职业生涯的劳动权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对此,国家应出台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对就业歧视的概念、分类作出明确的界定,使其与相关国际公约的要求保持一致。1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对中国政府履约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指出中国法律尚未按照《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要求,为“对妇女的歧视”作出定义,建议中国“按照《公约》第1条的规定在本国立法中通过关于歧视妇女的全面定义,以确保妇女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会受到直接和间接的歧视。尤其是,缔约国应当确保有适足的执行机制和制裁措施配合禁止基于性和/或性别的歧视。”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中国第七和第八次合并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CEDAW/C/CHN/CO/7-8,2014年,第12、13段。在通过制定新法律或修订既有法律来扩大和明确平等就业权和就业歧视含义之前,也可以优先通过司法解释,对“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的适用范围进行扩大解释。
(三)确立就业歧视是一种特殊民事侵权诉讼
就业歧视在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和法律责任方面与一般民事侵权相比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就业歧视的司法诉讼中,法院应当从区别对待是否造成“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效果的角度来考查是否存在就业歧视行为。此外,特殊的举证责任和法律责任的确立也是非常必要的。“平等就业权争议应当属于劳动法领域的特殊侵权纠纷,适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国反就业歧视法应当建立举证责任转移制度和抗辩制度,将就业机会纳入损害赔偿范围,将强制缔约设定为独立的责任类型,并按照保护的法益建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2王显勇:《论平等就业权的司法救济》,载《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2期,第95页。
1.明确就业歧视案件的举证责任转移制度
在就业歧视诉讼中,举证责任转移是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的举证规则。为了减轻歧视受害者的举证责任,许多国家和地区规定了举证责任转移,即原告提出表面证据后举证责任发生转移,由被告举证证明其行为不是基于歧视事由作出。比如,欧盟理事会2000年11月27日发布的关于建立就业与职业平等待遇总体框架的指令(Council Directive 2000/78/EC)规定:如有明显的歧视情况,举证责任规定应与之适应,且为了有效应用平等待遇的原则,在提供此类歧视证据后,举证责任应转换到被告方。但被告无需证明原告坚持某一特定宗教信仰、有某种残疾、处于某个年龄或有特定的性倾向。成员国应根据其国家司法制度采取必要措施,在因被告未履行平等待遇原则而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原告向法庭或其他主管机构举出可能用于推测直接或间接歧视的事实时,确保由被告证明其未违背平等待遇原则,但不得阻碍成员国推出对原告更有利的举证规定。3Council Directive 2000/78/EC of 27 November 2000, establishing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equal treatment i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2000] OJ L 303/16, paras. (31) and (32) in the preface part,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L0078&from=EN.德国《一般平等待遇法》第22条规定,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间接证据推测歧视是因为本法第1条4德国《一般平等待遇法》第1条规定:“为了防止或者消除因为种族或者民族、性别、宗教或者世界观、残障、年龄或者性倾向的原因产生的歧视,制定本法。”列举的原因造成的,那么另一方当事人应承担证明其没有违反歧视禁止规定的举证责任。我国台湾地区的“性别工作平等法”第31条规定:“受雇者或求职者于释明差别待遇之事实后,雇主应就差别待遇之非性别、性倾向因素,或该受雇者或求职者所从事工作之特定性别因素,负举证责任。”1参见月旦知识库,https://www.lawdata01.com.cn/anglekmc/lawkm?@@1405098335。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无论是用“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还是“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起诉的就业歧视案件,都需要由劳动者承担遭受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也有法院试图让用人单位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从而与用“劳动争议纠纷”案由提起该诉讼时的举证责任保持一致。比如,在贵阳C先生用“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起诉的跨性别身份就业歧视案中,一审法院主张“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因的举证责任应该分配给被告”2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黔0103民初2174号。(该判决书由代理律师提供),但是二审法院仍然坚持应该“谁主张谁举证”,对C先生要求认定被告公司构成就业性别歧视的主张不予采纳。而在杭州闫某某地域歧视案中,一审法院主张:“对于是否存在差别对待现象初步的举证责任在于求职者,即求职者应举证证明用人单位存在将原本无序混杂的人群按照某一标准重新分割排列,触发归类效果,并对其产生不利后果。求职者完成前述证明责任后,应由用人单位举证证明差别对待具有合理依据,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若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待遇的差别是合理需要,则可判定歧视成立。”3杭州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192民初6405号。这与其他国家法律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有关规定中采用的举证责任转移规则类似。
在司法实践中,隐性的就业歧视非常普遍,用人单位经常会用某些借口来掩盖差别对待的真实意图,由劳动者承担过重的举证责任不利于对其平等就业权的保障。因此,在明确规定举证责任转移的反歧视立法出台之前,宜由最高人民法院对就业歧视案件的证据规则作出司法解释,把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的举证原则扩展适用到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中,从而明确和统一就业歧视案件的举证责任问题。
2.明确就业歧视的法律责任
目前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提起的就业歧视案件属于人格侵权之诉,原告能够获得的民事赔偿主要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赔礼道歉,工资损失、要求录用或复职等因属于劳动争议救济范畴而很难得到补偿。而且对精神损害的评估很难有统一客观的标准,即使是同样的歧视行为,对不同人造成的精神损害也不会相同,所以“至于精神抚慰金的金额,因精神损害系受害人痛苦之感受,然而受害人痛苦之有无、大小、长短,因人而异,精神损害既不具有金钱价值,又没有为人们易于辨识的物理特征,因此,受害人精神损害抚慰金之确定,须就个别案件,斟酌一切情势,始能实现抚慰金制度之抚慰、惩戒及调整功能”4杭州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192民初6405号。。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各法院判断的就业歧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不确定,随机性强;而且法官往往不认为“丢掉一个工作”会给个人造成多大的人格侮辱或贬损,所以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普遍偏低。比如近几年的几起用“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起诉的性别歧视诉讼1这3起诉讼分别为:郭某诉杭州市西湖区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一般人格权纠纷案,参见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4)杭西民初字第1848号民事判决书;邓某某诉北京市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等一般人格权纠纷案,参见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5)顺民初字第03616号民事判决书;梁某某诉广东惠食佳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等一般人格权纠纷案,参见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5)穗海法民一初字第1322号民事判决书。,劳动者虽然胜诉,但都仅仅得到2,000元的经济赔偿。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下的两起胜诉案件杭州闫某某地域歧视案和珠海樊某某怀孕歧视案中,劳动者分别拿到了9,000元和1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相关维权支出补偿和工资损失赔偿,法院还支持了原告要求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这是重要的进步。
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现有“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下原告能获得的救济和赔偿还非常有限。比如,德国《一般平等待遇法》规定,如果是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遭受了就业歧视,可以获得不超过3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2参见刘小楠主编:《反歧视法讲义——文本与案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03页。原文为“《平等待遇法》”,此处正文中为“《一般平等待遇法》”。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规定,被告雇员数在101人以下的案件每位受害者获得赔偿的上限是5万美元,被告雇员数在500人以上的案件每位受害者获得赔偿的上限是30万美元。3参见卢杰锋:《美国反就业歧视法律救济研究》,载刘小楠、王理万主编:《反歧视评论》第6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页。《1991年民权法案》加大了补偿性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责任,并规定对实施故意歧视的被告判处支付应发报酬、恢复原告原职。美国就业歧视的法律责任包括:雇用、升职、复职、赔偿预期工作损失(front pay)、支付应发的工资福利(back pay)、支付违约金;补偿性赔偿与惩罚性赔偿;赔偿利息损失;授予资历、禁令救济、赔偿律师费与诉讼费。4See Barbara T. Lindemann & Paul Grossman,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aw, 4th Edition,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Inc., 2007, Part VII.在加拿大,“一旦就业歧视行为被确认,那么歧视受害者可能获得的法律救济包括:停止歧视行为、恢复职务、给予赔偿以及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不超过2万加元)。如果法庭认为歧视行为人具有故意或者放任情节,可以对其课以不超过2万加元的惩罚性赔偿”5刘小楠主编:《反歧视法讲义——文本与案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02页。。
我国在就业歧视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了应该增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补偿劳动者遭受的实际经济损失,也应充分考虑就业歧视给劳动者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比如劳动者因失去特定的工作机会或者职业发展的机会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并适当增加对用人单位的惩罚性赔偿。这样才能更好发挥法律的教育、引导、威慑功能,有效遏制就业歧视的发生。
五、结语
通过对2019—2020年间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起诉的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法院用平等就业权纠纷的视角取代传统劳动争议纠纷的角度去认定和裁量案件是否构成就业歧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区别对待等就业歧视认定问题进行了更为充分的讨论,有利于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保护。但是,“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的增加仍然无法完全解决就业歧视的司法救济问题,法院对于就业歧视的构成及其危害以及“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的适用范围仍然存在认识不清的情况。对就业歧视进行清晰界定,并设置相应的认定标准、举证责任和法律责任,是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和司法仍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