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小说的别样叙述
文|张学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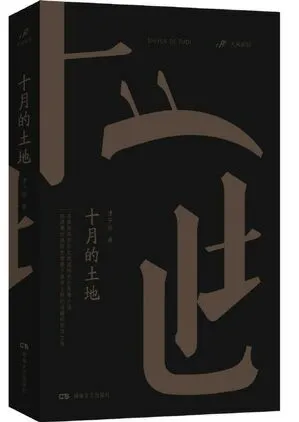
津子围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2021年1月定价:48.00元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津子围无疑是内敛低调的。早在1980 年代他就开始文学创作,有评论者称,相较于余华、苏童等知名作家,津子围是“被落下的人”,语义之中不无惋惜。诚然,在40 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津子围并没有在文学的天空划过石破天惊的绚烂彩霞,但他长久的坚持,默默的坚守便是对文学最为虔诚的致敬。他以写实的态度注视生活,探求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小人物的命运,尽管他的线条粗粝,却描摹出社会众生相的真实底色。尤其是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更是在那些为生存而奔波的都市知识分子和各色小人物身上,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内涵。所以,当我翻开他的长篇小说《十月的土地》,便有了一丝惊诧,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津子围。
《十月的土地》讲述的是东北某地章姓家族两代人在时代巨变中的风雨沉浮。从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时间跨度整整半个世纪。这里有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残杀、乱伦、背叛;也有在国难当头之际的不同人生选择,家族叙事与历史叙事、乡土叙事“混搭”出镜,所有这些似乎都与那个一度沉浸在日常生活中,去探求人生意义的津子围截然不同。然而,当我读完这部30 多万字的长篇,我似乎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津子围。在《十月的土地》中,津子围没有延续《白鹿原》《古船》《旧址》《红高粱家族》等宏大的家族叙事路径,他书写的依然是沉淀在历史尘埃中的小人物,不动声色地注视黑土地上一个家族的变迁,以“零度”姿态投入到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没有史诗的悲壮,没有对英雄的歌颂,没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批判,只是在回到事实本身的“现象学”中,让读者自己去触摸来自那个遥远家族的声音,从而,在各自的经验世界里更有温度地去感受,去理解,去思考。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家族叙事并不陌生。家族是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基石,数千年来“家国同构”的文化观念影响深远,由此,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家族小说成为一个重要的支脉。这些家族小说大多是以家族为叙事原点,最终将民族、家族和个人整合到一起,在叙事上表现出对民族国家想象的诉求。与此相比,津子围可谓另辟蹊径。尽管他依然在民族危难中书写一个家族的命运,但他更多的是将视角聚焦到家族的内部,在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与争斗中去挖掘人性,同时,去探究一个乡村的大家族是如何从内部腐朽坍塌的,让历史在家族伦理的印记里呈现出别样的色彩。我认为,这无疑是对家族叙事的一种有益尝试。
津子围的家族叙事有着明显的伦理预设,文本聚焦于章姓家族的两个支脉——章兆仁和章兆龙两家,隐含着善与恶的对立分野。章兆龙是家里的大掌柜,统领整个家业,一生坏事做尽,成为传统道德链条中脱钩的“逸出者”。在章兆龙那里,一切家族伦理,如忠孝、慈爱、仁义等,都被彻底颠覆了。而这种摧毁性的邪恶力量在他的家族中传承下去。他的二儿子章文礼与嫂子通奸乱伦,强行霸占堂弟的未婚妻,甚至不顾亲情,在大哥章文智被绑票后,竟然想趁乱杀死章文智,借此独吞父亲的财产。在此,人性的欲望遮蔽了家族伦理和亲情,道德堕落、两性乱伦与血缘危机,已经深入到家族制的肌理层面,将运行了千百年的家族制机器溶蚀成一滩模糊不清的腐烂器官,而传统家族文化的消散自然成为乡土精神衰亡的隐喻。

然而,津子围并不是一味地书写衰败,他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那就是章兆仁一家。与章兆龙不同,章兆仁诚实本分,热爱土地,靠勤劳致富,累积家产,符合农业文明时代的集体想象。尤其是他的大儿子章文德,更是贯穿文本始末的精神象征。章文德在大地的根性里呼吸着传统,传承着家族的血脉,以至成为一种传奇。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历史和文化始终有两条线索贯穿始终:一是农耕文明,一是儒家文化。千百年来,两者已然沉淀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并深深地融入到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肌理。由此看来,津子围将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的精神命脉凝聚到章文德身上,是将他作为挽回摇摇欲坠的家族文化的希望。从这个角度看,津子围无疑站在维护传统家族文化的立场。津子围正是通过家族内部的“看得见的矛盾和看不见的抵牾”,呈现了历史转型时期家族秩序的日渐解体,但是,他并没有发出感伤的哀婉,而是乐观地给予未来更多的希望。所以,在文本的最后,章文智用章文德弟弟章文海的名字,更换了自己的名字。这不仅是为了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章文海,同时也是对自己家庭的背叛,是对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和家族精神的认可。
当然,家族的发展不可能游离于历史和时代。在《十月的土地》中,随着日本人的入侵,文本由家族内部叙事逐渐转为家族与革命关系叙事。然而,总体来看,《十月的土地》中的革命叙事实际上是家族伦理叙事的延续。正因为如此,章文德在加入抗日队伍后,在“家”与“国”之间选择了“家”。
显然,章文海是典型的从家庭走出去的革命者形象。而对于章文德并不坚定的革命意志,津子围给予的不是批判,而是更多的理解和宽容。这一点,既不同于构建民族国家想象的家族叙事,也不同于张扬个体生命精神的家族叙事。我认为,在章文德和章文海两兄弟身上,分别承担了“家”与“国”的责任与义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一种递进的人生理想模式,又是一种平行关系,“平天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更好地“齐家”。由此来看,章文德从“平天下”回归“齐家”的人生路径,并没有偏离中国传统文化的轨迹,而且,在此基础上,也是对带有普世性的人类生命情怀的尊重。一如陈思和所指出的,“体现了民间不以胜负论英雄的温厚的历史观”。
在我看来,津子围实际上秉承着一以贯之的写作姿态。他以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高度的自觉,去勘探历史中一粒粒尘埃的故事,不动声色,以悬置的姿态让历史说话,让人物说话,力求去还原真实的人性,真实的历史。作为一部家族小说,《十月的土地》是优秀的。尽管文本的叙述节奏略显拖沓,一些情节缺少必要的铺排,导致阅读上的突兀感,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这部作品。其实,每一位作家都会面临各种不同的潜在的写作困境。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依然需要将其放在时代的语境中去审视其价值和意义。就家族小说而言,不同历史阶段的家族小说都是对一个时代的文化语境的深度折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家》《春》《秋》、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通过对封建家族制和封建文化的批判,表达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精神。到了上世纪50-70年代,“家族作为一种创作母题开始与革命历史的叙说结合,作家书写你争我夺的家族之间的斗争史、复仇史、苦难史,形成了革命历史叙事与家族叙事相互交织的文学格局”。进入1990 年代,面对文化全球化所带来前所未有的“身份焦虑”,家族小说呈现出浓郁的“恋家”情结,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忧患意识和民族精神的重建情怀。从这一点来看,津子围的创作同样也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同时,津子围又能够发出自己独特的、具有强烈辨识度的声音。他对家园意识的肯定和张扬,无疑为当代家族叙事增添了新的写作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