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远行的骆驼和骆驼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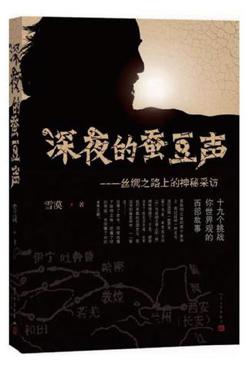

风真大,草地上天翻地覆了,许多落叶在滚动着,屋顶上也发出哗哗哗的声音,像是充满了各种水流。我知道,那是屋顶上的茅草开始不安分了。不过没关系,过了今夜,再铺便是,人生就是这样,总是在修修补补。要是在沙漠里,这阵候,就很危险了,那肯定是一场老黄毛风……你知道啥是老黄毛风吗?
就是沙尘暴。在沙漠里,除了流沙,沙尘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像世界末日一样……在外面也很可怕,离沙尘暴中心越近的地方,那沙旋风就越厉害,有时候,像一堵墙一样压了来,把啥都给卷了。一旦被沙风卷进去,别提人了,牲口也没命了,啥都没了。沙风也像刀子,瞧,现在的风还不利,说明风力也不算那么大,要是真的来了老黄毛风,那沙子就会像刀子一样刮你的身子。沙漠里的人,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危险。
很可怕。沙漠虽然很壮阔,有时像母亲一样温柔,有时却像死神、死亡之海……大自然很奇怪,它创造了多少美好,就会创造多少灾难。
是的,人生也是这样,丝绸之路也是这样。其实,丝绸之路也是人生的缩影。
人生的缩影?
是的,或者说人类灵魂世界的缩影。
一想到丝绸之路,我就想到骆驼,谈丝绸之路上的人,总觉得没了骆驼的话,就少了点什么。
骆驼是古丝绸之路上很重要的符号,但到了今天,骆驼客文化已经消失了,飞机、火车、货运取代了它们,毕竟,如果没法满足新时代的需要,被淘汰就是必然的。只是,想起骆驼和骆驼客在驼道上的相依为命,想起他们背影中浓浓的沧桑和孤独,总觉得心里有点遗憾。
我们带了两个大木箱,里面盛着黄货,很重。我们没说是啥,但也没人问。你知道,驼户们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多嘴。我们只说是皮影,是送朋友的。谁都知道皮影是驴皮做的,要是多了,也会重的——但这,只是一种说法。
你骑过骆驼吗?骑过就好。对于没骑过的人,还以为骑骆驼跟坐轿车一样,陷在驼峰里,会软乎乎的。是的,真软乎乎的。但那是你才上去的感觉,骑了一天,两天,十天,就一点也不软乎乎了。你会有被抖散了架的感觉。最难受的是屁股,你的尾骨处肯定烂了。所以,长途运人时,我们会置办两个大木箱,放在一个大轮架上,一边一个,人就坐在木箱里。
这回出去的有二十把子驼。因为驮费很可观,蒙驼也抢,汉驼也抢,事主儿怕得罪一家,就各用十把子驼。每把子驼十一峰。说好两支驼队在第三天的某处碰面。
那蒙古驼队也跟马家驼队一样有名,两家的过节很深了,谁也不服气谁。我后来想,要是这次行程不用蒙驼的话,也许会有另一种结局。
驼铃声中,夜从四下里偷围了来,盖住了大地。
第二次撒尿时,约在起程后十三里处。瞧,撒尿重要吧?好些二愣子,只使唤驼,不叫驼撒尿,驼就废了。勤撒尿真正的含意,除了排尿,还是为了缓驼,别太累着了它。每一站,骆驼要撒三次尿。走五里一尿,走八里二尿,走十几里三尿,剩下的路程,驼不再歇息,以疾行速度,直达驼站。每一站,约有四五十里。那一次,我们走了一百多站。你算算,凉州到野狐岭,有多少路程?
駝第三次撒尿时,天已变成了巨大的黑锅。除了驼铃,一切都寂了。驼掌软,行在沙上,只有轻微的沙沙声。静夜里显得很大的铃声,把那沙沙声也淹了。天地间充满了驼铃声。
行夜路苦,除了看不清石头坑洼外,还因为没有分心的东西。那行路,若有可观赏的景,边行边看,不觉间就是一站路,但夜里,一切都隐了。那沙山,那沙洼,那黄草,那城里人少见的一些物事,都叫夜吞入腹内,看不清嘴脸。人注意的,就是行走本身。而这沙上行路,若太注意了行走,便觉腿的分量在渐渐加重。虽然平素里也穿重鞋,但刚起场的十多天仍是最难熬的。那腿,总是像心脏那样轰轰地叫。为了不使腿肚上的那疙瘩肉消耗体能和制造腿疼,把式们都用牛毛织的带子打了裹腿,但这丝毫减轻不了行长路时腿的沉重。尤其在很静的夜里,那腿总在提醒自己在走路,且时时以酸困和疼痛的方式反抗主人。每次起场后,首先要过这一关,便是老把式也不能幸免。行过二十多天,人就精瘦了,行话说叫“塌膘”了,此后的行走,才会好受很多。
就这样,我偷偷尾随着驼,开始了我一生中最漫长的一次旅程。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呢。
你从那《驼户歌》中,可以看出一点我的艰辛:
拉骆驼,起五更,踏步第六省。
骆驼多,链子长,时时要操心。
前半夜,走得快,腰酸腿又疼。
后半夜,走得慢,瞌睡又丢盹,
你看看,这就是,拉骆驼,
才不是个营生……
在那漫漫的长夜里,除了驼铃声,让我最亲切的,就是那马灯。在无月的时候,把式们会点亮一盏盏马灯,虽然它们不很亮,却是那时的夜里最美的景致。远远望去,那串亮光就是我心中的希望。我虽然也时时会想到阿爸,想到阿爸教我的那些木鱼歌。为了排遣寂寞,我也会默诵那些木鱼歌。那时,我还不完全了解一些内容。我默诵的目的,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排遣孤独,当然,也是为了不忘掉那些阿爸心中最美的歌。
我一直忘不了那种在漫漫长夜里漫游的感觉。
前边是无边的黑暗和不知通向何方的路,陪伴我的,只有自己的脚步和远方的驼铃。
还有干渴。
还有饥饿。
我准备的那点干粮很快就吃光了。驼队要是路过有人的集镇和村庄的话,我还能顺便要一点吃食。我当然不敢全部吃完,我会留下干粮,准备在夜行吃。但是,大多时候,我很难讨到干粮,因为沿途百姓能吃干粮的人家不多。我只能讨到一些残汤剩饭。那些日子,我几乎绝望了。后来,我有了教训,只要遇到有人的地方,我一定会乞讨大蒜。天一热,饭很快就馊了。只要就着生大蒜,馊饭也成了美味。在没有其他食物时,我也会烧着吃大蒜。只是,烧大蒜吃得多了,鼻孔就实了,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了。嘿嘿,这是我独有的生命体验。这细节,不亲身经历,是编不出来的。
当我们行进在无人区移动的沙流里,肺已叫沙浆住了。我拼命地呼吸,拼命地挪动脚步。我感到一道道的沙流打向我的脸。我知道,这情景,很像纷飞的沙轮,要不了多久,我脸上的皮就没了。我脱下坎肩,蒙在脸上。我向后面传递着类似的讯息,我希望他们也这样。但我的声音刚出口,就叫风刮得不知去向了。我只好停了下来。我朝着大约是耳朵的所在,吼着自己想吼的话。我听到飞卿说,不要紧。你走你的,我叫他们贴在驼背上,脸贴在驼毛上。陆富基也像吼似地说,你走你的。别人不要紧。我们有驼呢。这下,我放心了。我知道,我只要开了路,别人就好走了。我于是拉了俏寡妇,继续往前摸。俏寡妇不愧是白驼,在这种情景下,还能镇定自若。它要是抡头甩耳的话,我能不能降住,还真是难说。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心里却明白,我们这时找所谓胡家磨坊,其实已成了一个美梦。在这种险恶的情景下,我们总得做点什么。
一个把式倒下了。飞卿拽住我的手,吼着叫我停下。我知道,让那把式倒下的,其实不仅仅是累,还有一种绝望。那绝望,也时时袭向我的心。只是我知道,我不能绝望。他们比我年轻,他们可以绝望,我不能。他们看着我,他们知道我肯定能找到胡家磨坊。他们相信。在这条驼道上,我走过很多次。每次,他们谈到我,都会说人家大烟客在包缕路上走了大半辈子。是的,我在包缕路上走了大半辈子,我们那软软的驼掌把石板都磨下去了半尺深。但他们不知道,这种末日,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只能叫他们认为我定然能找到胡家磨坊,仅此而已。
我们停了下来,我们将那个差不多瘫了的把式放上驼背。我们不能扔下他。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我叫他将头埋进驼峰里,免得叫流沙打烂脑袋。我听到那驼发出沉重的呼哧声。它也很累了。它还驮了我们吃的豆子和水呢。它定然也叫这阵候吓累了。许多时候,让自己累的,其实是惊吓和恐惧,是自己把持不住的心。只是那时节,我还不知道这个道理。
那时,我甚至觉得自己游行在沙里……不是在沙上,而是在沙里。那沙子成了水,我在水中游泳。只是这水似的沙子成了浆,我游起来很是吃力。你当然可以想象一个苍蝇在蜂蜜里游泳。真有那种感觉了。不过,蜂蜜里游泳的苍蝇尝到的,是甜,我则是累和绝望。
我们行进在无边的黑里。我们看不到方向。除了那各种怪声,我们也听不到别的声音。我不知道在白天呢还是在黑夜。我不知道,这流沙之后再有没有别的怪事,也不知道它究竟会延续多久。饿了,我们吃把豆子。渴了,我们喝一口水。体力早就透支了。身体早不像是自己的了。我甚至发现,我们即使在行走时,也大多在原地踏步。我当然知道,正是这种原地踏步,才能让我们免去被活埋的命运。在滔天沙浪扑来时,我们非常像在波涛中颠簸的落叶。在流沙的移动中,许多地形定然变了,我们的移动,能让自己时时踏在移动的流沙上。
不知过了多久,那峰驮人的驼倒下了。按说,它是不应该倒下的,但它还是倒下了。累当然是一个原因,我想它的心理承受能力已超过了极限。它其实放弃了努力。心一松,累就成了泰山,几下就压垮了它。它一卧下,那个趴在它背上的把式也滚落下来。他说,我也不想走了。你们别管我了。
于是,我们都停下来了。我们很想拉起那驼。我知道这阵候,要不了多久,它就会叫沙埋了。我能隐约地借那亮光看到驼长伸四腿躺了的模样。我只好随它了。我们将那软成一堆的把式放在俏寡妇的背上,还有那些豆子和水。俏寡妇叫了一声。
对那夜——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夜,也许它是另一种意义的夜吧——虽然我觉得经历了无数的事,我记忆最深的,不过两件事:一是那峰驼死了,是累死的。二是大嘴的脸叫沙打成了血葫芦,我叫他脱下坎肩蒙了脸,他不听。我们其他人,只是叫流沙打烂了衣服。我们的衣服都烂了。在后来的行进中,我叫大家都隐在骆驼身后,只我一个顶了那狐皮坎肩前边探路。我拉着俏寡妇,另几人就紧依了俏寡妇的身子,躲那风沙的袭击。不然,他们的脸也会成血葫芦的。
待得天渐渐亮了后,我发现,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叫沙重塑了。
一种巨大的静,向我压了来。胸口的牌位也疯狂地跳着,火烫火烫的,仿佛它也明白,某种情感正在摧毁它的期望。我紧紧握住那把刀,手已经握出了汗。
风很大了,它毫无遮挡地吹向我们。身边有强劲的气流在涌动,我也能觉出那气流里有沙流。粗糙的沙在打磨我的肌肤,其实我已经习惯了,这种事,过去常遭遇,只是阵候没这么大。
驼叫了一声,声音很是沉闷,我想它一定累了,或是它也叫这阵沙暴吓住了。它难道在提醒我们?或是在向我们诉苦?或是在发出只有它才明白的一种启示?我听不懂。过了一会儿,驼停下了脚步。
马在波喘着气,吆喝几声,用巴掌拍了驼屁股几下。驼又往前走了。
马在波说,不能停的,这会儿,不能停的,一停下,就叫沙埋了。
他又說,天大的雨,也会停的。天大的风,也会停的。
我没应答。我很想说,末日真到了的话,风雨停了,也是末日。
骆驼又停了,它没力气了。骆驼一停,我也萎倒在地。走了那么久,觉得汗已经流干了。马在波一把拉起我。他喊:坚持!坚持!这阵候,不能停的,一停,就叫沙埋了。我说,就叫埋吧,我走不动了。马在波说,天上有一丝儿亮了,这天,总会亮的。我说亮了又能怎样?马在波说,话不能这么说,你要是一直这样追问下去,当然啥没意思了。又说,人活的意思,就是活那个过程。
这道理,我当然懂的。问题是许多时候,道理解决不了问题。道理能解决的,只有心。可许多时候,身是不听心的。
除了累,还有渴、饿,体能消耗到极致了。马在波吆着驼,他的声音坚决而愤怒,差不多等于威胁了。驼当然也明白这处境,在我们的帮助下,它又动了。我眯缝了眼,看看天,我并没有看到啥亮光。不过,随它吧。黑是天的权力,走是我们的宿命。
我们就这样走着。我们时不时就摔倒了,然后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直到我真的看到了天边的亮光。
风静了的时候,我发现,地貌变了,一切都变了。我们的身边,有磨坊,但这磨坊已不是原来的磨坊了。以前的磨坊,有好几间,现在,只剩下有磨盘的那间房了——不,那甚至算不上房了,只能算是木架了。
在我们的转动中,磨一次次升高着。不,我们自己也在升高着。那倾泻而下的沙,都到脚下了。
我看到了胡杨树梢。以前的磨坊旁,有一棵很高的胡杨树,现在,我只能看到树梢了。远远地望了来,这磨坊,定然像挂在胡杨树上。
待得太阳重新出现后不久,我们也看到了飞卿他们。
他们一直在寻找胡家磨坊,这寻找,同样也救了他们。
他们给了我们一些水。他们带的水虽然不多,但却支撑到了第三天。
第三天,天降了大雪。
我们吃驼肉、吞雪,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野狐岭。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深夜的蚕豆声——丝绸之路上的神秘采访》 作者:雪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