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分级参与的地方金融风险应对机制
陈道富 王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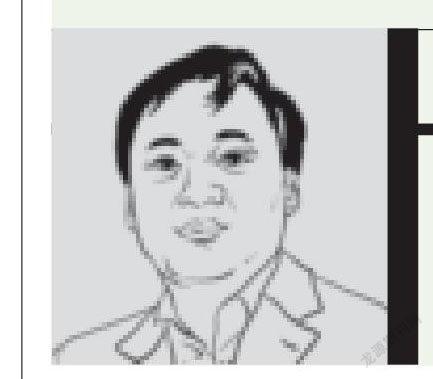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防范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值得关注。本文建议从立法、监管资源和系统建设等方面加强力量,核心是建立协调一致的应对机制,可考虑设立多个处置责任主体分级参与地方风险处置的机制,根据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和可能的外溢效应,逐步引入多个监管主体,加重监管责任,提高处置效率。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经济增速下行影响,我国金融资产质量加速恶化,区域性金融风险仍处易发高发状态。系统性风险防范化解,主要涉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与金融制度、规则和政策有关。地方作为规则和政策的执行部门,监管“7+4”类机构(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融资担保机构、小额贷款公司7类机构,以及投资公司、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4类机构),并对地方风险处置负有属地责任。因此,地方在风险处置中关键是提高执行效率,实现风险的“早发现、早识别、早处置”。当前,地方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中面临定位不清、职责无限、资源有限、协作乏力和基础不牢等问题,需要从立法、监管资源和系统建设等方面加强力量,但核心是要建立协调一致的应对机制,克服当前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难题。我国已建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牵头和省政府牵头的两类地方金融协调机制,但近期调研中发现地方风险处置协调效率仍不高。调动有关部门积极性,从“治病救人”角度降低风险处置成本,在当前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意义。
协调不畅制约地方风险处置效率
第一,地方风险处置机构种类多,多种管理模式并存,且涉及央地多个处置责任主体和资金。地方参与处置的机构和行为包括:由中央部委或省政府代管的地方经营主体,包括省内非独立法人机构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城商行、村镇银行等地方法人机构;由地方金融监管局直接监管的“7+4”类机构和市场;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非法集资三类。涉及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等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人民银行、地方金融监管局、存款保险基金四个保障基金及地方财政、国资委和公检法等部门。
第二,多个处置责任主体间协调不畅制约了地方风险处置效率。筆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地方金融监管局在地方风险处置中往往代表地方政府,成为协调和办事机构。但其已为省政府直属机构,且市县两级机构设置不统一,较之以往挂靠省级政府办公厅,跨部门协调能力事实上明显下降。加上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责任在肩、手段缺乏,没有枪、没有炮,只有一把小螺号”,经常处于“平时进不了机构的门,进门就要处置风险”的尴尬境地。地方反映:懂情况的“不表态”、有权管的“不了解”、扛责任的“干着急”。中央银行负责地方金融风险监测和风险评级,对风险状况较了解,但缺乏监管权限,且担心因“最后贷款人”身份承担出资责任,经常“不表态”。监管部门担心金融机构倒闭会被认定为监管责任,出风险后也希望推迟处置。地方财政和“三类基金”则缺乏早期介入机制。
协调不畅带来高沟通成本,易拖延到风险过大了才处置,错过了早期纠偏、快速处置的黄金时期,处置成本高昂。
协调不畅的内在原因分析
难以达成共识是协调不畅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三个原因造成“共识难”。
一是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法规。现有关于地方风险处置的条款散见于多个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碎片化严重,表述较原则,缺乏明确的可操作标准和授权,如风险处置启动标准、地方可用处置工具、损失分担和资金救济机制等。实践中地方风险处置普遍采用“个案谈判”模式,沟通成本高,没能及时将个案处置经验形成共识制度化。
二是过程参与不足,事后处置时信息严重不对称,制约了对事件的准确判断。地方往往是在风险暴露并决定处置后,才协调相关处置责任主体参与。由于没有参与事前审批、事中监管,其间更没参与现场检查,对被处置对象缺乏全面的现场感知。仅在处置时基于部门汇报形成感知和判断,难度大,验证成本高。进入处置程序后,各方须直接承担责任和损失,更难形成共识。
三是责任和损失承担不清晰,实践中还存在“倒逼机制”,不利于低成本、快速风险处置。我国的地方风险处置带有因地因时制宜的协商特点,损失与处置成本并不完全是按照法定顺位承担,公共资金发挥了重要作用。各方责任虽有文件规定,但在具体场景中的理解并不清晰和一致,如地方政府有属地风险处置责任,但参与时间、路径和具体责任并不明确等。在个别财政困难的案例中,还存在对央行先行垫付资金的“倒逼机制”。金融风险处置越早成本越低,但处置责任主体缺乏动力快速处置风险,增加了最终处置成本。
构建分级参与的地方金融风险应对机制
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稳定理事会在借鉴国际上主要国家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经验教训基础上,发布并完善了《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机制核心要素》。其中,事前预防性监管和早期介入,提供多种工具和手段快速灵活处置是最重要的特点。我国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原则。为此,我国可考虑设立多个处置责任主体分级参与地方风险处置的机制,根据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和可能的外溢效应,逐步引入多个监管主体,加重监管责任,并提高最终的处置效率。
具体而言,可根据金融机构的规模、业务特性和风险暴露等,结合机构的风险和监管评级变动情况,由央地金融监管部门定期协商,将地方各类金融、准金融机构的风险状态分为四级:正常、关注、早期介入和处置。当机构处于正常状态时,按照现有监管模式监管。对中央监管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只要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机构风险评级或银保监会监管评级有一个结果下调即纳入“关注”类,对地方监管的“7+4”类机构和场所,只要相关非现场监管指标恶化或风险评级下降,即列入“关注类”。被列入“关注”的机构将被纳入央地联合非现场监管机制:除需要接受现有监管机构的监管外,还需要接受央行、其他监管部门(原归中央部委监管的机构,引入地方金融监管局;原归地方金融监管局监管的,虽不至于引发系统性风险,但为有效处置跨区域风险,须引入负责“制定规则”的中央监管部门)的非现场监管。一旦被定为“早期介入”,除了接受额外的非现场监管外,还需要接受央地监管机构共同或专门的现场监管,并引入最终可能承担弥补损失责任的各类主体,如存款保险机构、保险保障基金、信托保障基金或中小投资者保护基金,启动与地方财政和国资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确定为“处置”,则引入各类处置手段,并按照法定顺序弥补损失与处置成本。这种操作方式的好处有如下几点:一是风险应对从“处置”环节提前到预防性的“监管”环节。相关主体可在参与中全面了解和沟通,调动积极性,引导建设性的早期纠偏和治病救人。可与当前通过地方专项债券补充中小金融机构资本金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夯实地方金融机构体系。二是可克服直接启动风险处置的敏感性,避免因责任承担等问题内耗,延误介入的最佳时间,发挥多部门的专业判断,构建地方金融风险阶梯式动态调整机制。三是可实现激励约束相容。分级参与适度加大了高风险机构的监管责任和成本,激励控制和降低风险等级的行为。
为使该机制更有效运作,还须完善以下配套措施:
第一,在国家层面尽快出台与地方金融监管有关的三部条例,分别为《地方金融监管条例》《处置非法集资管理条例》和《非存款类放贷人条例》。尽快通过条例的方式明确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法律地位和职责范围,建议明确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7+4”类机构的监管事权,对新兴金融机构与业态开展日常监管,保护投资者、消费者利益;探索发挥地方政府的组织、协调、管理作用,允许地方政府以适当途径参与或配合中央政府的金融监管。确定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7+4”机构为类金融机构,也需要持牌经营,只有获得监管部门批准后才可以去工商部门登记,并为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处置非法集资提供法律依据。鉴于中央负责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建议中央监管部门加快针对地方监管的“7+4”类机构监管细则的出台进程,使得地方金融监管有据可循。
第二,制定风险级别调整方式。可分自动和商定两种,前者规定量化的硬性风险级别调整指标,后者可在人行、监管部门的评级基础上由双方商定。
第三,设立地方风险处置基金。为避免事后挤占地方财政资金或倒逼中央政府兜底,可参照国际上“生前遗嘱”制度,以资本金或营运资金的一定比例一次性汇集辖区内金融风险处置基金,并由地方监管部门日常维护。
第四,进一步厘清不同类别机构中央和地方风险处置责任内涵。分清政府作为股东的救助责任,与运用公共资金救助、属地维稳责任的差异,在各省区市金融议事协调工作机制下将地方党的领导责任、地方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责任、辖区风险处置责任和维护社会稳定责任统合起来,落实属地责任。
第五,一旦金融机构进入处置程序,建议明确处置组责任并借鉴国际经验赋予其灵活有效的处置工具。如限制股东权利、更换高管和董事、调整和终止合同、存款人快速赔付、设立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SPV)处置不良资产或组织收购承接等。
(陈道富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刚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法与金融监管基地特约研究员。本文编辑/王晔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