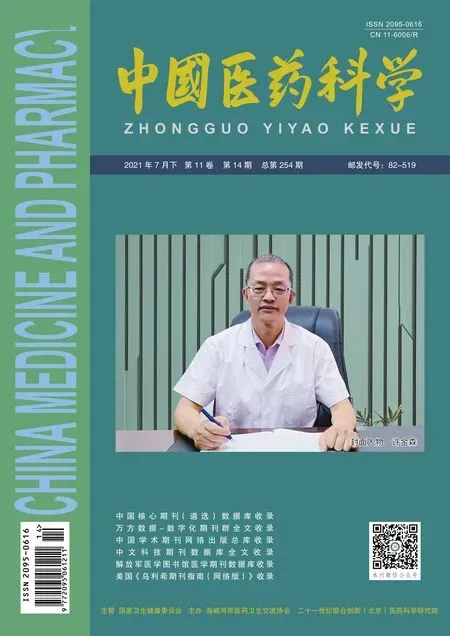创伤骨折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及诊断治疗进展
徐会涛 吴立生 吴俊玲 贾庆运
1.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山东泰安 271000;2.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创伤外科二病区,山东临沂 276000
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DVT)是指血液中的血小板、纤维蛋白和红细胞在深静脉腔内非正常地凝结,阻塞静脉管腔,造成肢体血液循环障碍,肿胀疼痛严重者可脱落致死。DVT发生率在创伤骨折患者人群中普遍较高,且多在下肢静脉血管或骨盆深处静脉血管中形成[1]。虽然血栓的预防药物及多种机械预防措施已被临床医生广泛应用,但下肢深静脉血栓及其导致的肺栓塞发病率仍然很高。在接受治疗的DVT患者中,约20%~50%的患者在DVT后出现血栓后综合征[2],3%的患者在肺栓塞后出现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3]。血栓后综合征,其特征是慢性、潜在的严重下肢肿胀和皮肤溃疡。包括心力衰竭和肺动脉高压在内的长期后遗症可迅速致命[4]。DVT延长了住院时间,增加治疗费用,给患者带来痛苦,同时也增加了患者的死亡风险。目前,国内有研究报道DVT在其所观察的24 049例各部位损伤患者中的总发生率为6.41%[5]。国外有研究报道DVT在创伤骨折的发生率为33.3%[6]。虽然国内外对DVT的报道存在较大差异,但无一例外的是DVT的发生率都较高。由此引起医疗费用及病死率上升的现状仍然相当严峻。因此,掌握DVT的危险因素并采取积极有效预防措施和正确治疗就显得非常重要。以此来采取针对性防治措施降低住院时间、减少医疗费用、减轻痛苦、降低病死率、提高生活质量。
1 创伤骨折患者DVT发生机制
目前Virchow提出的血栓形成三大要素理论即血管壁内皮损伤、血流瘀滞、血液的高凝状态,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同[7]。时至今日,这些因素被认为是识别风险和预防静脉血栓栓塞的基石。创伤骨折可以导致血管损伤,血管内皮细胞结构和功能受到破坏,暴露内皮下带负电荷的胶原,首先FⅫ结合到胶原表面,并被激活为FⅫa。FⅫa和被损伤的组织释放进入血液的组织因子分别开启内外源凝血途径;创伤后的骨折、失血过多、受伤组织出血水肿,压迫血管,影响静脉回流,造成血流缓慢、术后卧床、患者肢体制动等都会引起血流动力学改变,致使血流淤滞;同时创伤引起机体发生应激反应,多种促凝物质包括纤维蛋白原、血栓素、二磷酸腺苷和五羟色胺等开始增多。这些物质又促使炎症物质释放,引发机体炎症反应,外周血白细胞增多,血小板数量增加,进而导致人体血液向高凝状态转化;最终这三个方面因素大大提高了血栓形成的风险。
2 创伤骨折患者DVT危险因素
2.1 手术与DVT的关系
创伤骨科手术DVT的发生率与骨折所选择的固定方式及发生部位有一定的联系,这一点国内外均有报道。有研究显示股骨干骨折的患者DVT发生率高达20.69%,髋部骨折的患者发生率为20.29%,DVT在粉碎性骨折患者中的发生率为27.92%,3处或3处以上骨折患者发生率高达50.00%,骨折伴休克者DVT发生率为22.22%[8]。发生率高的原因可能为:失血过多、受伤组织出血水肿,压迫血管,影响静脉回流,患肢长期制动造成血液瘀滞;创伤及手术导致血管及组织细胞损伤为DVT形成提供了条件。研究表明手术时间也影响DVT的形成。李进[9]分析了126例行骨科大手术患者的住院资料,其发现患者DVT的发生率与手术时长呈正相关。杨志等[10]研究了185例外科手术,发现手术时长在2 h以内DVT发生率为11%,手术时长在2 h以上DVT的发生率为24%。原因可能与平卧时间长、止血带使用时间增长、创面暴露久炎性反应加重、促凝物质持续释放有关。另外术中骨水泥的应用、止血带的使用时间的延长,术中采用全身麻醉亦被报道可以增加下肢DVT的发生率。Fukuda等[11]发现在全膝关节置换术中止血带的应用对患者术后深静脉血栓发生率影响不大。然而Mori等[12]通过对109例全膝关节置换患者的研究发现,术中使用止血带不会增加近端DVT的发生率,但会明显增加远端DVT的发生率。目前止血带的应用是否会增加术后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还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
2.2 患者的基本情况与DVT的关系
DVT在种族方面存在差异,与白人相比,黑人发病率较高[13],然而黄种人发病率较低[14],这种差异的具体原因尚未阐明。冯振中等[15]研究了266例创伤骨折患者,发现患者年龄、性别、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高低、存在吸烟史与DVT的发生率有着很深的联系。另外损伤发生的暴力方式、采用的麻醉方法、手术进行的时长及术中是否输血等因素均被发现与DVT密切相关[15]。其中男性、BMI≥25 kg/m2、年龄≥60岁及吸烟史者,骨折并患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患者DVT发生率显著增高,这与之前的研究[8]一致。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糖尿病并不是创伤患者DVT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16],其发生率的增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烟中的尼古丁和烟碱对人体危害非常大,易导致血管内皮的损伤,引起小血管痉挛。一般认为吸烟是DVT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有研究[1]认为其作用并不能独立决定DVT的形成,仅作为增加DVT发生风险的因素之一。还有报道[17]指出在骨盆髋臼骨折患者中DVT发生率与一般认为的危险因素,如损伤严重程度评分、性别、BMI分数及合并内科疾病均无关。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大样本的研究证实。Michetti等[18]发现在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住院的创伤患者中,住院时长与DVT的发生率存在正相关。其中4~10 d住院患者与住院1 d相比,DVT发生率翻了2倍,而住院>10 d患者DVT发生率与住院1 d患者相比翻了4倍。但是在重症监护室治疗时间与DVT发生率之间关系是多因素的,可能受到疼痛、损伤程度、镇痛镇静药物以及呼吸机或其他设备的影响。另外急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呼吸衰竭、风湿病、炎症性肠病、基因突变、恶性肿瘤也被认为是增加DVT发生风险的因素[19-20]。
目前创伤骨折患者下肢DVT危险因素,国内外学者之间存在争议,尚无完全统一的定论。但患者年龄偏高、骨折发生部位、手术时间延长、合并其他部位损伤是导致DVT发生的危险因素已经得到普遍认可。
3 创伤骨折患者DVT的预防
3.1 基本预防
术中规范操作,减少血管内膜损伤,避免副损伤,缩短手术时间,止血带的正确使用,术后给予患侧肢体抬高,可以提高血液在静脉腔里的流动速度,也有益于肿胀消退。指导患者早期功能锻炼,可以适度增加液体入量,稀释浓缩的血液。禁止在下肢同一静脉反复穿刺。
3.2 物理预防
目前间歇性气压泵(intermittent pneumatic compression,IPC)、梯度压力弹力袜等机械性预防措施已经广泛用于创伤患者,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措施促使下肢静脉腔内血液的流动速度增加,避免血液在静脉管腔内淤滞,增加静脉血流量,降低静脉压力,从而增加动静脉压力梯度。血流的变化引起内皮细胞的拉伸和剪切应力,导致循环组织纤溶酶原激活剂、前列环素和一氧化氮的增加,减少了术后下肢DVT发生风险[21]。特别对髋关节附近骨折患者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并且机械性预防措施与药物预防相比有着更低的出血风险发生率,且不会增加DVT患者肺栓塞的发生率[22]。但是物理预防措施是有缺点的,与药物预防相比其效果较差[20],对严重创伤患者单独使用物理预防措施可以导致不良事件增加甚至死亡。学者们普遍认为充血性心力衰竭或肺水肿者、下肢DVT形成或肺栓塞发生者、下肢局部异常病变者应禁用或慎用物理预防措施[23]。这些物理预防措施单一使用或联合药物预防被证明是有效地,可以作为药物预防的辅助方法降低高危患者DVT的发生率。
3.3 药物预防
目前在临床工作中常用以下几种预防血栓的药物:①普通肝素:可以降低DVT风险,但是其存在多种药物-药物和食物-药物反应,因其治疗窗窄诱发血小板减少和出血,现临床上已经很少使用。②低分子量肝素:可以明显降低骨科大手术后患者DVT与肺栓塞的发生率,较安全,且具有大出血发生风险低、减少血凝系统监测的优势[24]。③维生素K拮抗剂:这类药中最常用的是华法林,可减少DVT的发生,但有增加出血的风险。其价格低廉,可用于长期预防。维生素K拮抗剂的不足:容易受药物和食物影响;治疗窗相对窄,且需要频繁监测国际标准化比值增加患者痛苦;半衰期长,显效慢等[25]。④Xa因子抑制剂:常用药主要包括利伐沙班和阿哌沙班。这两种药都是针对单个有活性的凝血因子不依赖抗凝血酶。其特点是治疗窗宽、不需要常规血液学监测、口服给药应用比较方便,严重肾功能不全者禁忌使用[23]。有研究报道指出利伐沙班治疗6个月后在血管再通方面优于华法林[26]。⑤抗血小板药物:常用药有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分别通过抑制血小板环氧化酶生长和抑制二磷酸腺苷与血小板受体结合而发挥功效,二者均有预防血栓形成的能力。
4 DVTD的诊断
4.1 临床表现
腿部DVT的临床表现包括肿胀或凹陷性水肿、发红、压痛和存在浅表静脉扩张[4]。DVT脱落会导致肺栓塞,肺栓塞的体征和症状包括突然出现呼吸困难或现有呼吸困难的恶化、胸痛、晕厥、低血压或休克、咯血、心动过速、呼吸急促、头晕等[27]。然而临床表现并不总是那么可靠,许多DVT患者的临床表现并不明显,需要几项额外的检查确诊DVT。
4.2 预测分数
因为临床表现和身体检查在深静脉血栓中是不可靠的,研究员在建立和验证预测分数以帮助诊断深静脉血栓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常用的是Wells评分(表1)[27-28]。它结合了患者多个临床特征因素,每个因素得分为1分,以便将患者分层为低、中或高风险组。评分中有一个主观因素,其中负2分用于替代诊断,用以排除与DVT相同表现或更有可能其他诊断。

表1 Wells评分表
4.3 生物标志物
诊断深静脉血栓最常用的生物标志物是D-二聚体,一种纤维蛋白的降解产物。D-二聚体的优点是灵敏度高但特异性低,怀孕、创伤、最近的手术和恶性肿瘤均可导致其升高。这些因素降低了D-二聚体的特异性,这意味着它是一种优秀的排除方法,而不是诊断方法[29]。如果D-二聚体与Wells评分表结合使用准确性就会显著提高。临床发生DVT可能性较高的患者无需进行D-二聚体测试,应直接进行超声检查。D-二聚体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然增加,因此老年人D-二聚体检测静脉血栓栓塞的特异性较低。为了增加D-二聚体在这些患者中的有用性,对50岁以上的患者得出了年龄调整后的D-二聚体阈值,定义为患者的年龄乘以10 μg/L。与传统的固定阈值500 μg/L相比,年龄调整后的阈值在50岁以上的所有年龄组中具有更高的特异性和相似的敏感性[30]。
4.4 影像学检查
静脉造影术是诊断深静脉血栓的“金标准”,但在日常实践中很少使用,它具有侵入性、昂贵、技术要求高、疼痛、过敏或肾功能不全时禁忌、难以解释,且观察者之间和观察者内部差异很大[31]。超声已经取代静脉造影成为诊断DVT的首选方法。美国胸科医师学会循证临床实践指南要求对有高风险概率的深静脉血栓患者或低(中)等概率且D-二聚体检测阳性的患者进行腿部超声扫描[28]。有两种不同的超声方法可用于排除有症状患者的深静脉血栓:压迫超声和全腿超声[32]。压迫超声是一种简单、快速的床边方法,不需要专门的操作员或高范围的技术设备,广泛应用于急诊科和医院病房。全腿超声是以连续的方式扫描腿部的整个深静脉网络,从股静脉通过腘静脉到远端静脉。通常专业人员进行,此外,它需要专用的高级别机器[33]。
5 DVT的治疗
5.1 一般处理
下肢DVT后,患者应停止患者活动卧床休息,禁按摩理疗避免肢体活动后导致血栓脱落引起肺动脉栓塞危及生命。抬高患肢,促进静脉血液流动增加回流,有利于肿胀消退,同时应用药物促进血栓溶解静脉管腔再通。
5.2 抗凝治疗
抗凝是DVT的基本治疗措施,即可以抑制血栓在管腔中蔓延,又有利于血栓自溶和血管再通。静脉血栓的治疗需要大约3个月的时间,进一步的延长治疗时间有助于防止血栓形成的再次发作。决定3个月停止抗凝还是继续治疗,首先受复发的长期风险影响,其次受出血风险和患者偏好的影响。其他的治疗方法包括溶栓介入手术切除等均需要在抗凝的基础之上展开,临床上常把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维生素K拮抗剂、直接Xa因子抑制剂、直接凝血酶抑制剂等作为DVT治疗的一线药物。直接口服抗凝剂,包括直接凝血酶抑制剂达比加群和因子Xa抑制剂利伐沙班、阿哌沙班和艾多沙班由2016年美国胸科医师学会和2017年欧洲心脏病学会指南推荐用于DVT[34-35]。这些抗凝剂与维生素K拮抗剂相比有几个优点,包括起效快、药物相互作用少、允许固定剂量和可预测的药代动力学特征以及给药方便,它们还消除了定期凝血监测的需要。但是当患者肾功能严重损害时禁用直接口服抗凝剂,维生素K拮抗剂仍然是严重肾损害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法[36]。
5.3 溶栓治疗
溶栓治疗已成为血栓治疗的常规方法,已在临床普及推广。溶栓药物有第一代尿激酶、链激酶(现已少用)、第二代重组组织纤溶酶原激活剂和阿替普酶、第三代瑞替普酶等。溶栓治疗的并发症包括出血、肺动脉栓塞、过敏反应等,需要及时发现对症处理[37]。其中最常见的并发症是出血,应该及时监测血小板、凝血功能和D-二聚体,决定进一步治疗方案。
5.4 介入治疗
介入治疗包括经导管接触性溶栓治疗(catheter directed thrombolysis,CDT)、经皮机械性血栓清除术(percutaneous mechanical thrombectomy,PMT)、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percutaneousintraluminal angioplasty,PTA)及支架(stent)植入术。介入治疗有着创伤小、较安全、缩短抗凝时间、术后恢复时间短、可重复操作的优势。另外也有皮下、黏膜及内脏出血和一过性溶血、血管壁损伤、残留血栓和血栓复发、肺动脉栓塞、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和支架植入术后血管阻塞和再狭窄的风险[38]。随着血管腔内微创治疗技术的进步,DVT的介入治疗方法增多,进展较快,需根据DVT的临床分期分型、禁忌证、适应证灵活应用,以期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5.5 静脉取栓术
静脉取栓术适用于髂-股静脉血栓患者的发病急性期,尤其对股青肿、股白肿患者非常适用。静脉取栓术的近期疗效显著,但是复发率比较高,并且只适用于发病在3~5 d内的中央型或混合型DVT患者。郑亚成等[39]研究了30例深静脉血栓患者,研究发现手术取栓联合腔内介入治疗急性深静脉血栓能获得良好的早期临床效果。
6 小结
综上所述,DVT是创伤外科医生必须要面对解决的问题,要做好DVT的防治工作,需要对患者全面评估。找到危险因素后再采取对因对症防治方案。对DVT高危患者应积极采取物理及药物预防措施,临床效果明显,可有效减少肺栓塞的发生。抗凝治疗仍是DVT预防和治疗的基础。DVT后经积极抗凝、溶栓及介入治疗,能够实现部分或全部再通,DVT可防可治。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新型医疗器械的发展、加速康复(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理念、新型抗凝、溶栓药问世及血管腔内微创治疗技术的进步与成熟,DVT的防治工作必将跃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