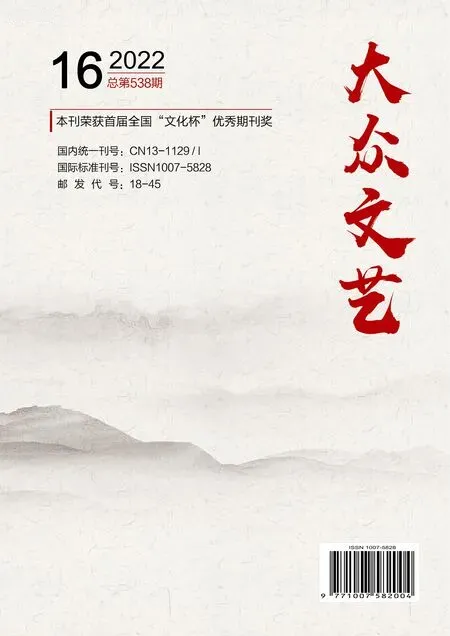语言哲学中的“我”
周毫广
(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 650000)
西方近代哲学以降,哲学家们对自我的认识一直没有超出笛卡尔心身二元论的范畴。这种局囿直到维特根斯坦的出现才被彻底打破。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是,维特根斯坦对自我的分析是否是完全正确的?
一、维特根斯坦对“我”或自我概念的分析
笛卡尔以后的哲学家们,对于意识或者心灵有着这样一种普遍的信念,即把心灵看成是具有各种属性和能力的,控制着身体的活动且能独立于身体而活动的非物质物。比如,洛克说:“我并不否认在身心两方面,都有各种官能;它们都一定有动作能力,否则它们便都不能动作。”
维特根斯坦认为这只是哲学家们的个人意见,并没有提供真实的认识,而仅仅是向我们建议了一套用来述说“心”以及“自我”的言说方式。维特根斯坦划分出两种“我”的使用方式。第一种是主格的“我”(I-as-subject),第二种是宾格的“我”(I-as-object)。主格的我见于包含着“我”的第一人称经验命题或心理学命题中。诸如“我好痛”“我喜欢这本书”等。宾格的我在使用当中指涉着身体或身体的某部位。诸如“我高一米八”“我有双迷人的眼睛”等。
主格的我,维特根斯坦明确地认为它只相当于一身呼喊、呻吟或者身体动作。比如当某人说“我好痛”时,他也可以不说“我好痛”,而直接挣扎地呻吟一下。说“我好痛”与一声呻吟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一样的,听者会做出相似的反应。宾格的我,维特根斯坦认为在使用中无法不指涉一个具体的身体。“我高一米八”,一个这样说的人如果不是说他身体的长度就是荒唐的。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我”只有以上两种用法。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在变化无定的交流中,使用“我”的语句中的“我”都能归于这两种用法中的其中一个。这样看来,传统观念认为“我”指称着一个自在自为的“心灵”的这种观念是没有任何凭证的。因为,第一,包含主格的我的命题没有施行一个指称的功能。主格的我是语法虚构,不指称任何东西。(虽然,第一人称经验或心理状态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蕴含着一个“真”或“假”的问题。比如,一个说“我很痛”的人,我们可以实地地考察一下他是装疼还是真的在痛。但是,这句话无论“真”或“假”即他是装痛还是真的在痛,都不会让“我很痛”这句话失去其自身的交流意义。)第二,虽然包含宾格的我的命题有一个指称功能,但是所指称物是一个具有特定时间、地点和状态的身体。
二、“我”的复杂和不可捉摸
(一)“我”和“我的”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日常交际中,“我”和“我的”常常为我们一并使用,复杂也由此产生。维特根斯坦指出了“我的”的两种用法。第一种可称为“与格”的用法,第二种可称之为“属格”的用法。与格的“我的”用来表示那些在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有着密切关系(通常是占有关系)的事物。比如“我的书包”“我的车子”等。属格的“我的”用来表示我们的身体及身体的某部位。比如“我的手”“我的皮肤”等。
我认为,“我”和“我的”的复杂关系只能看成是:宾格的“我”和属格的“我的”二者间的可替换性。首先,主格的“我”不能和属格的“我的”以及与格的“我的”相互替换。主格的“我”的使用不关涉具体某物。主格的“我”的使用的是以言为行的。维特根斯坦说“我很痛”相当于一声呻吟,相当于说第一人称经验和心理学命题乃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比如,一个人说“我很累了”是要表示他不想继续某事——由于不关涉具体某物,便不存在“真”和“假”之说。而属于格的“我的”在使用中就在于关涉具体某物。二者在被使用时所要达到的功能不同,所以不能相互替换。其次,宾格的“我”不能和与格的“我的”相互替换。二者虽然在使用上都关涉着具体某物,但是身体对于我们来说有着完全不同于外在某物的意义。第一,我们对身体的感受是直接的,身体的状态直接向我们呈现。第二,身体时刻伴随着我们,这像是先验决定的。第三,身体是我们跟外物发生交际的途径,也是我们大多数活动的目的。
但是,赖尔认为:第一,有时候属格的“我的”能替代主格的“我”和宾格的“我”,有时候则不能;第二,有些与格的“我的”能被主格的“我”和宾格的“我”代替。我认为他的看法欠妥。针对第一点,他以“我在火堆前暖我的身体”可以替代“我在火堆面前暖我自己”为例来说明属格的“我的”能替代主格的“我”和宾格的“我”。但是,这里没有出现主格的“我”。“我的身体”替代“我自己”,明显是属格的“我的”替代了宾格的“我”。他以“我没有被烧焦,只是我的头发烧焦了”和他认为矛盾的话“我没有被烧焦,只是我的脸和手烧焦了”做对比来说明属格的“我的”不能替代主格的“我”和宾格的“我”。但是,这里没有出现主格的“我”。“我没有被烧焦”这句话的“我”明显是宾格的“我”。不仅如此,人们说“我没有被烧焦,只是我的头发烧焦了”等于是说“我的身体只有头发这一处无关紧要的地方被火烧到了”;“我没有烧焦,只是我的脸和手烧焦了”的自相矛盾之处无关乎属格的“我的”和宾格的“我”的关系,而是关乎于我们的脸部和手部是否是我们身体的重要部位。针对第二点,他举例说“我撞了邮筒”意思等同于“我的并且我驾驶的汽车在行驶时撞了邮筒”。但是,这里并没有主格的“我”的出现。汽车和人的关系是从属关系,“我的并且我驾驶的汽车”中的“我”是属格的“我”。由此看来,赖尔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二)主格的“我”和宾格的“我”之间的复杂关系
主格的“我”和宾格的“我”的复杂关系分为两点:第一,“我”既能以主格的方式进行述说,又能以宾格的方式进行述说;第二,“我”被某些人说成能同时指主体和客体。
对于第一点,且看维特根斯坦之言,一个人问“谁需要蛋糕?”,另一个人回答道“我”“我”“我”。维特根斯坦牵强地将这里所出现的“我”都解释为主格的“我”。这里的“我”何尝不能被解释成宾格的“我”呢?因为,这个想要蛋糕的人想让分蛋糕的人知道他所在的位置而大声说出“我”的可能性是不能被排除的。在这个可能情况里,“我”就权当为宾格的“我”。
我认为,第二点完全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无论是Schoemaker认为任何主格的“我”都以宾格的“我”为基础才得以可能,还是Evans认为任何宾格的“我”都要以主格的“我”为基础才得以有意义,都隐含着“我”同时指称着一个主体和客体这一前提。这是混淆思维过程和思维对象的结果。“我”作为语词,其所要述说的目的,只能是主格的或者宾格的。Schoemaker和Evans的错误就是把独立的主格的“我”和独立的宾格的“我”拼接起来,认为在一个思维中“我”既是主格的又是宾格的。
John V.Canfield在指出主格的“我”是一种语法虚构时,同时指明了一种“叙述的我”。比如,当被问道“你来自哪里?”这样的问题时,人们想要得到的回答明显是文化上的而不是地理上的(虽然地理事实干涉着文化上的答案)。由于文化上的回答是一种“杜撰性”的回答,这里便暗示着一种语法的“虚构”。他指出,叙述的“我”如同在一部小说中根据个人生活以及个人所处的社会和历史而编撰出来的担任小说主角的“我”。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一个“我”。我们在使用叙述的“我”时——比如回答上面这个问题为“我是南方人”——我们并没有像使用宾格的“我”那样指涉着一个“物体”,而是像主格的“我”一样被我们盲目地认为指称着一个“心灵”或“主体”。我想把John V.Canfield的叙述的“我”归为主格的“我”,因为叙述的“我”和主格的“我”二者的语法是同一个语法,只是被嵌入的命题的分类有所不同(比如,“我是南方人”中的“南方人”在一个文化的范畴内,而“我好痛”中的“疼”是一种经验)。
三、可加以描画的“我”
可以看出,“我”的复杂性中主格的“我”和宾格的“我”的复杂由“我”这个单词造成,“我的”和“我”的复杂联系是由于属格的“我的”和宾格的“我”在使用上有所交涉才导致的。维特根斯坦严格地固执于主格宾格这个区分,没有细致地分析实际的复杂情境。赖尔对“我”是过度分析的,没有看清虽然“我”可以互相指代,但是我们仍旧可以做出区分。Schoemaker和Evans都犯了前提性错误。John V.Canfield补充了文化上的“我”。
我认为,“我”的复杂性不止于上述。在语言被我们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并不需要遵守什么法律法规。辞达意是语言是否有意义的标准。语言习得后,每个人都是语言的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比如,“我没有被烧焦,只是我的脸和手烧焦了”这句话在一节“心灵哲学”课上就不会违和。语词因此可以被张冠李戴地“错误”使用。“我”自然不在例外。但是,这种在“不可捉摸”的使用情境下“我”的复杂性,依据的仍旧是主宾格“我”的基本用法。比如,这里“我没有被烧焦”中的“我”乍看起来是宾格的,实际上是主格的。也就是说,虽然,“我”的言上之意是嵌入各个具体而微的语言使用情景中的,对其言上之意的理解和说明必须回到情景中才可能。但是,支撑着“我”的言上之意的言下之意则是确定的,即我们依然能划分出各个“我”事实上是宾格的还是主格的。
正由于这点,我们仍能对“我”进行描画。这个素描图是这样的:“我”有主格和宾格之分,“我”必然会被划分成主格或宾格的其中一个;宾格的“我”和属格的“我的”在使用上有重叠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