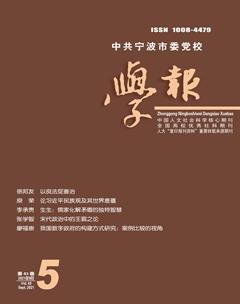我国数字政府的构建方式研究:案例比较的视角



[摘 要]建设数字政府是持续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基于TOE理论框架,提出了我国数字政府建设路径的组态理论。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我国政府数字化水平近年来得到了有效提升,地方政府在数字化建设进程方面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基于地方政府的典型案例比较,发现竞争引致路径、需求牵引路径和内生驱动路径是数字政府建设的三种主要方式。其中同级竞争压力、数字经济需求以及公共数据开放等变量,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政策建议方面,进一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快新型互联网信息技术利用,完善线下政务服务平台,积极回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
[关键词]数字经济;信息技术工具;数字政府;案例比较
[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4479(2021)05-0074-10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加快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其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将会对市场主体和民众产生重要的影响;建设数字政府,成为新时代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有哪些因素影响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数字政府的建设路径存在哪几种方式?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数字政府是社会治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数字治理是治理任务和治理情景复杂化背景下的新需求,因此针对数字政府的研究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一个领域。现有的研究主要从三个视角展开:第一,数字政府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分析,主要从制度体系、组织机构、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探讨数字政府的内涵和外延[1-3];第二,信息技术赋能数字政府的视角,这类研究认为信息技术赋能政府管理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要义[4-7];第三,机构改革驱动数字政府的视角,这类研究认为组织架构深度变革才是数字政府的关键所在,信息技术仅仅是一种工具和手段[8-9]。上述三类研究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影响数字政府建设的因素,非常具有借鉴意义。但是,数字政府建设作为一项回应治理复杂化的系统性工程,单一因素难以解释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路径,因此需要一个综合的视角。
本文基于组织创新采纳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一个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框架,从技术层面、组织层面和环境层面,选取了6个变量,探讨我国数字政府的建设路径。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我国政府的数字化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同时在地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阶梯化分布状态,数字政府的建設水平是不均衡的。进一步的案例比较分析发现,数字政府建设主要有竞争引致型路径、需求牵引型路径和内生驱动型路径三个类似,对应着不同的变量组合。本文的研究发现拓展了学界对数字政府建设路径的认识,并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政策抓手,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现有关数字政府建设的相关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数字政府供给侧和需求侧视角。从供给侧的角度看,政府作为政务服务的供给主体,其数字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务服务供给的方式和效率[10-11]。从需求侧的角度看,企业法人和公民自然人对政务服务有着多种多样的需求。一般而言,政务服务的需求端主要包括用户访问、信息资讯、信息检索、服务引导、咨询问答以及监督评价等方面的内容。数字政府的建设,应该重点加强政务服务供给端和需求端的连接和互动,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提高政务服务供给效率,降低政务服务成本,为企业和公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清华大学公开发布的《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2020)》,将数字政府的建设维度分为四个部分(如图1所示)。数字政府供给侧因素主要包括制度体系建设和组织平台架构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制度体系建设包括“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用情况、数据标准化制度、数据安全和监管制度等方面的内容。组织平台架构主要是指为推动数字政府发展设立的专门领导小组、管理部门以及相关的产业联盟和行业协会等内容。数字政府的需求侧因素主要是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两个方面。治理能力包括数据开放程度、政务服务质量和政务平台管理水平等内容。治理效果主要包括公众对于政务服务供给的满意度、政府工作人员对民众需求的有效回应,以及数字化政务服务供给方式的覆盖度等指标。
第二,信息技术赋能数字政府的视角。信息沟通技术(ICT)对组织机构的赋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尤其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型信息技术如何赋能组织机构,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议题[12-14]。信息技术赋能数字政府建设,主要指的是通过将技术工具引入到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当中来提升政府运行效率和政务服务水平。对于企业而言,“互联网+证照办理”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优化了企业所面临的营商环境。信息技术的应用,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性阶段,对于数字政府的整体建设水平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基于信息技术的治理创新,对于提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机构改革驱动数字政府的视角。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驱动力在于机构改革。信息技术固然能提高信息传递效率、降低沟通成本,但其本质上仍是一种工具。政府如何推动自身机构改革和组织变革才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所在[15]。笔者前期的相关研究从组织机构与职能应用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问题,但忽视了治理环境的因素[16]。数字政府并不是简单地将信息技术和科层制政府结合,而是以信息化建设为契机,推动政府管理运行方式的彻底变革。因此,推动数字政府建设需要加强对机构改革的关注,尤其是一体化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等跨部门、跨条线的机构改革事项。
总结来看,上述三类研究分别从供给侧需求侧、信息技术赋能和机构改革驱动的视角展开,揭示了数字政府建设在不同方面的驱动型因素。遗憾的是,数字政府建设涉及技术应用、组织改革和环境驱动等多种类型的因素,单一视角的分析失之偏颇,因此有必要综合不同角度的因素对数字政府的建设路径进行分析。
TOE理论主要用于分析组织机构创新,TOE分别是技术(technology)、组织(organization)和环境(environment)三个因素的建设。TOE理论框架有效界定了组织机构创新的三类因素,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17-18]。比如基于TOE理论框架探讨我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电视问政创新在全国范围内的拓展等相關研究的相关研究[19-20]。基于上述分析,以TOE理论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一个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框架。
在TOE的理论框架下,技术、组织和环境是影响组织创新绩效的核心要素。根据中国治理的情景,本文构建了我国数字政府建设路径的分析框架,一共包含6个主要变量,涵盖了技术要素、组织要素和环境要素。第一,组织要素。该要素包括政务服务中心和财政能力两个变量。首先,任何数字化组织结构都离不开线下的实体性支撑。现有的政务服务中心和政务大厅,一直是数字政府建设的线下依托和实体支撑。具体表现为数字通信基础设施一般布局在政务中心,线上政务服务的工作人员通常会在实体性大厅集中办公,以及大量的数字政府访问终端设置在政务大厅等。其次,财政能力是组织发展变革的重要影响因素,会对数字政府建设产生深刻的影响。互联网信息设备的采购和升级,尤其是数字治理人才的培养,都离不开财政资源的支撑。
第二,技术因素。信息技术应用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其中电子政务的质量和数据开放是两个核心变量。电子政务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步骤之一,核心在于业务和服务上网。没有政务服务和政府管理的线上实现平台,数字政府建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公共数据开放而言,安全有序地推动公共数据向社会开放,是实现数字赋能的关键步骤之一。
第三,环境要素。任何组织机构都在一定的环境当中,会受到来自环境因素的影响。就数字政府建设的议题而言,同级竞争和数字经济需求是两个主要的变量。同级竞争指的是就特定地方政府而言,其推动数字化建设的进程中会受到同一竞争位置其他政府的影响。同级竞争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当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此外,数字经济需求对于数字政府具有重要的影响[21-23]。在当前推进“放管服”改革和营商环境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如何有效回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是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
二、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特征分析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自2016年以来,我国政府的数字化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从横向比较维度看,不同地域数字政府建设呈明显的梯度分布。从驱动因素角度分析,可以发现不同地方政府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力量来源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
(一)政府数字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随着电子政府建设的持续推进,我国政府的数字化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依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公开发布的《省级政府网上政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的数据,我国省级政府在线办理事项的完备度不断提升,网上办理能力不断增强。2016年,全国省级政府在线办理事项完备度的得分为69.56分,2017年得分为73.96分,2018年得分为77.17分,2019年的得分为78.62分,2020年的最新得分为79.65分。以相关数据为基础,本文绘制了图2。
如表1所示,从2021年最新的数据来看,我国省级政府数字化政务服务能力总体上居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海市、浙江省和广东省三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数字化政务服务能力排名并列第一。数字化政务服务总得分为95.38分,其中上海市在线服务成效度得分为95.41分,浙江省在线政务服务成效度得分为93.66分,广东省在线服务成效度的得分为94.40分。这三个省(直辖市)的数字政府建设具有标杆性的作用,在技术赋能、机构优化以及环境协调三个不同的面向共同发力,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首先,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通过引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工具,有效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水平,提升了企业和公民在获取政务服务公共产品过程中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其次,在政府部门架构优化方面,北京市通过整合政务服务职能,通过优化服务流程有效减少了科层壁垒对政务服务的掣肘。上海市以“一网通办”数字系统为依托,加速了政务服务流程,有效提升了政务服务绩效。广东省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府机构改革两个方面“双管齐下”,有效提升了治理效能。最后,在治理环境匹配方面,数字治理服务于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发展需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数字治理行为与数字治理环境的匹配度。总的来看,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是其他地方政府追赶的目标和对象。北京市和江苏省的数字化政务服务得分为93.06分,总体排名并列第二,其中北京市在线服务成效度得分为90.93分,江苏省在线服务成效度的得分为91.92分。贵州省总体得分为92.02分,在线服务成效度得分为89.57分,排在第三名。作为地处西部的省份,贵州省依托数据产业和数字经济需求,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持续发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安徽省总体得分为91.02,在线服务成效度得分为89.26,排在第四名的位置。四川省和福建省分别排在第五名和第六名,数字化政务服务总体得分为90.18分和89.09分,在线服务成效度分别为87.44分和83.99分。湖北省排名第七,总体得分为88.04分,在线服务成效度得分为83.46分。河南省总体得分为87.38分,其中在线服务成效度得分为82.06,排在第八名。排在第九名和第十名的省份分别是河北省以及江西省,总得分依次为86.89分和86.28分。在数字化政务服务总得分排名中,西藏自治区、陕西省、青海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排在相对靠后的位置。其中西藏自治区的数字化政务服务总得分为78.13分,在线服务成效度得分为68.49分。陕西省的数字化政务服务总得分为78.08分,在线服务成效度得分为67.85分。青海省的数字化政务服务总得分为76.36分,在线服务成效度得分为71.24分。这些省份和自治区在政务服务供给数字化的方向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政府数字化水平是如何提升的?国务院层面推动的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2016年国务院公开发布了《“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国办函〔2016〕108号),制定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系统平台的具体实施标准。“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目标是实现“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实现全流程的统一申请和受理、集中办理、统一反馈和监督等环节。数字空间政府对政府的组织构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实现上述功能,从线上政务服务门户建设、管理服务中台搭建、业务办理后台完善以及共享数据基座四个方面发力,我国政府数字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二)数字政府建设呈现阶梯化分布特征
各个省份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数字政府能力的水平在我国是不均衡分布的,存在着五个不同的梯队。依据在组织机构、制度建设、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四个方面的得分,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进行了排名比较。依据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2020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本文绘制了图3。
 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的数字治理分别处于不同阶段,分别是追赶型、发展型、特色型、优质型和引领型。具体如下:第一梯队,引领型数字政府能力得分均在70分以上,包括的省级行政单位有上海、浙江、北京、广东。这些省和直辖市,在治理能力、治理效果、组织机构和制度保障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應。其中上海市的得分为76.7分,排名第一。浙江省得分为74.5分,排名第二。北京市得分为71.6分,排名第三。广东省得分为70.1分,排名第四。第二梯队,优质型数字治理得分在65分至70分之间,主要的省份有四川、福建、贵州、山东。这些省当中,既有沿海省份,也有内陆省份。山东省和福建省等沿海省份主要依托发达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在制度建设和数字生态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地处内陆的四川省和贵州省,通过数字化政府建设,也在治理效果和治理能力方面获得了一定的突破。尤其是贵州省,基于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具有优势的电力资源,将数据产业作为重要的产业基础。通过大力发展数据产业,吸引了大量的网络服务器落地贵阳,是“阿里云”“腾旭云”的云端数据的线下实体,由此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升级。在数字治理的组织机构、制度保障、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四个方面的得分比较均衡,在上述各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绩。第三梯队,特色型数字治理得分在60分至65分之间,主要的省份有江西、江苏、天津、湖北、海南。这些省在数字产业方面的基础相对薄弱,治理效果和治理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和第一梯队的引领型和第二梯队的优质型相比,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但是由于在制度建设和组织机构方面有一定建树,做出了一定的特色,因此整体的数字治理得分要优于第四梯队和第五梯队。第四梯队,发展型的数字治理得分在50分至60分之间,主要的省份包括安徽、重庆、河南、广西、湖南、宁夏、吉林、内蒙古、山西。这些省份以中西部省份为主,数字生态的基础薄弱,进一步发展受到产业能力的掣肘。在组织机构建设和制度等方面也处于亟待加强的局面。第五梯队,追赶型的数字政府能力得分在50分以下,对应的省份有陕西、辽宁、黑龙江、河北、甘肃、西藏、云南、新疆、青海,主要是以东北省份和西北省份为主。这些省份的数字治理较弱,一方面是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技术能力低、市场生态发育严重不足、用户端需求牵引能力有限等等;另一方面,在组织和制度建设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的数字治理分别处于不同阶段,分别是追赶型、发展型、特色型、优质型和引领型。具体如下:第一梯队,引领型数字政府能力得分均在70分以上,包括的省级行政单位有上海、浙江、北京、广东。这些省和直辖市,在治理能力、治理效果、组织机构和制度保障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應。其中上海市的得分为76.7分,排名第一。浙江省得分为74.5分,排名第二。北京市得分为71.6分,排名第三。广东省得分为70.1分,排名第四。第二梯队,优质型数字治理得分在65分至70分之间,主要的省份有四川、福建、贵州、山东。这些省当中,既有沿海省份,也有内陆省份。山东省和福建省等沿海省份主要依托发达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在制度建设和数字生态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地处内陆的四川省和贵州省,通过数字化政府建设,也在治理效果和治理能力方面获得了一定的突破。尤其是贵州省,基于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具有优势的电力资源,将数据产业作为重要的产业基础。通过大力发展数据产业,吸引了大量的网络服务器落地贵阳,是“阿里云”“腾旭云”的云端数据的线下实体,由此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升级。在数字治理的组织机构、制度保障、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四个方面的得分比较均衡,在上述各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绩。第三梯队,特色型数字治理得分在60分至65分之间,主要的省份有江西、江苏、天津、湖北、海南。这些省在数字产业方面的基础相对薄弱,治理效果和治理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和第一梯队的引领型和第二梯队的优质型相比,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但是由于在制度建设和组织机构方面有一定建树,做出了一定的特色,因此整体的数字治理得分要优于第四梯队和第五梯队。第四梯队,发展型的数字治理得分在50分至60分之间,主要的省份包括安徽、重庆、河南、广西、湖南、宁夏、吉林、内蒙古、山西。这些省份以中西部省份为主,数字生态的基础薄弱,进一步发展受到产业能力的掣肘。在组织机构建设和制度等方面也处于亟待加强的局面。第五梯队,追赶型的数字政府能力得分在50分以下,对应的省份有陕西、辽宁、黑龙江、河北、甘肃、西藏、云南、新疆、青海,主要是以东北省份和西北省份为主。这些省份的数字治理较弱,一方面是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技术能力低、市场生态发育严重不足、用户端需求牵引能力有限等等;另一方面,在组织和制度建设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总结来看,通过持续的建设和推动,我国政府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水平得到了较为显著的提升,同时不同省份之间数字政府建设的阶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
三、我国数字政府构建方式的案例比较
本文分别从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三个角度展开,分析我国数字政府建设路径的差异。借鉴布尔代数和集合论的相关思想,本文从电子政府、数据开放、政务中心、财政能力、同级竞争和数字经济6个变量的不同维度,对数字政府建设路径进行比较分析,主要结果如表2所示。
(一)竞争引致路径
竞争引致路径是指同级竞争压力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驱动力量,其他要素和条件居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典型的案例包括天津市、安徽省和云南省。
天津市作为紧邻北京的直辖市,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存在显著的竞争压力。在其他变量方面,天津市作为一个港口城市,通过积极推动电子政务建设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天津市通过电子政务服务的集成化建设,2020年将原有76条政府热线整合为一个号码,由天津市民服务中心统一受理。根据国家发改委《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20)》的数据,2020年共接收来自企业和民众的咨询和诉求847.99万件,专线电话接通率达到了97%以上,总体的办结率超过95%,企业和公众对专线电话的满意率达到了98%。在数据开放方面,天津市暂未出台有关公共数据开放的管理办法,在推动数据开放的工作方面比较保守。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天津市具有雄厚的财政实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数字政府的建设进程。
安徽省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驱动力量在于同级竞争压力。在地理位置上,安徽省紧邻浙江省和江苏省,这两个省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必然会对邻近的省份造成一定的竞争压力。在电子政务建设方面,安徽省推出了24小时电子政务服务地图,实现了数字化政务服务“永不打烊”。从2020年8月上线到2021年3月,安徽省政务服务地图囊括了全省各级政务服务网络终端6000余台,包括2.4万个政务服务场所,服务事项达到了191万个,平均每日的访问量接近40万人次。除此之外,安徽开发运营的“皖事通”移动政务APP已经成为安徽省数字化政务服务的一张名片。“皖事通”2018年9月上线运行,实现省市县三级全覆盖,成为全省统一的移动应用端。截止到2020年1月,已经接入政务事项882项,下载了1400万,注册用户达1500万。
云南省的竞争压力主要来自贵州省。同样作为西部省份,贵州省依托大数据产业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贵州省数字政府评价体系当中的部分指标,已经接近上海市、浙江省和广东省等沿海省份和直辖市。因此云南省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与贵州省的竞争是一项重要的充要条件。在电子政务建设方面,云南省主要在线上服务事项标准化管理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同一事项同标准办理。具体指的是就同样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省市县同一办理标准,包括办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结时限和办事流程等等要素。对于云南省的数字政府建设而言,公共数据开放、政务大厅建设以及数字经济需求等因素并不存在明显的推动作用。
(二)需求牵引路径
需求牵引型路径,指的是数字政府建设受到数字经济需求的有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政务服务新需求,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变量。此外,在数据开放、电子政务、政务中心以及财政资源等变量的共同作用下,数字政府建设取得一定进展。典型的案例是北京市、贵州省和重庆市。
北京市表现出强劲的数字经济需求,尤其是文化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趋势,迫切地需要政府提升数字治理水平。北京有发达的文化出版行业,以及数量众多的互联网公司,对数字经济的需求十分强劲。2020年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2年)》,将服务好数字经济发展作为市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进一步推进政府数字化建设,为文创产业的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其次,电子政务方面,通过“吹哨报道”“接诉即办”等一系列的电子政务治理创新,为公民和市场主体提供优质的电子政务服务[24]。
贵州省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客观需求,倒逼政府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2020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报告》显示,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排在全国第三位,仅次于北京市和广东省。贵州省大数据应用规模达3873亿元,涉及到的应用行业超过20个。大数据产业与实体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对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显著的助推作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强劲市场需求,倒逼政府提高管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从而有效推动了贵州省的数字政府建设进程。在数据开放方面,由于贵州省的大数据产业具有深厚的市场积淀,因此对于公共数据利用的需求也比较突出,贵州省顺势而为地推动了公共数据的有序开放。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贵州省作为西部省份的标杆,并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压力。
重庆市近年来旅游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带来的数字化需求,同样对政府的数字化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电子政务建设方面,重庆市推出了政务服务移动客户端“渝快办”,通过将高频公共服务事项和企业法人事项汇聚在移动客户端,有效地提升了民众和企业的办事体验。2020年,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制定了《重庆市公共数据开放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有序推动重庆市的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开放和共享数据资源,实现对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赋能。进一步通过开放公共数据培育数字化产业,扎实推动公共数据在产业发展、城市运营和民生保障等领域的高效利用。
(三)内生驱动路径
内生驱动型路径指的是电子政府、数据开放、政务中心、财政能力和数字经济5个变量同时具备,同级竞争要素条件不存在,建设数字化政府是治理能力提升的必然选择,呈现出“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内生驱动型数字政府建设路径的典型案例主要有广东省、浙江省和上海市。
广东省作为珠三角区域的领头羊,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广东省通过在电子政务建设、公共数据开放、线下政务中心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依托充足的财政资源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有效回应了数字经济需求,数字政府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第一,在电子政务建设方面,广东省“粤省事”政务应用已经成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标杆。第二,在公共数据开放方面,虽然广东省公共数据开放的起步比上海市和浙江省晚,但是近年来总体的进步幅度最大。同时在数据开放的标准方面,广东省是继上海市和浙江省之后,第三个正式出台公共数据开放地方标准的省级行政单位。第三,在线下实体性政务服务中心方面,深圳市、江门市和东莞市等地级市,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2000年之前在全国率先建立起行政审批中心。随着行政审批中心的地方创新在广东省内扩散,并且逐步发展成集成式的政务服务中心。物理空间的政务中心,是数字治理落地实践的重要载体。在财政能力方面和同级竞争方面,广东省作为珠江经济带的核心省份,拥有雄厚的财政资源,同时在整个区域走在前列,不存在明显的区域竞争压力。第四,在数字经济需求方面,腾讯、华为等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总部均在广东省。以大型互联网公司为基础,广东省培育了健全的数字产业,对于数字治理的需求十分强劲。
浙江省通过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了信息技术赋能数字政府的治理变革,政务服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居于前列。第一,在电子政务建设方面,浙江省是最早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省份。以线上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为抓手,通过将业务搬到云端,实现了企业和公民办事“最多跑一次”。随着电子政府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一次都不用跑”正在成为现实。第二,在开放公共数据方面,2020年6月12号正式发布了《浙江省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81号),浙江成为继上海之后第二个出台法规推动公共数据有序开放的省级行政单位。第三,在线下政务组织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已经成为浙江省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一张名片。在推行政务服务优化的过程中,浙江省的实体性政务服务中心实现了流程再造和业务优化,服务效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在财政能力方面,浙江省作为沿海发达省份,拥有雄厚的财政实力。在数字经济需求方面,因为阿里巴巴集团总部在杭州,以阿里巴巴为核心的相关网络产业链集中布局无疑具有强劲的数字经济需求。
上海市“一网通办”已经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性作用。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上海市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走在了前列,“一网通办”已经成为上海市政府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的一张名片。第一,在電子政务方面,上海市政府将企业法人事项和公民自然人事项逐步上线,通过“一网通办”政务平台实现了信息化。上海市聚焦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重点推动高频涉企事项“一次告知、一窗受理、一表申请”,有效优化了营商环境。第二,在公共数据有序开放方面,2019年上海市颁布了《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1号),将数据作为一种市场要素,有序向社会开放,这一项创举为其他地方进行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树立了标杆。
总结来看,数字政府建设的路径并不是单一的,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能够通过不同的条件组合,推动数字政府的建设和发展。其中竞争引致、需求牵引和内生驱动是典型的三种建设路径。
四、主要结论与讨论
数字政府建设是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式,其建设路径是一项重要的政策议题。以现有理论为基础,本文提出了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框架,分别从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三个层面提炼出影响数字政府建设的6个变量。借鉴布尔代数和集合论的思想,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路径主要有竞争引致路径、需求牵引路径和内生驱动路径。
从理论上看,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都会对数字政府建设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三类因素的组合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方面。“条条大路通罗马”,单一的信息技术应用,抑或是组织机构变革,都难以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起到突出贡献[25-27]。技术、组织和环境要素的耦合,以及不同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数字政府建设的成效和水平。在这些因素和变量中,电子政务水平、数字经济需求和同级竞争压力是比较重要的三个方面。
进一步推动数字政府建设,需要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突破。第一,积极推动组织机构改革。治理情景的不断变化要求政府的组织机构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数字经济诞生的新形态需要政府的监管和服务及时调整。因此在建设数字政府的过程中,积极推动组织机构的改革,适应新的数字治理情景,成为整个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环节。第二,着力优化政民互动。建设数字政府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数字政府建设应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优化政民互动过程,有效提升公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跨省通办、“不见面审批”“一件事一次办”等政务服务供给方式,是数字政府落地实践的典型表现。第三,有效利用技术工具赋能社会治理。云计算、区块链和5G等信息技术工具正在逐渐产生广泛的影响。政府治理应该积极拥抱信息技术工具,在防范风险的同时充分利用技术工具赋能社会治理,提升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
[参考文献]
[1] 陈娟. 数字政府建设的内在逻辑与路径构建研究[J]. 国外社会科学, 2021(2).
[2] 王文章. 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J].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21, 43(1).
[3] 江小涓. 以数字政府建设支撑高水平数字中国建设[J]. 中国行政管理, 2020(11).
[4] 张鑫媛, 赵军锋. 政务会议: 公共治理任务的科层传递方式[J].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21, 43(1).
[5] 王玉生, 曾庆熹. 大数据技术嵌入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转向与风险[J]. 创新科技, 2020, 20(11).
[6] 廖福崇. “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了营商环境吗?——基于31省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电子政务, 2020(12)
[7] 李瑞昌. 技术赋能城市综合应急管理的路径[J]. 求索, 2021(3).
[8] TanH., ZhaoX.,Zhang N. . Technology Symbolization: PoliticalMechanism of Local E-Government Adoption andImplementation[J].International Review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20, 37(1).
[9] 竺乾威. 行政生态与国家治理能力: 政治—行政角度的分析[J]. 求索, 2021(1).
[10] 刘民安, 刘润泽, 巩宜萱. 数字空间政府: 政务服务改革的福田模式[J]. 公共管理学报, 2021, 18(2).
[11] 李文钊. 界面理论范式: 信息时代政府和治理变革的统一分析框架建构[J]. 行政论坛, 2020, 27(3).
[12] 廖福崇. “放管服”改革过程中畅通政企沟通渠道的实证研究[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7(2).
[13] 郑家昊, 韩莉. 治理的界面与界面的治理——对“界面治理”的反思性阐释[J].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21, 43(1).
[14] 陈睿绮, 李华晶. 创业生态系统绿色化与数字化协同演进研究——基于功能性状的案例分析[J]. 创新科技, 2021, 21(1).
[15] 郑磊. 数字治理的效度、温度和尺度[J]. 治理研究, 2021, 37(2).
[16]廖福崇.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类型学分析[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21(4).
[17] 朱春奎, 陈彦桦, 徐菁媛. 技术因素如何影响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与行为?——基于上海市公务员调研数据的探索性研究[J]. 创新科技, 2020, 20(2).
[18] LiaoFuchong. Singular or Plural? Administrative Burden and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Journalof Chinese Governance, 2020, (6).
[19] 金珺, 李诗婧, 黄亮彬. 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研究[J]. 创新科技, 2020, 20(6).
[20] 徐换歌. 中国城市电视问政创新扩散的多元路径分析——基于组态效应QCA方法的研究[J]. 公共管理评论, 2020, 2(3).
[21] 张越, 刘萱, 温雅婷, 余江.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模式与创新生态发展机制研究[J]. 创新科技, 2020, 20(7).
[22] 翟云. “十四五”时期中国电子政务的基本理论问题: 技术变革、价值嬗变及发展逻辑[J]. 电子政务, 2021(1).
[23] 竺乾威. 国家治理的三种机制及挑战[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0(3).
[24] 王程伟, 马亮. 绩效反馈何以推动绩效改进——北京市“接诉即办”的实证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20(11).
[25] 廖福崇.營商环境建设何以成功?——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组态比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2).
[26] 郑跃平,杨学敏,甘泉,刘佳怡.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模式:基于公私合作视角的对比研究[J].治理研究,2021,37(4).
[27] 廖福崇,张纯.“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建设——制度成本的分析框架[J].秘书,2020(4).
责任编辑范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