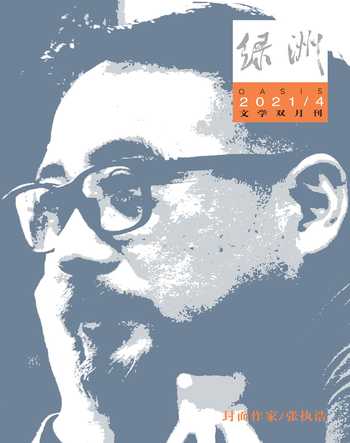人间花事
卜珊珊
桃花运
春天点名时,无论叫到了谁,我们都要让桃花先答应一声。因为只有桃花在春光里敞开心扉,大地上的春运才算正式吹响号角。
我所理解的春运,意思是说,只有春天才有力量把你运往诗意的远方。这个看似异于常理的概念,其实是被春天所认同的,它早已为花所知,却鲜为人类所知。
春运的号角吹响之后,大自然就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客运高峰。熙熙攘攘,你推我搡,那么多的桃花是从哪里来的?我猜是冒失的春天在黄昏失手打碎了一瓶粉色的墨,把漫天的云染成了粉红色,三月的春风就派上了大用场,春风原本就是一把剪刀,把粉色的云当成粉色的布,我们听不见剪刀与布的摩擦声,但一朵朵小小的五瓣花被它悄悄裁好了,就是桃花。
桃花美则美矣,却倔强,非要赶在新叶萌发之前绽放。不过在这趟春运的过程中,并不曾有一片花瓣因拥挤而受伤。一车又一车的花瓣,浩浩荡荡,从南向北,直至占领一树树枝干,桃花才笑了起来。
桃花一笑,春天就不走了。桃花是世界上最热情的花,婀娜多姿的花瓣将枝条压得低低坠坠,密密匝匝,连风都不能吹透,每一朵花,都散发着甜蜜的味道。桃花的味道,就是桃树的体香,就是大地的乳香,是让人喜欢并记忆的味道。一种我们喜欢的花朵的味道,就像我们喜欢的人的味道一样,走出多远,味蕾都铭记着它。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灼灼桃花是绵绵春雨在一夜之间点燃的。这般柔润的好时节,花随风潜入了夜,也说不上是哪个清晨,我睁开眼就发现远处灰蒙蒙的山被一树树粉侵占。
在春天,我只想和桃花一起虚度时光。山坡上的那些桃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哨兵似的守在这里,仿佛怕外面的喧闹传进来,怕这里的宁静逃出去。所以我去看桃花,也得蹑手蹑脚。桃花开在山坡上,一蓬一蓬,一坡一坡,远看它连缀成粉色的云,近看它又破碎成粉色的心。我尽可以一株一株地看,一朵一朵地爱,没有人会责怪我花心,而我坚信一朵桃花的确是有心的。她们变了法子地使你出乎意料,使你看过一重,转个弯,又看到不同的一面,眼睛永远不累,心也不会发腻。这样好的桃花,也被人说过俗气,如果这也叫俗气,那她就是要俗气,你管得着吗?这样的随性劲儿,让人欢喜,又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惭愧,仿佛不能用文字替她洗刷这无妄之评是我的过错。
一见桃花,我就不想走了。我最爱在桃林里发呆,就单单是发呆,也是件最美好的事情,在桃林里,空气永远干净、芬芳,每一缕都清新如泉,每一缕都温馨如光,每一缕都甜蜜如糖,没有一点暮气,是柔软的、年轻的好时光。
在这样的时光里,我常常忘了自己,我的脑子里只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诗句,一个女孩,要出嫁了,多像一瓣桃花,收敛了飞翔的羽翼,静静等待桃子的萌发。诗经里的这瓣桃花,被采诗人做成了标本,夹在泛黄的书页里,保存完好,只要后来人一翻书,它就飘落人间。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也有一朵情怀怅惘的桃花,开在他的期待里。初识时,人面和桃花一样惊艳,只是后来,故地重游,伊人杳然,再浩繁美丽的春天,对于崔护,都黯然失色了吧。
人间事,尽悠悠,有多少人一经相遇便成了刻骨的思念,又有多少人一经相识却成了无奈的永别。开在城南的这枝桃花,是开在盛唐最美的相思。而今,在岸边,在田野,在烟雨迷蒙的三月,洒脱的桃花依旧笑对春风,把千年的往事融进生命的嫣红。不知城南小路之上,是否还有一个桃花样美丽的姑娘倚门回望。
桃花曾是相思,曾是爱情。我身边也有一树桃花,让我可以凑近了看。一朵,两朵,花儿粉唇微张,似乎在倾诉,那脱口而出的诗句,全都泊在春的枝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意近了,芳心醉了,多少年桃花倚着春风笑得花枝乱颤,抖落一身花瓣又随流水悄然远逝了。人面桃花都杳无踪迹了,变成“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我想起电影《山楂树之恋》里静秋和老三的相识相恋,开始也是这般甜蜜,结局也是这般让人惆怅。
春来不是读书天,两个少年飞快地骑着山地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打断了我的思緒。春天多风,可那风早已经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了,自然困不住少年的脚步。他们手里拿着风筝,是在寻找合适的空地准备大展宏图。小时候我也爱放风筝,风筝得求着舅舅做。舅舅铺开篾条儿,撑个四角儿,糊上报纸,再坠上两条带子,就告诉我这是“蝴蝶”。舅舅的“蝴蝶”怎么也飞不高,眼看着飞起来了,翻几个筋斗,就栽下来了。我怪过风,怪过自己细细的胳膊和腿,可从来都没质疑过舅舅的手艺。
少年们把车子停在远处,很快一只“大蝴蝶”就自由地飞上了天空。过了一会儿,“大蝴蝶”渐渐低落下来,少年赶忙拉着线小跑起来,风筝飞过桃林,高高地飞上天空,我的目光也随着风筝的起伏延伸到高处。
我羡慕那飞向云端的“蝴蝶”,人生在世,谁也无法做一只自由自在的风筝,不知桃花羡不羡慕高扬在桃林上空的“蝴蝶”。假如桃花羽化成蝶,那她要带我们去哪里?晋太元中,武陵渔人误打误撞进入的桃花源,成就了千古文人的桃花梦。桃花从此成了一扇门,一面是尘世喧嚣,另一面是出世隐逸,我不能参破它的哲学况味。
胡兰成说: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在我身边,此刻,山野桃花确实是静的,开多少花,结多少果,她不知道撒谎。我甚至能听见,风吹过来,它们优雅落下的声音,像大地上又多了一层厚厚的诗行;山野里的风是静的,它在外面虚张声势可到了山里也得收敛起横冲直撞的脾气;日光是静的,我看见它把我的影子和花的影子轻轻排放整齐;石头是静的,尽管它是山村里最耐劳的工匠,一点点把自己镶嵌进大山的腹地;在地里为桃花授粉的人也是静的,她端着小小的药瓶,用自己的一寸寸光阴点缀这十里桃林;桃树的枝干是静的,甚至干枯、灰暗,像二胡的弦,上面正流泻着《二泉映月》,带着哀而不伤的调子;我在这里的时光也是静的,因为心,在这里也沉淀了下来,声音都被那些土那些石那些花收纳了,只有一群鸟,聚在一起飞,遗落在桃林里的鸟鸣变成跌宕起伏的乐音。在乐音声中,我一次次学着反刍人生的浮与沉,反刍人生的高峰与低谷,反刍人生的明与暗,反刍人生的苦与甜。
不管怎么说,在春天,总要和桃花见上一面的。一个人,想把春天永远留在身边是不可能的,可一个人却可以把自己暂时地隐在桃林里,看桃花的花瓣一层一层落在自己的肩膀上。桃花若是爱你,这份运气就叫桃花运,桃花若是不接受你的表白,也会一路繁花相送,和桃花打交道的我们,从来就没有吃过亏。
祖母兰
祖母爱侍弄兰花,家中最精致的花盆就都给了它。兰很少开花,像小脚的祖母,行动缓慢,让人等得着急。祖母不急,她常说,一朵花哪能急着开呢。
一年到头,祖母的兰似乎只在春节那几日绽放。农村多的是月季,月季如农家饭桌上的白菜萝卜般通俗,它好养,栽在门口,一瓢水就能长成很大一株,月月开花,朵朵艳丽。明明月季更适合农家,或者格桑、蜀葵、鸡冠花也是皮实的,我不懂祖母为什么要养兰。
祖母的冬天离不开火炉,她的炉子上永远煨着热水。她在屋里用瓷盆搓完衣服,才迈着颤巍巍的脚步,把灰白色的洗衣水泼到院墙角,浑浊的泡沫边淌边破。洗完衣服,祖母守着她的火炉给我讲故事啊。祖母对待孩子是最有耐心的,童年时我听过多少关于大山的故事。在祖母口中,不听话独自上山玩耍的女娃被山神变成了山鸟,日日飞在山中却不能回家。兰花世外人一般兀自开着,花香里沾着肥皂的香,伴着咕咕咚咚的开水声,我昏昏欲睡。
我趴在椅子上要打盹了,祖母还在絮叨她的回忆。她说她小时候也念过三年书,她的小姑姑每天给她梳最整齐的辫子,在门口的土堆上培燕子窝(一种游戏)的时候,也跟她父亲学习过“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样的诗句,只是那些像丝巾一样柔软的日子,出嫁之后就一去不复返了。
祖父家的日子真难熬,白天是永远没有终止的农活,她就夜里给孩子们做衣做鞋,乡村寂然无声,陪伴她的只有一盏煤油灯和兰,兰花已开过了,叶子趁着夜色往厚处堆。时间长了,她眼睛见光流泪,头也开始疼。哪有钱去医,疼极了就去东村土郎中那里要点草药煎服。她家徒四壁,却有六个孩子,两个小姑子,婆婆一直瘫痪在床,一家人糊口越来越是问题。
三十八岁那年,她头疼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有一次实在是太疼了,她觉得自己头要炸了,她顾不得这个家,顾不得孩子了,她把头撞向墙壁,她想她的生命或许就要终结在此了。她撞晕了,血流在脸上还是热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她就不知道了。
等她醒来,她第一次睡在了医院里,她在输液,她睡了一天一夜。穿白大褂的医生走过来说,她不能再熬夜了,她太累了,她得了脑血管痉挛。她留下了感激的泪水,对医生,也是对老天爷,她一直以为自己就要死了,没想到只是这么轻的毛病,脑血管痉挛!她控制住自己,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她为自己的想法羞愧,她这个年纪怎么有资格在看病上花钱呢。快走吧,她撞墙的时候还想她的幼儿只有三岁,隔了一天,她又可以回家给他洗衣做饭当娘了。她让医生开了药,就和祖父一起回家了。她握着手里小小的药丸,就像握着自己的命不敢撒手。
后来她又吃过多少药,她也记不得了。总之,她忍着药的苦,忍着生活的苦,把孩子们个个喂养成人。
兰之猗猗,与善人居,在时间的幽微浅淡处镌刻了我的童年时光。
长大了,我继续爱着大朵的月季,也学会了欣赏兰。这世上有万千词语可以形容一朵花的美,要准确匹配并不容易。花朵有出身,词语也有,有的出身寒门,有的生而高贵,有的叫大家闺秀,有的叫小家碧玉,要相得益彰,要门当户对。为兰,我也找到了一个词语:兰心蕙质。
“芝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君子的心叫过丹心、冰心,那一颗在岁月里守望的初心呢?
大抵应该叫兰心。
一种植物,一旦有了执着,就有了性情。兰,翠绿丛中,花苞初绽,宛如饱读诗书的大家闺秀,身着长袍,轻挽发髻,整装待发。正因她并不刻意去出风头,所以总能保持优雅稳重……兰,就在那么一种谦和、简约、随意的氛围中,诠释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道理。或孑然一身,或形影相随,它总在大开大阖的游刃之间,一点一点散发自己的兰心蕙质。无花时节,兰更为低沉,把自己没入草丛,深沉积淀,为的是固守年年岁岁的承诺。
谁能洞悉兰草经年的负重,谁能洞悉祖母经年的负重?祖母从来不为自己叫苦,在岁月里,用耐心一点点等待花开,等待美好生活的到来。只是啜饮过生活风霜的我自己开始领悟,在沉重的日子面前,农人如何能轻盈得起来?祖母养兰,或许就是为了让日常生活的目光有所停顿。
我也常常在书里为兰停顿。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离骚》里回环往复的兰,一瓣就是一句结构精巧的诗。“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丛。”陶翁的茅屋草舍前,幽兰满阶,而不知其为兰,只当是闲庭野草,但只需要一缕风,兰就不再遁藏,内敛的风华悉数展露。
这些绵绵不断的情思,正是兰花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作为花,兰花和别的花太不一样了——它懂得要成为一朵真正的花,高贵的应该是追求,隽秀的外表只是一层华衣。
兰生幽谷,如影随形的暗香,荡漾着它的风采尽显着它的意境。诗人罗伯特·勃莱有一句诗:“贫穷而能听见风声也是好的。”或许兰香正是贫穷的日子里,生活向我们走漏的甜蜜风声。兰香,原本是烟火人间呈现的平凡诗意。她悄悄把日子描摹成一段段有形有色的格调,像戏曲、书法、诗歌一样,表达和升华,又重新渗透到质朴的农家生活中。因为和兰花相识,我对大地上和祖母一般的农人又多了一层认识。
长大以后,我爱在植物园里寻兰,爱在兰展上赏兰,爱在书里读兰。不管在哪里见到兰,都能让我放弃所有杂念,以便从一缕兰香里,让心更贴近从前的草木时光。或许,从偏僻乡村走出来的人们,不管走得多远,心中都有一条通往故乡的路,蜿蜒崎岖,芳草萋萋,而我的那条路上,永不会缺席的就是祖母的兰。
今年过年回家,祖母养的兰有两株开花了。一株是寒兰,养在家里五六年第一次开花,暗绿色的叶,前部边缘有细细的齿,花为狭卵形,蕊柱稍向前彎曲,两侧有狭翅,淡黄色的唇瓣并不艳丽,但香气浓烈。另一株是墨兰,叶呈带状,全缘,近革质,暗绿色,有光泽,花瓣比萼片短而宽,向前伸展,覆于蕊柱之上,眼看那花瓣上坠着闪闪荧光,起初我以为是露水,凑近拿手捻了一点儿,放在嘴里,甜,才知道是蜜。
祖母呵,我和弟弟一直唤你奶奶,父亲母亲一直唤你娘,祖父一直唤你孩子奶奶。我一直以为你没有名字,直到祖父去世了要带户口本去火化,我翻开户口本才知道你叫薛瑞兰。
多好听的名字,兰。
桂花落
桂花在这座园子里开放的时候,香味是纸包不住的,是窗户挡不住的,扑簌簌的桂花香,茫茫然,却直往鼻子里钻。这个时候,平淡的日子被桂香托举,陡然间疏阔起来。我的心情和画家黄永玉一样——他对表叔沈从文说:“三月间桃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有杜鹃叫,哪儿也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朋友远远地来看桃花,听杜鹃叫……”
春天且去看桃花,聽杜鹃叫,秋天就闻闻桂香,一样是人间乐事。
纵然有四季桂,可桂是属于我心目中的秋天的。若是秋天没有桂,便要单调许多。秋分前后,空气里渐渐多的那层味道,那层浅甜的,飘浮的,幽微的暗香,虽然雾气一样缥缈,可我知道那就是桂。
阳光映照青石苍苔,盛夏的喧闹渐渐走远了。桂是秋天到来最明显的线索,桂花疏疏落落的花瓣,抱在一起,一朵,便可比拟一阕清词,使得一整株桂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本精妙的选本了。
桂,叶子还没有老,还油汪汪的,花就开了。桂花不突出自己,它太小了。桃花、梨花、杏花、梅花纵然也小,但附着在老旧的枝干上依然是耀眼的,它们的花谢了才长出叶子。桂就藏在叶子里,与叶子和谐共生。
桂花是啥时候开的,香味是啥时候在这个园子里漫漶起来的,我说不清楚。我想,成熟的秋天应该还葆有一丝童真,是她伸出调皮的手,挠了挠桂树的胳肢窝,桂就绷不住脸了,满树花就集体笑了,那么多的小姊妹们一起笑,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哪能没有声音呢,只是我们不曾留神罢了。
白日喧嚣,桂香如同游丝若隐若现,只能闻其香而不见其树,像我这般大意的人自是分不清桂和其他乔木的,但循着桂香这条线索,步入那些高楼背后的幽静,那些平日里我似乎总没有空停留半分钟的鹅卵石小道,我就一定能找到它们。一株桂,见到我就不笑了,她只对王维笑。王维写“人闲桂花落”,意思是王维有空陪她开放,也有空陪她凋谢,桂花感念诗人的陪伴,就一直在诗句里流芳。谁不渴望这种陪伴呢,这不正是爱尔兰诗人叶芝那首久负盛名的《当你老了》——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桂绽放得别有情怀,一点点地私语,不惊动别人,然后,悄悄落下,仍然不惊动别人,其香又那么醇厚绵长,这种情怀抓不着,说不出,也画不出,却一直在心头萦绕。被一树树桂香围绕,人特别容易发痴,有时候连眼神都是游离的,仿佛有心事一般。其实,那根本不是在想心事,只是桂花的香味有一种轻微的迷幻作用,人在其中久了,就会陷入回忆的风暴。
我想起外祖父便是桂花开的时节去世的,当生命走到尽头,杜冷丁也无法为他止痛了,他就搬个马扎坐在院子的桂花树旁。粗瓷壶泡出来的粗茶,陪伴着他,琥珀色的液体诚心实意地倒映着他微霜的鬓。就这样,一上午过去了,一下午过去了,仿佛那只是日子最普通的一种表现形式。阳光穿过枝丫,亮堂堂的,是秋天所特有的天光余韵,给他尘世最后一抹温暖。他的头发、衣领、裤脚、不离手的烟袋上,都悄悄附着了花瓣,与阳光融为一色,贯穿我整个秋天的回忆。
一晃十五年过去了。外祖父是我第一个去世的亲人,我觉得他去世时还年轻,那时候我怎么懂什么是永别呢,不过觉得他走得仓促,没有来得及和他见最后一面。而他的遗愿,是养一群羊,继续支持儿女们单薄的家业,支持孙辈们未竟的学业。有时我想,外祖父的一生不也正如一朵藏在叶子里的桂花,在芸芸众生里不起眼又默默散发着香气。
他十六岁便没了父亲,在舅舅家的屋檐下生活,要供养小脚的母亲,抚养两个年幼的妹妹。待成家后又相继养大六个孩子,生活的重担让他没有半点喘歇的机会。他耳朵聋得早,跟他说话要喊,母亲说他年轻时很严厉,但对待孙辈却和蔼得很。他讲过很多往事给我们听,有些如木心的《从前慢》一样美好,但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却很伤感——
他曾陪他的岳父去市里看病,回来晚了,没有了公交车,却又没钱住旅店了。他就搀着病中的岳父深一脚浅一脚,从市里一步一步走回家。开车从市里回家要一个半小时,搀着病人步行得多长时间呢?我想过又不敢往深里想,只是如今每次从市里回家我都忍不住东张西望——多希望真的有时空穿梭,我们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重逢了,我可以捎他们一程,让他们劳累的双腿歇上一歇。有时候,这般想着想着就落下泪来,也无法和身旁人解释这情绪的源头。
死去元知万事空。桂花树下,花瓣无声坠落,时如骤雨,时如轻露。无需多时,桂树下大地裸露的肌肤就被涂抹上一层淡黄,细小的落花,安然地睡在微凉的大地上,让人生怜。它们身后的背景里恰好生长着一株肥硕的芭蕉,秋桂的金黄,芭蕉的碧绿,浓墨重彩地洇在大地的宣纸上,有写意的恬静淡然。即便没有风雨侵扰,桂花也会这么快就离开了母体,这世间的别离大多如此轻飘飘,让人猝不及防。
也是这个秋天,读到郁达夫《迟桂花》里的名句:桂花开得愈迟愈好,因为开得迟,日子才经得久。从前,未曾好好看看身边的亲人,也未留意过桂花与别的花木不同,但愿往后年年,与花香树木,人间亲人,好好相伴。
在梅边
在冬天,走进鲁南这个小小的村庄,邂逅湖就像在夜晚一抬头和漫天繁星撞个满怀,是一种孩提式的敞露,一抹深邃的意境,一个拥抱的温柔,这份意外的惊喜让我不禁放慢了脚步。
湖叫燕柳湖。燕柳湖,想必春来湖水绿如蓝,它的莺歌燕舞、柳浪闻莺肯定能让游人流连忘返。然而我的到来却是在冷寂的冬天,没法确认它的热闹之美。湖在冬天是寂寞的,我环顾四周,离湖最近的是芦苇。只是我该如何描述冬天的芦苇丛呢?它们太安静了,仿佛只是一折星霜月痕,亦或者一个安然却浅浅的梦境。我望向芦苇,但它们低下了头。
我可以想象一丛丛芦苇盛长时的景象,水鸟飞翔,绿浪起伏。只是曾经的荡荡芦苇,如今都残败了,孤独清冷。画家吴冠中画过不少残荷,他着笔于线之曲折,倒影荡漾,藉此呈现花叶的迷宫。残荷可入画,冬天的芦苇亦能打动人心。在冬天,反季节蔬菜可以在大棚里旺盛生长,但大地上自然存在的一切,比如眼前这一株株沉寂下来的芦苇,仍然会唤醒人们对生命的敬重。芦苇样貌羸弱,但每一株芦苇应该都有一件终身信守的信条,否则它们何以做到可以在方寸之地扎根,并且一待就是一辈子。芦苇在湖畔度过春夏秋冬,到了冬天,它低下了头,守望着湖底这泓养育它的水。水一遍一遍在风里荡漾,安然地听芦苇叙述往事,眷眷不散。
把目光从芦苇身上移开,仔细观察还能发现,草木的命运到了冬天并不尽是凋零,燕柳湖畔隐隐还有梅香。仿佛在这寒冬里,依旧要让人体会那藏在林木深处的春天气息,它们的力量常常让我热泪盈眶。
从青少年开始,早就已经背下了太多关于梅的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平时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我想起电视剧《甄嬛传》中,甄嬛初进宫时,性情简纯,在除夕之夜,独自跑到倚梅园挂小像,所许的愿望便是“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一个女子,背后有一座倚梅园做底子,真像水墨画里的那朵色彩浅浅的梅,骨子里都透着清凉的芬芳。
我走近梅,梅就开在湖畔不远处。梅出生在低处、在偏僻、在旮旯。风吹来,有花瓣落下,使她有一种遗世独立的美。她绝不讨好谁,因为扎根大地就能活得很好的缘故。她随意站在雪地里,幽幽地吐着香,婉转,朴素,却意态悠远。她开得很好,没有人舍得把她折下来。幽幽的清香不动声色、不卑不亢、不绝如缕。她那样骄傲,没有人敢把她折下来。生命的风骨之美,真的是穿越风霜之后才有那份昂扬自信。
有时,我会赖在梅旁不肯离去。看着这些树,这些没有言语的树,分明在逆生长,老旧的枝干到了冬天才著上花朵,人不能越活越年轻,但是梅可以,在梅边,才让人懂得什么是韬光养晦,什么是厚积薄发。偶尔会下雪,雪裹挟着风,翻过一朵朵梅。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那些开在枝头的梅,似乎早就得到了冷热的讯息,不曾流露一点讶异。漫天的雪花飘落,落在梅花上,也落在燕柳湖里,我看到雪花落到梅花上点缀的花心晶莹剔透,雪花落到湖面甚至激不起一点涟漪就融化了。
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里写道: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谁也帮不了谁。此刻,虽然在梅边,但我无法替一朵梅抖掉它身上的雪。
我想起那些回荡着自己浓重叹息声的夜晚,孤独与无助如汹涌的潮水将我吞噬。因为那也是我一个人的冬天,那是我才能感受到的冷。或许我们有很多理由和机会去跟别人痛斥自己正遭受着的冷与痛,但更多时候,我们都是一个人,纵然岁月一步步往深处走,将渐渐成落光了叶子的枝干,不甚明媚,有一点灰褐的暗淡,但熬过来的心会是那傲寒的一朵梅,梅从来没有怕过生命里的冷。
就该学学梅,它安然走着自己的时令。直到所有的花都开过了,所有的叶都凋尽了,它才长舒一口气,缓缓绽放。读大学的时候,宿舍在一楼,窗外恰有一株梅,梅是老梅,与年轻的面庞相映成趣,成了我们寒冬腊月里蛰伏的小确幸。多
少年,“平时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意境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扬州八怪之首清代书画家金农,善用淡墨干笔作花卉小品,尤工画梅。也有《画梅·老梅愈老愈精神》的诗作传世——老梅愈老愈精神,水店山楼若有人。清到十分寒满把,如知明月是前身。是老梅的真实写照。老梅,不知陪伴过多少青春,听过多少怅惘满怀的歌谣,依旧蓬勃鲜活地向上长着。疏密有致的枝柯,如虬蟠一般,弯曲地向四面躬着,向八方展着。年轻的时候满脑子浪漫想法,我想穿越千年,邀陆游来赏梅,他是那个痴情的人,而这里梅香如故;我想邀李清照来小住,听谁家横笛,抚慰漂泊天涯之苦;我还想邀陆凯来看梅,这里才应该是《赠范晔诗》的出处。梅,让泉城舜耕路40号上的山财(山东财大)充沛着古典气息。
爱梅惜梅的人太多了,梅为妻,鹤为子,林和靖是其中最痴狂的一个,他在西湖边把一个人过成了一个家。所以他写下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想必多少个日子,一个人什么也不做,就静静看梅花开在黄昏的冬季里。
如果一株植物是一盏灯,那么香味就是它的光。我探过头去,想嗅嗅梅香。忽然,我被梅小心翼翼地抚摸了下脸颊。那朵花,凉凉的,滑滑的,有着木质的清香味,树脂的油香味,还有着山野的草木味。
在落雪的冬季,也有人像我一样来看梅。我猜不到他是谁,只有一串通往燕柳湖的脚印成了告密者,無声地指示着他的去向。何必知道他是谁,这世间多得是不怕冷的傲骨。在有暖气的室内待久了,也该到冷的地方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冷总是更适合省察内心,思考是形而上存在的,不然长长的冬天,德国哲学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如雷贯耳的哲学家。那震慑人心的哲学厚度和深度,也跟远处的群山一样,让人觉得此刻适宜保持缄默。
责任编辑车前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