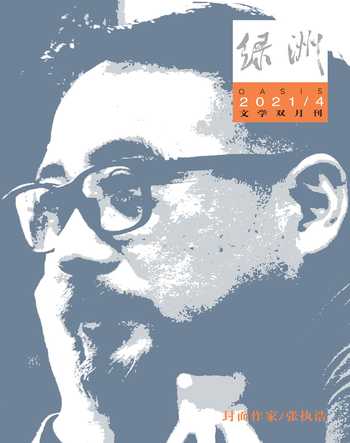饮食男

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奎虚图书奖、滇池文学奖、红豆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中国文章》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
饮食男
去年初还是前年底,忘记了,朋友相约家宴,临时要我做两道菜。
那顿饭大家吃得不亦乐乎,事后居然封我为“饮食男”。人生在世,草木一秋,都是匆匆過客,挣个名头不容易。“饮食男”这三个字,我一听到,就暗暗叫好,神采奕奕,精神焕发,有奢侈在嘴的感觉,或者说是寄情于胃的感觉。眼前蓦然呈现出这样的场面:
一个穿白衬衫的青年,文质彬彬地闲逛菜市场,穿过繁华的街道,左手提着一尾鲜活的鲤鱼,右手篮子装满苦瓜、豆角、青椒、山药、马铃薯、蒜薹之类。青蓬蓬的菜叶兀自探出来颤巍巍抖动,正是:
满篮蔬菜装不住,一棵莴笋出头来。
这青年正是饮食男,他提着一篮蔬菜走在回家的路上。蔬菜的淡香飘在身边,浮过热闹的街道,钻进人们的心头,饮食男视而不见。白衬衫上新染了一道碧茵茵的菜渍,那是别在胸前的一枚植物印记,仿佛来自遥远乡村的绿月亮,浅浅一弯,像油画一样清晰,又如水彩般清逸。水彩的时光那是别样的春愁,事关记忆,速飞的大脑一空……
水龙头下洗菜。自来水冲出一道白亮的弧线,打在指间,旋在瓷盆里,菜叶漂浮,仿佛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饮食男就是捕捞的渔民,或者是看海的逸士。时间猛地跳回到客居青岛的日子,和朋友一起在栈桥的海旁挑螺蛳、吃牡蛎、啖牛肉烧烤、喝扎啤,俗俗的充实拧成淡淡的风雅。这些饮食带来的享受,都是穿过喉咙的美好记忆,经年不忘。
电饭煲里的大米熟了,一股清香溢出锅盖,飘荡在四周,轻轻一嗅,胃里爬满饥饿,饥饿得双腿发软。放油入锅,饮食男开始工作了,煎炒煮炸焖炖,轮番上阵,这些基本功是作为饮食男最起码的素质吧。
我以前喜欢吃肉,现在偏爱吃鱼。城市米贵,肉价飞涨,只得吃鱼了,哪天鱼价再涨,干脆戒了荤拉倒,像兔子一样专吃青菜。不过厨艺好的人,烧的青菜堪比鱼肉。这年头,青菜很难流行,但我爱吃。家常青菜,色如翡翠,盛在瓷碗里,香腾腾的,有股暖心的透彻,有股明润的透彻。譬如蒜蓉莜麦麦菜,放酱油,爆火速炒,滋味直逼人心,然后风韵弥漫。再如酸辣大白菜,放陈醋、辣椒粉干炒,出锅后,清爽中有一丝酸辣,令人舌齿生津,惜乎那种滋味,只可意会,无法言传。
饮食之道,讲究风韵与心境一体,表相共味道相依。饮食男女何尝不是如此?但许多人往往徒有其表,就像所谓高级酒店的饭菜,看着漂亮,吃了不爽啊。
酒不入肠
酒不入肠,我也醉,你醉的是酒,我醉的是字。
我喝酒,与其说喝,倒不如说是读。常常在书中读出酒味,从比喻写起:
先秦古文如陈酒,魏晋文章如米酒,唐诗宋词如黄酒,明清小品如清酒,元明话本如啤酒。
有人的文章是药酒,有人的文章是红酒,有人的文章是糟酒,有人的文章是果酒。有人的文章不是酒,是醋,是红烧肉,是排骨汤,是猪食,是狗粮,是鸟粪,是一地鸡毛,是漫天大雪。一地鸡毛忽然又做了漫天大雪。有一天我路过屠宰场,看见几个少年拿鸡毛当令箭,不,抓鸡毛当武器打架。只见一地鸡毛做了漫天大雪。恰恰又是白鸡之毛,那雪越发雪白。
前些时朋友托我给她朋友的朋友的诗集作序,我这么写道:
说奇怪也奇怪,说不奇怪也不奇怪,我突然觉得书中“风雨兼程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可以对上。王维这首《送元二使安西》上一句恰恰是“劝君更尽一杯酒”。劝君更尽一杯酒!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沉醉三天三夜
喝酒是奢侈的,在盛世喝酒,未免浪费,所以我不知酒味。如果生逢乱世,大概会喝点酒。清风明月下,国破山河中,醉眼迷离了刀光剑影。如果还能散发,如果还有扁舟,如果还有曹操、嵇康、陶渊明、辛弃疾,我要沉醉三天三夜。
闲饮酒
菊花开了,飘散清淡薄香。街道的树叶慢慢转黄,阳光淡了,心情也清淡起来,居然想找人清谈。那就读书,取一册《世说新语》,简约生姿的文字,可以下酒。古人以史书下酒,我借笔记下酒。没有酒,以茶代之。春天时朋友从家乡寄来的新茶,舍不得喝完,存在柜子里快成旧茶了。泡一杯在手,有友情的温暖,还是喜滋滋的。
茶不如新,新茶馥郁满口。酒不如旧,陈酒飘香一室。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酒被剔除在外,这实在不公平。酒的重要,与酱醋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送人有饯行酒,接风设洗尘酒。好事饮庆功酒,坏事喝安抚酒。婚庆是喜酒,吊唁有丧酒;小儿出生满月酒,老人生日摆寿酒。可谓人不离酒,酒不离人。
喝酒是一种心境,以酒助味,借酒消愁。世故不可无茶,有趣不可无酒。一大桌人,半生不熟的,夹生夹熟的,滚瓜烂熟的。来来来,吃菜吃菜,到底显得小家子气了,也烘托不出气氛;干干干,再喝一杯,这才像话嘛。如果恰逢丽人在席,虽推犹劝之下喝上半杯,脸红若桃花,眼媚似云霞,也可算饭桌边一处春景。总之茶是越喝越淡,酒则越喝越浓。
茶淡似妻子,酒浓如情人。茶馆是爱情萌芽的地方,酒吧是艳遇泛滥之场所,区别即在于此。古人让酒居四戒之首,真是明察秋毫。西门庆与潘金莲苟合,王婆将盘馔都摆在桌子上。三人坐定,把酒来斟。西门庆拿起酒盏来,说道:“娘子,满饮此杯。”那妇人笑道:“多感官人厚意。”三盅酒下肚,哄动春心,禁不起西门庆再三以言语相挑,两个就在王婆房里脱衣解带,无所不至。正是:
须知酒色本相连,饮食能成男女缘。
张爱玲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鲫鱼多刺,三恨曹版红楼短篇章。我却多了一恨,四恨肠胃无酒量。我畏酒如药,茶只是喝,无视品种。酒只是不喝,不论价位。
小时候见父辈喝酒,猜拳呼喝,好不痛快,以为酒是仙丹。趁无人之际,悄悄喝了一口,又辣又呛,舀了满满一瓢水漱了好几遍口才缓过气来。从此视酒如鬼神,敬而远之。如今年岁渐长,酒量却不增分毫。最近读书,见“痛饮从来别有肠”一句,心下豁然,生时无别肠,喝酒一事,努力也属枉然。
大袖翩翩的六朝人喝杜康酒,李白、王维喝新丰酒,民国时,文人热衷黄酒,现代许多人喜欢啤酒,文化越来越浅倒也罢,酒量也越来越小。文章是古人的好,酒量也是古人的好。我辈不羡古人,且偷浮生。几碟小菜,两盘点心,喝點小酒,不谈风雅,只论风月,倒也快活。
有肉有酒,闲饮闹市,自在潇洒。手持玻璃樽,仿佛身在亭台,于楼阁间闲看闲聊闲饮。喝到微醺,醉也不是真醉,醒也不是真醒,几个人相拥着回家,低头是朦胧的灯光,抬头有半圆的月亮,一路踏步而歌。
喝酒要有闲气。这闲,是好整以暇,是置之度外,是闲情逸致。今人喝酒每每总是出于意气,喝得一身匪气,吐得一地酒气。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梁实秋先生说此种趣味,最令人低回。倘能如此,算得饮酒之妙境也。
饮酒记
在山里农家晚饭,鱼头汤火候正好,几道时鲜清爽可人,不油不腻。嚼着新嫩的笋干,晚霞刚刚落下,村口山月升上树梢,主人家拿来柿子酒,没喝过,想尝一口,到底止了意念。饮酒之心退潮了,再也涨不上来。三十岁后开始喝一点酒,不过只在逢年过节亲友相聚时浅尝一点,并不能入诗肠添锦绣,更没有壮雄心气冲斗牛。
家族善饮者不少,父辈以上,无酒不欢,人人皆有酒量有酒胆。几个叔父辈,近年居家紧要事是自酿米酒,费时费事,不厌其烦。每年酿百十斤甚至几百斤,用瓦钵装得满满的,靠壁放在堂屋,一罐罐粗粗憨憨。
我第一次喝酒在苏州。在古镇、园林、村落游荡几日,离别之际,友人动了酒心。拿来一瓶白酒,以鱼佐酒,两个人不知不觉喝下一瓶。秋日陶然春色,三分忘我三分迷糊,一路风吹着,觉得通透。此后喝过大酒喝过小酒,也有过花生米、烤肉就瓶酒随意而饮。
有年暑天友人招饮大蜀山下,暮气昏然,楼头灯火迷蒙,坐列无序,不分宾主,至微醺小醉,其间颇得佳处。几个朋友都是好年华,酒酣耳热,饭后在山里放浪而走,月色晦暗,心情晴朗。现在怀想,颇有些怅惘,不过六七年时间,那样的辰光仿佛隔了一个世纪。
也是暑天,在云南抚仙湖,与老友坐在藤状植物缠绕的绿棚下,吃铜锅鱼、喝高粱酒。雨落在湖里,也落在我们头顶,水面安静得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又起了雾,恍然如仙境。两个人在雨中饮酒,悠然自得。友人酒量大一些,我浅尝了几杯酒,微风轻拂。“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样的情景,觉得是唐诗宋词的情味。
印象中北方人比南方人善饮。去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一带,酒客有侠风,生怕酒淡,唯恐不醉。那年在鲁南微山湖畔夜宴,一场豪饮,来客皆一两斤之量。席毕,个个满面红光、精神抖擞,无人醺然,靠墙处一排酒瓶列阵布兵,蔚为大观。去台湾与福建一带,席上用的是牛眼大的酒盅,主人每每分作三两口才尽落喉中。
喝了几次白酒,心里还是畏惧。果酒、米酒、黄酒遇见了还稍有喜心,偶尔喜心浩大,气吞山河。在绍兴逗留过几日,与黄酒脾气相投,每天除早饭外饮之不断。那酒以白瓷饭碗斟上,仿佛酱油,多则近十碗,少则一两碗。每夜酒后且能作文,无有醉意,心下称奇,同行者皆觉得咄咄怪事。那样的豪兴后来再没有过。
绍兴黄酒像苦雨斋的文章,绵软,后劲十足,苦雨斋的阿弥陀佛里是有金刚大力的。我过了三十岁才开始喜欢知堂的,他的文章近乎砖铭,需要人凝神细读才得滋味才知风神。
某年远游归来,朋友请饭洗尘。座上有黄酒,兴致颇好,两盏下去,不料得了大醉,平生第一遭唯一遭。至此方明白祖父当年说的话,喝一生酒丢一生丑。醉后意识虽在,然身体不听使唤,两腿进退艰难,难逃丑态,不必细表。
大小酒场二十几次,奇怪的是,酒量不仅未能见长且越来越减退。苦海无边,索性回头,写过一篇《酒诰》:
无酒不成席,我当然也喝。今年饮酒十二场,天增岁月人增寿,唯酒量不增。多喝易醉,往往做不得事。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十榼,李白斗酒,古之圣贤无不善饮。我本布衣,三杯即乱,明年决定戒了。熟也罢生也罢,官也好民也好,无论男女老少,不分贫贱富贵,多吃菜少喝酒,认饭不认人。买酒费钱,喝酒伤身,此事两相无益。座上皆是客,相逢茶一杯,正可谓君子之交。酒少喝或不喝,对谁都好,对我好,对你更好。以此告四方友朋,也警示自己。时在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此后虽未能滴酒不沾,往往寒夜客来茶当酒,对杯中物尽量避之躲之。
花露烧
花露烧的名字好,好在妖娆。“花露”二字有江南烟雨气,烧字后缀,雨过天晴。味道出来了。花露烧的色泽也好,八年陈酿花露烧在玻璃杯里剔透如融化的玛瑙。艳丽,晶莹,清透,嫣红,摇动杯子,风情出来了,而且是异域风情。花露烧的味道更好,有清甜有辛辣,甜非甜,辣非辣,点到为止。鲜美、软嫩中带一点烧酒之烈。
一杯花露烧浅浅歪在酒杯里,舍不得喝也不忍心喝,怕扰了美人心事,扰了“绛唇珠袖两寂寞”的气氛。
近年饮酒,在江苏遇见两款佳酿:十月白,花露烧。十月白有深秋白月光下的清凉,花露烧是初夏正午的阳光。
十月白,花露烧,是女人也是古琴。一尾琴十月白,弹出平沙落雁,弹出深秋的安静。一尾琴花露烧,弹出高山流水,弹出初夏的况味。
春天里喝花露烧,坐在玉兰树下吃春膳,玉兰像生长在枝头的瓷片,田野的花香与酒气一体。夏天喝花露烧,坐在竹丛旁,身边有开花的树,桌上有新鲜的鱼,喝到夜雾凝结。秋天,坐在月亮底下,喝到夜深露重。冬天喝花露烧,窗外最好下点雪,坐在小室里,风日大好。
花露烧,如梦如花,如露如电。饮着花露烧,耳畔有啸声,顿生空明。
即兴
暮春之夜的小城,感觉大好,可惜找不到句子来描述。街头不冷不热,温水一般,三五成群的男男女女谈笑着轻轻走过。酒足饭饱的人做梦去了,闲情未了的人喝酒闲聊。路边小店暗红色的灯光下,几个妖娆的女子倩笑盈盈左右张望。
魏先生说,出去喝酒吧。寂寞的夜晚,能做什么?喝不了白酒喝啤酒,喝不了啤酒喝红酒,喝不了红酒喝果子酒,喝不了果子酒喝果汁,总之要喝点什么。忽然起了酒兴。据说酒能乱性,我铁石心肠,它奈我何哉?
魏先生点了三个菜,鸭血炖豆腐、酒糟焖小鱼、韭菜炒螺蛳,外加一盘花生米。韭菜炒过了头,过犹不及,吃在嘴里少了嚼劲。酒糟焖小鱼,第一次吃,没见过代表作和力作,说不出所以然。鸭血炖豆腐,味道清淡,红是绛红,白是乳白,红白相间。大为悦目,极其爽口。我要了鲫鱼汤,蒜姜同烧,味道在不经意间。
虽然吃过晚饭,还是连喝了两碗。有人恨鲫鱼多刺,现在看来,还是做不得法。
三人围桌而坐,心境甚好。心境好了,大菜也是大餐。别人都睡了,我们半夜方归。别人都睡了,我们谈兴正浓。
稻米书
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与气候风俗相关联。譬如稻米,在南方是一日三餐的主角,在北国,却是日常生活的客串。面食在南方是饮食中的客串,在北国,却是餐桌上的主角。虽非定论,南北食俗的情形大抵如此。
在南方生活了二十年,吃面食的次数屈指可数。不是说面食不好,主要因为周围缺乏吃面食的环境。
后来客居北方,天天面食果腹。开始还怀有思黍之心,渐渐也习惯了馒头、包子、面条、烧饼,吃得不亦乐乎。可见我这人性情不定,容易忘本。因为饮食关乎一个人最基本的生活立场,不是说改就改的。一个人可以时不时闹婚变情变,一个国家可以动不动搞政变军变,但一个人一个国家的饮食习惯,往往难以改变。
有北方朋友去南方工作,回来说那里山好,水好,人也好,就是吃不好。稻米饭吃起来像含了一嘴沙子,不安本分,四处乱窜,无法下咽。我告诉他吃米饭要慢,胡嚼一气,米还没碎,吞急了容易噎着。吃米饭时,专心一点,舌头卷起,缓缓地送到板牙上咀嚼,这样才能吃出滋味,吃出清香。
稻米是清香的。白米质朴,黑米厚实,红米轻灵,红米比白米、黑米、小米都要清香。
吃饭吃的是菜,严格说来是稻米和蔬菜同吃。如果是一杯茶,它们应该就是水和茶叶的关系。饭菜饭菜,茶水茶水,须臾不分。没有菜,再好的米饭也味如嚼蜡。
我吃过很多品种的稻米。稻米的品种每每以地域区分,皖南稻米,苏北稻米,泰国稻米,加拿大稻米……
一粒晶莹的大米,能反映出一方风土人情。不同地区的米粒,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气味。东北大米呈椭圆形,饱满充实,像关外大汉。江苏大米,狭长纤细,呈锥尖形,像江南仕女。泰国大米,长着女子的外形,骨子里却是男人,口感肆意,可谓十足人妖。
以颜色论呢?白米是中年人,黑米是老年人,红米则是青年人。我每每看见红米,心里总平添了一份热情。
前些时候去一粮库。那么多稻米装在麻袋里,白花花倾泻而下的场景,壮观极了。稻米坚实而闪耀,像丰饶充沛的河流。刹那间泻下的不只是粮食,还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光。
一粒米,一段成长的过程。一碗饭,一些生活的片段。一碗热腾腾的米饭,一粒粒闪耀着琼浆色泽的稻米,让人心里踏实。
小吃
小吃的小,是外形的巧,是体积的小。小吃的吃,是名词一食,是味道一绝。有些地方,这辈子不可能涉足,但吃一份颇具当地风味的小吃,也就有了远足他乡的况味。饮食之旅就是味觉漫游,尤其是地方小吃,其中可见地域风情。
大餐是相似的,小吃各有不同。饮食上,应该南北通吃。小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市井文化,品尝小吃,就是品尝民间味道。
小吃这个词始见明清之际。《醒世恒言》写钱青在高赞家吃饭,“三汤十菜,掭案小吃,顷刻间,摆满了桌子。”《儒林外史》里说景兰江、匡超人、支剑峰、浦墨卿四人小聚,“叫了一卖一钱二分银子的杂烩,两碟小吃。那小吃一样是炒肉皮,一样就是黄豆芽”。《镜花缘》中李汝珍借吴之和谈时人饮食习俗,除果品冷菜十余种外,酒过一二巡,则上小盘小碗,其名南唤“小吃”,北呼“热炒”,少者或四或八,多者十余种至二十余种不等,其间或上点心一二道。
我喜欢旧小说中的饮食谈。和吊人胃口的传奇相比,一份静躺于古书纸页间的小吃,更让后人怀慕。历史深处的烟火气息是前人的体温。
小吃品种繁多:粥、酥、团、卷、饼、条、冻、饭、包、饺、糕等等,数不胜数。
和南方相比,北方小吃歷史悠久些。西安的羊肉泡馍、锅盔,散发着秦汉的古意;开封、洛阳的许多小吃,颇有唐宋遗制。
时间让我们和古人不能谋面,小吃却让彼此口味相连。热气腾腾的点心,白居易吃过,欧阳修吃过,王安石也吃过,油然生出风雅。品尝小吃,享受的不仅是一份美味,更能体会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我非美食家,但一个凡人更难拒绝美食的诱惑。美食家曾经沧海,除却巫山不是云;饮食男孤陋寡闻,见风就是雨。
如果说大餐是精雕细琢的刻意,小吃就是家长里短的随便。大餐是满桌名菜,小吃是几样点心;大餐是富丽堂皇中宾客言欢的觥筹交错,小吃是茶余饭后款款生情的低声细语。
大餐不过平凡生活的几丝点缀,小吃却是风雨人生的一份守候。守候是动人的,有朴素有温馨弥漫其间。小吃的小是浅浅一笑,小吃的吃是百味人生啊。
今天晚上的饭局就不去了
越来越失去参加饭局的热情,疲倦。
午睡刚醒,几拨朋友约晚饭。书画家聚会,诗人聚会,散文家聚会,闲人聚会,商人聚会,这是聚会的年代。一个人喝酒吃饭,多闷啊,一大帮人,这样才兴高采烈。今天晚上的饭局,我推了。虽是好朋友,也聊得来,因为心里排斥,还是告诉他:
今天晚上的饭局就不去了。
说是排斥,到底还是怕。闲散惯了,怕敬酒,怕记不住人名,怕规矩多。
下班后,买了毛豆、买了土豆、买了扁豆、买了四季豆、买了豇豆,回家烧饭。今天的晚餐够丰盛,醋熘土豆丝,干煸四季豆,红烧豇豆,毛豆炒鸡蛋——豆类的盛宴。
吃过晚饭,时间还早,时间还早是说离睡觉时间还早。泡了一杯茶,三五片茶叶,历历在目。
喝完茶,时间还早,拿出冯梦龙的《三言》,读完《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复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再读《王娇鸾百年长恨》,读出女子多情,男人无义。洪昇《长生殿》说得好,有道是:
“从来薄幸男儿辈,多负了佳人意”。
恨不能钻进书中,替了那负心人。于是读《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心头稍微多了暖意。
读完书,时间还早,写了篇随笔,换点菜饭钱。城市米贵,居之不易,必须勤写苦读。少参加几次饭局,多收了三五斗文章,也说不定。
笋干
闲时读友人新作,像深冬吃火锅,有汤有水,有荤有素,可以下酒,也能下饭。某些作家的文风像食物的口感。譬如读鲁迅的杂文,像喝陈年老酒,绵厚辛辣,余味袅袅。看金庸的小说像啖西瓜,痛快淋漓,汁水四溅。读张中行的随笔,如吃山药粥,有老到极处的幽意。废名的散文,清凉中有深味,如凉拌海蜇。而知堂小品近笋,微涩,口感清远。汪曾祺是春初新韭,秋末晚菘。贾平凹乃羊肉泡馍,料重味醇,肉烂汤浓。我自己呢?胡竹峰大抵算小水萝卜吧,不能果腹,茶余饭后吃一个,嘎嘣咬下半截,脆生生,甜丝丝的。不说了,不说了,再说,下次有人看书会生口腹之欲。
上午无事,在厨房做笋干老鸭煲。将老鸭切成块,放入沸水中焯去血污,用大火煮开,再以文火轻熬。
我炖汤不怕耗时间。这几天春寒微凉,厨房里暖和些,可以伴火读书。汤汁慢慢厚了,放进几块腱子肉,让它们猪鸭一家。再投以葱、姜、野山菌,还有笋干。笋干被切成细条状,它是有灵性的,在汤水里几度沉浮。野菌摘了根部,像船又像伞,在汤面漂荡。静候着山菌与笋干的清香。这样的汤是清风明月。
笋干是老家野生水竹的笋,一段段成丝条状。唯恐易尽,烧过一次笋干炒肉,藏了起来。很多年前,我抽过水竹笋,回家后剥出笋肉,在开水里焯熟,再切成丝,金黄的颜色,细匀匀的,放在竹匾里晒。晒干后,一斤仅余二两。这样的笋干,口感绝妙。隔了十多年,居然再次撞上,真是天赐良缘。
乡下,一到冬天,天气晴朗的日子,常看见竹林里有挖笋人。没什么秘诀,拿把锄头,专从裂缝或者凸起的地方下手,准有收获。
冬笋似小船,微微翘起,两头尖尖,肉色乳白,壳薄质嫩。冬笋味道清苦,含禅意,有内敛之气,荤素百搭,炒、烧、煮、炖、煨,均有一番风味。冬笋终日藏在土中,颇有世外桃源的旧民之风。
冬笋价贵,春笋格贱,是不是因为太粗大了,太喜欢出头了?春笋涩味稍重,吃得人舌尖发麻。有人说春笋味鲜如鱼鸡,梁实秋在一篇文章里赞其细嫩清脆。口味真是太私人化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嘴巴有一千种味道。
味道,味道,味可言道。《道德经》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味道自有无法言传处,口感玄之又玄,一张嘴几乎就是众妙之门。不过春笋模样清新水灵,像江南人家的女孩,看着舒服。
母亲会炒笋。上好的冬笋切成片,过一遍水后放两个辣椒,加腊肉红烧。不见经传,却有真手段。
刀和棒
吃喝里是有刀和棒的,鸿门宴众所周知。
当年商臣指使潘崇逼宫弑父,楚成王祈留一命。潘崇说:一国岂能容二君!楚成王知道熊掌难熟,想争取点时间等待救兵,又问:已令厨师烹制熊掌,能等我吃了再死吗?潘崇识破了他的心事,取下自束脖颈,命兵士将成王勒死。商臣即位,史称楚穆王。这是吃喝背后的尔虞我诈、刀棒相加。
食物的外形上,我觉得豇豆也可称为棒,四季豆可称为刀,柳叶刀,扁豆则有人称为刀豆,像太极刀吧。实则扁豆是扁豆,刀豆是刀豆,有人把刀豆叫作挟剑豆。
豇豆长在菜园里,农民说风调雨顺,文人说满园春色,商人说一地富贵,绿象牙?翡翠棒?我说兵气盈目,一根根棒子悬在那里。
痴迷《水浒传》时,每次路过菜园,看见豇豆垂地,棍棒如林,风一吹,木墩墩轻轻有声。不免想起“景阳冈打虎”一回文字:“武松放了手来,松树边寻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里;只怕大虫不死,把棒橛又打了一回。眼见气都没了,方才丢了棒……”
看见四季豆、刀豆,想起《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一节:
“李逵道:‘正是你这业畜吃了我娘。’放下朴刀,胯边掣出腰刀。那母大蟲到洞口,先把尾去窝里一剪,便把后半截身躯坐将入去。李逵在窝内看得仔细,把刀朝母大虫尾底下尽平生气力舍命一戳,正中那母大虫粪门。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把,也直送入肚里去了”。
因为这样的想象,也因为这样的故事,我对豇豆、扁豆、四季豆久吃不腻。喜欢豇豆的碧绿,让人心旷神怡。
挑一勺猪油放入锅中烧滚,青椒切成丝,快速过油入盘,然后将掰成小指长的豇豆下锅爆炒,火开到最大,豇豆翻滚,迅速吃油,绿得深沉熟透时,放入青椒,即成一款美味。有这样一盘豇豆,我可以多吃一碗饭。
小时候屋前屋后闲逛。瓜蔓地种有四季豆,新豆初出,那么多绿色的小刀,不知不觉着迷驻步了。那些绿藤上的小花很美,紫红泛出几丝白,那白因了紫的映衬,越发清雅。如果是清晨,白紫花开在清凉的露水里,嫩嫩的,柔柔的,引得一个少年俯身来嗅。
与豇豆相比,四季豆有股青涩味。不论清炒或者红烧,都要放姜或者蒜瓣,否则生气未尽,入嘴豆腥犹存。我烧出来的四季豆,豆身自始至终是绿的,却熟得透,豆肉细嫩,盛在金边瓷盘里,真个“金玉满堂”。
四季豆又名芸豆。芸豆让我想起《浮生六记》里的芸娘,林语堂眼里“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四季豆在老家被称作“五月梅”。五月梅这个名字,大有诗意,不知出自哪位乡贤之手。
有人称扁豆为藤豆、鹊豆、羊眼豆、膨皮豆,我老家则唤月亮菜,月儿弯弯挂树梢。白扁豆,银光匝地;黄扁豆,清辉漫野;紫扁豆,紫气东来。那是乡村的诗意。
豌豆饭
豌豆上市,我乡人好掺糯米煮饭,是为豌豆饭。或以芝麻油与豌豆、糯米搭配,或加咸肉、春笋。盛在瓷碗里,清清白白,清香盈室,有清白家风。
吃着豌豆饭,想起范文澜故居。范氏故居小园遍植草木,我仅识芭蕉、桂花、铁树三种。厅堂悬有“清白世家”匾额。越剧《玉卿嫂》有唱词说:“我本是清白人家出身好,家在村里名声高。”范文澜是范仲淹后裔。范仲淹徙知越州,在绍兴龙山发现山岩间一废井,井中有泉,使人清理冠名为“清白”。一来取其颜色清澈,二则以清白自律。家风如此,没得说的。
补记:豌豆尖亦可入馔。取其嫩茎叶,热锅下油稍清炒,起盐,脆嫩中透着清澈,鲜美鲜媚。
粥
关于粥,《随园食单》如此定义:“见水不见米,非粥也。见米不见水,非粥也。必使米水融合,柔腻如一,而后谓之粥。”此等说法,深得我意。
熬粥,在水量控制和谷米掌握上,需要讲究,火候也很关键。
淘洗过的大米外加几颗大枣、半把绿豆、一勺薏米、若干红米,舀瓢凉水淹没它们。静静地在电饭锅旁等待,锅内渐渐变得滚烫,汤水慢慢呈现出暗红的黏稠。那些白米、红枣、绿豆融在一起,咕噜噜冒泡。拿本书,在一边守候,蒸腾的白气淡淡地弥漫着,粥的淡香在四周飘溢。
吃粥的时候,就咸菜或鸭蛋,很惬意,有世俗人间烟火之美。
我在黄山脚下吃过一次粥,薏米熬就,稀烂入了化境。微盐,进嘴清香,淡如春风之际,暖意上来了。暖意是炭火的温存。几段猪肚蜷缩碗底,素简以一抹膏腴画龙点睛。佐咸菜笋干,顿去经日行旅风尘。连吃四碗,草长莺飞,徽州的九月,吃出一片江南的暮春。
鸡蛋
母亲将鸡蛋一颗颗攒起来,存放五斗橱。踮起脚尖,拉开抽屉看看。一颗颗圆润的鸡蛋白花花摆了一层,有种说不出来的富贵。
乡下,鸡蛋被老百姓称为鸡子。小时候,邻居家孩子比我大,说过不少孔子、庄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的故事,说这些人都是很久远、很古老的智者。他们的名字后面都带一个“子”字,我长期把他们想象成鸡子的模样。
想象中孔子圆滚滚,庄子滑溜溜,韩非子像荷叶上的露珠,公孙龙子是掌心的玻璃球。
葛根粉
将葛根粉在白瓷盏里以凉水稀释至液态,再冲入滚烫的开水——洁白褪去,灰褐走来,碗底凝凝冒着热气。撒入白糖,挑一匙入口,其味妙绝。
冲开的葛根粉,像琥珀,透明清亮,充盈着淡淡风雅。一股青气不时扑面而来,仿佛水乡夜航船,弥漫着河岸草木的味道,润朗、水灵、鲜活。
葛根粉是质朴的,带着乡村气息、民间气息、山野气息,不世故不圆滑。吃在嘴里,一线清凉从唇到齿,再顺着喉咙流至肠胃,有种褪尽铅华的口感。
冲好的葛根粉,色如枯草叶尖之秋露,味似薄荷凉茶之甘辛,具清热、降火、排毒诸功效。据说真正的吃家,为求滋味醇正,冲葛根粉时不放糖。不放糖的葛根粉也吃过,略嫌平了些,好在入口有夏夜的草气,让人发思古之幽。
在窗台边,背阳坐着,捧一碗葛根粉,温润在手心,滋养着舌头。一些快意漾開了,红的、黄的、绿的、紫的、蓝的,各色鲜花在晴朗的心头朵朵开放。时逢阴雨,情绪亦然。
一靓汤
两匙新鲜的猪油,烧滚,剥好的毛豆倒入锅底,炒至七分熟,放盐及相关作料,添水,待开后,捻碎青菜叶一撮撒上,淋下搅好的鸡蛋糊,半分钟起锅盛碗。只见豆粒于碗底沉浮,荚衣在汤面出没,鸡蛋随汤匙荡漾,青菜如轻舟徜徉。馋意袭人,轻呷一口,浮生如梦心自醉,仿佛天上人间。
耳食者
大餐名菜不好写,吃得也不多。粗茶淡饭的文章,让人有过日子的感觉。我等文人,更多时候是在家里念“一尺鲈鱼新钓得”“桃花流水鳜鱼肥”之类的诗词。鲈鱼是何味,鳜鱼怎么肥,耳食终日,偶尔吃个一两次,不得要旨。日常生活还是“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蒸梨常共灶,浇薤亦同渠”,是为耳食者也。
知味不易
近年写出不少饮食文章,是先前没想到的。有个阶段,见不得谈吃喝的文字,闲来读书,凡涉饮食部分一律跳过不读。为什么呢?说不出。吃到一款美味,自然高兴,吃完,也满心喜悦,但告诉别人如何美味,太虚无。鱼肉青菜嚼在嘴里的滋味,能描述吗?有人没吃过榴梿,问什么味道,答曰“软软的,有些臭”,分明答非所问。在湖边吃新捕的鲜鱼,滑嫩鲜美,经年不忘,别人问起,也只能说滑嫩鲜美而已。要说怎么样的好吃,也是一言难尽。五官的感受都是如此,借助文字,越发乱花迷眼。
后来读李渔、张岱、周作人、梁实秋诸位饮食文字,或有膏腴之美,或有蔬笋之气,或有春韭秋菘之味,终生心悦。饮食文字的写作,仿佛秘戏,有私密的快感。写其他文章,也有私密的快感,感受不如饮食文字深也。
人分妍与媸,吃有色香味。食物有绝色之表,人才生怜香之情。人有怜香之情,方存知味之心。《中庸》云“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可见知味不易。我认为,能知味者,非几十年的嘴上功夫不可,而要把食物的色香味立于文字,光靠嘴上功夫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笔下手段。
味道无法言传,这是饮食文字的难。将意会处录成文字,免不了自说自话、梦呓翩翩。忘了谁的笔记,说山里人不识海味,有客海边归来,盛赞海鲜之美,乡间人争舐其眼。此乃说味高手也。
发饭癫
新炒的蔬菜,冒着油光,米饭里拌了肉汤。我大哭不止,不肯吃饭。祖母说:“莫理,由他发饭癫。”咄咄逼人。
祖母生于一九三三年,历经沧桑,饱受磨难。一个人面对着白花花的米饭大吵大闹,在她看来,天理难容。
白色城堡
白色城堡,扭头可以看到,盘踞在桌子上。大块的白色,是她无边的心事。大块的白色,是她干净的想法。白色的身子散发着清香,有稻米的清香,蔗糖之甜香。
第一次看到丰糕,就认为她是米做的白色城堡:圆顶建筑,那圆顶的弧度圆润仿佛屋顶,四周是高而挺的墙。真舍不得吃。吃掉一个白色城堡!我又不是阔少,还没奢侈到那程度。只好摆放在那里,当秋天餐桌的清供。
每天上班,总要看她一眼,茕茕孑立的样子,却不寂寞。其实她还有一个伙伴的,我送人了。大清早能看到丰糕,寓意很好,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丰糕的丰是丰收的丰。秋天了,稻米入仓,做一点丰糕,瑞雪兆丰年呵,白色的丰糕是大地的瑞雪。丰糕的丰是丰满的丰,像财主独生的丫头,养得白白胖胖的,待字闺中,爱上了长工的儿子。
深夜。纸窗下两个剪影。跳动的烛光下传来一个苍老的女声:“这丫头实心眼得很。”末了,又叹了口气,“嫁给他以后日子怎么过?”这时一个苍老的男声说道:“慌么事?丫头眼光不错,那后生勤劳,嫁他不亏,老婆子莫管,我心里有数”。
丰糕上会写上字,“新春大吉、寿比南山、万事如意、富贵吉祥”之类。我的丰糕是无字丰糕,上面撒有红丝,那红红得朴素,红得不动声色。
去桐城玩,朋友送我两块丰糕。丰糕的名字,有村野的富贵气。王府的富贵气不稀罕,村野的富贵气才富得饱满,贵得真实。
丰糕,米做的糕点——以米粉、白糖蒸制而成。可蒸食,油煎,泡汤,不一而足。我的丰糕该怎么吃呢?看看再说吧。
桐城丰糕像桐城文学,大块文章啊。
松花饼
松树开花了,黄灿灿如马尾挂满枝头。在山里走得久了,风吹过,头面有松花的气息。将松花晒干掺糯米粉做饼,蒸熟即食,是为松花饼。
松花饼颜色颇好,像桂花糕,淡淡的嫩黄,仿佛夏日鳜鱼游过溪流,水底倒影绰绰斑驳,心境一时舒朗。松花饼不算佳肴,但得了谷物的滋味也有山林的野趣,糯米的甜腻中一股馥郁的松香,如云在野,轻逸悠悠。
宋人林洪喜欢松花饼,说用其佐酒,心头洒然起山林之兴,驼峰、熊掌也没有那等风味。读书人风雅如此,是颜回心性的一记回声。宋朝做松花饼与今人不同,掺入蜂蜜,状若鸡舌、龙涎,味道香甜。
前日吃得一回松花饼,有旧味也有自然风韵,一时也多了林下之思。
松花味甘,性温,益气,主润心肺,除风止血,也可以酿酒。松花酒没有喝过,我沾酒立醉,友人越醉越喝,不独是宋人风味,更近似松下的魏晋人了。
责任编辑惠靖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