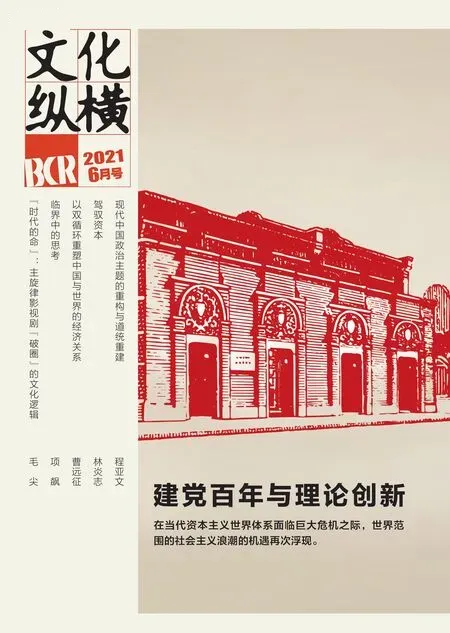回归革命史观*——《觉醒年代》的史观转向
本刊记者 董牧孜
继《大江大河2》《山海情》等主旋律电视剧赢得收视、口碑双收之后,革命历史剧《觉醒年代》也火了。这部呈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创建全过程的电视剧,在网上被年轻观众不断催更,并登上微博热搜。一部主旋律献礼剧能够在大众尤其是年轻人中成为流行“燃剧”,这种意料之外的影响力堪称“破圈”。2021年4月6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围绕《觉醒年代》组织了一场聚谈,本文围绕《觉醒年代》展开的历史观讨论,受益于罗岗、周展安、毛尖、倪文尖、孙晓忠、王锐、林凌、萧武、张炼红等师友的观点。
《觉醒年代》讲述了从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的6年,它通过塑造出新文化运动中一群我们耳熟能详的个体形象,呈现了一场完整的思想运动。它不但“活化”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干将的身影,而且,也叙述了新文化运动中那些相对保守的学人是如何思考文化和文明的重建。《觉醒年代》这部电视剧的特点,正在于它是通过塑造新文化运动中代表性人物的形象,还原当时的思想场,处理复杂的历史事件与思想脉络。也许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觉醒年代》略让人觉得单薄,但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对于历史的呈现,不仅留下某种属于大众的历史性痕迹,也在讲述历史的同时创造新的价值观。
《觉醒年代》如何呈现一场思想运动?
正如王奇生在《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一文中指出,《新青年》在当时非但不是什么名刊,反而经历过很长一段惨淡经营的时光。这种状况直至陈独秀来北大任教,《新青年》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之后才有所改变。[1]
但作为大众文化作品,《觉醒年代》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它对史实是否绝对忠实,而是它以极具艺术表现力的手法,通过场景的还原、人物的行动与思想的讨论,将新文化运动的人物群像,呈现于时代的大思潮中。在电视剧中,我们今天称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三股思潮,始终处在动态的角力之中,体现出五四前后政党政治、大众运动和战争条件下文化运动的独特性。
《觉醒年代》大致用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再现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在知识分子群像中,“相约建党”的陈独秀与李大钊,是展现知识分子走向20世纪激进革命的绝对主角,胡适则代表了反对“救亡压倒启蒙”的精英声音,北大及其校长蔡元培在思想场域发挥的作用也被极力渲染,至于黄侃、刘师培则被误归为与辜鸿铭、林纾沆瀣一气的保守复古派。这其中,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工读主义实验被格外突出。在新文化思想场域的外围,则是对北洋政府官员如“辫子军”张勋的漫画式刻画,以及对农民苦难、麻木与工人觉醒等的呈现。
作为一部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特点在于它用细致的影像语言,耐心而又细腻地呈现出在五四的大时代背景下,不同思潮的分分合合,清晰地回答了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会催生出革命力量。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觉醒年代》较为浓墨重彩呈现的片段。电视剧将国内的行动与“巴黎和会”的进程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在极具运动感镜头的推动下,《觉醒年代》对“巴黎和会”的呈现,使新一代观众更直观地意识到世界大战及战后秩序重建对广大亚洲区域的深刻影响,不能再只寄希望于先进者与启蒙者的善意(如战后初期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对美国和威尔逊总统带来新秩序的热切期待),而应该对帝国主义秩序提出自觉性的挑战。五四运动并非只从属于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和文化运动,也是更广泛的亚非觉醒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浪潮中的组成部分。相比于之前影视剧中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描绘,《觉醒年代》的特殊之处,正是将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思想差异,呈现在这种世界与中国历史的剧烈变动过程中。正是因为它可以从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动态交汇中细腻而丰富地呈现新文化运动,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会由新文化同仁走向分道扬镳——胡适终其一生都将新文化运动视为一场文艺复兴,而事实上,五四时期的启蒙,更紧迫的任务是救亡。

《觉醒年代》呈现了五四大时代背景下不同思潮的分分合合
《觉醒年代》所呈现的这场思想运动的有趣之处,还体现在如何塑造反对派的形象与如何理解传统文化。这也是这部电视剧经常被人挑毛病的地方。比如,剧中被刻画为守旧派的刘师培,实际上并不那么“守旧”。刘师培的思想相当复杂,他在清末民初以政治立场多变而著名,先是鼓吹排满革命,继而宣扬无政府主义。刘氏时常利用中国古代学术中的乌托邦理想,来阐释自己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德里克也曾指出,晚清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更关注中国广大平民的苦难。[2]而人们印象中小辫长袍遗老形象的辜鸿铭,电视剧中虽然也是这般形象出场,但也强调他“生在南洋,学在东洋”,接受了完整的西方教育,其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可能比胡适更为深刻。在辜鸿铭身上,《觉醒年代》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新旧混杂性,他的传统复古思想借鉴自西方保守主义及浪漫主义资源,而他恰恰是以中国传统儒学的逻辑,来表达自己西方化的视角和价值追求。[3]虽说在电视剧中,复古守旧派和新文化派的分歧,往往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调和之下往“和谐”的方向发展,但《觉醒年代》在弥合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保守派的裂缝所做的努力,也让我们看到“新旧”之辨的艰难。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环境在趋新与守旧两端,“新派”亦非泾渭分明,更准确地说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新旧杂陈。[4]《觉醒年代》对于“新旧之争”的呈现方式虽然有点浪漫化了那段历史,但相较新文化知识分子激烈反对传统文化的姿态,它确实也反映出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当弘扬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流,在电视剧中,今人那种整体性的文化自信与五四新文化派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就会呈现出某种调和。
新文化运动中“启蒙与革命之争”“新旧之争”的思想现场当然远比影视作品所能呈现的人物动态更为复杂。尽管如此,《觉醒年代》依旧反映出了一场思想运动的内在张力和思想特征,尤其难得可贵的是,它作为一部电视剧,竟然可以全景式地以不同人物体现出“德先生”、“赛先生”、个人主义、激进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不同思潮,呈现出社会改造和爱国救亡的强烈情感。比如电视剧中对于陈延年等人以工读主义实验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呈现,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是一种别样的感受。尽管电视剧中强调了他们的俭洁食堂经营不善,自我改造的一腔热血最终不切实际,但工读主义思潮是要对几千年来中国士大夫的寄生性进行大胆改造,其背后构想未来的乌托邦力量,在那个左冲右突寻找出路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显得耀眼。

《觉醒年代》呈现了革命派陈独秀、李大钊如何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分道扬镳
《觉醒年代》反映了怎样的史观?
《觉醒年代》尽管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五四新文化叙事,着重精英知识分子主导的思想场域,但与前些年流行的“民国范”叙事仍然有显著的史观差异,简单来说,《觉醒年代》体现出精英史观、群众史观、革命史观之间的张力,它并不遵循“救亡压倒启蒙”的思路,而是回到了毛泽东的大历史观,即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将新文化运动也纳入其中。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与爱国主题对立起来的观点一度成为主流,其立场很切近胡适对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对立起来,认为是学生运动的兴起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终结。[5]这也是90年代“反思激进主义”的滥觞之一。“激进主义”不仅指涉学生运动,而且也指涉以五四为转折点的中国革命。“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无疑具有鲜明的“后革命”色彩,《觉醒年代》在这个意义上是回归了革命史观。在电视剧中,赵世炎、陈乔年等年青一代之所以会卷入新文化运动,恰恰是来自“一战”、中华民国的“共和危机”以及俄国革命等政治上的刺激,这使得文化运动的目标最终偏到了政治上,而激进革命运动是以建国为目的的。可以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这段时期的文化运动是没有指称的”[6]。
《觉醒年代》讲述的是建党前史,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然性,回应了中国为什么会走向社会主义。《觉醒年代》最为成功之处,是突出了大时代里一代知识青年的道路选择问题。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转向提倡社会主义,1920年9月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3~1926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觉醒年代》不只呈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主线叙事,也大篇幅地呈现出了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等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者的转变。陈延年等青年无政府主义者,在电视剧结尾出现时已成为牺牲的中共党员,这一身份的改变,也揭示出那个历史阶段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因应现实在思想与实践上发生了转向。
从历史过程来看,当时的知识青年,对于到底是追随胡适之先生还是陈独秀先生,是迷茫和有争论的。胡适主张的实验主义,在当时也是有吸引力的。客观上说,民国精英阶层与中国士大夫之间存在脉络延续,但“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信念有其内在限度。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以“中等社会”来界定20世纪初期出现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他们是上等社会皇权之外的知识者、工商业者乃至士兵等,是为改造乃至颠覆皇权专制出现的社会力量,并由此催生了新的知识阶层。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就出现在中等社会担任中国社会演变动力的历史延长线上。[7]
蔡元培等知识分子也推崇“劳工神圣”。当时突出劳工的概念,主要是因为“一战”中参战者只有劳工,是为了强调中国“战胜国”的地位。不过正如罗志田指出,“劳工神圣”出自蔡元培等名流之口,仍有较大的象征意义和影响力。《觉醒年代》也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意识到只有精英的文化启蒙是不够的,中国的救亡必须动员更广大的社会力量,动员更广大的民众。这其中李大钊的思想转变是较有代表性的。早期李大钊具有威尔逊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色彩,包括他对俄国革命的解释,其实一定程度上融合了欧洲革命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概念。[8]但正如剧中所述,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李大钊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对社会底层有了更多感知,而当时工人阶层的赤贫生活,也使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只有文化运动是不足的。通过这种社会意识的觉醒,一部分眼光敏锐的知识人意识到所谓上流社会和中流社会不足以堪当大任,需要眼光向下看到民众。
当然,群众史观的认识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经过上世纪20年代的发酵,1930年前后中国知识界掀起了“社会性质大论战”等一系列论战,社会各界出现了更切合实际的对中国社会的具体调查,比如1927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社会性质大论战对于新中国的革命建国至关重要,它消除了知识青年由于好学深思而容易带来的行动迷茫,中国未来的道路因此变得清晰。[9]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重新发现了中国农村、内地和边疆。尽管这已经溢出了《觉醒年代》所再现的6年时间,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观念和口号,以及投身和奉献的精神与热情,正是由此开始下沉,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具体层面。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落地的时期,也是《觉醒年代》中尚且较为模糊的群众史观得以明确和延续的阶段。
年青一代的史观转向
如果《觉醒年代》早几年播出,很可能不会流行,甚至招致差评。在过去二十余年中,官方表述与大众舆论经常处于分离的状态,官方叙事对社会大众来说往往缺乏经验性的、可感知的影响力。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脉络来看,在文艺作品中占据主流的往往是精英史观和“民国范”的美化想象,这种叙事对中国革命采取解构和消解态度,其叙事主体以文化精英为主。《觉醒年代》的“破圈”,恰恰是契合了这些年社会舆论风向的转变。正如周展安指出,一方面,如今享受国家发展红利的年轻人已成为爱国主义主旋律的自发扛旗者;另一方面,伴随社会发展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比如996、加班猝死、大公司垄断等,加深了年青一代对于资本主义的直观体验和认识,反过来也逐渐增进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认同。对于历史及生存现状的体认,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沉浸爱国情感的同时,也萌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兴趣——而二者的起点正是五四。

群众史观的认识建立并非一蹴而就
五四的政治结果是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独立自主的、不再受威胁和欺凌的国家,其文化结果是将社会思潮导向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觉醒年代》电视剧富有张力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知识分子的所思所为,但不再只是局限在文化人之中讲五四运动,它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进行了真正的联结,突出了青年人对理想的追寻,在陈独秀、李大钊等父一辈到陈延年、陈乔年等子一辈之间,建立了连贯的时代线索。应该说,五四青年的救国并非源于士大夫的朝堂意识,而是具有传统背景的精英突破传统,打破或改革旧的、狭隘的政教秩序,全面组织民众的崭新追求。[10]年轻人不再追求个人主义的小日子,而是走上为国为民奋斗、为更宏大的目标奉献青春的道路。这种革命与青春的结合对于年轻观众具有感召力量。
有评论指出,《觉醒年代》最大的问题是剧情分配不合理,1919年以前太拖沓,1919年以后太跳跃,认为电视剧应该多讲北大之外的故事。[11]不过《觉醒年代》作为建党前史所呈现的“觉醒”,更多是讲述中国士大夫阶层逐渐在一场思想运动中生发出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不同的觉醒与道路倾向,以及为什么社会主义最终会成为时代的主流。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共和危机之下,知识分子突然意识到19世纪末期以降被视为楷模的西方模式突然失去了自明的先进性,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并不是造成民族危机的唯一替罪羊,与此同时,俄国革命开启了理解西方历史的新契机。正如剧中借毛泽东之口对陈独秀的追问:“您真的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落后的文化传统问题吗?”陈独秀对此的回答是,“中国落后的不是文化,而是缺乏指导社会持续发展的科学理论”。不论是抨击中国的旧文化,还是拥抱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都是为着“不破不立”,寻找新的道路。
今天的观众,以及作为历史后来者的我们,同样面临当代的“觉醒年代”。今天我们同样面临深刻的世界性危机,疫情加剧了全球风险治理的困难,很多国家共同面临发展停滞、人口危机及气候危机等困局。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美国的理想形象也不复存在了,贸易战、民粹主义与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打碎的不只是美国梦,也是很多人此前对于“灯塔国”的理想投射。
可以说,是这些年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变化教育了中国人。正如丁耘指出,今天中国社会面临崭新的挑战:“现在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单独的资源能去应对目前这样一种复杂的内外危机。儒家传统没有遇到过宗族解体之后的社会;资本主义传统没有遇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长期执政,扶持、引导并且规范民间资本的共和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没有遇到过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由主义者也没有遇到如此广泛复杂的世界体系危机。”[12]
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的形态、党本身的形态以及中国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但《觉醒年代》的历史时刻仍然能为我们提供思想资源和能量。20世纪曾经产生过一种具有高度能动性的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迸发出自我创造的机会,这些选择不是被动的,也不是个人化的,我们创造自己的政治,个体生活都被组织到集体之中。如今,我们需要吸收能接触的一切思想,全面地调动、综合这些资源,使之在我们的头脑中组织成相对完整的体系以应对当代的危机。就像丁耘所说:“希望中国的未来,是在一些明智的青年手中,他们会对中国的传统(包括古代传统与革命传统)带有温情和敬意,带有冷静的思索和自信的肯定。……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现实,态度要从容,需要谨慎、勤奋和耐心。”[13]
注释:
[1]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 刘师培1907年提倡成立“农民疾苦调查会”,写成《农民疾苦会调查章程》,组织调查农业生产基本状况和农民疾苦。他在发现无政府主义政治立场难以践行后,开始转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参见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2~94页。王锐:《“病民之根”——刘师培对代议制的批判》,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3] 史敏:《辜鸿铭研究述评》,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4] 罗检秋:《五四新文化与晚清学术传统》,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5期。
[5] 罗岗:《五四:不断重临的起点——重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汪晖:《再谈五四:以文化运动为方法》,载《东方学刊》2019年第1期。
[6] [12] [13]丁耘:《文化的“五四”与政治的“五四”》,载《文化纵横》2009年第3期。
[7]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周展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扎根的逻辑与特质》,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
[8] 罗岗:《霸权更迭、俄国革命与“庶民”意涵的变迁——重返“五四”之一》,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 周展安:《“现实”的凸显及其理念化——对“五四运动”思想与文学内在构造的再思考》,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3期。
[10] 丁耘:《从“两个三十年”到“三个三十年”——纪念五四运动 95 周年》,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4月25日,第A04版。
[11] 傅正:《〈觉醒年代〉如果多拍北大之外的故事,会更好》,观察者网,2021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