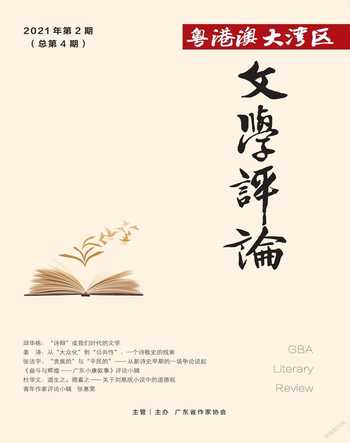论张惠雯近期小说中的母亲书写
陈翠平
摘要:美国华裔作家张惠雯的小说以短篇为主,承接现代主义小说传统,题材广泛,风格多变。继寓言小说《水晶男孩》引起国内评论界关注后,2018年又在国内出版了最重要的小说集《在南方》。在近年来散见于国内报刊的小说中,张惠雯较为集中地书写了母亲形象。《沉默的母亲》以互不相识的三个母亲的故事揭示女性生育后的困境,《二人世界》进一步探讨女人在生育之后如何与男性区分开来,与孩子形成核心世界,《飞鸟和池鱼》则探讨成年儿子与衰病母亲之间的关系,三个短篇相互指涉,探询着关于母亲的存在之思。
关键词:张惠雯;母亲书写;《沉默的母亲》;《二人世界》;《飞鸟和池鱼》
一、致敬传统和经典的写作
张惠雯1978年出生于河南省西华县,其日后关于这个县城的回忆让人想起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对故乡小城的描述。“它的中心是一条南北街和东西街的交叉口,当地居民称它为‘十字街口’。这条南北街和东西街之所以被称为大街,因为路面上铺着一层已经坑坑洼洼、处于半毁损状态的柏油。”[1]张惠雯先是通过高考进入山东大学,继而于1995年获新加坡教育部奖学金赴新留学。异国求学期间的孤独和乡愁,使张惠雯寄情阅读和写作,并最終以此为毕生的志业。
张惠雯不追逐名利和热闹,始终按照自己的标准和节奏,通过不同题材和风格的作品去抵达乃至穿透人的内心世界。张惠雯在散文集《惘然少年时》中坦承自己信奉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创作观和批评观。艾略特认为作品最好的以及最个人的部分源于不朽的传统,而传统必须经过很大的努力才有可能习得。[2]文学并非一味地标新立异,作家只有在和前人的联结和对照中,在对历史和当下有着清醒而敏锐的认知时,才有可能使自己的创作成为经典。张惠雯在各种访谈、创作谈和随笔中,多次提到自己阅读沈从文、鲁迅、契诃夫、福楼拜、詹姆斯、卡夫卡、福克纳、昆德拉、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库切、帕慕克、博尔赫斯等作家的经验及受到的影响和启发。在这个主要由西方现代主义经典构成的文学传统中,张惠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审美取向:淡化情节,注重细节,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且明确了自己对于短篇小说的偏爱。
早期的《古柳官河》接续沈从文的风格,以美好诗意的笔触书写理想化的乡土生活。稍后得到余华赏识并获“新加坡国家金笔奖”的《水晶孩童》致敬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写艺术和美受到伤害的寓言故事。《垂老别》题名取自杜甫同题诗歌,写年老体衰的王老汉被两个儿子视为累赘,最终选择独自流浪的凄凉悲伤。受屠格涅夫《三次相遇》和亨利·詹姆斯《四次相遇》的启发,张惠雯写了《两次相遇》,讲述一对小城男女在两次相遇的五年间,从生动、纯真、热情,变得黯然、呆滞、乏味。《暴风雨之后》让让人想起张爱玲的《封锁》,写一对男女在暴风雨中的汽车内怦然心动,却在下车后形同陌路。从这些例子中,不难看出张惠雯向传统和经典致敬的态度,她也不讳言自己经常从阅读中获得创作的灵感。她不仅在创作谈中坦白自己的灵感来源(如《水晶男孩》),也会在作品前以引文的方式直接给出线索,一如曹禺在《日出》前引用老子《道德经》和《圣经》中的话,《怜悯》开篇引用奈保尔《花炮制造者》中的句子,《绳子》开篇引用左拉的话,《心曲》开篇引用席勒的话,《路》开篇引用《圣经·马太福音》里的话,等等。
张惠雯小说的题材和主题十分广泛,既有《水晶孩童》《空中图书馆》等寓言小说,也有《古柳官河》等乡土小说,既有收录于《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中的书写各种情感的小说,也有《垂老别》《我们埋葬了它》《怜悯》《绳子》等进行伦理和人性拷问的小说。她的小说中既有《如火的八月》《良民周三》中的底层民众,也有《欢乐》《醉意》中的中产阶层。在《相伴》《安娜和我》等小说中,动物以及动物与人的关系成为书写的主题,《安娜和我》更是虚构了异邦印度中一个人和一头象相伴一生的动人故事。
自2013年移居美国后,张惠雯自然而然地开始了移民题材的书写。这些小说多以美国南方城市休斯敦为背景,后来收入小说集《在南方》。小说集中的《夜色》写珍妮丝找了个黑人男朋友,父母极力反对。珍妮丝意识到:“在美国存在着这样一群像她母亲这样的人:他们最怕白人歧视自己,为此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却尽力地歧视着其他肤色更深的人。”在这个短篇中,张惠雯既写了华人移民家庭的代际冲突和观念分歧,又反思了华人在种族问题上自相矛盾的态度,表现出一种历史的眼界和世界的格局。
小说的素材可能“来自感官所及的现实,来自逐年载记的历史,来自生活经验,来自想像,来自神话,来自传说,来自新闻,当然,也来自其他(前行者的)作品”,[3]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移居美国后,张惠雯成为母亲,她在《在南方·后记》中写道:“你有了可不假思索为之牺牲的沉甸甸的爱,但日常琐碎的重压、自由的丧失也会令你烦躁焦虑、脾性大变,这其中的矛盾、居家主妇的抑郁,也是我为人母后才明白的事……总之,生育后,人会意识到诸多事理和真相,生活会向你呈现另一面貌。这些新的认识日后都会渗入我的写作。”的确,从近几年散见于国内刊物的小说来看,张惠雯明显对和母亲相关的材料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并有了相比之前更为集中和深刻的书写。
二、关于母亲的神话与现实
创作于2014年的小说《华屋》讲述了静姝和静怡两姐妹的故事。两家在较好的社区合买了房子,“每栋华丽的房屋仿佛一座岛,人们在自己的岛上自给自足、自成一体”。封闭沉闷的华屋之内,姐夫对妹妹偶然心动的出轨情事不过是死水微澜,更为惊心动魄的则是姐妹人生的空虚。只有姐姐和外甥在家的夜晚,她凑到他耳朵边用唱歌般的调子说:“只有我们俩,只有我们俩,宝宝才不会跑,这是我们的家……”故事结束在这个乍看平淡、细品惊悚的场景之中。姐姐日复一日的家务劳动没有得到尊重和回报,养育成人的儿子形同陌路,进入中年的丈夫失去激情,只有天真幼稚的孩子依恋着她,填补着她的空虚,于是她紧紧地抓住这个孩子,第二次做起母亲。妹妹受过高等教育,却不想工作,整日睡觉、购物、打扮自己、逛街、吃饭。她任由姐姐替自己照顾孩子,用丈夫的钱消费,以自己的“女性魅力”为生存资本,懈怠、麻木地生活。从本质上说,这对姐妹并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说《华屋》侧重揭示两姐妹孤独、空虚的生存本质,发表于2018年第5期《江南》的小说《沉默的母亲》则试图替沉默的母亲发出声音。长期以来,母性被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被推向神坛,究其实,“‘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4]随着网络的普及,产后忧郁症、育儿焦虑症等名词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当生育成为可讨论的问题,这本身就意味着看见,看见总是有意义的,看见是改变的起点。《沉默的母亲》让人想起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韩国作家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及日本作家角田光代的《坡道上的家》,虽然艺术上的构思和表现各不相同,但这些作品都在揭示作为母亲的某种真相。
在《沉默的母亲》中,张惠雯讲述了三个互不认识、互不相干的母亲的故事,以审视并探询“母亲”这个主题词下包含的问题。昆德拉曾说:“我觉得短小的章节各自形成一个整体,促使读者停顿、思考、不受叙事激流的左右。在一部小说中有太多的悬念,那么,它就逐渐衰竭,逐渐被消耗光。小说是速度的敌人,阅读应该是缓慢进行的,读者应该在每一页,每一段落,甚至每个句子的魅力前停留。”[5]昆德拉的看法正可对应于张惠雯这篇小说的阅读。
小说的第一段题为“沃克太太”,这个称呼点出了女主角的华裔身份。本是广西一个小城市的初中英语老师的李霞,27岁时因跨国婚姻成为沃克太太。“她其貌不扬,身材很瘦小,像是没有发育成熟的女孩儿。她说话细声细气、磕磕绊绊,说话时几乎不好意思直视对方,但在沃克先生眼里,她自有几乎不复存在的顺从、贤良的古典妻子的魅力。”度过婚后最初几个月的悠闲生活后,她开始完成沃克先生“多生子嗣、创建美好大家庭”的梦想,八年生了三个孩子。她无法融入邻里妈咪圈,“因为她看起来那么被动、怯懦,像一只容易受惊吓的麻雀,连她的发型、衣着都给人一种垂头丧气的感觉。对她们来说,她实在既无魅力也无亲和力可言。”邻里妈咪的印象和沃克先生的印象相互呼应,其中的反讽跃然纸上:沃克先生需要的不过是一个顺从的生育机器。对于沃克太太而言,迫切的并不是身份认同的问题,这和白先勇在《安乐乡的一日》中的处理有着明显的不同。在白先勇笔下,“她们生怕依萍不谙美国习俗,总争着向依萍指导献殷勤儿,显出她们尽到美国人的地主之谊。这使依萍愈感到自己是中国人,与众不同,因此,处处更加谨慎,举止上常常下意识的强调着中国人的特征。”对依萍来说,构成困境的是她的华人身份和中西文化冲突,而非她的主妇身份,因为她“在国内是学家政的,她一生的愿望就是想做一个称职的妻子,一个贤能的母亲”。作者以简单至极的一句话,略去了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可能面对的困境。《安乐乡的一日》发表于1964年10月的《现代文学》,而此前不久的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版了揭示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困境的《女性的奥秘》。
回到发表于2018年的《沉默的母亲》:“沃克太太不太为没有朋友这种事困扰,因为她真的忙不过来”,泵奶、做饭、哄睡、陪玩、买菜、做饭、搞卫生,“每天在单调琐碎而又永无休止的家务和吵闹的孩子们中间晕头转向”。有时,她会想:“一个女人的生活是否本该这样,还是应该有别的乐趣或意义?”沃克太太没有意识到偶尔浮现又被她刻意抛开的问题,恰恰是《女性的奥秘》开篇提出的那个著名的“无名的问题”:“这一问题埋在美国妇女的心底,无人提及,已经有许多年了。这是美国妇女在20世纪中叶所经受的一种奇怪的躁动、一种不满足感、一种渴求。……她甚至不敢在心里对自己发出无声的诘问:‘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6]半个世纪过去,女性的处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在沃克太太这里,处境甚至更加恶劣。沃克太太的问题不仅在于无法进入公共空间实现自我价值,更在于易卜生在1879年的戏剧《玩偶之家》中揭示的女性困境。
如果说娜拉是玩偶,沃克太太就是工具,压倒沃克太太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经济上的依附性。鲁迅在1923年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和1933年的杂文《关于妇女解放》中反复提及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要性,沃克太太花了八年时间终于领会到了。在两人的关系中,沃克太太不能为任何事做主。结婚时,婚宴的钱由女方出,男方只负责购买钻戒。生育时,沃克先生不同意岳母来半年帮忙照顾孩子,只让他自己的母亲来帮忙一周。岳父需要做手术,沃克先生不肯出三万人民币。沃克太太终于醒悟:“在这个家里,她没有任何决定权,这里的什么都不属于她,她在这里的意义就是生养一个又一个孩子!”心如死灰的沃克太太生病了,她不吃饭,只在一个人的时候狂吃滥嚼各种垃圾食品,以填充内心巨大的空虚。
小说的第二段题为“水族馆的一天”,讲述“我”和丈夫周末带一岁多的宝宝去水族馆的经历和心情。作者以水族馆里的鱼来比拟困在家中的母亲,“困在小小的天地里,游来游去、转来转去,仍然还在那里。”在这个故事里,女人的生活以生育为界限分成了两个世界,她们由灵动的女孩变成了进退两难的母亲。正如卡斯克在非虚构作品《成为母亲》中所说,“孩子的出生不仅将女人和男人区分开来,也将女人和女人区分开来,于是女性对于存在的意义的理解发生了巨变。”[7]一方面是“我”成为母亲后的变化:来不及化妆,衣着宽松,不修边幅,不再穿裙子,不穿浅色的衣服,不能每个周末去餐馆、电影院剧院、酒吧、咖啡馆、朋友家;另一方面是“我”和他的对比,他继续每天离开家去上班的生活,像一只准备飞向自由的鸟,“我”则是留下来陷入琐碎日常的那个,像玻璃罩里的海马。卡斯克分享自己成为母亲后的体验:“我渴望获得自由,生孩子前我也许有过却没有珍惜的自由。于我而言,母性是一座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围城”。[8]最无奈的是,母亲们已经无法重回过去的自由生活,有了羁绊的母亲,只能继续爱、忍耐,以及等待。
小说的第三个片段即《沉默的母亲》,这个故事中的母亲已经因为育儿忧郁症自杀,无法在故事中发声,只能成为一种“沉默”的存在。作者以“沉默的母亲”为小说总题,象征着社会对母亲群体处境的盲视。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的儿子,在父亲的讲述和旧照片中試图还原母亲在成为母亲后的处境。儿子的缺憾和父亲的追悔构成了故事的基调,“但在当时,他没有时间去了解她的问题,也没有想到要去了解。”2015年完成的小说《十年》同样以男性的追悔为叙述基调,丈夫离开临产前的妻子独自去南非做生意。“在想象中,她总是抱着女儿在那小小的厅里来回走动,轻轻摇晃着,唱着歌,而那婴儿总是哭泣着。这是他从电影里看到过的镜头,不知道为什么,它倒给他一种安宁祥和的感觉。”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他的这个浪漫化想象真是一个不动声色的绝妙讽刺。男性主动或被动地隔绝于养育生活之外,女性则从一个无忧的少女变成一个需要无所不能的母亲。在这个故事里,作者巧妙地隐藏了母亲生活的细节,父亲多年后的追忆充满了大片的留白。这种留白既呼应题目中的“沉默”,又予读者以想象和思考的空间。三个故事讲述三个母亲,她们虽互不相识,却共享了相同的经验。她们在生育之后,得不到社会和伴侣的支持,独自面对繁重的家务和育儿责任,成为无法实现自身价值、失去个人自由的母亲。重压之下,她们都患上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甚至选择自杀。作为小说家的张惠雯提出了问题,她没有给出答案,但给出了思考。
三、母子关系的形成与倒置
孩子出生后,父亲继续外出工作,母亲留在家里照料孩子,这样的分工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沉默的母亲》给出了思考。似乎意犹未尽,张惠雯在《收获》2019年第2期上发表的小说《二人世界》中,续写了《水族馆的一天》中的故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更为复杂的勘探。小说同样写到成为母亲后的变化:家务、育儿、不修边幅、没有自己的时间和自由,甚至出现了产后忧郁的症状。但和《水族馆的一天》相比,母亲的心态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她不再羡慕女孩,不再渴望回到过去。“女性魅力”这个词甚至会让她涌起些许轻蔑感,更重要的是,她开始体会到陪伴孩子的快乐,“她从一个烦躁幽怨甚至刻意冷漠的母亲变成了一位心甘情愿的、坚定的母亲”。精神分析领域有诸多关于孩子和母亲关系的论述,这些理论大多着眼于儿童的心理发展,张惠雯则是从母亲的角度出发,探讨以母子为核心的微型世界形成的过程。
生育之后,“丈夫对她来说即使不是变得无足轻重,也已经处于仅仅环绕她的那个核心世界之外了。对她和儿子来说,他有时就像个外人。”作者甚至不惜冒犯道德,为她安排了一个情人,以证实母子之间不容任何第三者介入的强大联结。不论是丈夫还是情人都不能理解她作为母亲的经历,她感觉与他们之间产生了永久的隔膜。和情人分手,对性爱冷淡,“但这难道是她的错?她的身体曾爆炸般地膨胀,而后它猛地缩回去,变得松弛、干燥、过于平静,像冬眠的土地。她不再善感,这的确让人悲哀,而男人不了解这些,又增加了一层悲哀。……他们不明白,总有一天,柔媚的女性会像漂亮光彩的羽毛一样从她身上褪去,宽厚、强韧的母性取代了它,这和万物生息、生命更迭一样自然、无法抗拒。”如今,她的世界变小了,小得只剩下母亲和孩子,但她却甘之如饴。波伏娃指出有的母亲会以受虐式奉献来弥补自己的内心空虚,而包括张爱玲《金锁记》在内的很多文学作品都曾描写过母亲和儿子之间畸形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大多表现为母亲对孩子强烈的控制欲。张惠雯的描写没有先入为主的理论和观点预设,而是近于一种田野观察:怀孕和生育带来的身体变化导致的性欲减退,和孩子日复一日的亲密相处催生的情感体验,以及放弃公众价值后生成的私人意义。
看到“二人世界”这个题目,读者的心理预期通常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作者有意造成读者的“误会”,并在故事的推进中加入生育前已在交往的男友这个角色,使得悬念和误会再次发生,直到小说的后半段才点出题目中的二人世界指的是母亲和儿子。从艺术性的角度看,在一个容量有限的短篇中制造出连续的误会,足以见出作者巧妙的构思和良好的节奏控制能力。从思想性的角度看,这样的反转也带动读者的思考:何以如此?如此这样正常吗?合理吗?随着孩子的长大,这样的二人世界又会怎样?这样的思考或许正是基于张惠雯有意经营的留白和隐藏。
熟悉张惠雯的读者可能会想起,她此前的作品也曾深浅不一地描述过成年后的孩子和母亲的关系。《华屋》中的儿子到外地读书后,与父母形同陌路。《维加斯之夜》中那个计划在维加斯结束童贞的男子在心里对母亲冷笑:“你的‘小’儿子已经三十八岁了”,你却永远只会在电话里唠唠叨叨地问他吃饭如何。《欢乐》中的男主角在欢乐的聚会中回忆自己与刚去世的母亲从亲近到疏离的关系。他来美国二十年,两三年才回去看一次母亲,每次不超过两个星期。二十年来两人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是母亲来美国和他同住了三个月,而这三个月双方相处并不愉快。“这大概就是一个女人和她儿子的故事,他长大了,她老了,他想离开她、摆脱她、甚至无法再爱她。”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长大的儿子和老去的母亲之间的故事是从儿子的角度讲述的。吴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及柯勒律治的“雌雄同体”,并说:“任何写作者,念念不忘自己的性别,都是致命的;你必须成为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9]而张惠雯亦曾说过:“我有时候不知不觉地就从男性的角度去写了,并且觉得这样做十分自然。”“如果说我的内在里也存在着一位男性,他也是个对女性尊重、具有同情心的男性,他不折不扣是由最富同情心的文学培养出来的男性。”[10]
无论是自觉还是不知不觉,在发表于《江南》2020年第2期的小说《飞鸟和池鱼》中,张惠雯仍然以男性视角讲述了成年儿子和衰病母亲之间的关系。写作时间相近的《二人世界》和《飞鸟和池鱼》,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解读为一次母子关系的倒置书写。“我们两个倒换了角色:前三十年,我是她的孩子。现在,她是我的孩子。”两个故事中的父亲都是缺席的,《二人世界》中的父亲整天上班,《飞鸟和池鱼》中的父亲已经去世。
从小学开始,儿子便致力于离开小城,到更好、更广阔的地方去。但在广州读书、生活了将近十年之后,因为母亲身体的衰老和精神的疾病,儿子只能“回到这个小地方,就像我不曾走出过,就像过去的那些年,我付出的努力、得到的一切不过是徒劳地转了一个圆圈,最后,起点和终点重叠在一起。”这个比喻让人想起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吕纬甫自嘲从年轻到中年,像个绕了一点小圈子又飞回来的蝇子。“五四”落潮后的知识分子活成了自己年轻时所蔑视的模样,吕纬甫的悲剧有时代、社会的因素,也有个人的生存困境。对于《飞鸟和池鱼》中的儿子来说,这个困境就是母亲的衰老和疾病。张惠雯不仅点出了这个困境,更在这个困境中试图探讨母亲和儿子更深一层的关系。母子关系形成于儿子的幼年期,又在母亲老迈的时候,以倒置的方式重现,人生由此形成一个闭环。
飞鸟和池鱼既是儿子的两种状态,也是母亲的两种状态。母亲和儿子都向往飞鸟的状态,但又因为对方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成了池鱼。不堪重负的儿子曾一瞬间闪过任由已然成为负担的母亲坠楼的念头:“她这次可能真的像鸟儿一样飞走了”,但他毕竟“猛然惊醒过来”,拉住了那双“干燥、皱巴巴但温热的手”。“我感到心脏重新在我的胸腔中平稳地跳动。现在她再也飞不走了,我抓住了她,抓的很紧、很结实。我和她又连在了一起,无论是身体还是命运……这比什么都好。” 虽然一再探询人性的阴暗幽微与惊心动魄,但张惠雯的底色毕竟是温情和悲悯的,这使得她的作品自有一种平和的力量。
从初为人母的焦虑紧张到母子亲密关系的形成,从母子疏离再到母子重新建立联结,这其中的种种心境与情感,张惠雯都有细致的观察和呈现。她近期关于母亲的书写,既揭开了成为母亲的现实和真相,也探讨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相爱相杀的复杂关系。张惠雯通过艺术的方式,试图抵达的仍然是不同人的存在之思和意义探询。
[注釋]
[1][ 10]张惠雯:《惘然少年时》,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版,第1页、第171—176页。
[2][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卞之琳、李赋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3]张大春:《小说稗类·卡夫卡来不及找到——一则小说的材料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
[4][日]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
[5][英]乔·艾略特等:《小说的艺术》,张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6][美]弗里丹著:《女性的奥秘》,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7][8][英]蕾切尔·卡斯克著:《成为母亲》,黄建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第2页。
[9][英]弗吉尼亚·吴尔夫著:《一间自己的房间》,贾辉丰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25页。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