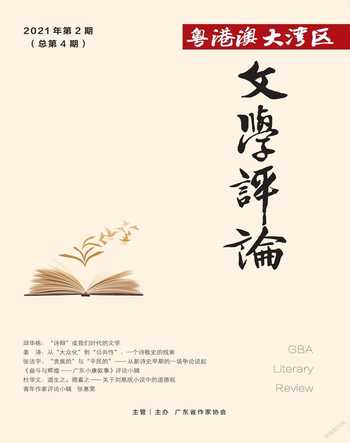从“大众化”到“公共性”:一个诗歌史的线索
姜涛
摘要:左翼文学视野中新诗“大众化”的展开,依托于革命的动员政治和对印刷文化的自觉扬弃。在当代语境中,由于强力革命政治的缺席,当代诗的写作和阅读又落回新诗现代化的传统中,虽有传播、接受方面的争议,但“大众化”问题或许并不迫切。相比之下,当代诗对公共性议题的卷入,倒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如何突破个体或群体的既有感知框架,在与他人及社会的有效联动中,获得深厚的社会感,也是重建当代诗公共性的一个难题。
关键词:大众化;公共性;诗与公共世界;当代诗
有关新诗大众化的讨论,似乎是一个相对陈旧的话题。“大众化”的提倡,虽然出自左翼文学的立场,但从新诗的发生之日起,新诗就包含了开启民智、“情动”社会的诉求。所谓 “平民”与“贵族”、“看得懂”与“看不懂”、“普及”与“提高”的张力,也反反复复,贯穿了新诗的历史展开,早已沉积为新诗史内部一种常态的问题结构。而且,相关的研究已很充分,如继业兄的著作《新诗的大众化与纯诗化》,就立足原初材料的考掘,深入檢讨过“大众化”诗学脉络及其与“纯诗化”诗学的互动。如今重提这个话题,在我看来,可能要考虑如何挣脱原有的讨论框架,从更整体性的视野出发,探讨一下“大众化”历史起落的若干前提。比如,为什么要“大众化”?其目的和现实指向是什么?大众化得以展开,依托的媒介形式是什么?
从某个角度看,“五四”时代白话新诗的出现,是近代以来文化“下沉”社会、传统士大夫文化衰落的结果。新诗不仅是白话的、自由的诗歌,也应该是平民的诗歌,早期白话诗质朴的社会写实,以及北大诸公对民间歌谣的兴趣,都大致体现了这样一种文化民主的理念。不能忽略的是,新诗同时也是现代都市文化兴起的结果。与旧诗相比,新诗主要是一种朝向“发表”的诗歌,其写作、传播和评价的机制,离不开报刊传媒的发展和读者大众的生成。这里的读者大众,以城市知识分子、部分市民以及青年学生为主,并不包括后来左翼文学所发现的“工农大众”。与此相关,虽然有“普遍与真挚”的文学想象,但新诗也主要是一种“内面自我”的表达,奠基于“个人的发现”一类现代性文化。普遍的共同体意识与个人化的书写“装置”,二者实际上有所矛盾。20年代初发生在俞平伯、周作人、梁实秋之间的“平民”与“贵族”之争,就是这种矛盾的一次显现。比如,俞平伯倡导“诗底进化还原论”,认为“平民性”是诗的本真质素,只不过被后来的贵族色彩遮蔽了,所以“进化还原”即是一种返本归真、“把诗底本来面目,从脂粉堆里显露出来”的过程。在他的表述中,“平民”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民众、大众,更多是一个发生学意义上文学普遍性的指称。
事实上,到了30年代,诗歌大众化问题的提出并变得迫切,并不是延续“五四”时代平民主义、文化民主的构想,恰恰是要超克“五四”的逻辑,依托于新型的政党政治、革命动员政治,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在革命政治提供的视野中,“大众”也不再是笼统的、不分阶层的“平民”,而是需要被唤醒、组织的工农;“大众化”追求的也不单是文化的普及,而是动员的武器,为的是将“无声的中国”转为“有声的中国”,强力构造集体性的经验,从压迫中翻转出反抗、觉醒的力量。
包括诗歌在内,文艺如何对大众说话,进而让大众自己说话,创造出自身的文艺,是左翼大众化的核心命题。这也涉及另一个前提,即诗歌大众化所依托的媒介形式、传播方式、以及诗文体的功能。最近出版的《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一书,就从“听觉”和“身体”的角度,对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歌谣化”实践进行了饶有意味的讨论。作者康凌指出“中国诗歌会”所尝试的路径,是从民间歌谣小调中挖掘劳苦大众最为熟悉、适应的身体节奏,以“自然”的方式触动大众的身体记忆和生理回应,塑造其听众/读者的集体性身体感知,从而起到组织、动员的功效。当“听觉”与“身体”的激荡,相对于“视觉”和“大脑”的理智,取得了更大的优势,这也意味着新诗媒介的转换:如果说“五四”以来的新诗是写的、发表在报刊上,依托文字书写和印刷媒介,供读者去阅读、去沉思默想,那么大众化、歌谣化的“新诗”,则是听的、唱的、诉诸劳苦大众集体性的身体经验。抗战时期兴盛的朗诵诗,延续了左翼大众化的脉络,同样具有强劲的跨文体、跨媒介的意识,在听觉、节奏和身体的互动之外,还引入戏剧艺术、广场艺术的形式,让新诗进一步成为可以表演的、行动的艺术。在李广田、朱自清等批评家看来,这样一种“行动的诗”,打破了印刷文化的限制、向公共世界敞开,其实已不再是过往的“新诗”,而是一种“新诗中的新诗”。
依托动员型的革命政治,扬弃印刷文化和口头文化的差别,最终指向群众文艺的“大众化”实践,在“大跃进”时代的“新民歌运动”中达到了高潮,同时也将内在危机全面引爆。伴随了一系列“告别革命”的社会转型,这样的“大众化”在当代诗人和批评家这里,自然已不大会被认同,甚至会被认为是五四新诗传统一种偏离。“不认同”也说明,当代诗似乎又落回新诗的“常态”之中。诗人的群落虽有所谓“地下/地上”“官方/民间”的分别,但无论“作协”系统的老派抒情,还是“诗江湖”上的莽汉先锋,诗歌的写作和阅读,大体上说还是回到“文学现代化”的轨道上,以个人化的内在体验和语言创新为前提。当激进的革命政治逐渐消退,诗歌也不再可能承担动员社会、组织大众、塑造政治共同体的功能,被“边缘化”的命运不可逆转。相应的,当代诗阅读与接受,重又收缩到文艺青年和城市小资或中产阶级的圈子中。这个圈子不大,却也相对稳定,刚好配合了当代文化消费多样性的景观。当然,今日亦如当年,有关诗歌远离读者、不够“大众化”的质疑和焦虑,仍挥之不去,时不时也会激起讨论的声浪,但这里的读者大众,与左翼文学视野中的需要被唤醒并创造自身文化形式和领导权的“大众”,内涵早已迥异。美国学者江克平多年前曾用“从‘运动’到‘活动’”的说法,来概括当代中国朗诵诗的流变。这是一个简单也有效的概括。
贸然做一个判断的话,由于“大众化”依托的文化政治前提已流失或转变,在当下的语境中,虽然诗歌传播、接受问题仍然存在,但“大众化”问题或许并不突出、也不迫切。因而,要谈论当下诗歌与社会接受、公众阅读的关系,可能有必要转换一下考察的视角、框架。1940年,朱自清翻译了美国诗人阿奇保德·麦克里希的《诗与公众世界》一文,借此传达对诗歌之时代处境变化的感知。这篇文章探讨了私人情感、经验在现代历史中不断公共化、政治化的趋向:
我们是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在这时代,公众生活冲过了私有的生命的堤防,像春潮时海水冲进了淡水池塘将一切都弄咸了一样。私有经验的世界已经变成了群众、街市、都会、军队、暴众的世界。众人等于一人、一人等于众人的世界,已经代替了孤寂的行人、寻找自己的人、夜间独自呆看镜子和星星的人的世界。
对于麦克里希的判断,朱自清有强烈的认同,多次在文章中引用,他时刻关注正是抗战时期“个人的心”与“群众的心”激荡中产生的新诗乃至新文艺的可能,他对朗诵诗的认知兴趣,就生成于这种关注的延长线上。某种意义上,“诗与公共(公众)世界”的关系抑或“诗的公共性”,其实也可挪用过来,作为审视当代诗的一种可能的视角。
具体而言,随着社会问题的累积、阶层的分化与固化、公共灾难或事件的频发,新世纪以来当代诗的写作和评价,越来越多卷入到公共性的议题之中。无论从2008年的“地震诗”到2020年的“抗疫诗”,还是有关底层写作、草根写作、工人诗歌、“余秀华现象”的热议,似乎都引发了较高的社会关注度。特别是相关的讨论、纷争往往会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热闹展开,并非局限于诗坛内部,或由诗人和批评家来推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冲击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形成的当代诗歌“场域”。在部分批评者看来,对社会苦难和重大事件的回应,体现了当代诗难得的现实性和道德感,突破了先锋诗歌美学和伦理上的封闭,此类写作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崛起”。另一部分或更多的诗人和批评家,则对“道德归罪与阶级咒符”(钱文亮兄语)保持充分的警惕,强调诗歌写作更应捍卫自身的伦理,不能投机于公共性的道德。爱尔兰诗人希尼在《舌头的管辖》一文中的断言:“诗歌有自身的现实,无论诗人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社会、道德、政治和历史现实的矫正压力,最终都要忠实于艺术活动的要求和承诺”,就为很多当代中国诗人所激赏,并被频频引用到自己的辩难之中。
希尼的断言高亢又妥帖,申明了“诗歌伦理”的不可化约性,但似乎又过于稳妥正确,过于自圆其说了,以至可能回避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个话题并不能就此终结,可以进一步追问:“忠實于艺术活动的要求和承诺”,写作是否就能打开新的感受层面,而不只是屈服、回收于现成的社会、道德、政治的要求?书写底层艰辛、社会问题的诗歌,在避免沦为“祥林嫂式的诉苦”的同时,又如何能突破旁观与反讽的习惯位置,获得一种深切感知他人的能力?当诗歌卷入公共的世界,是否能在引起热点话题之外,进一步打破社会文化的区隔,在作者、读者、批评者的联动中,形成一种新的共同体感知?诗人翟永明多年前的《雏妓》一诗,就将这些层次以自我反观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这首诗的前半段,诗人为读者勾画了一个“雏妓”的形象,被拐卖、被伤害、却无知懵懂,看似冷静的陈述背后,有按捺不住的悲伤和愤怒。然而,这首诗的关键,在于随后的翻转:
看报纸时我一直在想:
不能为这个写诗
不能把诗变成这样
不能把诗嚼得嘎嘣直响
不能把词敲成牙齿 去反复啃咬
那些病 那些手术
那些与12岁加在一起的统计数字。
不能为这个写诗!“雏妓”的故事和形象,是“我”从报纸上读来的,而每日的报纸、新闻会让我们的眼睛收集到类似的成千上万的资讯、图像,它们“刮伤我的眼球”,却也是“一掠而过”,带来的恰恰是一种新的冷漠。这冷漠以同情为包装,正像“巨大的抹布,抹去了一个人卑微的伤痛”。
要不要为这个写诗?当代诗之“公共性”的难题之一,就表现在诗人即便真诚地以“个人化”的感受力、想象力,去深入社会的状况、体知他人的处境,但“个人化”的视角,往往会受限于直观性、习惯性的道德反应,而且受到了互联网、社交媒体所提供的单向度信息的影响。这样的“真诚”,还是隔膜于他人的实际经验,介入公共世界的写作,最终回收于城市中产阶级对社会苦难的观看和消费中,进而反噬自身,让写作变成对抽象价值立场“嘎嘣直响”的反复啃咬。这样的“公共性”,显然不是诗人所期待的。
当然,如何突破个体或特定群体的认知框架,能在与他人、与不同群体有效的乃至实践性联动中,达至相对深厚的某种社会感、形成某种“社会想象力”,是人文知识界共同面对的课题。诗人马雁在《北京城》中曾这样写道:
有那么些人常常聚会,
无谓地研究问题,这城市
热衷于责任而毫无办法。
“热衷于责任而毫无办法”,这大概是某一类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画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常常聚会于京城,其中自然也包括诗人和她的朋友。在这样的总体性状况中,要求诗人独自担当重建“公共性”的难题,是有些过分苛责。可换一个角度来提问:在文化“公共性”被挤压、萎缩的时代,从艺术自身的“要求和承诺”出发,诗人是不是也能另辟蹊径,找到自己的“办法”?
在这里,有必要重温一下阿多诺“抒情诗与社会关系”的讨论。在阿多诺看来,抒情诗之退回自我、发掘自我,看似远离社会,但远离的可能是社会的表层,一首高明的抒情诗,会将主观性转化为客观性,在语言的最深处与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抒情诗“不流于口头谈论和报导社会而富有社会性,它以愉快的表白与语言自愿的结合而富有社会性”。阿多诺的说法很是显白,也提醒我们注意,从话语的层面介入现实、表现社会性的议题,这是当代诗“公共性”的一种表现,但不是唯一可能的表现。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构造,诗歌的表达不一定对应于具体的社会状况,却可与深植于社会结构中的感受结构形成一种内在共振,引发连绵的情感共鸣,以及对自身及他人状况的不断领悟。换言之,诗歌的公共性不仅是一个朝向外部的问题,它同时也可在写作内部、批评的内部来重建。
最后,不妨以马雁的一首诗为例,就这个话题稍作展开。马雁在10年前早逝,她身后由友人整理出版的诗集和文集,吸引了众多年轻诗人和文艺青年。这种喜爱或追捧,并非因为过早离世而造成的诗歌史效果,也不简单源于她诗风的强劲、饱满,对于很多喜欢她的年轻人而言,马雁好像一位知心人。她诗中表露的热情、对个人伤痛的开掘、对亲密关系的向往,都颇能切合在成长中充满困惑又有所认信的青年心境。一位90后诗人就谈到在她和朋友们的眼中,马雁与其说是一个诗歌偶像,不如说更像姐姐:“她并非以诗人身份,而是以自由、强大的生活方式,以及隐藏在自由内层、‘建造生活’的严肃态度吸引我们。”这样一种心意相知的感受,对于理解诗歌内部的公共性,多少是有些帮助的。马雁于2010年底写就的《我们坐过山车飞向未来》,就是一首洋溢了公共化感知力的诗:
我们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
他和我的手里各捏着一张票,
那是飞向未来的小舢板,
起伏的波浪是我无畏的想象力
这首诗写得热烈又强劲,飞向未来的“过山车”,显然是由诗人“无畏的想象力”所构造,隐喻了现代社会以及人生在世不得不选择的各种轨道,这些轨道让一切加速起来、飞转起来。在湍急展开的诗行中,诗人似乎在指点我们看“过山车”的上下:有巅峰的创造者,有传奇的讲述者,有底层的匍匐者,有智慧的耳语者,还有接吻的恋人、无辜的儿童和动物。有人被抛向高处,有人被甩到半空,一座盘旋的文字“过山车”似乎被直接搬到了纸面上:“如果存在一个空间,漂浮着/无数列过山车,痛苦的过山车……”。
這首诗的基调“全是痛苦,全部都是痛苦”。但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这首痛苦的独白之作,却有着一种奇异的卷入力量,其人称在“我们”,“我”和“他”,以及“我”和“你”等人称之间急速转换,似乎能把所有读到这首诗的人都带到“过山车”上,与“我”一同感受呼啸的节奏,在惊惧中反观自身、警醒不已:
哦,每一个坐过山车的人
都是过山车建造厂的工人,
每一双手都充满智慧,是痛苦的
工艺匠。
“我们”,包括读者和诗人,既是过山车的乘客,同时又是过山车的制造者,共同参与了纵横轨道的设计与铺设。痛苦的呼语、急迫的节奏、不断转换的人称,都强化了一种人与人“共在”的感受,强力揭示出在现代社会体制、诸多理性人生规划中,普遍被碾压、被扬起又抛下的生存处境。借用阿多诺的说法,这首痛苦的、主观的抒情诗,实际也是客观化的,包含了“情动”他人、通向社会洞察的可能。
这里的“情”,不只是激情之情、共情之情,也可以对应于情势、情理、情况,包含了现实状况中人之境遇的理解。如果经由阅读、批评和再阐释,语言激起的感受力波纹,便可一圈圈荡漾开来,由“我”及“你”、及“她(他)”、及“他们”(“我们”),并延伸到更大的社会性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说,诗人没有热衷于责任,却在这首诗中找到了自己的办法。虽然这办法还是直观式的,缺少生活实践、社会实践的支撑,有待进一步整理、打开,但相比于“嘎嘣直响”的抽象责任,要探索当代诗的公共性,这倒是一个较为切近的起点。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