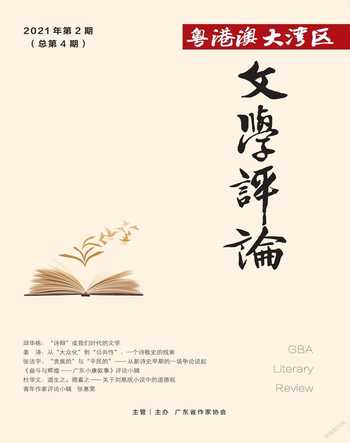乡村少年的自我确证与道德激情
祁春风
摘要:“80后”作家郑小驴的小说创作迄今已呈现出多个面目,从新历史小说、“计生”题材小说到乡土小说、底层青年叙事,驳杂多变而充满生机。他的小说始终隐藏着一个乡村少年的叙事主体,这不仅指叙述上的惯用视角和青春叙事底色,更蕴含乡村少年的记忆、情绪和伦理观。他常常运用“犯罪小说”模式,揭示社会深层痼疾和复杂幽深的人性,并完成一种“想象的惩戒”,宣泄其淤积多年的愤懑之情,显露出鲜明的艺术个性。但他以后的创作应规避两个误区:一是,沉溺于自我的感伤主义;二是,在文学上远离故乡。
关键词:郑小驴;乡村少年;城市底层青年;犯罪小说
郑小驴是“80后”作家中走传统文学道路的代表之一。他在读大学期间开始创作,毕业后辗转于多个城市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在《作品与争鸣》《江南》《清明》《青年文学》《十月》《上海文学》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并陆续推出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痒》《少儿不宜》等,以及长篇小说《西洲曲》《去洞庭》。郑小驴曾获得海男、残雪、谢有顺、贺绍俊等前辈作家和评论家的认可,被视为提升“80后”文学品质的新生代作家。“事实上,‘80 后’已逐渐成为当代文学一支最富生机的力量,他们远不是所流行的‘80 后’文学那么单调、时尚、浅薄。因此,强调郑小驴是一名‘80 后’,也是为了校正‘80 后’文学这个词语在大众中已形成的印象。”[1] 近几年,他的短篇小说《可悲的第一人称》、长篇小说《去洞庭》等作品又产生较大反响,被金理、黄平等青年评论家推崇并作为个案阐释时代与青年的关系。确实,郑小驴拒绝时尚化写作,信奉文学经典,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他的小说创作也呈现出多个面向,从新历史小说、“计生”题材小说到乡土小说、底层青年叙事,驳杂而充满生机。但在笔者看来,他的小说始终隐藏着一个乡村少年的叙事主体,这不仅指叙述上的惯用视角和青春叙事底色,更蕴含乡村少年的记忆、情绪和伦理观。
一、楔入历史与自我确证
郑小驴早期引起关注的新历史小说,如《1966年的一盏马灯》《一九四五年的长河》《舅舅消失的黄昏1968》《1921年的童谣》《鬼子们》《秋天的杀戮》等,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习作,深深打上了莫言、余华、格非等先鋒小说家的印记。在《1966年的一盏马灯》中,父亲临死前透露出一段隐秘的家族史,他当年与村支书的小儿女阿珂私奔失败,被迫与保管员之女结婚,所生子即叙述者吴克。而阿珂逃走后生下腹中之子吴军,现在已因抢劫杀人,沦为死囚。叙述者吴克找到阿珂,探望同父异母的哥哥,询问外公,最终依然疑窦重重:当年父亲与阿珂两人私奔失败到底是谁告密,那盏马灯中藏着的传家宝小金人现在何处?这部作品在家族历史事件中留下空白,引领读者步入迷宫般的小说情节,显然有格非的影子。其后,相对圆熟的《秋天的杀戮》也是如此。1942年的秋天,抗日游击队员郑岸杀死了博,这是枪支走火,还是两人之间发生情杀,抑或处决汉奸?最终悬而未决。而《舅舅消失的黄昏1968》《一九四五年的长河》讲述了彪悍的湘西土匪的故事。郑小驴出生于湖南省隆回县的乡村,这一区域毗邻湘西,或者说属于泛称的湘西。但他此时的写作兴趣并非地方史,只不过受到莫言写土匪抗日的启发。尤其《一九四五年的长河》,无论是情节设置,还是主要人物与叙述者的关系,都有模仿《红高粱》的痕迹。另一部中篇小说《1921年的童谣》则让郑小驴获得“小余华”的外号。叙述者“我”讲述了家族中各个人物的命运,其中,祖母是大家闺秀,擅写古诗词遣悲抒怀,前夫被镇压后下嫁祖父,在“文革”中自沉清江。祖父出身贫农,当和尚打道场,处处留情,过惯了逍遥自在的生活。解放之时,祖父与相识的红军湘西佬有一段有关“革命”“翻身”的对话:“祖父说,那还不是要吃饭的。湘西佬说,他娘的你就知道吃饭!祖父说,我们做百姓的,这一辈子,人一个,卵一条,不为吃,为啥?你们的那些革命,太高深了,我们也明白不了,我们只关心每天有没有吃的,有吃的,就翻身了,这天下便太平了。”[2]这部作品既学习余华讲述历史的凝练,也延续其代表作《活着》中的民间立场。
郑小驴的这些新历史小说通过家族史的形式演绎了一番中国近现代史,国内革命、抗战、建国、饥荒、“文革”等重要历史事件无一遗漏。然而,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先锋小说家们创作的新历史小说相比,郑小驴的这些作品徒有其表,缺乏内在的激情和叙述动力。一方面,“80后”这一代人已不需要颠覆革命历史叙事,他们生活在多元文化并存、大众文化逐渐兴盛的时代,革命历史叙事早已不占据主流地位。另一方面,“寻根”文化思潮也已消退。随着城市化、全球化和新媒体的兴起,青年一代所面对的问题,无法从祖辈、父辈,或者家族史中寻找到答案。在《1921年的童谣》的结尾,叙述者所生发的感慨,只不过是莫言小说《红高粱》中叙述者寻根话语的回声。“或许,这才是她一生的写照。而我们这些后辈,依旧唯唯诺诺地活着,什么也不是。”[3]当然,郑小驴在模仿和习作阶段依然获益匪浅。他从这些先锋小说家们身上学习了“写什么”和“怎么写”,既获得人性、人道主义的眼光,也操练了小说叙事艺术,形成文体创新的意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抚慰近现代史,郑小驴敏锐地感受到乡村的“常”与“变”,这是他作为乡村之子的自我确证。作者虚构家族史,是追溯一个乡村之子的前史,看清了自己的来路。乡村中恒久不变的似乎只有山山水水以及人间的苦难本身,而生活方式、信念习俗、道德人心都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蜕变。这些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几乎都是乡村少年,读者能够明显感受到“我”面对乡村历史的感伤与忧郁。
当郑小驴转向现实乡村生活和自己的成长经验时,他发现了可以摆脱前辈作家影响、超越模仿阶段的创作方向,即“计生”题材小说。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在顶层设计中有改善国民经济、优生优育乃至移风易俗的考虑,但在乡村和基层的实施过程中却常常扭曲变形,出现暴力执法的现象。由于题材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前辈作家中少有涉及,莫言的《蛙》是重大突破,从长时段考察这一问题,并试图用当事人的“忏悔”来化解冲突。此后,郑小驴不断推出“计生”题材或者涉及“计生”问题的小说,包括长篇小说《西洲曲》、中短篇小说《鬼节》《不存在的婴儿》《我略知她一二》《倒立人》《入秋》《蓝色的脑膜炎》等。虽然计划生育国策在新形势下有所松动,这些创作仍然显示出郑小驴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长篇小说《西洲曲》通过乡村少年罗成的视角和叙述,把“计生”在乡村社会被野蛮执行以及“以暴抗暴”的复仇故事写得阴森可怖。亲戚北妹在“我”家躲“计生”,有一次村支书八叔领着主持“计生”工作的罗副镇长,故意在“我”家检查很久,造成北妹在地窖中缺氧而流产。北妹伤心投河自杀,她的丈夫谭青假装外出打工,潜伏在当地,伺机杀死了罗副镇长之子罗圭,并虐杀八叔、火烧镇政府未遂,最终被判死刑。在地窖中躲“计生”而流产,这是郑小驴同类题材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情节。此前的《鬼节》写“大姐”头胎生女,再次怀孕后藏在娘家,躲在地窖中流产。《不存在的婴儿》则以夭折婴儿的灵魂叙事,讲述了相同的流产情节。实际上,这一共同情节来自作者难以忘怀的亲历往事,郑小驴的堂姐曾在他家地窖中躲“计生”而流产。他在《西洲曲》的《后记》中说:“我借用那段青涩的少年记忆,书写我们这代人对计划生育的记忆与看法。”“深夜的手电筒、狗吠、敲门声,干部的威逼利诱与专横跋扈——它们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想同龄人中也有很多人和我拥有同样的记忆,计划生育算得上是八〇后这代人的集体记忆了。”[4]
从虚构家族史到书写亲身体验的“集体记忆”,郑小驴楔入历史的方式不再那么生硬。那些新历史小说题目中的年份数字,泄露出他把个体楔入历史、把自我融入时代的执念。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也有类似倾向,如《飞利浦牌剃须刀》,在一地鸡毛的家事中点缀着世界大事——伊拉克战争,产生了些许反讽效果,却仍显扞格不入。他的“计生”题材小说成功地避免了这一弊端,一方面“计生”无疑是当代史一叶,是关涉家国历史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计生”是作者亲历,浸染着真切的记忆而显得细腻,感人。通过“计生”题材小说的创作,郑小驴开始成功地在历史巨流中锚定和表现自我。
二、从乡村少年到城市底层青年
其实,不必涉足近现代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也不必着眼“计生”这样的当代家国大事,每个人都生活在时代变迁中,处于流动的历史中的某个片段。郑小驴逐渐发现,新世纪以来青年一代面对的城乡巨变和自我成长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历史经验。事实上,长篇小说《西洲曲》除了讲述惨烈的“计生”故事,也内含着第一人称叙述者——乡村少年罗成的“成长”叙事。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而在长篇小说《西洲曲》和短篇小说《少儿不宜》等作品中,他开始试图处理一些切身的历史经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5]郑小驴“自己的风格”起步于刻画主人公从乡村少年到城市底层青年的转变,以及反思这一“成长”过程所付出的代价。
首先,“逃离乡村”是这类小说的核心事件,而且作者往往细腻地展现乡村少年逃离故乡的心理机制。《西洲曲》中的叙述者罗成在火车上听闻一位清纯美丽的女大学生要去北京,立刻激起心中波澜,“北京!多么充满魅力和想象的城市!”他游荡在陌生的县城,“内心深处的某个东西一直提醒着我:忘掉石门,忘掉南棉!你不应该再回到那个鬼地方!”[6]在见证北妹之死、谭青复仇以及经历自身家庭变故之后,罗成对故乡产生了厌恶之情,视之为“鬼地方”。他渴望逃离故乡,向往“充满魅力和想象的城市”。而那位前往北京的女大学生,则是他在青春期性觉醒时的幻想对象,是城市的“魅力”的组成部分,是等待他征服的目标之一。如果说《西洲曲》中故乡的衰败主要由于乡村政治的荼毒,那么《少兒不宜》中的乡村则受到了城市文明的侵袭。乡村里的温泉被外地大老板开发为度假村,实则变相的色情场所,出入浓妆艳抹的外地小姐和坐着豪华车的外地人。当地人的生活和思想被极大地改变,包括主人公中学生游离。“游离依旧想着宝马车。他不无忧愤地猜想今晚那三个男子要干的事。就在这片家乡的土地上。”[7]乡村传统随之崩坏,乡村少年纷纷反抗“父法”,退学“南下”打工,甚至在“逃离”之前焚烧曾经敬畏的庙宇。与乡村的物质贫乏、道德保守相比,城市所显露的商品的丰盈、生活方式的开放,更契合少年们日益觉醒的欲望和各种幻想。在郑小驴的故乡湖南,珠三角城市是许多人的选择,“南方”成为魅惑人心的想象空间。短篇小说《少年与蛇》中的主人公被作者直接命名为“少年”,少年和他的朋友南誊,得不到家人的关怀,孤独而迷茫,最终他们被收购蛇的丰满妇人激起了欲望,从故乡失踪了。“结尾是耐人寻味的,少年与南誊消失了,并非失踪,而是走向了他们所渴望的‘南方’。性成为成长的象征,他们闯入了新的世界。”[8]可以说,在郑小驴小说中,乡村少年逃离故乡的心理动因包括乡村的败落、城市的魅惑,以及青春期的欲望觉醒,而这三种因素相互激荡,发酵,最终促使他们走向城市。
其次,郑小驴书写了乡村少年转变为城市底层青年的宿命,弥散着悲观主义情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全球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尤其是高校扩招和商品房价格飞涨,农家子弟无论是考上大学还是进城打工,境遇越来越艰难,往往沦为城市底层青年。《少儿不宜》中的“堂哥”考上了大学,曾经是“伯伯”的骄傲,却因为无法在深圳安家,在出租屋与女友争斗后,跳楼自杀而瘫痪。《西洲曲》中的“哥哥”退学“南下”打工,掉入传销陷阱,殃及亲戚朋友。另一篇短篇小说《痒》写一对初恋情人胡少和小骚在南方城市重逢。这对人物的设置颇有意味,胡少是考上大学进入城市,而小骚很早就进入南方“如蚁巢般的工厂”,但他们面临的困境却似乎并没有太大差别。看了一场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之后,“两人聊了一会儿电影,都说假。她说靠个人奋斗来改变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9]青年批评家李云雷把近几年出现的《世间已无陈金芳》《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录音笔记》《章某某》等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命名为“失败青年”,“这些作品描述了当代青年在社会巨大鸿沟面前个人奋斗的无望感,虽然着眼于个体青年的人生命运,但却对当代社会结构及其主流意识有着深刻的反思。”[10]郑小驴笔下的这些青年形象无疑也是“失败青年”,同样揭示了在全球资本主义操控下的阶级鸿沟,以及城市底层青年个人奋斗的挫败。另一方面,在这些城市底层青年身上仍具有乡村少年的精神特征。他们在内心深处保留着从乡村带来的质朴和纯真,往往由于难以割舍乡村记忆和抛弃传统品行,而无法真正适应和融入消费主义、欲望化的城市,自然也无法挣脱“失败青年”的宿命。这一点给郑小驴的此类小说涂抹了悲观主义的感伤情绪。
再次,郑小驴还揭示出乡村少年逃离故乡、走向城市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心理代价。作者不仅讲述乡村少年进城后难以摆脱物质上的困厄,而且更主要地表现他们在精神层面的失落和苦痛。其一,道德沦落感。乡村传统道德是相对保守的,当乡村少年被城市不良文化激发出难以把控的欲望和行为时,他们总会感到纯洁之身的玷污,产生道德上的沦落感。《西洲曲》中的叙述者罗成在临县住宿时被卖淫女纠缠。“当我的手触摸到她的乳房时,心中对美的幻想全被这个女人玷污了。在坠入罪恶阴暗的深渊中,我内心发出了一声窒息的呼喊。”[11]《少儿不宜》中主人公游离着迷于外貌清纯的卖淫女阿倾,去温泉度假村里找她,被卖淫女们嘲讽。这是造成他逃离故乡、退学“南下”的关键性事件。《痒》中两个“失败青年”相见,胡少和小骚已经变得随便和放纵,但他仍不断回忆她过去的清纯。其二,无根感。与第一代进城农民不同,新世纪进城青年不再渴望荣归故里,除了他们的身心被城市文明牢牢捕获,乡村的空心化也是重要原因。郑小驴的早期作品《小驴回家》讲述“我”短暂回乡,带着包工头与老乡少斌工伤的协议书。少斌爹同意老板私了,却因悲伤而喝农药自杀,似乎隐喻着乡村的反抗。尽管如此,这篇小说中的乡村,由于妻子儿女的温情,还能带给“我”许多安慰。其后,这种家庭温情基本上消失了。如《能不忆西洲》《少年与蛇》《望下去是地球》等小说中讲述的另一番情形,由于丈夫在外打工长年不归,乡村里常常发生乱伦或偷情之事。在《痒》中,小骚发出如此感慨,“可我已经不喜欢家乡了,越来越不喜欢。越来越没有当年那种感觉了,被城市榨得干瘪丑陋无比,像个弃妇。”[12]个体的道德沦落感以及乡村变迁造成的无根感,是他们精神上的双重苦痛,长期郁积,很可能发展为精神疾病。在《痒》中,小骚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最后两个“失败青年”都觉得浑身发痒,恨不得抓得“血肉模糊”。在近期的长篇小说《去洞庭》中,“北漂”女孩张舸恋爱失败,又中了网络相亲圈套,变得放纵堕落,最后患上了严重的妄想症。
郑小驴在《芭茅溪日记》中说:“‘空村’,像全球化的浪潮一样,已经席卷了整个中国农村,这儿的农村自然也无力抗拒。”“我们将面对一个完全陌生化的故乡,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故乡。那时我们都会变成故乡的弃儿。”[13]郑小驴能够生动地塑造从乡村少年蜕变为城市青年的人物系列,正因为他在现实中也是其中一员,深深地体验着时代巨变赋予的这一精神苦痛,尤其是道德伦理上的困境。
三、“犯罪小说”与道德激情
郑小驴的许多小说含有“案件”情节元素,如中短篇小说《大罪》《七月流血事件》《枪毙》《赞美诗》等。两部长篇小说《西洲曲》《去洞庭》也是如此,前者中的“案件”是谭青为流产的胎儿和自尽的妻子复仇杀人。《去洞庭》中大案套小案,叙述视角在主要人物之间转换,一步步解开悬疑。小说开头快递员小耿犯下强奸、抢劫案,挟持受害者开车逃亡,却遇到车祸。车祸另一方是一对偷情者,引出一起大案。成功人士史谦娶了小二十岁的顾烨,后来却收到顾烨与她的情人岳廉的艳照,继而发现他无比宠爱的儿子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史谦在破产后决定报复,开车挟持顾烨,并买凶绑架岳廉。所收买的凶手正是小说开头的逃犯,在他投资的饭店打过工的小耿。
这是借鉴通俗小说、类型小说的写法。有学者指出:“毋庸置疑,《去洞庭》是一部‘好看’的小说。”“作者找到了中国传统小说中讲好故事的传统,找到了最适合这个复仇悬疑故事的方法和节奏,榫卯相接,拼贴调度,在看似闪转腾挪的非线性叙事下,暗循着内在的起承转合故事脉络,让小说文本凸显出强劲的叙事张力和故事魅力。 ”[14]不过,在郑小驴小说中,尽管许多行凶者有“复仇”动机,但在现代法治社会,“以暴抗暴”仍属于犯罪,不能视为“侠义”之举。而且,这些小说常常运用犯罪者视角,不是传统的“公案小说”或者“侦探小说”,近似于“犯罪小说”。甚至以警察为主人公的《大罪》也不例外,青年警察小马很可能为了尽快实现调回城的目标,故意把小案造成大案,是真正的杀人罪犯。这是小说中不断出现蛛丝马迹却最终没有给出答案的悬疑之处。所以,与其说郑小驴从中国传统侠义、公案小说中找到了“复仇悬疑故事的方法”,毋宁说欧美和日本现代推理悬疑小说的流行对他产生了影响。比如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献身》《白夜行》《解忧杂货店》等作品,近些年连续在中国热销,被改编。
郑小驴并非完全为了“好看”或畅销而借鉴“犯罪小说”模式。首先,犯罪是社会问题的极端化和爆破口,作者以“犯罪小说”揭示社会深层痼疾和复杂幽深的人性。有的作品写乡镇干部的枉法。除了前述的“计生”题材的《西洲曲》等小说,《与一具薄皮棺材有关的》以独特的第二人称儿童叙事,讲述了一个乡村妇女因病猝死后被偷脑子的惊悚故事,既表现乡村社会的蒙昧,又暗示执法者被收买的真相。有的作品写城市底层青年如何滑向犯罪。如《七月流血事件》写专科毕业生小曾留城打工,却交不起房租,新买的电动车还被交警扣下,为了赎回电动车又被骗,最终阴差阳错地杀死骗子。有的作品干脆描写社会边缘人的命运。如《柏拉图的洞穴》写几个逃离家庭的青少年,过着所谓自由的生活,泡妞打架,抽大麻造成车毁人亡。
其次,“犯罪小说”的叙述方式释放了作者的心理能量,完成一种“想象的惩戒”,宣泄其淤积多年的愤懑之情。《西洲曲》以受害者的“复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作者“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计生”带来的惊恐记忆。《七月流血事件》中小曾在城市底层挣扎,又面对不合理的城市治理制度,他的行凶似乎小题大做,甚至找错了对象,然而也可视为“兔子急了也咬人”般的“弱者的反抗”。饶有意味的是短篇小说《枪毙》,通过不断转换的叙述者,逐渐呈现一个完整的“案件”。一位空巢老人被乡村混混在抢劫中杀害,杀人犯光头李最后被押上刑场。“那黑漆漆的东西凶狠狠地对着死刑犯,大叫一声‘爷’!旁边的武警都还没有回过神来,只听见啪啪的两声,死刑犯双眼放出绝望的光芒,霍地倒了下去。”[15]作者似乎觉得法律程序中的“枪毙”是不够的,还需要道德上的判决。“小孩”用玩具枪为“爷”报了仇,光头李受到“小孩”的判决而产生“绝望”和悔恨。在某种程度上,《枪毙》似乎具有“原型”意义,郑小驴的写作如同这部小说中“小孩”的行为,是道德情感所激发的“想象的惩戒”。
然而,郑小驴的道德激情和伦理化书写需要进一步审视。一方面,对于掌权者、执法者,作者相信个人能够凭借“良心”超越“政策”和“规定”。《西洲曲》中,谭青怒斥村支书:“别什么都往政策上推,你以为按照规定办事你们就无需为此承担责任了吗?你们就不用遭到良心的谴责了吗?”“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16]对于此,有评论者认为:“这可能是作家的一种善良想法,命令他们去施暴的不是人性,而是一级一级找不到具体人的科层制,这是我们置身其中的卡夫卡式生存困境。假如这些基层的施暴者是道德高尚的人,能扭转这种局面吗?”[17]然而,不可否认,个人的“良知”和善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价值。实际上,执法者对政策和法规的把握,对执法的宽严,都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自由选择空间,此时执法者的个人道德就会发生作用。由于掌权者或者执法者的个人品行,在普遍现象中造成地区性差异的情况比比皆是。具体到“计生”的执行力度和方式,省与省、县与县、乡镇与乡镇,甚至村庄与村庄之间都有差异,这正是执法者的“良知”和个人道德使然。另一方面,对于底层群体或受害人,作者同情他们的反抗,乃至对其出于“复仇”心理的“以暴抗暴”或犯罪缺乏相应的道德谴责和心理惩罚。《西洲曲》中的谭青,杀害了无辜的副镇长之子,虐杀村支书未遂,尽管被捕伏法,却显然获得了作者较多的同情。《去洞庭》中,通过小耿的视角讲述其两次犯罪,也没有太多的罪恶感,反而充满底层生活的忧伤,甚至被收买也是为了挣钱给患病的父亲换肾。可见,郑小驴的犯罪书写及道德激情隐含着一系列传统伦理观念。他寄希望于掌权者、执法者的“良知”,同情弱者的反抗,即使后者犯罪也有一些道德豁免的理由,如受害者为亲人“复仇”,因为“孝”走入歧途,或者因血缘关系被玷污而报复。当然,作者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写作倾向,开始抑制作为乡村之子所生发的道德激情,在近期的《消失的女儿》《盐湖城》《死刑》等短篇小说中,他把主人公的“复仇”行为进行延宕或者落空的处理,不再完成“想象的惩戒”。然而,不可忽视郑小驴以传统道德伦理叩问现代制度的写作价值。因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制度和法律日趋精密和完备,但现代制度不能凭空而来,必须从传统社会、乡土中国中生长出来,由原始正义向现代正义转化,由个人道德向社会正义转化。正如罗尔斯所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安排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之名也不能逾越。”[18]也许,我们不能“扭转”包括“科层制”在内的現代制度本身,但应该反思某一具体社会制度的“德性”“改造或废除”那些不正义的“法律和制度”。个人的“良知”“善”以及“正义感”,对于“良序”社会、正义制度的建构与维持,发挥着不可缺失的作用。郑小驴基于道德激情的书写,既肯定了个人“良知”的重要性,又考量了制度的德性,实际上也嵌入了具体政策和法规的“改造”历史之中。
总体而言,乡村少年身份作为郑小驴创作的原点,不仅影响其对于历史、现实题材的选择和切入方式,而且形塑其小说的人物形象、叙述模式和叙述动力。他的“计生”题材小说、底层青年书写是对于时代的有力地回应与表现,他的“犯罪小说”模式的运用及其背后的道德激情也呈现了鲜明的艺术个性。以此为新的起点,郑小驴的小说创作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但需要规避两个误区。一是,沉溺于自我的感伤主义。在《去洞庭》的《后记》中,作者称“感伤主义是作家的分泌物”。[19]其实,这是“80后”作家的通病,郑小驴也未能幸免。由于在青春期经历时代文化的巨变,“80后”作家普遍遭遇自我认同危机,他们在文学创作中过于关注自我的成长和个体境遇。而且,这种自我表现常常不过是情绪的渲染和倾泻,具有感伤主义倾向。他们应该对于自我多一些理性的认识,对于时代多一些客观的剖析,更加有效地表现自我与时代的复杂关系,同时借鉴主客体相融合的“抒情传统”,深刻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抒情’从感官和意象获得彰显,但究其极致,足以成为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思想、文化与伦理模式表征。”[20]具体到郑小驴而言,他可以把自怜自叹的“感伤主义”转化为具有“文化与伦理”意味的抒情性。二是,在文学上远离故乡。在现实生活中,作家从乡村走向了城市,对于故乡产生了隔膜,难免生发“故乡的弃儿”之感慨。但在文学创作中,作家不应该抛弃乡村经验和故乡记忆,因为地域性具有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写出个人的成长记忆,就写出了地方的历史记忆;写出独特的人,就写出了独特的地方特征,也就创造出了地方的真正灵魂。”[21]在《去洞庭》等近期小说中,洞庭湖等乡土景物的描写过于缥缈,人物与故乡的关系也显得空洞。希望郑小驴不要远离南棉、石门和青花滩,对于故乡进行持续、深入地书写,创作出一个完整的新颖的文学世界。
[注释]
[1] 贺绍俊:《疏远时尚 亲近经典——谈郑小驴的小说》,《文艺报》,2013年3月25日,第2版。
[2][3]郑小驴:《1921年的童谣》,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第44页。
[4][6][11][16]郑小驴:《西洲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页、第248页、第251-252页、第230页。
[5] 李德南:《在大视野中审视历史与现实——郑小驴论》,《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10期。
[7] 郑小驴:《少儿不宜》,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8] 王学谦、李张建:《向内挖掘的力量和魅力——郑小驴小说的爱欲书写》,《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
[9][12]郑小驴:《痒》,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页、第205-206页。
[10] 李云雷:《全球化时代的“失败青年”——读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文艺报》,2016年3月25日,第5版。
[13] 郑小驴:《你知道的太多了》,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230页。
[14] 陈小手:《途中之镜——读〈去洞庭〉》,《文艺报》,2019年5月20日,第3版。
[15] 郑小驴:《蚁王》,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
[17] 项静:《冒险的行程——郑小驴小说读札》,《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4期。
[18][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9] 郑小驴:《去洞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30页。
[20][美]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7页。
[21]贺仲明:《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38页。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新时期小说青春叙事的流变研究”(编号:2018M630794)、山東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青春文学阅读与初中生作文能力培养研究”(编号:YZ201904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