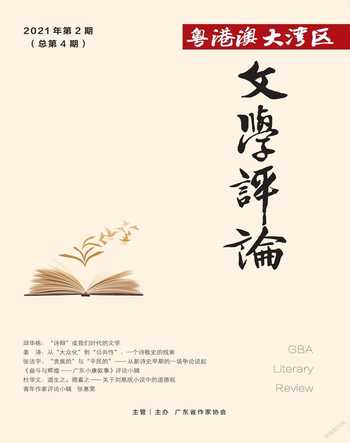何为现代、如何现代、怎样叙述与广东经验
杨丹丹
摘要:由张培忠先生总撰稿的《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以非虚构的方式讲述了1978—2020年期间广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曲折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广东经验和广东模式。对该书的价值和意义应该放置在中国百年新文学关于“现代国家想象”的脉络和谱系中去理解和阐释,该书既是中国百年新文学“现代国家叙事”的延续,同时又突破了文学传统的限度,生成了新的审美经验。
关键词:《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现代国家叙事;审美经验
由张培忠先生总撰稿的《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以非虚构的方式讲述了1978—2020年期间广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曲折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广东经验和广东模式。作为国内第一部全方位呈现广东建设小康社会的史诗性著作,该书的价值和意义应该放置在中国百年新文学关于“现代国家想象”的脉络和谱系中去理解和阐释,该书既是中国百年新文学“现代国家叙事”的延续,同时又突破了文学传统的限度,生成了新的审美经验;重新定义了文学与历史、时代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在全新的时代语境中如何表述历史的问题,该书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由人物衍生出来的故事及其故事背后的精神话语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拓展和丰富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维度;更为重要的是,该书不仅呈现了广东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更发现了真实的“人”,在鲜活的个人生活史中挖掘出现代意义上的“人”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在此基础上,该书对新时代的公共性话题“小康社会”的讲述为当代文学如何表述新时代提供了全新的经验和借鉴。
一
在儒学经典《礼记·礼运》中“小康”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概念在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中提出,孔子认为尧舜禹时代寻找的是大同社会理想和平均主义意识,经济上消除私有制、按需分配,政治上依靠贤君、忠臣的德政和民主管理,文化上遵循儒家文化规范,提倡减少个体之间的纷争,以此构建一个“小康”社会。从夏代到西周时期是典型的小康社会,但私有制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政治、经济和文化開始出现私有因素,财产的私有、政治的世袭和个体道德的滑坡使小康社会出现裂痕。但以“礼义以为纪”的儒家文化仍然能够保持相对的社会正义和公平,因此建设小康社会仍然是中国社会的理想,也推动了小康社会思想的发展。东汉的何休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提出的“三世说”,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对大同社会的描述,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人的自由、平等、独立和解放的论述,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观点都与小康社会的想象和建构相关。[1]尤其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传统小康社会思想基础上,对何为小康社会、如何实现小康社会、如何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思想,并形成统一共识: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这表明在“现代化”视阈中“小康社会”的建构和确立经常被看作一个国家进入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标志。虽然一个国家面临的文化传统、历史语境、时代境遇和处理的现代化问题存在极大的差异,但在建成现代国家的诉求上却呈现出一致性,成为国家设计、引领、规划政治、经济和文化行为的核心动力。
对中国而言,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使中国被强行拖入世界现代秩序,也激发和塑造了中国关于现代国家的全新想象,并由此衍生出不同的现代化想象和实践方案。因此,对现代国家的想象和实践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始终,20世纪中国历史不断发生的各种激进革命和温和改良事件的终极诉求都与建立现代国家相关,也可以把20世纪中国曲折发展的历史理解为不同的建立现代国家方案之间的竞争、抵牾、冲突、对峙和和解的过程,也是寻找最优方案的过程。同时,这种独特的历史主题及其衍生出来独特历史进程、形态和面相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决定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因素。简单而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文学为肇始,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新启蒙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等不同文学思潮都将“现代国家想象”作为核心主题和叙事中心,“现代国家想象”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叙述的伟大传统。
这种叙述传统一方面为《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提供典范的审美经验和叙事范式,但另一方面也对其构成审美焦虑,如何突破中国百年新文学形成的坚固传统,建构新的审美原则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也决定了《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的审美和精神高度,而《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恰恰做到了这点。从总体而言,《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采取以历史横截面的方式审视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伟大进程,从总结独特历史经验出发,重新理解和阐释了“何为现代国家”“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问题。从该书讲述的“百端待举”“风生水起”“攻坚克难”“逐梦飞扬”四个总体性故事中可以发现,从宏观上而言建设现代国家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现代化,这与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叙事保持内在一致。但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叙事中这种现代化是以西方为参照,并加入了明显的民族主义因素,从而使现代国家叙事显现出明显的焦虑和紧张,实际上仍然是按照西方现代化经验和模式构建中国的现代化,致使在构建自我现代国家形象中走向对抗和封闭。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塑造的现代国家形象显得抽象而空洞,讲述的现代国家故事很大程度上是不同历史阶段国家政治故事的转喻,关于何为现代、如何现代等问题仍然缺乏自己的独特认识和表述。而该书力图超越过去现代国家观念中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既与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相契合,又把其从政治话语的藩篱中解放出来,更为关注在建设现代国家过程中存在的切实问题,以解决问题的方式推动现代国家建设。也就是说,该书在正视“社会主义贫穷困境”、政治观念保守、经济体制僵化、官僚意识严重等问题基础上,通过讲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牵扯出如何建设现代国家的问题,而且解决问题的途径始终抓住“改革”这一核心话语,而且改革的终极诉求在于实现人民的富裕生活,解决人民切身现实生活难题,让人民真切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利益,逐渐树立人民的现代意识和观念,从而形成整体社会对现代国家的期盼。这样“何为现代”和“如何现代”的问题对人民而言就不再是抽象、空洞的符号,而是始终在场的现代生活,也不再强调现实生活的政治属性,摆脱了“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而是关注现代生活的世界意义,真正把人民代入世界现代生活秩序中。
同时,在不回避建设现代国家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分歧和危机,把克服内在危机作为调整现代国家实践方案的重要动力基础上,不断修正国家、民族、地方、人民之间的复杂关系。该书第一卷开篇就讲述了广东省宝安县布吉公社沙西大队南岭第一生产队发生的“大逃港”故事,但该书没有涂抹故事的传奇色彩,而是把目光聚焦在故事引发出来的问题:人民现实生活的贫困,以及在香港现代生活对照下这种贫困引起的精神刺痛。实际上,这种“故事情境”的还原关涉到改革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基层治理方式、社会观念、政治态度与人民要求现代生活之间的矛盾。因此,如何面对、处理、解决逃港问题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应对偶发性社会事件,而是要彻底根除建设现代中国过程中出现的顽疾,只有全方位的彻底改革,使人民生活真正富裕起来,才能抵制香港的诱惑,“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站在新时代的时间点上,反观当时广东省实行的“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反偷渡策略,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建立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等一系列改革方案的出笼、落实和推进使人民开始摆脱“社会主义贫穷困境”。由此而言,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是重塑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过程,只有实现国家命运和人民命运的内在统一,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二
《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从改革前广东社会的真实困境和人民现实生活内在危机出发解决和重塑“何为现代”和“如何现代”问题之后,如何表述这种独特的现代体验成为下一个关键问题。20世纪中国文学通常采取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方式表述这种现代体验,“典型环境”基本上与历史总体性命题贴合在一起,照应不同历史阶段国家制定的相关政治、经济、文化大政方针和具体的实施政策,基本上是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塑造文本的典型环境。例如,柳青的《创业史》反映的是国家在农村实施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历史过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呈现的则是改革开放前后“城鄉交叉”地带转型期的内外变局,草明的《乘风破浪》是按照“鞍钢宪法”精神设置的文本语境;“典型人物”通常指社会主义“新人”,基本集中在革命英雄和社会改革者身上,他们有着类似的面相:紧随国家政策的召唤,具有社会主义集体精神和中国传统伦理,而且能够起到典型示范功效。例如,《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这些社会主义“新人”符合时代的整体诉求,但也极容易演变成抽象、空洞的政治符号,在发挥社会典型示范效应的同时丧失了个体生命的现实感和鲜活性。针对这种叙事局限,该书一方面充分挖掘人物的时代性,把人物与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重要节点、重要事件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注重人物的日常生活性,从人物的切身现实生活体验出发,让人物自己发出声音,把人物的时代性和个体性有机结合起来,而且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但正是这些“小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真实再现了改革开放的惊心动魄,“小人物”与“大历史”之间的互动和博弈重新定义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内涵和边界。例如,女工人叶秀珍作为香港怡高实业公司在广东投资建设的石岩上屋热线圈厂的第一批女工人,对改革开放的体验不是源于国家制定的改革政策,而是肇始于日常食物的改变,人民公社时期叶秀珍家里平时舍不得买肉,但到了线圈厂工作之后随着工资的提高,不但家庭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还添置了家用电器等“奢侈品”。同时,叶秀珍发挥了典型示范效应,“带动了小姐妹们,大家每个月一拿到工资,就给父母家用、添置物品、给弟弟妹妹交学费,无不兴高采烈。她们改变了家庭的贫困状况,感受到人生的变化,对线圈厂感情日渐加深,对青春价值、生活品质和人生追求有了更多的向往。”从叶秀珍的个案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这一抽象的时代宏大命题与个体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就隐藏在小人物日常细微褶皱中,该书也正是由此探寻广东改革开放的宏伟历史。再如,前国营锅炉厂的铆焊工高德良凭借“周生记太爷鸡”快速致富,第一个月的纯利润达到2000元,是以前做铆焊工月工资的十几倍,从个体收入差距的对比中再现改革开放引起的社会巨大变动,“成了推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后来个体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成分在国家法律与政策上获得明确肯定。”除此之外,经营大排档的梁锦华、承包鱼塘的陈志雄、承包菜地的张建好、承建白天鹅宾馆的彭树挺等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成为时代的典范。
该书在重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同时,更为注重呈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建设现代社会中形成的独特经验和模式。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在四十年的改革实践中逐渐探索出富有成效的创新性的发展道路:以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为试验田,在建设和完善经济特区基础上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的对外开放格局,在开放中推动改革之路,在改革中总结开放经验,始终把改革开放置于各项工作的首位,最终确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典范地位;广东的改革开放始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市场化改革,以经济改革促进政府管理方式、社会群体观念、法治建设、文化革新等全方位改革,这种从点到面、由外而内、从单项到综合的改革路径和方法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借鉴;广东改革的成功及其取得的辉煌成就与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地方政府治理观念的转变有直接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为广东省对外开放提供了强有力的特殊政策,同时广东地方政府也不断加大改革力度,提供了诸如“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等政策保障,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政治活力;除此之外,广东的改革开放与社会思想解放有着内在关联,1980年代初期对“两个凡是”的讨论成为中国社会的思想焦点,广东省力主打破“两个凡是”思想的拘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先后发表《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史伟大的历史潮流》两篇重磅文章,力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观念的革新为广东经济改革根除了精神上的顽疾。1980年代后期,“姓资姓社”的论争使中国经济改革出现摇摆和反复,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广东省政府提出“敢于从实际出发,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标准,摆脱不符合形势发展要求的旧观念和理论束缚;敢于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不去人为地给它贴上‘姓’什么的标记;敢于从经济发展差距看到思想认识的差距 ”的观念,明确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思想基调。从1990年代至今,勇于突破陈旧的历史观念,思想改革的常态化成为广东社会的集体认知,形成了“敢为天下人”的精神话语,并演化为一种思想力量,不断实现创新性发展模式,推动改革的飞跃式前进。可以说,广东模式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社会推动四种合力的产物”[3]。
该书第二卷开篇讲述了1991年中国社会掀起了大规模的“姓资还是姓社”论争,在这种思想和舆论环境下,广东社会出现了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媒体不断报道进城务工人员的负面事件,遣返这一庞大的群体成为基层政府的主要工作,“从前晚起,一支由市政府、公安、交通、劳动、民政等部门组成的疏导队伍,上路截查进入东莞的乘客,凡没有劳工三证者,便要当地折回。”“流动人口有碍社会观瞻”成为主流观点,但如何妥善处理和精准定位外来务工人员关涉到改革能否顺利进行。成浩作为在广州工作的外来人员,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劳务问题和经济问题,而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决心、气度和格局问题,让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自由流动,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待遇,在思想上给予充分认同,让他们彻底融入广东社会,为改革开放提供发展动力是未来不可阻挡的趋势,以粗暴方式阻碍他们流动将会为广东改革开放的长远发展设置阻力和障碍。因此,成浩筹划和拍摄了电视剧《外来妹》,真实再现了广东外来务工人员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发现广东改革开放的大历史,引起观众的精神共鸣,这部电视剧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表明了广东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是广东社会思想改革的集中体现。在解决百万外来务工人员进城问题的同时,如何吸引科技人才将决定广东改革开放的高度。珠海作为全国首批经济特区,为科技人员设立科技重奖、科技激励措施和激励机制,开创了全国先例,“走出一条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项目和人才到珠海创业发展之路。”巨人集团总经理史玉柱、“中国信息化最具影响力35 人”之一的陈利浩、同望集团的刘洪舟就是这种科技激励机制培育出的人才。珠海引进科技人才的成功不仅为广东梳理了典范,也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四川等省份纷纷效仿。可以说,思想开放为广东改革打下了牢固的精神基础,也确定了广东以高科技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深圳的改革之路清晰地印证了此点。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由世界加工厂转型为世界科技的高地的过程离不开深圳人对高科技的执着追求,华为、腾讯、大疆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落户深圳,在深圳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以科技成果普惠于民。该书第四卷第三、四章对此情境进行了详细描绘,“广东无论是电子信息产业、电信运营业,还是互联网企业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电信和互联网用户规模全国第一。乘着4G技术到来的东风,信息消费、物联网技术应用、云计算技术应用、大数据应用等行业和领域发生了关键性变革。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化发展,早早就达成了一个共识:信息化是引领广东未来发展的大战略,广东会大力推进新一代宽带技术与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全面融合,以移动互联支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应用,积极拓展内容服务,深入实施惠民服务、惠农服务、产业服务和政务服务”,正是高科技产业的集群式高速发展为深圳和广东的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动力,使改革进入快速路。
三
《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在呈现广东改革开放40年的独特经验和发展模式的同时,为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范例。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跨越式提升,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成为世界关注和探讨的公共性话题,如何讲述“中国故事”,重塑中国的世界形象,让世界公正、客观、理性地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在世界秩序和结构中的位置,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诉求,但何谓“中国故事”,如何表述“中国故事”,如何构建“中国故事”的话语体系等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界定和统一认知。从《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来看,“中国故事”是一个新的创造性的故事,并非存在一个先验的中国故事和确定的中国形象,而是从中国独特的历史发展中生发出来的故事,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再现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及其蕴含的情感体验,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召唤力和未来可能性。与此相对应,讲述“中国故事”需要以一种宏阔的历史视野去表述建设“现代中国”这一历史总体性命题;能够承载和呈现这一历史总体性命题的是“现代中国人”及其独特的人生际遇、情感体验和精神指向,透过“现代中国人”看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表述“现代中国”中的“现代中国人”并不存在哪种文学体裁和哪種文学范式更为适用的问题,而是将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将“中国故事”演变为一种深刻的民族记忆和精神资源,以此召唤一个全新的中国和世界。因此,讲述“中国故事”就意味着塑造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需要作家以全新的思维对中国社会进行重新观察、创造和想象,摆脱长期以来在西方文化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东方主义”思维及其构建的负面的、落后的、孱弱的、封建的中国形象。当然,这并不是要求作家强行遗忘中国的屈辱历史,但这只是作家审视中国社会的历史出发点而非全部,在全新的时代语境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不再是西方现代国家的追随者,凭借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拼搏,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发展之路,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优势,这必然要求作家以新的思维和眼光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同样,“在价值观念与美学风格方面也是这样,我们讲述的中国故事,既要是‘现代’的,又要是‘中国’的,我们可以继承传统中国的某些价值观念与美学风格,但也要融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熔铸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美学。在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新的艺术世界,其中凝聚了我们共同的经验与情感。”[4]例如,通过《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广东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惊人成就和艰辛历程,也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时代的巨变,甚至可以说,广东经验和广东模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典型样本重组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构了人民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关系。
我们之所以强调《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的宏观视野与个体故事的融合,是因为关于“现代国家想象”的文学叙事就是从个体故事开始,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乡土文学、女性文学、城市文学都讲述了个体如何打破封建体制、封建家族和封建思想的限制,追求解放、平等、自由和民主的现代生活,以个体故事为中介勾连起家族故事、乡村故事和国家故事;即使是讲述革命故事的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也是从个体故事为入口,通过个体成长呈现中国现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虽然个体故事在革命宏大话语的辐射下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行为,但在革命话语忽略的“中间人物”“边缘人物”“小人物”故事身上仍然能发现真切的现代体验;新中国至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间,建设现代工农业强国叙事更是把个体故事和国家故事捆绑在一起,《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讲述的都是个体与国家如何融合在一起的故事,但1980年代中期以后,史诗性的国家民族叙事逐渐被个人主义话语思潮淹没,个体故事不再承载国家、民族、历史、时代和社会意义,个体从繁复的关系网中脱离出来,致使个体故事的意义变得单薄而轻飘。在此意义上,《辉煌与奋斗——广东小康叙事》在重建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个体故事与国家故事的内在一致性上,重建关于现代国家想象的历史视野和美学规范,中国故事的叙事主体既是国家也是个体,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既是当下的更是未来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阶段性目标,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辉煌与奋斗——广东小康叙事》的故事主体除了中国与人民之外,还存在一个隐形主体:世界。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样本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明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在处理“非典”和“新冠”等人类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中国的崛起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推进人类社会进步中的重大意义,中国如何重新认识世界,世界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关涉到的根本问题都是世界如何重建和发展的问题。因此,“在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时代,能否讲述或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如何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变化,如何理解中国内部的变化,可以说对当代中国作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很显然,《辉煌与奋斗——广东小康叙事》为中国作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和范例。
[注释]
[1]王兰坤:《从传统小康社会思想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学习论坛》,2003年第5期。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肖滨:《演变中的广东模式:一个分析框架》,《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6期。
[4]李云雷:《何谓“中国故事”》,《人民日报》,2014年1月24日。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