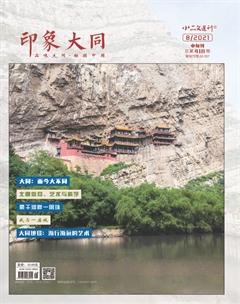黍地沟
朱占群


草地上随意地走着,漫无目的,惊起的蚂蚱飞过来,飞过去,褐色,个子不很大。小时候见到的蚂蚱最多,除了褐色的,还有绿色;有的方头,有的尖尖的脑袋长长的身子,飞的时候翅膀下面会变出来一团粉红色。尤其是秋天,捉将回来,个头小的喂鸡,大的下油锅,炸酥炸脆,撒上细盐,要比现在饭馆的菜好吃多了。
黍地沟的蚂蚱印象最深。就在我们所住房屋的后山坡上,葱绿的蚂蚱体形肥大,飞起来翅膀扑楞扑楞,声音很大,尤其那一双长长的刻着锯齿的后腿,强劲有力,一跳好几米,扣在手心里还一弹一弹,闹不好手还被划破。
比老曹年龄大的同事都喊他“曹老弟”,参加工作的一批人里属他岁数小,但是他的厨艺最老练。不用多说了,我们吃饭都是他掌勺,我就坐享其成,不会做饭不一定没有好处。直到现在,他家里炒菜做饭,老曹都不让老婆插手。越来越霸道,尤其是做海鲜,蒸螃蟹、蒸扇贝、蒸牡蛎、炒海兔、炒小龙虾等。
最引以自豪的就是做花蛤,做出来的花蛤有形有色。可以清炒,可以辣炒,清炒就是原汁原味,清新自然,辣炒的话味道更浓郁一些,配上葱头或青椒,根据个人口味轻重,豆瓣酱可多可少。我最喜欢吃辣炒的,并且喜欢重口味,倒两杯牛二,就是绝配,还经济实惠;炒菜时还要用生菜、萝卜、黄瓜等抠出花儿,摆上造型,非常讲究,看到餐桌上杯盘狼藉,风卷残云,他两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黍地沟,大同西北附近的一个小村落。在工地旁边的山坡下,垒起一排红砖房,七、八间,房子很低,站在屋里,抬起手臂就能摸到屋顶,一根根木棍的上面架着一簇簇的树枝,时不时地掉些土坷垃在床上。我和同屋的尚用塑料布和细铁丝把整个屋顶给封了起来,还是能听到悉悉窣窣的土掉在塑料布上的声音。
墙上抹了一层不算太粗糙的细泥,屋里放了两张用四条腿的木凳支起来的床板,床头是用设备包装板做成的木箱,装些衣服、鞋子之类的生活用品,两床之间是一张桌子,桌子上还有蜡烛。电灯是装了,只是要用发电机发电才成。
93千瓦的柴油发电机在白天供给施工机械用电,晚上生活照明就大可不必了,除非晚上加班,才会打开,屋里就亮堂多了。发电机离我们宿舍有三十米距离,突突地轰鸣声,让人有些焦躁和不耐烦。
靠门口是一座砖砌的炉子,炉盖是铸铁的,大圈套小圈,小圈套着铁盖子,小铁盖中间有个小铁环,炉灰口开在墙外,烟囱是白铁皮的,一节一节拼起来,用弯脖拐了个直角弯儿。烟囱顶上黑黑的,烧煤是当地产的,闪着亮光,份量很轻,划根火柴就能点着似的,炉灰如同柴禾烧过的灰烬一样,没有一点炉渣。
尚同志喜欢把屋里的温度弄得高高的,墙上还特意挂上了干湿温度计,而我喜欢清冷一些,就为这个缘故我俩不知吵了多少回。他气得把火勾子摔地上,愤愤不平,脸涨得通红。
面对寒冷我从不畏惧,从小就这样,由它冷去,老子我不怕,当年上学时手冻成了胡萝卜,又粗又肿,姐夫看不过去,给了一件蓝棉袄,我记住了衬里是白底浅红色竖条格子。
单位的领导来到了黍地沟。当时我在柴油发电机跟前,因为蓄电池的原因,发电机还没有启动;领导弯着腰走进了我们的宿舍,屋子本来很小,容不下几个人,因为窗户也开得小,屋里很暗,走出屋后,我看到领导眼里闪着泪光。后来听说,领导在机关里大发雷霆,因为来了黍地沟看到条件太艰苦。
一间房子用来做饭,厨师是在古店村里雇的一个中间妇女,身材高大,胖胖的,黑红脸,眼睛很大,一看就是一个能操持家务、里里外外一把手的女强人,就是说话的口音有些拗,这也怨不着她本人,山西人说话都这味儿。
古店村里小卖部的火鸡腿却是相当不错,我们改善生活的时候,火鸡腿是必不可少的,骑自行车来回近一个小时的路程也不嫌远。
水是从村里用拖拉機送过来的,四五个大大的塑料水桶,拧上盖子存起来,能吃好几天。冬天麻烦一些,水桶上面会冻得很厚,就用钢钎、大锤把冰层捣碎,再把一块块冰块放入锅里。
那时和家里人联系还是以写信为主,就一部大哥大,还在赵队长手里,比砖头小一些,信号不好,还要跑到山上去打;那时,女儿和她妈还在租房住,房东有一部座机,打通了,房东要到二楼去喊一声,不但房东不情愿,通话也不方便。
有一次,我一个人晚上值班,别人都去了村里的队部,我屋隔壁的屋子,就是西头把头的那间,放了一台小型雅马哈汽油发电机,在突突地喷着青烟。因为隔墙上面是连通的,我躺在床上看东西,不知什么时候感觉到头有些眩晕,想要昏昏欲睡,浑身软绵绵的,突然意识到大事不好,发电机尾气放出的一氧化碳要熏死我了!
跌跌撞撞出了门,坐在地上,歇了一会儿,骑上自行车,赶往黍地沟村里的队部。应该是秋天,月亮挺圆挺亮的,总算万幸,捡了一条命,当时如果有个电话该多好。
在黍地沟的第二年春天,天气依然寒冷,我们这个闭塞、荒凉、经常被风沙肆虐的地方,却迎来了不少家属,闺女还没上学,和妈妈一起过来了,还有我的对头尚同志的夫人和女儿“上好佳”,立强家的夫人和小公子等,宿舍前有一棵大树,孩子们在树下嬉戏,小郝有时带他们去地里玩耍。他的孩子才几个月,没有来,我在回想,当时这几间矮小逼仄的房子,是怎么住下来的,可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在黍地沟的头一年,曾写了一篇《重返黍地沟》,钢笔是蓝色的,带红格子的信笺,装进信封寄到了单位的宣传科,还引起了小小的波澜。
后来,我们从黍地沟搬到了大同县一个长满了苤蓝的农场里,黍地沟那一排低矮的房子里,开始变得空空荡荡。
选自“洗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