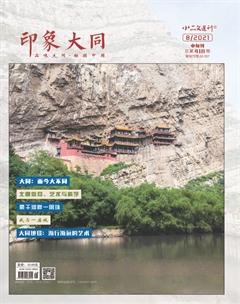吃杏儿
郭宏旺

瓦窑村有我家的老院儿,老院里曾经有座老屋子,老屋的后面曾经有一棵高大的老杏树,老杏树留给我好多的回忆。
我六七岁记事之时,屋后就有了那棵老杏树。我认为我爹小的时候就已种下这棵杏树,因为我六七岁的时候,这老杏树就大概有三十年的树龄。
老屋后的那棵杏树古老而高大,比老屋的屋脊还高几尺,树干粗壮。蓬勃的树冠宽展,树冠下浓荫满地。
老杏树结的杏儿,与别人家树结的杏儿不一样,别人家树上结的杏儿,看颜色鲜红亮丽,但吃起来并不太香甜,有点酸硬还带点咬不动的硬丝。而我家老树的杏儿,个头不大不小为椭圆状,外皮看上去黄中泛点绿,但里面是一派水淋淋的橙黄。味道糯润,酸甜刚刚好,越吃越想吃。记得人们就把这种杏叫“里熟杏儿”。
杏儿熟的季节,有杏树的人家会把摘下的杏儿,先给左邻右舍送一些过去,余下吃不了的杏儿,也会想到卖出一些的,价格一定不会太高。我家杏树大,每年下的杏儿足有三四斗盆。娘说咱们也吃不了那么多,卖上一些,还能凑孩子一点学杂费,不顶个多,也顶个少。而爹觉得自家种的一点杏儿,要卖给别人多难为情。但若真的白送,有的乡亲们又太拿心,不好意思来白取。最终便是这样的:有人来买时,若要买五斤,爹娘就往袋子里再硬塞五、六斤进去。这样好啊,有了一点小收入,更重要的是乡里乡亲,情分也更浓了。村子里的人非常淳朴,他们把这情分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小时候的我,贪嘴是免不了的。到了杏儿快熟的时节,放学后我便想办法从后院门悄悄溜到屋后,脱掉鞋子顺着粗壮的树干爬上去,钻进茂密的樹枝里,偷吃个够够的。因为前后左右都是橙黄剔透的杏儿,像无数只小桔灯一般挂满整个树头,所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每年夏秋之际,正是放暑假时候,住在矿上的我的三哥和六哥他们,都会回来看望我们。刚进家门,爹和妈就让我赶快领着他们去吃老杏树的大杏儿。
我骄傲地爬上老杏树,摘下金黄金黄的杏儿噼里啪啦往下扔,三哥和六哥在下面支开衣服接着,够不着的地方我就用一根小棒敲打,我们边打边吃,幸福的笑声在后院回荡。
在大矿山长大的三哥对吃个杏儿应该不太稀罕,可这一次不一样。那种里熟杏儿过于好吃,三哥在树下吃得有点急,不小心把一个杏核噎在喉咙里,上不来也下不去。三哥噎的眼睛睁得大大圆圆的,气也出不上来,这下我们慌了神。好在我妈有办法,让三哥弯下腰,妈用手掌在三哥后背上拍打了几十下,忽然三哥站了起来,尴尬地笑着,嘴里吐出一枚满是唾液的扁杏核。
我妈笑着说我三哥:“没事了,没事了,接着再吃去哇,三妈家那杏儿就是好吃哇。”
应该是一九八二年左右吧,老杏树开始衰败,先前一两年是不怎么结杏儿,数量极少。又过一两年老杏树有些枯朽,三年后彻底枯死掉了。
那棵老杏树死去了,但老杏树给我们留下:六支褐红色的擀面杖,一块大案板和一张没刷漆,却色泽纹路极漂亮的杏木大炕桌。
如今又到吃杏儿的时节,母亲说院子里那棵小杏树也结了一些杏儿,让我回去带一点,只是母亲说这杏子再没有那棵老树的杏子好吃。
人们说阳高的杏儿出名的好吃,我却觉得也一般,倒不如家乡汉圪塔兴然种养园的杏子好。一周后就要开园啦,那里的大京杏不错,小红杏小白杏儿味道更是一绝。有朋友说,天镇县的糖唐儿听说比阳高的杏儿好,我不大确定。不过我这么说,也许是因为再也吃不到曾经那棵老杏树上那种杏子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