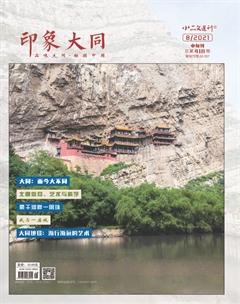叽溜
姚维儒


叽溜,文雅一点叫蝉。自古以来,文人都有一种爱蝉的情趣。文人眼中,蝉性情高洁,入土重生,蜕变新生,这些都符合文人追求的洁身自好、寻找新生的朴素愿望。所以,蝉在文人的笔下,总被赋予了诗情画意,值得耐人寻味。
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画“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汪曾祺在《夏天的昆虫》中,介绍了蝉的品种、习性。有一种叫“海溜”的蝉,个头大,色黑,叫声宏亮,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进一步又写,北京的孩子捉蝉,是在竹竿头上涂了黏胶捉蝉。而汪曾祺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粘。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昆虫的喜爱和对童年生活的眷恋。
汪曾祺还告诉我们,还有“一种是‘嘟溜——一嘟溜——一嘟溜,一种叫‘叽溜,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
长时间生活在城市的人是很少听到叽溜鸣叫的,晚饭后与夫人在运河堤上散步,听到路边树丛中传来几声“知了知了”的叽溜鸣叫,那激越欢快的鸣唱一下子把我拽回了孩提时代。
蝉,也叫知了,但我们那里一直习惯叫叽溜,小一点的就叫“嘟溜”。每当天热的时候,叽溜的叫声便会适时地响起,它们鸣叫的分贝,似乎也与气温的高低成正比。它们喜欢停落在树上,特别是杨树和榆树,当它们此起彼伏的叫响时,预示着农村要收割麦子了。
从小,我虽然住在城里,但门口有一条河,河边长了一排排高大的榆树。有树必有叽溜在,纷扰喧嚣烦人心,叽溜的叫声准确地说属于噪声污染,特别是休息时,简直是扰人清梦。“蝉噪林逾靜,鸟鸣山更幽。”用蝉噪来写夏天的寂静,可一旦真的天天听蝉噪,恐怕人就会躁动了。然而对于孩童的我,丝毫没有这种感受,反觉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乐趣。
叽溜们无休止说“知了,知了”,其实,我们对它是知之甚少。
叽溜为何而叫?有“求爱”一说,因为天热适应叽溜的交配,所以雄性叽溜就用胸部的鸣叫器官发出洪亮的声音,当雄性叽溜高声鸣叫时,能把周围的雌性叽溜召唤过来。当雌性叽溜飞到近距离时,雄性叽溜不断发出特有的低音量的“求爱声”,吸引雌性叽溜的靠近。与此同时,雌性叽溜也能发出低音的应答声,以此达到交配目的。雄性叽溜一旦完成交配后不久便会死去,雌性叽溜完成产卵任务后也相继死掉。为了生命的延续,它们真是死得其所。卵在树枝上越冬,到第二年夏天,借助阳光的温度,孵化出的幼虫就掉落在地上;幼虫便一个劲地钻进土里,吸食植物的根,在地下生活4年之后再钻出地面;然后爬到树上,依次脱壳最终变成美丽的成虫,即所谓的金蝉脱壳。
叽溜快乐的歌唱在夏季,但代价是在地下的黑暗中潜伏多年,生命是短暂的,在享受阳光的同时放声高歌,这也是叽溜一生的梦想。“我们不应该讨厌蝉喧嚣的歌声,因为它掘土四年,才能穿起漂亮的衣服,长起与飞鸟匹敌的翅膀,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我很敬佩的生物学家法布尔这样说。
了解了叽溜的生命演变过程,对其的不良印象顿觉消除,且生敬意。叽溜是土话,是方言,我喜欢“知了”的名字,更喜欢“蝉”的称谓。据了解,古人把蝉当成餐风饮露的高洁象征,据说连“禅”都是脱胎于蝉的,借的就是金蝉脱壳的通灵之寓意,也借喻人的修身养性、脱胎换骨是需要经过一个漫长且痛苦的过程。所以说,叽溜们的高调歌唱,是生命之光的释放,是成功者的凯歌,也真不失为是“千古绝唱”。
叽溜、知了,特别是蝉……,好优雅的名字;寒蝉凄切,薄如蝉翼,金蝉脱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些又赋予了情感的内涵。自古以来,人们对叽溜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它的鸣声,它为文人墨客所歌颂,并以蝉声抒发高洁的情怀,辛弃疾写过:“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的文字,苏轼则有“林断山明那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的意境。叽溜一直不知疲倦地用高亢而舒畅的调子,为大自然增添了浓厚的情意,难怪有人称它为“昆虫音乐家”“大自然的歌手”。
捉叽溜,成了孩童最动心的事。用一根竹竿,顶端沾一些面筋,抑或松香油之类的,轻手轻脚地走到树干下,对准目标一沾,很少有逃脱的。也有在竹竿顶端用铅丝圈个环,再请家长缝上旧袜子做个网兜,岁数比我们小的,后来就不用旧袜子而改用尼龙丝网袋代替了,“活捉”叽溜特灵。叽溜有会叫的,也有哑巴的,据说会叫的是雄性。叽溜好像没有听觉,它听不见周围发生的声音,甚至连自己声嘶力竭的鸣叫也完全听不到,至少是个“半聋”,只有触接到它才会飞走,这也是叽溜相对好捉的原因之一。嘟溜就比较机灵,栖息的位置也高,也不容易捉到。叽溜壳是中药材,中药房里常年收购,也可以与敲糖的换麦芽糖吃,所以寻捡叽溜壳也是孩童们乐此不疲的事。
农村田埂大圩上到处是树木,这里就成了叽溜们的乐园,它们就干脆肆无忌惮地来个“民族大合唱”,且喧嚣个无休无止。夏季叽溜的鸣叫,年复一年,可那鸣唱显然有着不一样的内容,虽然唱歌的叽溜换了,声音亦一如既往,然听的人却没有变。诚然,叽溜寄托着很多童年的美好回忆,然而,身为知青的我们,面对叽溜的鸣叫,早没有了孩童时的快乐。我们想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前途,想的是“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的丝丝烦恼。文人们是在顾影自怜、以蝉自诩啊。在他们心中,蝉高洁得不食人间烟火,生命短暂,却照样奏响生命的乐章。这的确很像一些文人生命的自画像。我想,这恐怕也是文人爱蝉的原因吧!
选自“汪迷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