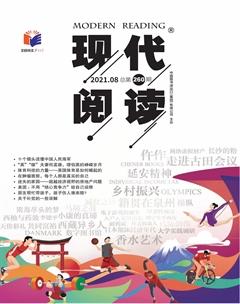在肿瘤面前,每个人都是真实的自己


生命是很脆弱的,每一位我们救治的患者死去后,他们就像是变成一道又一道刻在我们身上的伤痕,这些痕迹不会消失,然后成就了现在的我。
新手医生的必经之路
1995年到1996年,我三十多岁,遇到两名患者,和我是同龄人。
一个男孩,胃癌,一米八几的个头,一表人才。他在我们病房待了将近两年,从术后的辅助治疗到复发、转移,都在我们这里就医,反反复复入院出院几十次。
那时候我还是年轻大夫,经常值班,大部分时间都是泡在病房里。同龄人之间总是很聊得来,我值班的时候,他没事就来办公室找我们医生、护士聊天,开开玩笑,大家慢慢就熟悉起来。
他的家人也都知道,这是一个预后很不好的病,但他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我记得他做完胃癌手术后,人特别瘦,但他每次见到我们总是一握拳一弯肘,鼓着肱二头肌说:“看我的胳膊。”隔着宽大的病号服,也看不到,我就会顺势捏一下他的胳膊。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因为这个部位能看出病人脂肪储备、肌肉力量等各方面的情况,可以评估他的全身状况。每次我捏完,他会很得意地说:“我,男子汉。”
随着病情的发展,他出现了转移,先是腹腔转移,然后肝门淋巴结转移,还出现黄疸,而且对很多化疗药物都不敏感,治疗没有什么效果——那时候也没有现在那么多的治疗方法。
我心里也越来越难受,甚至害怕见他,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给他希望,我给不了他希望。每次和他家人谈话时,看着他的父母,那种老年人即将失去孩子的压抑哭泣,都会对我造成一种特别大的冲击。他的孩子还很小,妻子每次来,在我面前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几乎都是陪着一起流泪。后来我就很怕和他们交流,但我又必须去交流。
在他不可避免要走向死亡的那几天,我已经不敢到他病床旁边去了。但作为他的主管医生,我不去谁去?非去不可的时候,我硬着头皮,挤出笑容去面对他,其他时候能躲就躲。连路过他的病房,我都是快步走过去,但因为太熟悉了,只要我的脚步声一靠近,即使他本来是半躺着的,也会一下子坐起来,眼睛盯着门口。我不敢正眼看,但又忍不住用余光去看他,然后就会看到他那满眼的期盼。
这种目光,刻在我心里很久很久。我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觉得自己很无能,这么阳光的年轻人,自己的同龄人,我却救不了他,只剩下深深的挫败感。
他是在医院走的。他走的时候,我其实就在病房的办公室里,但我不敢到他跟前去。在交班时,其他医生说,他走了。
作为医生,我们悲痛时不会像别人那样痛哭,但是对心理的影响会非常久。直到现在,过去近20年了,我仍然记得他高高的个子,还有他最后的眼神,那时他的黄疸严重到连眼睛都是黄的,黄色的绝望和期盼,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从那以后我就告诫自己,永远不能和病人走得太近。但这是每一个年轻医生的必经之路,不知不觉就扎了进去,共鸣、痛苦、惋惜,渐渐学会掩饰,然后内心强大到看起来有些“冷酷”。其实,我们只是把自己装进一个“壳”里,既是自我保护,也是让自己尽量保持客观理性,最大限度作出正确的医疗决策。
亲情是生命最后最需要的
生命极其复杂,我们肿瘤科医生所遇到的人生百态,是任何编剧都编不出来的。我们遇到病人,自然而然会去比较,尤其是遇到情况相似的两个人时,那就像在进行人生的对照研究。
在我50岁左右时,同时接诊了两个女患者,也都是五十出头。
A是一位公司老总,精明能干,肠癌,刚开始治疗效果还不错,熬了不到6年盆腔转移了,然后各种治疗,特别折腾,但她很坚强。我记得她的女儿在英国读书,和我女儿差不多大。几年的治疗过程中,我就看着这个孩子从像小猫一样依赖妈妈到一天一天坚强起来,反过来妈妈对她越来越依赖,生命的强弱就发生反转了,两个人的角色都变了,孩子一天天长大,妈妈一天天虚弱。这就像生命能量的一种转移,从妈妈身上转移到了女儿身上。
另外一个病人B,也是肠癌,转移路径和A不一样,但活的时间比A短很多。她依从性比较差,虽然有老公,有儿子,但老公没什么主意,儿子粗线条。所以,在她身边你看不到那种温暖的亲情,看到的都是单位领导、朋友来来往往,我就觉得她很孤独。
這两个患者几乎在同一时期来我这里就医,这种反差让我很感慨。A有丈夫、孩子,还有一个姐姐陪伴,这些家人都在帮她想办法作决策;而B只有她自己,身边来来往往的都是单位领导、同事,治疗费用都是单位领导在出面解决。
其实A和B的情况差不多,而且从肠癌的类型上说,B实际上比A还好治一点。但是B没有一个真正关心她的家人在身边,没有人帮她作决策。比如,最后两人都脑转移时,我说应该做手术把转移灶拿掉,A的家人很支持,做了微创手术;而B就不愿意做手术,只好做放疗。发展到最后,B特别痛苦,头痛欲裂,痛得眼球都凸出来了,但是我又给不了她什么帮助,只好躲着不见她,我受不了看她这么痛苦。后来,她转到另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医院去了,我经常去会诊,直到她最后离开。
所以,从A和B两个病人的经历,我最大的感悟就是,生命最后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其实还是亲情。人需要亲人,单位的领导、同事、朋友再好,都不能替代家人帮病人承担责任和义务,不能帮病人作决策。
时间无法医治一切伤痛
2000年,我38岁,正准备去美国留学。当时我父亲才七十出头,身体很健康,在北京给我带孩子。
父亲是一个凡事很想得开、很豁达又意志坚强的人,但不知为什么我走的时候,他特别伤感,以前从来没这样过。他说:“你这一走,去那么远(的地方),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我当时也没有多想,还和他开玩笑说:“爸,您说啥呢,以前去美国要坐三个半月的船,现在飞机一天就回来了。再说,我一年就回来了,我不喜欢待在美国。就算不回来,我也一定带着您一起走,也让您出去转转。”
我走的时候是2000年6月,按计划2001年7月回来,但由于课题还没做完,需要办延期。正在办理的过程中,父亲病了。但事先谁也不知道,“五一”节时,我给家里打电话,父亲耳朵不太好,平时打电话都是母亲接。母亲说父亲记忆力明显下降,现在回过头去想,其实是因为他病了。母亲说:“你爸想跟你说几句。”然后把电话交给了父亲,父亲拿着电话,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特别难受,但远在美国,只能在电话里安慰他说:“您别难过,我很快就回去了,马上就能见到我了。”
父亲并不是一个细腻的人,平时也不是多愁善感的。他之所以这样,现在回过头去想,我觉得当时他一定是有预感,但又不好对家人诉说,包括我去美国之前他的情绪异常。
“五一”这通电话,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心里很难过,却故作轻松地跟他说笑。后来母亲也安慰我说:“没事没事,你爸挺好的,最近可能有点多愁善感。”然而,没过几天,父亲就脑出血,紧急做了手术,做完手术我哥才给我打电话。他说,出了120毫升血,我一听就蒙了,脑出血120毫升很少能抢救过来。但他马上告诉我,现在生命体征平稳,应该是缓过来了。我说我抓紧把美国的事处理完尽快回来。
父亲是5月6日病倒的,在ICU(重症监护室)待了56天。在ICU的时候他没有意识,我每次打电话回来都无法和父亲交流,母亲在电话里就是一个劲儿地哭,我哥为了让我安心,就一直说“爸爸挺好的”。
终于在6月29日我回国了。我回到北京已身无分文,回医院向主任借了2万块钱后直奔火车站回徐州,路上需要14个小时,第二天早上7点多才能到家。
但是,就在我快到家的时候,我先生告诉我,父亲走了,凌晨2点多。就差5个小时,他终究没等到我。
我哭了两天两夜,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不仅是父亲的离世让我悲伤,还有深深的自责、内疚、后悔,各种感情全部涌上来。
家人一直在安慰我,说父亲的去世跟我在不在身边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医生,大家都已经尽最大努力,也找到了当地最好的医疗资源,我在不在都无法改变这个结果。
当你最擅长的事情,你最强的技能,却不能为家人服务,不能为家人作贡献,不能为自己最亲的人尽一点点责任时,这种伤痛会贯穿你的一生,无法排解。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缺憾,无法重来,一旦错过就是永远错过了。我常常安慰自己:这就是人生,本来就不会事事如意。这些我做不到的事,就是命运给我的枷锁,必须承受,要让我的人生有缺憾。
父亲去世后的那几年,也是我一生当中最艰难的日子。母亲患上了抑郁症,我将她接到北京带在身边;孩子跟着我从美国回来,初中入学的事不顺利;我自己的工作也一直不顺。
但这也是我真正成长起来的时候,作为家庭的顶梁柱成长起来。以前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我的孩子也扔给他带,家里有任何事情,他都说你不用管,他是顶天立地的父亲。他一走,所有的重担都压到了我身上,当我从那几年的艰难中走出来以后,我一下子就豁达了。
生扛過来之后,我真正成熟了,那时候差不多40岁,我又恢复到以前那种做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的自信中。
这是父亲给我的力量。父亲所给予我的财富,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他用离开告诉我,人生是不可能处处都随心所欲的,他让我经历生命中一个永远不会磨灭的烙印,然后我才能长大成熟。
亲人的离开,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在向死而生,但我们永远想不到亲人会在什么时候离开,有些人见不到就是见不到了,你所见到的他,就是当你离开时,他在家门口的样子;当你上车的时候,他在后面挥着手跟着你的车,或者连挥手都没有,就在后面默默地跟着你、看着你的样子。
你可能想不到,这就是告别,因为这样的情景,你从来不把它当作一种离别。尤其像我这种16岁就离开家上学的人,天天都是在外面,总是认为我还要回去的,总认为我还能见着的,只要回去,父亲就在那里等我。
面对亲人的离开,医生会比普通人多一种遗憾,就是觉得自己有能力救他但又没有使上劲儿,这是特别痛苦的。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在人间:肿瘤科女医生亲历记录》 主编:沈琳 戴志悦 本文作者:沈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