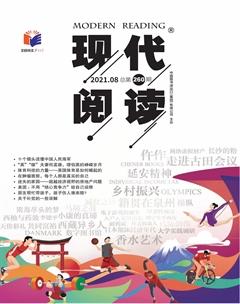中国“城中村”与国外“贫民窟”

许多人担忧中国的“城中村”会演变为国外的“贫民窟”,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那么,“城中村”是否会变成“贫民窟”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贫民窟”是一种负面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国家阶级过度分化导致的社会分配失衡产物。贫民窟的问题从19世纪开始一直困扰西方国家长达一个多世纪,是社会职能缺失与经济增长失效的集中表现。不同国家的文化、经济、制度导致“贫民窟”形成的机理存在较大的差异。
以南亚国家印度为例,印度贫民窟形成的根源是3000多年来“种姓制度”导致的社会等级分化。这种制度虽然在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被废除,但留下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地笼罩在印度的社会体系之上。在意识形态的引领下,印度的分配制度与商业制度都倾向权贵组织,从而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这种贫富差距不仅体现在物质基础上,还蔓延到教育、健康等领域,导致印度难以摆脱贫民窟的包袱,被称为“世界上最绝望的贫民窟”。
而巴西与墨西哥的“贫民窟”比较特殊。巴西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4%的农民可以养活96%的人口。这样一个国家却依然有着世界“瞩目”的贫民窟。
20世纪50年代,巴西掀起了全国性的城市化发展热潮。1950年,巴西城市化率仅为36.2%,到了1980年城市化率竟然高达67.6%,仅用了30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需要100年才能完成的城市化进程。但是,城市化率并没有提升巴西的GDP,这与城市化率增长的速度严重不匹配。因此巴西成为世界上唯一高城市化率的“貧民窟”生产国。
墨西哥作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样“制造”了不少世界著名的“贫民窟”。2005年,墨西哥约有42%的城市人口还处于贫困状态,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的人口高达1470万人,约占城市总人口的20%。墨西哥贫富差距严重的原因是有失公平的社会制度。墨西哥自从二战以后就没有解决过分配问题,二次分配的制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贫富差距受马太效应的影响不断扩大,导致墨西哥“贫民窟”根深蒂固。
国外的“贫民窟”形成机理与中国“城中村”形成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城中村”是改革开放后,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劳动力快速转移所导致的。从空间结构来看,城市发展割裂了城市原有版图,导致传统的村庄被城市包围,从而形成配套不全、建设滞后的“真空”地带,与现代城市格格不入。城中村居住成本低,集聚了大量外来人口,这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挑战。从社会结构来看,城中村的形成也受“乡土文化”的传导,中国农村社会是“人情社会”,外来人口进入城市一般会根据地域文化的趋同结伴而居,比如深圳的“河南村”、慈溪的“江西村”等。
“城中村”与“贫民窟”之间的共性主要体现在城市快速发展中,因成本或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的自发性集聚,这些集聚受规划、配套、建筑先天不足的影响,导致公共安全与社会治理存在隐患。城市中弱势群体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决定了“城中村”和“贫民窟”的需求与价值。
中国“城中村”与国外“贫民窟”有本质上的区别,国外的贫民窟涉及种族矛盾、宗教矛盾等问题,具有严重的社会安全隐患。同时,国外的贫民窟主要是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积极性不高群体的聚集。中国城中村恰恰相反,是拥有梦想的年轻人与积极“出售”劳动力群体的聚集地。以深圳为例,有500多万人住在城中村,占常住人口的50%左右,这些人为工业企业与服务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与相对合理的劳动成本。深圳正是因为拥有这些资源要素,才在改革开放的数十年里持续高速发展。
深圳曾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导致第一代制造企业由于用工成本持续上涨而纷纷撤离。后来,由于富士康等企业数十万员工对生活成本的担忧发出呐喊,最终深圳市政府通过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提升了城中村的使用价值与治理水平,为外来人口创造了过渡性的居住条件。
根据深圳市官方数据,深圳城中村用地总规模约320平方千米,占深圳土地总面积的1/6。深圳城中村租赁住房约占总租赁住房的70%,是租赁市场供应最重要的主体之一。2017年10月,深圳发布相关规定,引导城中村通过综合整治开展规模化租赁。同时,为了配合租赁市场的需要,深圳计划推进100万套城中村存量房屋开展规模化租赁业务。2018年11月,深圳市在出台的城中村规划中明确了保留城市发展弹性,在特定的时间内保留一定比例的城中村。
相比之下,中国还有一些城市正高调地宣布“消灭”城中村计划。如果城市发展能够有效地解决外来人口住房问题,那么城中村的消亡也许是社会文明与经济发展进步的表现,只是请用点时间做一个缓冲,帮助那些为城市默默奉献的外来人群度过艰难的阶段。
城中村的问题在于不能有效治理,一拆了之实际上是一种懒政思维。按理来说,消灭城中村的唯一理由是城市的廉租房、公租房已经与外来就业人口的需求相匹配,否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城市的兴衰:基于经济、社会、制度的逻辑》 作者:郑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