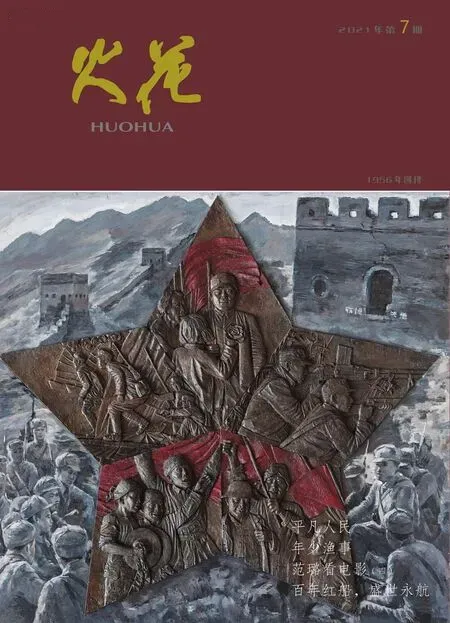日喀则,藏南的解答与献祭
曾龙

旅行就是对自我一生的寻找。
作为后藏政治文化中心,日喀则一如它所拥有的伟岸与神秘,在珠峰巅用信仰之光召唤着人世的向往与行吟。日喀则在国内的火车站中颇为另类,作为连接后藏的枢纽,火车站每天仅通两趟火车,皆相连拉萨,贴合着这片土地野性而坚硬的骨骼,用一张张稀缺而简易的门票,揭开它第三极的面纱之美。坐在一堆藏民中,一车厢的人缄默无言,却随处洋溢着友善与温和的气息。这种气息如此自然,不带有任何文明社会礼仪上的做作与修饰,正如这片土地生来的样子。
身边的一位大叔,闭眼念着我听不懂的经文。我双眼紧贴窗外,群山与粗犷的荒野牢牢镶嵌,如两头野兽正在大地上竞速狂奔。不时,又有温和的溪流注入旷野,抚来一片生与血的颤动。所有关于生与死的对话,所有关于灵与肉的缠绵都在大地上反复书写成野性之美,又复归到一种沉重的无言。没有人属于这里,只有灵魂在去往日喀则的旅途上飞。
在日喀则站遇到了最严格的防疫检查,足足耗去了半个多小时。在等待中有两位藏族女孩子站在了我身后,紧贴身后的一位身材稍显丰腴,熟悉的高原红染着她立体的五官,浸出一种异域而冷峻的美。我们双目开始对视,忽然,害羞的笑靥漫上了她的脸颊,刹那冲散了那不可逼近的冷艳。她对我自语了一声:“这里比拉萨还要严格。”沉默瞬间消解,破开了我们等待时的焦躁与默然。随后,我们开始了一路的攀谈,得知她就读于咸阳的西藏民族大学,学习英语师范专业。我问她有没有去过湖南,她说只去过成都与北京,皆是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我随即称赞她非常优秀,她却害羞得摇了摇头,面孔上的高原红又增染了一层红晕。我帮她将行李提下了楼梯,未曾作别,汹涌的人潮就将我们匆匆冲散。
简易住了一夜,第二日便启程赶往江孜。于城市,日喀则并没有在我心中激起过多的涟漪,就像那位擦肩而过的藏族女大学生,在情愫的退潮后又复归了陌生的冷峻。开往江孜的都是小型面包车,车上空间狭小,坐垫黝黑,似乎许久未曾清洗,弥漫着一股难言的异味。车坐满即走,我直奔向最后一排,图个安静与惬意,随后上车的藏民,皆与我在对视中互致和善的笑意。这时,一位藏族姑娘搀扶着她年迈的奶奶坐在了我的旁边,姑娘初中生模样,一脸朴实,带有高原姑娘熟悉的静默与柔美,一个藏族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坐在了我的前面,车满后轰鸣驶离。
从城市驶向旷野,车里的静默濯洗着一路的景色。心绪在大地上散动成五色的乐章,随远方的山河行吟成古老的欢歌,一切生灵都在阳光的触角中感知世间美妙的轻盈。而我们也仿佛悬浮于天际,与飞鸟追逐着祥云。这时,坐在我身旁的老奶奶掏出了几颗糖果,分给坐在我前方正因无聊而陷入发呆的两个小孩。顿时,一股温情在车内弥漫,荡起了满车厢的笑靥,孩子的母亲连连笑着致谢,而那位姑娘则一路抚摸着老奶奶的手,时刻感知着她的温度。因为热,我脱去了外套,然而在下车时却找不到袖口,老奶奶见状,忙拽起我的袖口穿入了我的手中,感动之余连连道谢。下车后,没有任何道别,所有相遇时的温情都如此自然而随意,就如人性之美生来滋养着这片土地。
出车站,宗山遥相可望,越近越如明珠般耀着夺目炽亮的光芒。忽然,一处人流窜涌,走近后发觉是当地的集市,里面果蔬、生活物品应有尽有。不过,最惹人眼目的倒是贩卖的羊肉皆被砍去了头颅,躯体以坐立状放置于木板,初见有些心悸。一旁,一群藏民围着一堆牛羊的头颅,中间一位老板模样的中年男子一手拿着一把零钱,一手拎住一只羊头的犄角,似乎在与周围的藏民竞价。不远的茶馆处,酥油茶的茶香和藏歌的欢腾一齐涌来,将眼前的死亡清洗得自然而澈亮。
江孜曾是西藏第三大城市,繁华的气息穿透时间的尘埃将眼前串联成一片繁闹的市井,这在百年前遗留的照片中依稀可见。比起日喀则,我更爱江孜,不仅是出于它历史与文化的积蕴,更是在于它恰到好处的城市范围。几条简易的街道就把历史与现代、繁华与僻静牢牢串系在一起,让人在静步中刹那破开眼前所有的奥妙与神秘,直抵这片土地炽烈的内心。
越近,我的心越发轰鸣。电影《红河谷》中格桑抱着心爱人的尸体,点燃打火机与英国侵略者同归于尽的一幕,将所有征服与抗争的悲歌带着鲜血的腥气截断于眼前。仅我一人在宗山遗址前凭吊,似走入了照片中那百年前的斑斑光痕。导演的匠心掩不了历史更加真实惨烈的沉痛,没有补给、没有外援,弹尽粮绝的江孜人民在宗山上孤军奋战了三个月,最后宗山被侵略者用炮弹野蛮地撕开了一道伤口,流出了滚滚血肉。英军吹着胜利的号角,摇起得意的旗帜冲入堡内,为了不被汹涌而来的强敌俘虏,江孜人民纷纷含泪歌吟,转身以跳崖殉国,在宗山上完成了生命的永铸。
“难道社会的进步就是用野蛮的先进来对落后进行毁灭与奴役?”琼斯心中的盘问又在我的耳畔响起。百年前,他们生于此,葬于此,生命已然在战争的献祭中完成了对虚无最好的抵抗。眼前的宗山,在血肉中完成了自我的再造,成为了一枚英雄与民族的符号壮烈镶嵌于历史的丰碑之上。行步中,我陡然发现墙面上似乎还布着当年勇士们的血迹,我逐一定睛注视,顿时呼吸粗重,心跳震响,是血?我不敢触那一片淋漓的血滴,似乎每一滴血渍都在翻滚,都在跳动,嘶喊出当年向侵略者发出的无畏怒吼。而城墙上正闪着银光的晶石,已然都变成了勇士们凝固的血肉。我在淌着英雄们血肉之躯的原地,逡巡、悲叹,一股热血顿然在我心中充盈,又在我泪目四望中回到了一片寂静。
来时空无一人,仅我独坐于山顶的旧址。整个下午,山顶上呼啸的风都在静默中疾驰往复,不停剪开历史结痂的疤痕。山下,城市的喧杂如排浪般袭入耳畔,在交杂浮荡中与山上的风声碰撞出时代的乱紊。百年的岁月驾驭着时代的飞轮奔腾成眼前一片繁闹的热烈,又在疾行中将往昔碾为厚重的沙尘。历史的悲歌凝于宗山,而所有对历史的盘问也在盘问中回到了自我的本身。没有谁是这片土地上的主宰,所有的胜者永远都是历史的锈迹与疤痕。百年前战争的惨烈、英雄的跳崖、文明的交锋已荡然无迹,仅有的也只是几尊雕塑屹立于山巅,带我们重返历史的伤口与悲愤,正如《红河谷》的最后在爆炸中毁裂的宗山,完成了信仰的升腾与人世的轮转。或许,无人会在未来惦记起这山巅的血肉歌吟,就如历史无法在疾驰中退回自我的背影,仅有的也只是无数游人在影像与文字中猎取一丝心灵的凭吊与伤叹。但请让我此刻独自伫立于山顶,恣意我的悲欢,随后淌在英雄的血肉中为生命的伟岸与悲壮快然饮泣。灵魂升腾,一切在百年的轮转中完成了自我的宿命,正如山巅的梦,从未苏醒。
远方,起伏的群山早已看惯这片土地上轮流的登演,统一与征伐,家族命运的盛衰。他们眼中的历史早已被横切成一块棱镜,耀着人世几点单调而简易的波澜。没有什么是永恒,就连旁观者自身也没有永恒的生命去延续自我的记忆。
所有的盘问与惊澜在山巅裂成一道百年的伤痕,倾倒着残酷的答案与悲欢。没有什么是永恒,就连岁月本身也会遍布斑驳与锈迹,不再被自我熟稔。历史,在生长中回到自我的本身,就如每个人在长眠后交还了自我的命运。这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知觉,让盛大的悲欢成为此刻心灵的锚点,激荡着一切生的悸动与狂澜,或埋于我的未来,将这片土地的伤口从我的话语或笔尖刺穿更多人疼痛的猎艳。刹那,我变成了一片羽毛,在这宗山上轻盈地飞舞,在历史浪涛上轻盈地飞舞。在最高处,我开始仔细窥察宗山的每一寸血肉与肌肤,每一根杂草的生长与宿命的倒流,他们的呼吸与倾诉,他们缄默式的回答与孤独,让我开始飞得更高更远,直至在太空中凝视这颗蓝色的星球。我是一刹飞影,这是生命在恒久前的规律与定理,但我此刻也因轻盈蜕去了一切的杂芜与皮肉,回到了自我的本身,回到了一切真实的疼痛与悲吟。这样的疼痛与悲吟让我的人生开始得到净化与升腾,最后在涅槃中将我的魂灵化作了一面明镜。那是我的前世,正在宗山上用英军的炮火洗浴着血肉,三个月孤军无援,山河寸断,英军用象征文明的利器撕开了古堡,冲入了宗山。我的前世含泪与战友高歌呐喊,在山崖上破茧成蝶后跳起了死亡之舞。羽毛落地,终于我与宗山、与这百年的岁月完成了最好的系连,完成了信仰的同属,完成了生与死的再造。历史的悲歌,在无声的苍穹下悄然启幕。
结束始于虚无,一切的虚无却又在抵抗中不断完成对意义的再造。这就像历史,永远在一条亘古不变的河流中恣意流淌,人世的存在与延续就是为了让这条河流不断隆起一座座高峰,让人们在所见中不断明晰自我生命的方向与高度,再向更高处,用一代代生命的激情与焰火,攀上更为伟岸的精神珠峰。

眼前的宗山开始变得不再虚无,历史也不再屈服于虚无与遗忘的恐惧。一切回到了自我的本身,借由意义与信仰的洗涤变得豁然可触,就如我化身的羽毛,开始在宗山,以及更多如宗山般的土地上安然落地。
宗山旁,一条古街在曲折萦绕中直通白居寺,古街上许多透着岁月斑痕的房子蒙着历史的暗尘。许多藏族老人闲坐于门前,与阳光和时间碎语。房屋前树着招牌,如一张张身份证,又如一道道鲜灵而面目明晰的历史典故,指明着每一座房子过往与身世的迷途。一只小牦牛被轩在一块木板下,板上留有罗措户(当时尼泊尔公馆,也是第一家咖啡馆)的字眼,将生的爱怜与岁月的斑痕相映成美的哲趣。我欲抚摸那头小牛,没想到它竟主动走过来与我亲昵,用毛茸茸的头颅直蹭我的腿肚,如孩子般的可爱淘气,我抚摸了会儿那柔软到有些粘手的毛发,随后用它不懂的话语道别离去。转身,岁月在我脚下勾起一道七彩的年轮。
越近,眼前恢宏的建筑群越在我心中敲击出震响的轰鸣。白居寺,这座萨迦派、噶当派、格鲁派三派共存的寺庙,此刻开始浴着佛光,将它雪白的色泽、独特的层垒构造、寄予的高贵象征,如焰火般嵌于我的双眼。在网上第一眼见它时便勾去了我的魂魄,来白居寺和宗山,便成了两条激涌的暗流,直引我奔向江孜。我走到白居寺的白塔前,两位老人坐在塔下窃语,暗诉这里的过往与前世,白塔耀着夕阳的彩光,在午后洗浴着俗世的杂尘。在不可攀触的神圣中,光影开始折叠时间的暗语,一道道循环人世的轮回,我在暗叹中开始随藏民一圈圈转塔,仿佛在我的脚步中走完了今生。灵魂瞬间轻盈破体,在塔尖俯瞰这世间的生死轮回,一时却丢了躯壳的踪影。
忽然,两位喇嘛将我的魂灵从塔尖唤回躯壳,问我是否买票。我摇头,“全然不知要买票,只是径直走入”,结果被斥声轰了出去。心含愠色走出白居寺,忽然两位可爱的藏族小女孩向我跑过来,调皮地都说对方要给我送东西吃,我望着她们无邪的面孔笑问,“你们要送给我什么好吃的呀?”她们听后却只是笑得越发热烈,又继而重复起刚才的话语。这时,后面一群藏族小男孩跑了过来,问我她们在对我说什么,我茫然地摇了摇头。随后,他们又复问我是不是来旅游,我边点头边问他们是否知道湖南,有个孩子立马抢答似地尖声嚷道,“我知道,我知道。”天真无邪的笑靥顿在他们脸上化作一道暖泉,直泻我的心底,我笑看着他们,顿时起意要带他们去超市买零食吃,孩子们听后立马欢呼。
进入超市后,我说随便拿,孩子们听后又复起一阵欢呼。在超市东挑西选了许久,孩子们才选定了自己喜欢吃的零食,心满意足地捧到收银台。见他们开心样,我老生常谈地开始勉励起他们要好好读书。有个孩子王模样的高个子听后立马提高了嗓音嚷道,“我是班上的第一名!”我听后满意地点头笑了笑,“好,你一定会考上清华。”从超市出来后,孩子们纷纷欢腾散去。看着他们背影上溅起的幸福火光,所有关于幸福的茫惑与艰奥顿然在我心中豁然明亮。
比起白日喧嚣的激涌,夜幕中的江孜则好像在静默中被星光洗净了躯体,静悄悄地等待着黑暗的交合。最繁华的上海路餐厅云集,不过顾客却寥寥无几,只有几点喧杂的车声与昏暗的残灯偶尔挑醒黑夜的昏睡。我在街道上来回逡巡,时而快跑,时而又突然凝步蹲下,俯首听这片土地下暗涌的风云。在江孜,我的灵魂轻盈得像夜空中任何一闪星光,像宗山上任意一块杂石。因为我知道,我早已成为江孜身上一根无名的毛发,一块随时会疼痛的肉身。
参观完帕拉庄园,第二日便匆匆赶回了日喀则,期待与扎什伦布寺来一场更加波澜四起的精神和鸣。帕拉庄园虽说是藏区唯一保存完好的庄园,但其面积狭小,许多展室紧闭,仅有的几个开放展厅也只是凸显了地主奢靡与农奴凄惨生活的对立,除了掠起几丝转瞬的愤慨与悲叹,便无更多可在历史中撷取的真理。
扎什伦布寺外人潮叠涌,除却珠峰这颗明珠,扎什伦布寺便是人们对日喀则最为憧憬的缘由。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四大寺”之一,除了伟岸尊贵的信仰地位,扎什伦布寺更多给我的是一种轻,一种灵魂之轻、气息之轻。甚至连这里每一座大殿,以及它们身披的群山都格外轻盈,这种轻要胜过庙宇中朝贡的青烟,这种轻要胜过鸟儿飞翔的羽翼。我就是带着这种轻飘入扎什伦布寺,坠作一粒埃尘。扎什伦布寺雪白的肌肤,面容的轮廓与我曾经所见的藏传佛教庙宇并无二异,只是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力量忽然间拨乱了我的心绪。随后,又在阳光的洗浴下复归到一种美妙的平静。这样的平静又在刹那间洗去了我全身的微尘,让我开始失去重量,在巷子与庙宇间轻盈地浮荡,时而变成庙宇们多变的光影,时而又成为喇嘛口中的经文,时而又复归了重量,回到了我沉甸的肉身。我开始用所有气息去触感这片土地的血肉与悸动,我逐一抚摸它的年轮,生长的线条,以及一切暗藏于土地下的奥秘,最后我抚摸到了自己,我的面孔、肌肤,我整块整块的肉身。我的前世或许就正镶嵌于这里某一块砖瓦与土地,而我此刻伫立于扎什伦布寺,就是为了让灵魂返程,与肉身相遇。
离开扎什伦布寺,夕阳拖着长长的羽尾在群山之巅冒着火光,飞鸟衔着夕阳回到了黑夜的窠臼,所有生灵已抵达了睡梦的归途。而我所有的情愫、叹息与行吟都已遗落于这片土地,等待黎明剖开我盘亘于此的宿命,献祭给饕餮的众神。
乘火车从日喀则回拉萨,我拿出背包里的《瓦尔顿湖》阅读,身边一位藏族小女孩一直紧盯着书上的文字,我望着她懵懂的面孔笑问:“你想看吗?送给你了,愿你也早日找到自己。”
(本文图片来自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