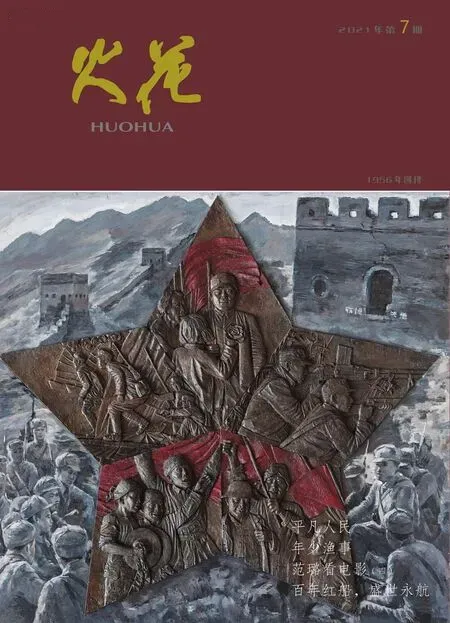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一)
鲁顺民 陈克海
2021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可以彪炳千秋、载入史册的年份。经过多年来全国人民不懈的共同努力,宣告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多年的扶贫工作中,发生过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我刊特刊发著名作家鲁顺民、陈克海创作的纪实文学《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以纪念这一段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历程。
第一章 赵家洼前传
一、村里来了工作队
2016年3月,岢岚县人大驻村工作队进驻本县定点帮扶村落。定点帮扶的村子叫赵家洼,属岢岚县阳坪乡。工作队一行三人,县人大农工委主任曹元庆老曹,县人大办公室主任科员周继平小周,还有一个县人大办公室主任科员陈福庆。当时就是工作队,也没有指定哪个负责。2017年1月,全县易地扶贫搬迁任务一天比一天重,县人大又派来财经委主任周胜贤老周。
老曹和老周,都是1962年生人,属虎,54岁,周继平则是1970年出生,不小了,46岁。只有小陈陈福庆,1976年生人,与两位老大哥差下一轮多,比周继平还小6岁,而且资历相对也浅一些,2016年才调回到县人大被任命为主任科员。当初三个人,后来是四个人,两老两少组成工作队。
从2016年3月一直到人大的车拉着三位的行李进村,老曹和小周似乎都愿意以小陈陈福庆为“班长”。从租赁房屋设立驻村工作站,到联络村“两委”班子,都是陈福庆跑前跑后。一来,因为陈福庆最年轻;二来呢,陈福庆对赵家洼很熟悉,村里好多人他都认识。
陈福庆1997年由忻州商业学校(现为忻州市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分配回县里,先在岢岚县西豹峪乡担任经济管理员,也即乡镇机关的“八大员”之一,后来调到阳坪乡,到2016年调回县人大之前,提任乡人大主席。
他在阳坪乡工作的时间不短。赵家洼村属阳坪乡,派他回来驻村帮扶,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最合适,是因为他最熟悉情况,他不做这个“班长”哪个合适?
他们租住的工作站,是赵家洼村马存明的房子。
工作队之所以租房子,是因为他们必须长住。县里规定,驻村工作队包点下乡,每周必须住够五天四夜,他们得住下来,沉下去。
新一轮脱贫攻坚开始,山西省落实“精准扶贫”精神,从2015年开始,从各级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优秀人员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
派选的驻村第一书记中,中央国家机关部委15人,省直机关单位506人,市直机关单位1475人,县直机关单位6483人,国有企业、事业单位916人;处级以上干部113人,女干部1275人,35岁以下干部2966人,都是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覆盖全省9896个建档立卡贫困村。
这还是第一支队伍,人数加起来,已经接近万人之多。
陈福庆他们在赵家洼工作一年之后的2017年,山西省再从省市县三级机关、事业单位选派10000名干部到乡镇挂职帮助工作,覆盖了全省1196个乡镇。
陈福庆和老曹、小周三人工作队,不过是山西省众多工作队中的一支,是两个“万名”干部队伍中的3人。
所以,县人大送他们到达村庄,包括铺盖在内的一应行李随他们进入临时租住的工作站。
村委会的房子坍塌得不像样子,院里的草长得有一人来高,多少年大门都没有开过,不能住,只能在村里租房。
陈福庆和房东马存明不熟,但跟他哥哥马贵明熟,马贵明也是阳坪乡的工作人员,早年做广播员,后来转成合同制干部,赵家洼村整村搬迁前,担任赵家洼村支部书记。
马存明搬到县城里住了,且常年在外头打工,农忙时才回村作务庄稼,房子平时就空在那里。房子空下好多年,三间正房还能住,另外还有三间危房。工作队进村,收拾正房,拆除危房,连房租带拆迁危房补偿,总共给了马存明一万元。
赵家洼是一个行政村,由小赵家洼、大赵家洼和骆驼场三个自然村组成。村委会就设在小赵家洼村。出县城,上干线公路,走7公里多左拐,跨过岚漪河,沿一条沟往西,经过一个宋木沟村,再过一个牧牛会村,拐过一架山梁,就看见沿沟坎排开的小赵家洼。小赵家洼西北2公里余,是大赵家洼,再进2公里余,才是骆驼场。“三个村子,谁也瞭不见个谁。”
算起来,小赵家洼村离公路最近,离干线公路只有5公里。骆驼场背后,一座大山横陈,林莽苍苍,大山的主峰矗立在钢蓝色的雾霭之中。大山的主峰名叫正沟背,属吕梁山脉。
岢岚县地处晋西北,北与河曲县、保德县接壤,西邻吕梁市的兴县、岚县,东则与五寨县相望,往南,就进入静乐县。河曲县、保德县、五寨县、兴县、岚县、静乐县,无一例外都是国家贫困县。几个“难兄难弟”簇拥在黄河左岸的版图上,是所谓集中连片贫困区域。数个贫困县集中连片,还仅仅是山西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一隅。
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域,山西省就有两处,分别是吕梁山和太行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共有58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其中有10个深度贫困县。
10个深度贫困县,与岢岚相邻的兴县、岚县、静乐县名列其中。
春节刚过,工作队驻村入户。岢岚山下的寒风像有人操着刀片在脸上一下一下细细地刮,刮得那个仔细。山里的汉子、婆姨,脸蛋儿都有一片老红,冷风刮的。积雪盈野,阳光刺目,脸冻得生疼。工作队先烧火温家,三间房子两盘炕,一炕是靠南墙的所谓“顺山大炕”,可以躺五六口人,另外一间靠窗户的则是一盘小炕。安顿下来,他们就可以入户走访了。
一行人分头入户走访,小赵家洼、大赵家洼、骆驼场,走访一圈下来,三个人面面相觑,连陈福庆都不敢再说他对这个村子熟悉了。
明知道好多人已经出迁在外务工,也明知道赵家洼跟其它村子没有什么区别,留下来的都是上年纪的老人,但赵家洼现在的情形让几个人都有些意外。
住在村里的只有6户人家,共13口人。
扳指头数:小赵家洼,住有5户,骆驼场已经空了,大赵家洼呢,还剩下1户。
王三女一家,老太太带着两孙辈,3口;曹六仁一家,老夫妻两个,2口;刘福有一家,老夫妻两人,带着90岁的老娘,3口;张秀清一家,夫妻两个,2口;杨玉才一家,夫妻两个,2口。5户人家,都住在小赵家洼,12口人。剩下1户1口,叫李虎仁,一个人住在大赵家洼一孔土窑洞里。
13口人,张秀清和赵改兰两口子还是壮劳力,一个49岁,一个48岁。下来数着的几户,王三女66岁,曹六仁58岁,刘福有69岁,杨玉才54岁,李虎仁已经71岁。
工作队驻村,寥落的村庄开始有了些生气。入户访问,几名队员很快跟大家熟络起来。陈福庆他们进村入户,到哪一户,都不空手,提壶油,抬袋面,要么一个人手里提一箱牛奶。陈福庆年纪小,推门就“大爷大娘、叔叔婶婶”地叫着,一村里十几口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亲戚上门也就是这个样子,何况人家还是“公家人”,是国家干部。村民们或搓搓手,或丢开手边的活儿,赶紧往门里让,赶紧让上炕。
老刘,刘福有,头一回听陈福庆叫大叔,愣了一下,马上脸红起来。阖村里头,老刘家的子弟最出息,孙子考上南昌航空大学,外孙女考上汾阳医学院,老刘说起来,满脸的骄傲。
山窝窝里出金凤凰,赵家洼走出大学生,当然不容易。
一个小村庄,能出两个大学生,而且出在一家,怎能不让人欣喜?
陈福庆更关心村里的日月,村庄的现状。他先从住房了解起。
岢岚县8万多人,有6.9万农业人口,算不得大县,但是县里村庄多而散,全县行政村202个,像小赵家洼、骆驼场这样只有几户人家的自然村就有115个。同处一个县境,村村不同,风俗各异。
陈福庆他们在工作站住下,打量租住的这三间正房。
陈福庆也是岢岚土著,家在岢岚县的三井镇。尽管三井镇在岢岚县说不上是富裕乡镇,但老百姓盖房讲究,虽比不得那些通都大邑来得精细与宏阔,但都是一水的木构起脊瓦房。梁、柱、橼、檩,包括起墙的砖,铺阶的石,都不敢有差池。
一栋房厦,是一个农民穷其一生梦想完成去,再加一个黑。低、矮、黑,起脊房架,染柱显然不太可靠,当地间还格外撑一根柱子。顶棚糊有“抑尘”(注:天花板),夜里睡下,动静可疑。不是房顶落泥屑,就是老鼠过境穿梭。墙皮脱落之后,露出里面的石块,石块垒墙,黄泥填缝,墙里墙外一律用黄泥抹面,远远看去,家家户户都是泥墙小屋,而且,年长日久墙体稍有变形。
村巷则一例泥路,遇雪遇雨,泥泞不堪。
最好的是老杨家的房子,相对宽展一些,屋顶上还覆着天蓝色彩光瓦,这一抹蓝色是村里唯一的一点敞亮颜色。就是老杨杨玉才的院子,虽然比起其他人家稍整洁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正户住人,厢房搭架储粮,院子里临时搭起一个棚子,存放着去年未出售的玉米。院落旁近,圈着一栏羊,有100只左右。
老杨家如此,家家如此。老刘家的牛喂在院子里,张秀清家的羊也喂在院子里,人畜杂居,卫生条件可想而知。低、矮、黑之外,再加一个臭,味道极不好闻。老杨说,这几年村里就他和张秀清家两群羊,过去有八九群羊,还没有进村子,就闻见空气里弥漫的羊臭味,成天鼻子里就是那个味道,真正上山有新鲜空气,一时还有些不适应。
老旧的房子,倒与留守在村里的这些村民出奇地浑然一体。
陈福庆跟老刘聊天,先聊房子。问咱们村里就没有人家盖新房子?老刘搔搔头皮,说:咱这村村,有30年没动土木了。
在乡村社会,莫说说起自家的村庄,就是说到自家,也没什么比“没动土木”来得更让人丧气。
乡间有俗语:兴盛人家,木泥两行;倒灶人家,神鬼阴阳。兴盛的、有生气的、有活力的、富足的人家,不能说每年都大兴土木,但每年对自家房屋进行修缮却必不可少。不兴土木,日月疲惫,病灾相因,只能求诸神鬼。
陈福庆说不出话。
二、赵也不是一个赵
一个春天,驻村工作队很忙。
岢岚县其实就没有春天。
春天只是一个概念。
诗人公木在1938年有诗:三月里,三月三,春风不上岢岚山。河滚水,鸟啼寒,塞外黄沙遮青天。几十年前农历三月如此,现在还是如此。过了“五一”节,杨树才把叶子吐圆了,赵家洼那里的桃杏树在山洼里探头探脑绽开第一朵花。然后,哗一下子,夏天不由分说就来了。前半晌还穿夹克,后半晌就得换T恤。
全县的无霜期特别短,一般初雪日为9月21日,终霜日为次年5月2日,最晚竟然到了“六一”前夕。平均无霜期为120天,最长139天。赵家洼所在的阳坪乡,平均无霜期只有105天,最长不过110天。
到了5月中旬,工作队才发现,村边田野里有草芽发起来,几天工夫就绿成一片。
有云在山间横陈,远处近处的山峦都变成一片墨绿。
他们忙什么呢?
精准扶贫,有六个“精准”: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不必详解其中具体内容,实施起来就是一套繁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通俗来说,就是“帮扶谁,谁来帮,怎么帮”。
工作队是带着任务而来。
岚漪河边冰消雪解,春耕即将开始。陈福庆他们对村里的情况也有了相当了解。
赵家洼村,在册54户115口人。经过一番筛查和评议,全村有22户共52口人建档立卡,确定为贫困户。按照总人口测算下来,贫困发生率在45%,远高于全省贫困发生率的平均值。
留守村庄的6户人家,有5户建档立卡。王三女是,刘福有是,张秀清是,曹六仁是,李虎仁也是。
过了“五一”劳动节,再过“六一”儿童节,山里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村里的人其实并没有把村子撂下,没有撂下村子的原因,是因为地不能撂荒。村里人陆陆续续赶回来耕作,准备把种子点下去。
赵家洼共有耕地1308亩,但其中大多不是坡地就是梁地,只有200多亩平整的“沟塌地”,沿村庄沟沿铺排开。坡地、梁地、“沟塌地”,都是旱田。
传统作物有土豆、红芸豆、玉米、胡麻、谷子、糜子、豌豆、黑豆、莜麦诸般。村里人挨着村落开辟少量菜园,种植白菜、黄瓜、西红柿、豆角,产出极少,仅足自给。上世纪70年代利用山泉浅表渗水打井一口,水量不丰,聊可灌溉。
农民撂不下土地,村落在春天显出生气。春天耕种是农民一年中忙碌的第一季,春耕罢是夏锄,夏锄罢是秋收。三季忙乱,果腹无虞。春耕要显得从容得多,耕地、覆地膜、追肥,包括播种,都需要雇工完成。牛工、人工、机工,分工明确,工资不等。
所以,春耕那么几天工夫,很快就完成了。
晋西北岢岚、五寨、神池等地,都是广种薄收,田野里的耕作很粗放。但粗放的耕作形式下,依然有着相当精细的制度。若不是有经验的农民,根本不知道其中讲究。
比方,必须讲“倒茬”,换算为标准表达,谓之“轮作”。简言之,就是一块地里,不能总种同一种作物,否则,既毁田力,又无效益。比方,同一块地,头年种土豆,第二年就需要“倒茬”种莜麦;种一茬莜麦过后,再需要“倒茬”,种豆类作物;豆类作物收获一季,来年再可以种莜麦、胡麻,或者土豆。这样,就可以把土地的肥力发挥到极致。
讲究“倒茬”,为的是保护和利用土地肥力,还有“间作”讲究。间作,即在同一生长期内,分行或者分带种植两种或两种以上作物的种植方式。赵家洼地区,一般是谷子、黑豆间作黄芥;谷子、糜子间作小豆、绿豆;土豆、玉米之间则可以间作小豆、黑豆、红豆;天旱年景,夏粮歉收,撒一季荞麦,还可以间作秋天的芥菜、蔓菁等等。
赵家洼坡梁地多,坡度大的地方,一块地上下的湿度、肥力不均匀,种三二年之后就精疲力竭。所以,这些坡梁地,肥力一旦降低,就需要弃耕撂荒,撂荒三五年不等,之后择伏天“扣荒”,俗称“扣伏荒”,即伏天耕耘翻土,要晒一个伏天,再经霜打一个秋天,还经积雪覆冻一个冬天,第二年冬去春回才能保证墒情,再可耕种。
陈福庆挨个儿做统计。村里有12户还继续耕种,总共100多亩,其余种不过来,都包给别人种去了。
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既然驻村,大家在地里忙,坐在屋里填表建档固然是项繁杂的工作,但坐不住,都是农家出身,哪里能闲下来?扳指头数数,留在村里的刘福有、王三女、李虎仁、曹六仁都上了年纪,大家商量,分头帮忙种吧。于是,三位工作队员也随村民下了地。
忙碌过一天,回村的人有些会留在旧屋子里歇一晚,第二天再继续劳作,村里的夜也不再寂寥。
村庄偏僻留不下人,布谷鸟会呼唤他们回来;山川贫瘠养不住人,碧绿禾苗下面的土地有一股血脉在;山在水在石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那成了个啥?
村庄在春天里才显示出应有的模样。
工作队员帮村里人干活,自然跟村里融在一起。三个人尽管是自己开灶,烩一锅菜,馏一笼馒头,但隔三岔五,老刘的老伴杨娥子婶儿就给他们端来烙饼,王三女大娘端来一笼莜面。一到晚上,工作站聚的人最多,说扶贫,讲政策,征求意见,当是题中应有之义。说罢正话,再说闲话。
但闲话也不闲。
俗话说,富人是穷人的孙子,闲话是正话的根子。
一族里,富裕人家子弟结婚早,贫穷人家则婚娶晚,一代两代下来,辈分距离就拉开了,五服兄弟,七老八少;而“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说闲话,实际上是说正事,这道理不用讲。村里没有闲话,农民闲话,机锋处处,信息量不一般。
就说起赵家洼的历史。
老刘,刘福有,是村里会说话的人。
老刘劳累一天,给两头犍牛上了草,还等着撞拌料,这空当,来工作站跟他们说话。老刘眼睛本来小,说话的时候,眼睛一挤一挤的。
老刘说,村子有年头了。
年头有多长?
实际上也不长。
老刘抬头想一想,仿佛能看见村庄第一缕炊烟冒起的情景。村庄仿佛是一位老人,迈出头一步走过来的模样还在他记忆里。
我们这个村,是乱家百姓(注:杂姓)一个村,一个村里有刘姓、李姓、赵姓、曹姓、杨姓、马姓、邸姓、田姓、崔姓、贾姓,过去还有白姓,人来自四面八方。
小赵家洼,大赵家洼,都是因为姓赵的先来安了家,山坡林地都是人家的,所以取名叫赵家洼。但两个赵家洼,却不是一回事,赵也“照”不到一起。
小赵家洼为甚(注:什么)叫小赵家洼?是因为最早来的赵凤梧他们家。赵凤梧老子叫赵玉娃,来的时候是弟兄两个,哥哥叫赵福义。两兄弟从静乐逃荒过来,先在这里安下窝,就叫下个赵家洼。
大赵家洼,是赵二毛家最早来这里安家的。赵二毛前些年就去世了。过去骆驼场有一通碑,是庙里的捐款人名字,我过去放羊的时候见过,领头的就是赵二毛的爷爷,人家是社首。
赵二毛的爷爷叫赵万和,从五台(县)东冶(镇)过来的。父亲叫赵正祥,生下赵二毛兄弟两个,哥哥叫赵五十七,赵二毛的儿叫赵润成,当过咱们赵家洼的村主任,那是2013年,意外车祸,死的时候才47岁。老子头年住了土家沟(注:坟墓),儿子第二年车祸。
和赵万和一起从五台过来的,也是一家赵,叫赵六小,和赵二毛他们是没出五服的从叔伯兄弟,就是一个老爷爷(注:曾祖父)。当年,赵六小的爷爷兄弟两个也是从五台东冶上来。怎么上来的?也是逃荒,先在这里安了家住下。
小赵家洼的赵,来自静乐;大赵家洼的赵,则来自五台。所以还不是一家赵家,“照”不到一起。
后来,七抽八扯来了乱家百姓。听老人们讲,来这里安顿的,都是从两个赵家租一些山坡地开荒,这样,两个赵家洼就慢慢人多了。
年代并不长,你看,最早,到我这一茬人,也就是赵二毛这一代,整个赵家洼也不过三代人,能有多长?
但说来就话长了。
老刘说到关键处,就不说了,呵呵笑笑。只是说,说来话长。“乱家百姓”,一家一个来历,话哪里能不长?
三、这一方土地
信息来得零碎,地边说一桩,井沿扯一件,当然,还是黑夜工作站叨叨得多。有一搭没一搭的,这些零碎信息还是被陈福庆一点一点整理出来,村落沿革逐渐清晰了。
正如刘福有刘大叔说,赵家洼村就是个由“碎砖烂瓦”垒砌起来的村子。
比方刘家,刘福有大爷笑说:我们村的刘家,也“流”不到一起,“不是一个刘”。
小赵家洼有三支刘姓。
刘福有这一支刘家,来自保德县东关镇新庄村。当年,刘福有的爷爷带着两个儿子三个姑娘逃荒至赵家洼落脚。
来了有多少年?
刘大叔说,往前推。刘福有1947年出生在赵家洼,已经69岁了。他父亲如果活着,是103岁,跟爷爷从保德来赵家洼,那时候还小。这样来估算,他们这一支刘家来赵家洼往少里说也有90年的历史。大伯后来走了口外(注:走西口),定居后套陕坝,即今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三个姑姑出嫁。
爷爷基本上没见过。但父亲说过,爷爷奶奶去世后,都安葬回保德祖坟。
刘福有是独子,刘福有自己则生1男4女。刘大叔说:我们这一门子,都是单苗苗往下走。

村里从保德县上来的人不少,跟保德有千丝万缕联系,老辈子人还亲戚走动,婚丧嫁聚都要知会一声,但后来,这种联系就渐渐稀了。刘福有父亲去世,因为路远交通不便,就地安葬在赵家洼。
保德移民上来的两支刘姓之外,另外一支姓刘的,是刘玉山家。刘玉山比刘福有年纪大些,73岁。刘玉山这一支刘姓,则是刘玉山一代从宁武迁来,单门独户。刘玉山现在有五个子女,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儿子刘卫东也有五十六七岁了。
赵家洼没有一户是岢岚土著,全是外来移民。刘家三支之外,曹家曹六仁由宁武迁来,到曹六仁这一辈共四代;张秀清的爷爷张六,则由内蒙古“中瓜地”(注:即内蒙古准格尔旗,过去称“准格儿地方”,民间讹称为“中瓜地”)迁徙而来;李虎仁的爷爷叫李增祥,由静乐移民赵家洼,后来从河曲县买了儿子李运来宝(保),生下虎仁、根虎、云虎弟兄三人。
骆驼场几户,李明居家,乃崞县移民;张二小、张三两家,河曲县王寺峁移民;还有一户张姓,张八八,大名张贵才,张八八应该是保德人,父亲早死,母亲改嫁张福财,张福财则是五寨人;贾高枝,兴县魏家滩移民;田孟珍家,五台县东冶移民;杨玉才父亲杨洪亮,15岁结婚,带一家人从保德杨家湾逃荒来到赵家洼。
历史上移民迁徙,并没有预先设定落脚地方。山西省历史上就是移民大省,北宋的“衣冠南渡”,明代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清代中期则是声势浩大的“走西口”,都上演过一出出悲壮的创业史。
像赵家洼这样在本省境内移民的现象也很频繁。
从河曲、保德过来的这些农民,早期移民,相对于黄河以北草地的“游牧”,则一直处于“游农”状态,两头跑,来赵家洼开荒,河曲、保德的地也没有撂下,两头有一个小气候差,种罢那一头,再来这一头,这一头收获之后,还需要回到那一头赶着秋收。
移民在此最后安家,是在抗战爆发之后。那时路途不靖,往来不便,没有办法才最后落脚。
赵家洼老支书马忠贤,原籍保德县王家滩村,4岁时,父母亲带5个子女逃难到岢岚县,先在油家沟,后迁小赵家洼才安顿下来。
邸建华1965年生,他听父亲讲,他们家在他爷爷那辈儿从宁武移民岢岚县,先在马家河,后在梁家会。不久爷爷被日寇枪杀,奶奶带着一家大小在赵家洼寻了一户人家才安顿下来。
还有许多户,或随母亲改嫁而来,或从别家过继过来顶门立户。
村里许多房舍虽然空了,但每一座人去室空的泥墙小院里面还装着关于家庭的故事。
陈福庆不禁感慨,刘福有大爷说这村子是“碎砖烂瓦”垒砌而成,真是一点不假。
陈福庆不知道,分布在吕梁山、太行山深处的数千山庄窝铺贫困村落,由一姓家族繁衍者绝少,大部分都是像赵家洼这样的“乱家百姓”杂姓村。有的村庄,五方杂处,方言未改,移民来源甚为驳杂,最复杂的村落号称“六省十八县”。这些村落的形成,大抵与历史动乱和灾荒关系甚大。
大致理清赵家洼的村落沿革,陈福庆才恍然明白,他在阳坪乡做人大主席的时候,阳坪乡各村,村村方音不同,整个村都说的是外地话,或保德话,或兴县话,或宁武话,当时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一下子,全明白了。
岢岚县在历史上就是边塞要地,北魏时因靠近岢岚山(注:即管涔山),始名岢岚,后汉设岢岚军,经唐代,历北宋,一直是军事要塞,元代设州,分立巡检,明代中期废州设县。
有地方学者考证,岢岚山虽然现今被称作管涔山,但为什么管涔山曾被称为“岢岚山”则不甚了了。实际上,“岢岚”乃“贺兰”汉字音转。这样的音转在晋北晋西北地区绝非孤例,神池县、宁武县、五台县老百姓方音里的“天”,读如“千”。学者考证,“千”乃“祁连”的音转,突厥语中,“祁连”就是“天”。“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何其哀伤!
当年,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千里跃进,直捣晋省腹地。管涔连绵,林莽苍苍,不由思念祖居的贺兰山,于是以“岢岚”名之。岢岚山,贺兰山,水清瘦,山素寒,望不断云飞雁去,念乡关。
学者考证有史实支撑倒在其次,岢岚作为古中国边塞要地则频频见诸史籍。唐代诗人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有诗《经行岚州》,诗曰:“北地春光晚,边城气候寒。往来花不发,新旧雪仍残。水作琴中听,山疑画里看。自惊牵远役,艰险促征鞍。”宋代诗人黄庭坚有《送顾子敦赴河东三首(其二)》,诗云:“月斜汾沁催驿马,雪暗岢岚传酒杯。塞上金汤惟粟粒,胸中水镜是人材。”到清代,岢岚作为军事意义上的边关地位不复存在,军备日驰,四境安然。《岢岚州志》有这样的描述:
岢岚环万山而为城,东西南北皆山也。层峦叠嶂,起伏迤逦。昔时流寇盘踞,干戈扰攘,民多被其蹂躏。今则边氛净扫,可幸安戢无事矣。北界五寨,东邻宁化。当年州卫交圻,兵民杂处,人亦苦其骚扰,今则汛防各守,幸经界既正矣。西北至正西,与保德接壤,水峪观、管儿沟诸处,萑苻每忧藏匿,今则盗薮悉除,亦幸山路遥通矣。西南至正南,与岚、兴接壤,赤坚岭、黄道川诸路,山林时虞阻隘,今则荆莽是辟,又幸石田可垦矣。顾此四境,寒谷荒崖,斜梁陡坡,虽有长流漪水诸河,莫资灌溉,袁志所谓“土田硗确,石骨崚嶒,旱则易萎,涝则易冻”,其势信有然也。地瘠则物无奇产,民贫则人自株守。利用无资,何所恃以厚其生也。是在披图者矜悯抚绥,庶蚩蚩之氓乃可生遂耳。
大致从清代开始,岢岚这块“地瘠则物无奇产,民贫则人自株守”的土地涌入大量“客民”,光绪六年(1880),聂鸿年在《续修岢岚州志序》中曾着意提到当地的客民问题:“第山高土瘠,绝少平原,地广人稀,苦无产殖,土人俭而不勤,业农贾者率多他乡外省之人,以故直、豫、秦、陇、川、楚客地错趾于境,往来靡常,而客富于主,又人丁欠旺,恒以外姓继暝蛉,岂五行有所克制欤?”《续岢岚州志》也载:“农,地广人稀,耕、必籍客户,每岁所获分给其半,其余所收仅足以糊一家之口。”
老支书马忠贤告诉陈福庆说:“咱们岢岚县就是一个养穷汉的地方,只要你勤快,能动弹(注:干活、劳动),不愁一口吃。”
“客民”与本籍百姓杂处,赵家洼一村如此,全县村落莫不如此。
就赵家洼村而言,这个不到百年历史的村庄,最大规模的移民涌入则相对较晚。根据村民叙述,陈福庆大致推算,一半以上的农户是在抗战时候才从各地迁移而来。
马忠贤80岁,他们家最典型。当年怎么迁来,如何安顿,如何生活,老人记得清清楚楚。
我是1936年生。老家在保德王家滩。因为甚往上迁?抗日战争那会儿,日本人来了保德,欺负得你不行,生活不了,这才上了岢岚。走的时候我才4岁,跟上我父亲母亲,还有我哥马忠良,两个姐姐,一个妹子,一家七口。
先在油家沟住了一年,住不住,又搬过小赵家洼,掏了个土窑子。也不是随便让你掏,地都是赵福义家的。人家是宁武人,来得早,整个沟里最先就他们一家人家,坡坡梁梁,都是人家的。这户人家养的有牛,有羊,地多,刨闹(注:收获)得可以。
问人家买了块坡地,给了16块大洋。掏出窑来,泥皮子也没刮,这就住下了。就是给人种地,掏坡坡,简单维持生活。保德人那会儿可多人上岢岚,后模嘴沟那边,一个村一个村的,尽保德家。先是伺候人家,过上几年后,又遇上减租减息,本来地里就产不下什么东西,再减也没法减,干脆就把地给你了。
日本人当时占着五寨、神池,经常到岢岚来扫荡。部队从中寨过来,沿着岚漪河,抓上当地人让带路,让人担水杀猪杀羊,就不让你回家,让你天天伺候人家。等到日本人走了,就高兴了,可算是走了。曾经日本人出发,要走哪里,好像就有通讯员得信了,一路上就有人来通知。我那会儿几岁岁,半夜三更,背上铺盖往山里躲上,怕得不行。来了被他们抓住,可就要往死里打,要刁(注:抢)东西。等日本人走了,这才敢回家。有事进城,你还得有良民证,有路条。
土改时候,又给分了些地,连坡梁地、平地,有个30多亩,这才个人有了地。那时候大伙儿过得都差不多,沟里头的好人家,也才一两户,一个是赵福义家,一个是白驼子家。赵福义家没后,接了个儿子。公私合营后,又把他儿子弄到供销社站门市。后来人家又搬到了东胜。白驼子家不知道是哪里的,他们到宋木沟多年了,都没生养,生养下也没养活,后来白驼子死了,老婆也跟人走了。
土改那会儿分下的东西也不多,就是些牲畜、粮食,两家才分得一头牛、一头驴,又从白驼子家还分得两间房、两眼石窑,就这么些。给人分了,没怎么斗争。将分下地时,个人刨闹自个儿的,种地还可以。
其实,不包括像老刘、老曹、老杨他们祖父自发从原籍迁入的“客民”,也不包括像老马家族在抗战初期自主性移民,从1943年开始,晋绥边区政府开始有计划动员河曲、保德农民前往岢岚开荒种地。
1943年3月春耕之前,晋绥边区二专署从河曲、保德动员100户农民移民岢岚。抗日民主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政府帮助移民找房子、耕牛和土地,供养给粮种,凭所在村公所和农救会证明借给资金,购买必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一个春天,100户移民共开垦100余公顷荒山。
1944年3月,边区政府统一安排,岢岚县二区在一个月时间就接收来自保德、河曲移民720户;是年5月,二区、四区再安排从河曲、保德、方山、宁武、神木、府谷等地移民1100户。民主政府为移民安排贷粮29625公斤,镢头250把,分配土地666.67公顷,调剂谷子和莜麦种子19875公斤。
赵家洼在抗战时期属于岢岚县二区,地处接收移民开荒的核心区域,赵家洼村民中其实有不少就是当年移民安置户。
被苦难、战争和灾荒驱赶着四处奔走的人们,沿着岚漪河进东川,入西川,东西两川成了好田园。他们拖家带口,他们面黄肌瘦,他们衣衫褴褛,他们仓皇而来,他们的身影倒映在岚漪河上,荒寂千载的山野有了人烟,也有了生气。这样,赵家洼和周边其它村落一样,慢慢人丁繁衍,村落中炊烟渐稠,鸡鸣狗吠。贫瘠的吕梁大山慷慨大方,张开怀抱,接纳下这些从四面八方赶来刨食谋生的黎庶苍生。
四、生产队当年
老贾贾高枝可能是赵家洼一个孤例。
他来得最迟,在1975年。那年,“农业学大寨正拧得紧”,老贾从故乡兴县来到岢岚,在赵家洼村落户安家。
贾高枝2016年68岁,家乡在邻近岢岚县的兴县魏家滩乡。虽然来岢岚已经41年,可一口兴县话怎么也改不过来。老贾说自己“嘴不巧”,口音硬,乡音无法更改。陈福庆跟他交流,有些话需要琢磨半天才能懂得。好在,陈福庆驻村入户访问,已经形成习惯,跟人交流的时候,打开手机录音,然后回去再在“民情日记”里整理出来。老贾的话不费多长时间就听懂了。
乡音不改,带来的交流困难可想而知。赵家洼虽然都是外来的移民,但老贾来得最迟,说话“侉里侉气”,大家都把老贾当外地人。彻底融入村落社会,势必就比别人来得时间长些。
乡音不改带来的困难还不止一端,老伴姓任,人问,老贾说:“迷些(注:兴县方言,意为“我”)婆姨,叫个任变嘞!”
大家从始至终都没弄明白她到底该是哪几个字,好在村里对妇女不直呼其名,一说起她来,就说是“老贾家里的”,谁都清楚。但是办身份证,难坏了乡派出所的户籍员,听半天不知道后两个字到底该怎么写,怎么写才是她准确的名字,电脑上输了个拼音,冒出一个“蚬”字。问老贾是不是这个字,老贾说:就那哇!于是,老伴的名字就确定为“任变蚬”。之后评贫困户建档立卡,给贫困户办低保,办大病保险和其它手续,都是“任变蚬”。
老贾说他迁到赵家洼的缘由。
1975年,还在农业社那会儿就来了,上来四十一年了,那时候二十七八岁。来的时候一家四口人,老婆子,还有两个娃娃,小子五岁,女子三岁。上到赵家洼,又生养了一个小子,一个女子。
因为甚往这上头跑?穷得过不下日子。
我老家是兴县魏家滩,当时是魏家滩公社。魏家滩可大了,一千六百来口人,四个生产队。从魏家滩上来的兴县人不少,少说也有十来户。兴县那会儿可是恓惶,每天就是个玉茭面,还吃不饱,净讨吃的。一到腊月,一村一村人到外头讨吃要饭,不然过不了年。上到岢岚,能吃上莜面、豆面,生活总算能维持住。改革开放后,人都回去了,我兄弟也回去了。魏家滩这会儿可以,有煤矿,也都移民了。
在魏家滩那,也是在山畔上抠挖个土窑子,到了赵家洼也是住的土窑子,打了两眼,门外头接个石头檩子。
我大(注:父亲)贾补存,还有我妈,还有我兄弟,1961年就迁到赵家洼,给人放羊,就在这给下了户。(19)61年,饿得人不行嘛。我弟弟叫贾近枝,来赵家洼之后才成亲,娶的也是兴县的。
那时候我已经结过婚,我大我妈一走,我家里四口人,全靠我一个。再一个是兴县那会儿抓得太紧,苦重。正是“农业学大寨”年月,女人们也当男的使唤,我一个月定的28天工,我老婆一个月定的是23天,顾揽不过来。苦重不说,还吃不下。我大给我带信来,说是赵家洼饿不着,我就带上老婆娃娃到了岢岚,虽然也是穷地方,倒是也能吃饱了。
也不是随便就让人搬。我大也是找了人家村干部。当时,大赵家洼地多,缺劳力,我二十七八岁,正是好劳力。村干部一听,就说来哇。给我把户口办了,这下就待了几十年。
来了也是年轻,先是让我当了两年保管,接着又当了几年会计,会计不当了,又当了一阵主任。就这么个。
赵家洼人少地多,做完了任务田,自己上山梁梁上拘个坡坡,也能刨闹吃点。农业社那会儿,只要你能动弹,上山开个荒弄点吃的,也没人来管。还是正经地多,掏荒地也没多少。就给你一点自留地,我那会儿五六口人,就给分了个亩数八分坡梁地。沟塌地里也能种菜,种些白菜、西红柿、辣椒。
生产队那会儿,我就没分过钱,家里人口多,全塌了口粮款。家里没劳力,就我一个硬劳力,老伴是个半劳力,挣个四五分工,一个工下来就挣个三两毛钱,要不叫全赔下了。我是在骆驼场,人口多,人均地就少,小赵家洼那边又好一点。骆驼场一年下来分不下个红,我家人口多,反过来还塌(注:欠)着的口粮款。直到改革开放,还欠队里好几百块。
1980年分开地,我弟弟回兴县老家。我人口多,就没有回去。父亲在赵家洼去世,去世之后安葬回兴县魏家滩。
赵家洼可以开荒,可以吃饱,可以养穷人,只要肯下苦,肯吃苦,拉破车养穷家没有问题。跟老贾贾高枝一样,刘福有回忆,赵家洼“最红火”的时候,应该也是生产队的那些日子。
合作化,公社化,大赵家洼、小赵家洼,还有骆驼场、宋木沟、赵二坡,五个自然村被划为五个小队,共同组成一个生产大队,统称为赵家洼生产大队。
五个小队,同处一条叫八达洼的沟里,沟里一条季节性河流,汇入到岚漪河。岚漪河为黄河一级支流,源出管涔山区荷叶坪的跑马泉,自东向西流,跨山越涧,最后到达兴县裴家川口与黄河相会。但五个自然村相距较远,“谁也瞭不见谁”,五个小队其实还是单独核算。一直到1978年,赵二坡、宋木沟才划到另外一个大队。
“最红火”的时候,赵家洼作为一级行政村,人口达到200多人,仅小赵家洼村就有120多人。
五个小队,小赵家洼最红火,全小队700多亩地,另外开荒100多亩,“五谷杂粮,甚也种”。其实,无论是农业立地条件,还是种植出产,小赵家洼并没有显示出什么特别之处,但他们不仅在五个小队中最突出,收入最好,而且在岢岚县也属于“上五类”好生产队。
老刘给陈福庆“倒学”(注:拉家常):
我们村的生活要好些,从没听见赵家洼有谁饿着,地里糜麻五谷甚也有。主食是莜麦、糜子、谷子,土豆就不用说了。那会儿还没人种玉茭子,豌豆、黑豆、高粱,都做了饲料。搞农业社那会儿,我们队里就有二十来头牛,还有驴骡之类大牲口,也是七八头。
那会儿,沟里的人们可辛苦了。河对面的田家会,他们队长为当官,任务要得多,把人们饿得。我们赵家洼没这,就是吃食堂饭那一两年饿过,那二年吃的都是定量,有粮也不叫你多吃,就是个玉米面和上谷子壳,后来就不要紧了。
口粮都有规定,要么三百八(十斤),要么二百六(十斤),就看每年收成,也有跟工粮。当年就是个搞平均主义,人都有了意见,说可不能这了,“谁受谁灰,谁坐谁成”(注:出力的不受重视,不出力的反而威风)。反映到大队去,公社也来了解情况,后来就定下,一个工分跟多少粮。这也不是死的,今年一个工分跟二两粮,明年可能就是三两。看一年打下多少粮食,看全村的总出工数,又把任务粮之类有的没的刨过以后,剩下的粮,这才能分。
赵家洼村实际早就实行包工制,锄一畦地算上几个工分,不管好懒,包给你,锄不好,下回还是你的,还得给返工,赖不掉。你一天锄完也行,三天锄完也行。你愿意不愿意,就这。
那会儿按规定,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都算一个全劳力。实际上,你在村里头,不管是七十岁还是八十岁,只要能动弹,都在种地。重活不行,轻松的活儿你也得参与,比方说老汉汉种些瓜,养点菜,也给你记半个工。年轻力壮的就得受最苦的,耕地担粪上山种树。老婆们娃娃们打些杂工,刨闹撒粪打土坷垃。都是按实际情况分工,不是死规定下你做甚就一直做甚。
这么一来,人们干起活来才有了信心。
最早实行工分包干制,小赵家洼的村民受惠不少,生活水平比邻村人好些,比保德县老家那一头不知道要高出多少。
1968年,刘福有21岁定了亲,需要回保德县老家跟亲戚们知会一声。受父亲派遣,刘福有头一回回老家,故乡亲人们的生活让他很吃了一惊。
当年,爷爷来赵家洼,带着三个姑姑。三个姑姑后来都嫁回到保德县去。大姑嫁到杨家湾,二姑许给崔家湾的人家,三姑则在桥头镇找了婆家。按说,在老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乡,这都是当地的富庶地方,但其实不是。
刘福有一路走来,先到杨家湾大姑家。大姑过得艰难,一日三餐,都是带壳子谷子窝头,实在是难以下咽,煮一锅土豆,不剥皮就吃。临走,大姑没什么给侄儿拿的,装了一袋带皮土豆,让他路上吃,他没要。路途遥遥,背一袋土豆怎么走?崔家湾二姑,临走给他带了两个红薯。桥头三姑家,刘福有报罢喜讯,歇过一栈要回岢岚,三姑干脆给他装了一袋带壳谷子窝头,他也没接。三姑又让他带红薯,左说右说,好歹拿了两个大的。
保德之行,仅是带壳窝头就难以下咽,刘福有并没多停,赶紧回岢岚县。回程进岢岚境,硬硬走了两天,在水峪贯住一夜店,再回到赵家洼。
结婚当天,姑姑们从保德赶过来贺喜,连两块钱的礼金都拿不出来,父亲做主,让账房写了“主收礼洋两元”。说是“主收”,实际上就是面子上好看些,到底是个“没收”。
赵家洼的生活水平明显比保德好出不知道多少。爷爷当年没办法来岢岚落脚,思乡过切,嫁女却又嫁回到保德县,从一个土窝窝推回到原来的苦窝窝,这都是为了啥?刘福有不明白爷爷的心思。
隔过苦不说,说好事情。好青年刘福有找对象就容易些,年近七旬,回忆起来满脸幸福。
老刘的岳父家在岚漪河下游的中寨公社坝湾村,赵家洼与坝湾村婚姻相通者甚多。有一回,刘福有给队里驮石灰,从城里拉上驮回赵家洼。在路上碰见未来岳父,一老一少相跟了有十里地,也就说了十里地的话。临别时老汉给刘福有说,他是赵家洼张秀清的姐夫,家里怎么样,你打问吧。话再明白不过,这是老汉看中了后生,想结一门亲哩!
回去跟大一说,大马上找到张秀清的爷爷张六小说项,亲事很快就定下来。一来,小赵家洼分红工值高,是个好地方;二来,刘福有能说会道识眼色,“好苦数”(注:有力气),肯下力,是个好后生。
坝湾岳丈果然没走眼,老刘家家底还好,婚礼花项总共280元整。一家三口都是好劳力,刘福有父亲平常给队里往来保德、岢岚两县之间倒贩粮食,手头毕竟“活套”一些。
婚礼酒席算不得好,但绝算不得差。有烟有酒,烟是三毛二分钱一盒的“白兰”烟,酒则从供销打来的上好“腰窝”老烧酒。酒席不丰盛,一盆猪黑肉大烩菜,然后就上糕。亲戚邻里来贺喜,出礼也不多。单人来,上五毛,双人去,上一块,舅舅过来算是最大的礼,上了九块钱。
结婚之前,刘福有跟娘老子还住在山畔上挖出来的两间土窑洞里,结过婚,就思谋盖房。那个时候,小赵家洼村的村民陆陆续续开始告别土窑洞,都到沟沿盖新房。那时候盖新房,不像现在可以雇专业的建筑队,都是村里人你帮我我帮你,大家换工,利用农闲时间,齐心协力,合力造屋。从积攒木料,再自制土坯,再挖片石,再备泥料,一来二去,三年两年,总算是盖起三间起脊石木结构的正房。
这三间正房,儿子刘永兵结婚就给了儿子。刘福有又盖了两间南房,南房并不大,只是经历三十多年之后,没想到最后用来接待党的总书记。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岢岚考察,来到赵家洼,入户三家,老刘就在这两间南房里接待了他。
马忠贤是赵家洼的老支书,到1996年才从支部书记岗位上退下来。他从小随父亲移民赵家洼,一辈子保德口音没变。保德人耿直、直率,也倔强,认死理。老马是赵家洼村公认的公道人,口碑甚好。
老刘说小赵家洼在集体化时候,大家都没有受制,生活比其它村强,得益于老马这个领头人公道,也得益于他的耿直,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随风倒,不跟风跑。2016年,老人80岁,陈福庆在老马闺女家找到老马,远远一个“陕甘大汉”走过来。
晋西北地方,说男人长得高大魁梧,就说这人长得跟“陕甘大汉”一样。
老人伸出一双手,像蒲扇那么大,笑容很好。毕竟“主政”赵家洼28年,风风雨雨,沟沟坎坎都是老人带着大家走过来的,他是政策落实者、村政决策者、农村变化亲历者,从集体化到生产队,再到农村改革开放,从赵家洼开始形成村落,再到“最红火”年月,再到衰落,都没离开过他的眼睛。他带着村民奋斗过,为村庄的发展谋划过,为村庄百姓获得劳动回报奉献过,当然,面对曾经“红火”的村庄走到今天这步田地,其忧伤、郁闷、沉思,要比别人更深一些了。
土改之后没过几年,就合作化了,分下来的地又归了集体。我先前念了几天书,后来娘死了,老子又娶了个后老婆,后老婆有小子,这下就不让我念了,前后也就念了个一年多。1956年,我二十了,就在队里给记工。
后来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都赶上过。后来,政策又回来了。
宋木沟和赵家洼、赵二坡一个大队,后边又和宋木沟、赵二坡分开。分开后一直没再变,生产队财产收入核算都下放到小队。小队经营了几年,直到联产承包。
我先是在队里当会计、统计,后边又当村主任、村支书。小队里由小队长领着种地,刨闹国家给的任务粮,然后再按工分算,一年下来,就是个受(注:苦熬)。
任务粮光赵家洼,一年得交个八九千斤。也是按年成好坏,最高也就是个万数,一般情况,就是个八千斤任务粮,一千斤油料,二十来个羊(注:晋北方言的口语中习惯将牛、羊等牲畜的量词表达为个)。分红也没个定数,一年和一年不一样,有时候七八毛,有时候五六毛,最多一个,像刘福有那样的壮劳力可以分300元出头。
副业也没个甚,就是养得些牲畜,贱买下,看见能多收两个了,就贵卖。大牲畜不能使唤了,也不能随便瞎买卖,归国家食品公司收购。
大田作物,主要种莜麦、豌豆、谷子、山药蛋,五谷杂粮都种些。
那沟里头在先(注:刚开始)也不种玉茭子。麦子产量也不高,一亩也就打个六七十斤,一年能打个万数斤。
在先那会儿没化肥,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上上化肥了,一亩能打个一百多(斤)。除过国家的任务,留下种子,剩下的就按人口分,一个人能分个五六十斤就算好的。糜谷像我们那个小村村,一年能刨闹个三万来斤。莜麦也能打个万数斤。山药蛋一个人一年能分个四五百斤。种些黑豆、豌豆,净喂了牲口。
牲口多,光赵家洼那会儿就有五六群羊,五百来只羊,还有三十来个大牲畜,骡马牛驴。这都是财产,别的村差些。
最红火时候,在沟里刨闹还可以,有点关系的,净往沟里跑。因为甚?分红大,吃粮多。
实际赵家洼生产条件并不好,赖地方,一出门就是灰山圪蛋(注:山包),净是坡梁地,平地没甚。有点平地,也是河滩宽,垫起来点土地。梯田那会儿也修了,修起也不行,遇上个下大雨,全冲塌。
我在村里闹(注:工作)那会儿,都是精耕细作,没把人们饿着。外头人也往村里迁,从兴县那来的就多,前后来了二十几家,改革开放后分田分地,又都回去了。这会儿,在村的也还有八九十口人。
林子也有,不大。自合作化以后,把沟沟岔岔的人都搬出来,不能种粮的地方,年年栽树,春去秋来,国家也号召,人们也有干劲,种不下粮食的地方全栽起树来。这会儿有万数(注:一万多)亩,种些松树、杨柳树、杨树、桃杏树。
1980年,联产承包开始分地,起初人们也有情绪,担心这,害怕那。分着分着,人们才盘算清楚,在一搭里(注:一起)也是不行,七余八扣,骗个肚子不饿都不可能。自己种,发现能吃饱饭了,你做甚也没人管,由凭你了,也没听说谁再受饿。
这个时候又开始缴农业税,加一些摊派款,七摊八派,乱七八糟,乡里头的,村里头的,都给人们摊上,我得一户一户收上去。
那会儿在阳坪乡,赵家洼也算是个可以的小村村,每年给国家的任务都是超额完成,剩余的口粮也解决了,人们也没饿着。
我闹的那几十年,还可以。在先那会儿,也是生活不好。村里没甚农机具,净种些梁地,就买下个铜草机、脱粒机、柴油机,这也是靠后了。还是七四(1974)年,村里通了电,我又给闹了个加工厂,推磨粮食再不用出外头。
接电当时也费了劲,没水利设施的地方,不给设备,不给架电。正好给村里打井,先组织人砍上木头杆子,把线接过来。再后来又农网改造,这才换上水泥杆子。
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我哥回了保德,我没回。我也是全凭种地,种了个四五十亩地。我有两个小子两个女子。
1967年,我当的赵家洼村主任,当了28年,1996年,满了60岁,老了,快退下去,让年轻人干去哇。
农业社那会儿,事可多下了。
所谓“最红火”的集体化时代,之所以“最红火”,其一村里人口数达到顶峰,生产大队超过200人,仅小赵家洼就有120多人,骆驼场都有23户几十口人。较之现在仅有6户13口人留守家园,真是要多“红火”有多“红火”。其二,村落集体经济保证了在短缺经济时代“饿不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地处偏远,各种政治运动冲击较少,接纳了许多外来逃荒者,救了许多人的命,一块相对安稳的世外桃源,怎么能不让人怀恋?其三,赵家洼“红火”的那段岁月,固然不能用“激情燃烧”“火红年代”这样的词语去描绘,但那里毕竟留下了至少两代穷苦农民为生存而挣扎、抗争、谋划、苦斗的岁月痕迹,披荆斩棘、拓荒开辟之功,任是谁都无法否认。
老人平静地叙述,陈福庆眼睛看着老人,静静侧耳倾听。他无法判断叙述者的态度是褒扬还是贬低,否定还是肯定,怀想还是留恋,他听出的,仅仅是一段历史的呈现。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