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从前慢故乡从前慢
陈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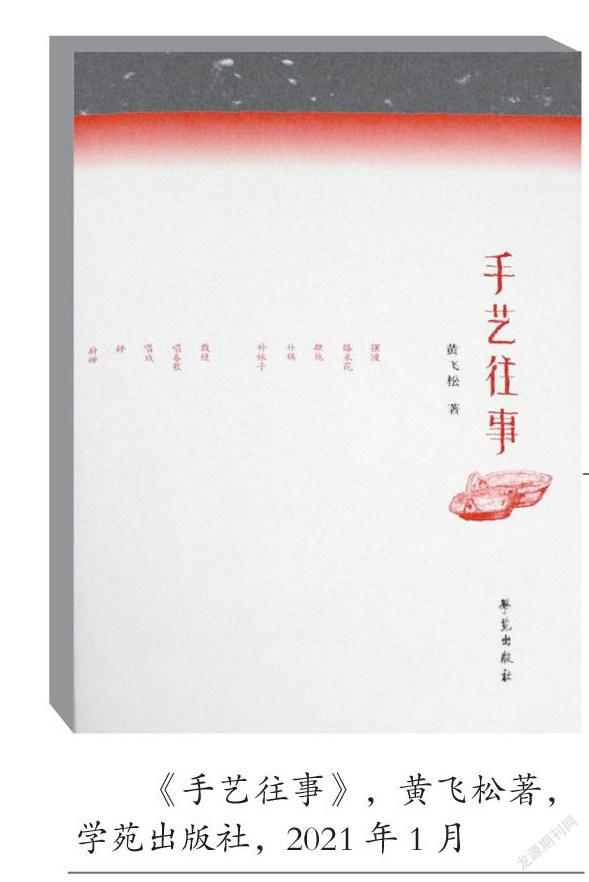
《手艺往事》编辑手记
泾县是个依山傍水的小城。上初中以前,由于父亲在水电站工作,我们一家住在远离城区的山坳里,即使后来搬进城,仍推窗可见远处延绵的青山。“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从小到大,父母都用这样的话激励我,让我好好读书,走到山外去,似乎山外才是更好的世界,更文明、更先进的所在。一路苦读,我也一步步远离故乡,最终在北京工作、结婚、安家。待自己一点点尝到了大城市生活的滋味,则愈发思念那个山清水秀、恬静温婉的小城。
前几年我来到学苑出版社工作,孟白社长一直偏重于出版非遗文化和民俗方向的图书,正是这个原因,才使我能不断接触到传统技艺、地方文化和故园风貌方向的书稿。逢人便说自己的故乡人杰地灵,是宣纸之乡,是千古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吟诵之地的我,一下子动了心思,自己可曾为它做过些什么?转眼已从事出版工作十余年,这点儿“手艺”是否可以为故乡做点什么?
在这样的思绪下,我决定从宣纸入手,做一些相关的选题。我辗转通过在老家工作的同学联系到了在宣纸研究领域多有建树的黄飞松老师。没想到黄老师数年前就与学苑出版社打过交道,这一下更是亲上加亲。自那时起,每次我回老家,一定会与黄老师见面,听他聊聊地方风物和故事。在一次闲谈中,黄老师说起自己写过一些地方手艺人的文章,也曾在文学类杂志上发表过,于是我便请黄老师发来给我看看。这一读,便放不下了。故乡生活的点滴过往,仿佛清晨面馆老板穿过氤氲水汽端来的那碗小刀面,鲜香热辣地放在眼前!我的爷爷做了一辈子的理发匠,奶奶以弹棉花为生,我是手艺人的后代,而现在做书时的心境,何尝不也是把它当作一门手艺?所以,与其说与黄老师签订这本书的出版合同是圆他的文学梦,不如说是圆了我自己的思乡梦。
出版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黄老师工作和社会事务繁忙,只能利用极有限的闲暇时间写作,而爬梳过往又总要耗费更多的心力,所以他写得不快。我知道这一切急不得,也不催他,只是不定期问问进展。结果一次他打来电话,懊丧不已地说自己为了随时随地写作,文章都存在一个U盘里随身携带,结果U盘突然坏了,数万字的文章就这样没了!我也很难过,但更怕他放弃,便对黄老师说:“我可以等,我们好事多磨,就把这当作老天的一次考验吧。”不知不觉两年过去,黄老师耐住性子把那些心底的文字一篇篇写了出来,即使是先前发表过的文章,他也重新创作加工,可以说,黄老师把匠人精神深深融入了这本写手艺人的书稿中。
裁缝、画匠、机匠、郎中、木匠、漆匠、石匠……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摆渡、唱春歌、放蜂、放簰、弹棉花、说书、磨剪子戗菜刀……是一段段尘封的往事。作为一个“80后”,黄老师笔下的这些手艺往事,有的我尚知晓,甚或熟悉,有的则闻所未闻。而时至今日,街巷中偶尔响起的那一两声吆喝,仿佛是繁复喧嚣的现代化交响曲中混入的杂音,干枯寂寥,旋即就被湮没了。不可否认,工业化社会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快捷与便利,商品丰富,物流发达,即使在小小县城,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买到世界各地的商品。我们不用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用再苦等游走的匠人和热闹的年节,只要花钱,满足即刻可得,可为什么我们仍怀念往昔?
我想,我们怀念的不仅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材料,“慢工出细活”这种行为所饱含的创造精神,更多的还有由手艺所交织串联起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情谊。正如黄老师在《裁缝》中写他父亲至今仍“每年都要与母亲一起,乘上两小时的车,到大山里看望一些人。这些人都是他年轻做裁缝时落脚的人家,这些老人都与父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剃头匠》中写剃头匠“先用热水将小孩头洗了,小心翼翼地拿着刮刀将小孩毛茸茸的头刮干净后,又拿出一只鸡蛋在小孩的头上旋着,边旋边念叨着‘鸡子圆,鸡子光,鸡子一抹光,不生瘌痢不生疮,头发胡子葱根样。小孩的妈妈听得笑呵呵,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早就准备好的红包”;在《杀猪》中写“我们全跟着杀猪匠,看着褪毛后的猪被一劈两开,耐心地等他们处理猪内膛。杀猪匠心领神会,在清理到猪尿脬时,会细心地将尿液放出来,用水冲了扔给我们。谁能抢到,这个便属于谁,而后找到口子对里面吹气。这就成了我们儿时玩耍的气球了”……“从前慢”的日子,慢中有情。
编书的时候,读着这些记述故乡旧事的文字,常常因几句方言勾起脑中许久未现的乡音,因某些特征极明显的人物描写勾起诸多回忆,或会心一笑,或黯然神伤,当然也有很多惊奇的收获——“啊,原来我爱吃的灌芯糖、炒发米是这么做出来的!”黄老师是个素爱对各种技艺做琢磨、做研究的有心人,所以这些回忆文章中,他从来不忘对手艺過程做细致的描述,同时,又约请朋友为这本书配上了数十幅手艺人做工场景的素描画,这也是这本书在文学性之外所富有的记录价值。而读完这本书,我也懂得了黄飞松老师之所以成为一位优秀的手工纸技艺研究者的心性养成之路。
《手艺往事》是一本可以慢慢读、细细品的小书,虽只描述皖南一隅,然其中人情妙味,四方皆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