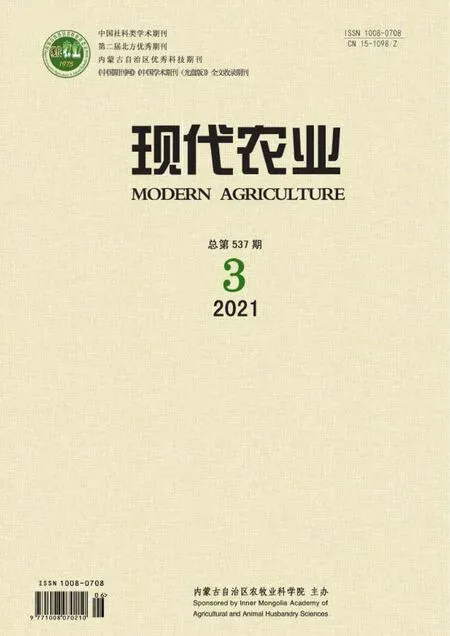我国乡村治理单元的调整逻辑
——以湘、鄂、粤三省治理单元改革为例
李裕良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 南充 637009)
在2000年初,我国乡村基层社会开始了合村并镇的改革浪潮,随后中央发起了一系列针对基层社会治理单元进行调整的号召与文件,对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单元进行调整,以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在这些政策文件的号召鼓励下,各省开始了对乡村社会基层单元治理的探索实践,2012年来,湖北秭归通过将自治单元下沉到自然村,缩小了治理规模;2016年湖南省、浙江省推动建制村的合并工作,实现单元合一、治理单元上移;2013年,广东省对乡村社会基层治理单元进行了实践探索,广东省各地纷纷调整自治单元,尤其典型的是清远市实现了行政单元上移、自治单元下移的改革。中国乡村基层治理单元从传统社会发展至今经历了多次变化与调整,治理单元的内涵与属性也在不断丰富,对治理单元的调整的逻辑无疑是想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那么对乡村基层社会来说,有效治理所遵循的逻辑是什么?如何才能达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1 治理单元概念的内涵拓展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对农村的治理是我国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乡村治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封建王朝时期的“县政绅治”模式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政社合一”模式再到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模式,不同乡村治理模式下对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单元进行了不同的设置。
在传统社会,县以下的乡村社会的管理实际上依靠的是一些非官方组织或者宗族势力来取代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比如乡里制度、保甲制度中设计的甲、保、乡、村等,而这些乡村组织基本上是当地有声望、家产的士绅、宗族势力组织,此时封建王朝社会的乡村治理就形成了秦晖所说的“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1]的局面,宗族他们虽然不是由官僚机构任命的政府官员,但却拥有来自人民群众的来自乡村社会的内生性权威,因此,乡村治理单元是由拥有血缘联系的宗族为单元的内生型组织,这种自治单元服务于农民的生产生活,而国家行政权力尚未渗透进乡村基层治理单元,因此,这时期的乡村基层社会的治理单元可简单地将其等同于自治单元。
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国家政权,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及合作化集体化运动,随着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逐步完成,我国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权力体系形成,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指的是将人民公社分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其中队为最基础一级,通过这三级的层层控制的人民公社体制完成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的同时乡镇被撤销,而乡村事务的管理和资源的分配全部由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三级实现,生产队作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单元,实际上集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管理功能为一体,“不仅含有政权组织的政治功能,还包括组织生产、宣传教育、社会服务等功能”[2]。从此时起,国家行政权力开始介入乡村基层治理单元,基层治理单元开始具有国家行政属性。这时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的内涵开始拓展,除传统的自治与经济职能外,行政职能逐渐被囊括进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单元。
随着人民公社体制弊端的不断暴露,农村地区随即放弃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以及人民公社体制废除的浪潮中,村民委员会在农民的不断探索中逐步建立,最开始的村民委员会建立在自然村一级。1998年在《村组法》中将村委会建立调整到了行政村一级,至此,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乡政村治”模式成立。由于国家的主动让渡,行政村作为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单元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权,发挥了其自治性,这种对村委会的行政规定性使村委会在执行政府的行政职能时有了更多的执行依据,行政村由此承担了大量的政府行政事务,因此这个时期的基层治理单元集经济性、自治性、行政性于一身。
2 新时期治理单元调整实践
进入新时期以来,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村干部与农民联系逐渐减少,农村基层社会出现了自治空转现象,为了解决此困境,各地地方政府纷纷对乡村社会基层治理单元因地制宜进行探索调整,其调整方式无外乎治理单元的扩大或上移,比如湖南省推动的合村并组改革;或者治理单元缩小或下移,如湖北秭归治理单元的改革实践;以及单元分设,既考虑行政单元的上移,又对自治单元进行下移,比如广东清远县的治理单元改革。
2.1 湖南省的单元合一:单元扩大及上移实践
2016年,湖南省发布了《湖南省乡镇区划调整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切实做好建制村合并工作的通知》以及《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工作的意见》后,开始了对地方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单元进行调整,逐步推进合村并组工作。
根据湖南省发布的关于合村并镇、合村并组的政策通知可以了解到其措施所涉及的方面主要包括对乡镇的合并以及对行政村单元的合并。不论是对乡镇进行的合并还是对行政村的合并,其合并措施都依据不同的地形划分了不同的标准,如对于行政村的合并而言,“平原湖区建制村人口2500~3500人;丘陵区建制村人口2000~3000人;半山半丘区建制村人口1500~2500人;山区建制村人口1000~2000人”[2],就合并结果看,对于合并后的乡镇和行政村,我们可以发现较之合并前的乡镇和行政村的情况来看,不仅所辖地域规模扩大了,而且人口规模也随之扩大,有效实现了治理单元规模的扩大和层级的上移。但就合村后的村庄治理效果来看,合村并组、合村并镇并没有减轻村干部的负担,村庄治理经费也没有减少,对乡村基层社会的公共服务并没有改善,并且由于“合村并镇”的决定并不是经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所以很多村民对合村抱有很大的意见。
2.2 湖北省的单元合一:单元缩小及下沉实践
在2012年以前,湖北省曾像湖南省一样,进行过合村并镇、合村并组的治理单元实践探索,但这种合并导致村民参与自治积极性不高,村民自治实践难以落实,被历史证明是不适合湖北省乡村基层社会村民治理的。为了解决这种困境,自2012年开始,湖北省地方政府在积极探索一种新的治理单元。例如秭归县实施的“幸福村落”建设,该建设计划以农民的基本诉求为导向,按照邓大才所说的“地域相近、文化相连、规模适度”[3]等原则将全县的185个行政村划分为2055个自然村落。划分后的自然村落在地域面积和人口规模方面都有所减少,每个村落的面积范围划定在1~2平方公里范围,人口规模方面规定每个自然村落安置最少30户最多80户人家。自然村落划分完之后还会在每个村落设立一个理事会,该理事会主要由村民推选产生的“一长八员”组成,其主要职责是为村落提供公共服务、开展公共设施建设、提供公共产品等非行政性事务,该理事会与村委会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在理事会需要村委会的支持和帮助时可向村委会提出申请。
湖北省秭归县的治理单元的选择与调整并没有对治理单元的复杂属性及功能进行考虑及拆分,所采取的措施是对建制单元整体的下沉以及对单元规模的缩小,由此治理单元也不断下移,治理规模随之缩小。
2.3 广东省的单元分设:行政单元上移,自治单元下沉实践
“无论是扩大、缩小抑或是上移,几乎都是将治理单元作为单一、不可分割的整体”[4],而广东省清远市对治理单元的调整则考虑了治理单元的复杂属性,其对治理单元的调整可概括为“行政单元的上移,自治单元的下沉”。2012年,广东省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中也面临湖北省秭归县所面临的治理单元过大,自治实践难以实现的问题。因此广东省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改革措施,总体上看,其调整主要表现为对行政架构的调整,以“乡镇-片区-村(原村民小组或自然村)”的基层社会建制单元体系代替现行的“乡镇-村-村民小组”建制单元体系。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
(1)将行政村发展成为片区,并建立片区公共服务站。清远市在乡镇以下根据地域、人口、面积等将乡镇划分为多个片区,并在片区设立公共服务站,作为乡镇的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责为承接上级派发的各种行政任务,为片区内的人员提供各项党政代办服务。公共服务站作为乡镇的派出机构,其服务经费由县或乡镇财政的专项资金统一拨付,人员的任用也遵从于乡镇人员人用标准,公开招录。因此,调整后的行政村实际发展为片区,不仅实现了管理规模的扩大,而且片区公共服务站的设立承接了政府在农村的大量行政事务,使得行政单元不断上移,减轻以往村委会过重的行政负担,有利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
(2)在自然村(村民小组)层面建立村委会,作为自治单元。为了方便群众自治,清远将村委会设立在了自然村或者村民小组一级,由此自然村或村民小组构成了清远乡村基层社会的自治单元。这样的将村委会由原来大的行政村设置在自然村或村民小组的自治单元改革的设置不仅实现了自治单元的下沉,而且实现了治理单元规模的缩小,有利于满足单元内部农民的共同利益需求,有利于激发村民开展自治的动力,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与湖南省湖北省简单的将治理单元合一,进行单元上移或者单元下沉的调整路径所不同,广东省清远市考虑到了治理单元的复杂属性,将单元分设,既对行政单元上移,又对自治单元下沉,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3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单元调整的逻辑
湖南省、湖北省以及广东省为实现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皆对其治理单元进行调整与重组,从重组的逻辑看,三省采取了不同的重组逻辑,而不同的重组逻辑归根结底是由于三省对治理单元改革所寄予不同的改革目标,这种差异化的治理目标导致了它们不同的治理路径。
3.1 行政有效逻辑
湖南省之所以采取一种单元规模扩大和层级上移的合村并组、合村并镇的改革方式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即以行政管理为目标调整治理单元。以此为目标,湖南省在对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单元进行改革于调整时,也只需考虑政府对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要达到这种高效的管理方式与服务方式,基于对成本、规模、效率等基本因素的考量,只有在大规模治理单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若是服务单元的规模过小,必定难以形成政府服务规模效应,服务成本因此会增加,长此以往会影响服务效率。可见,湖南省的“并村”改革完全是一种行政行为,是在行政逻辑主导下的改革方式,因此这种“行政有效”的治理方式对村民自治考虑欠缺,单元调整方式为自治消融于行政,调整路径实现单元合一,促进单元的扩大与上移。
3.2 自治有效逻辑
湖北秭归县采取一种将村委会设置在自然村的下沉和缩小治理单元的改革方式,其主要目标是为了方便群众直接参与自治,提高自治的有效性。而什么样的治理单元能够方便并且促进群众对自治的参与呢?自治的参与性与便捷性成为设置治理单元考虑的首要要素,而要提高村民自治的参与性,就首先需要考虑村民的利益,“面对农村内生的治理需求,利益相关的农民会自发地根据自身需求建立适宜的治理单元,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5]只有村民之间存在相关利益并且存在利益共同体,村民间才会产生集体行动。除了产生集体行动的动力,还需要考虑村民参与集体行动的便捷性问题,因此治理单元的设置还需要考虑地域规模,一般说来,治理单元规模越小,村民产生集体行动的阻碍会越小,参与自治也就越方便。可见,湖北省秭归县对治理单元的改革主要目标是为了实现村民有效自治,想要实现的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是一种“自治有效”的治理,而对于行政有效考虑甚微,因此,依托于自治逻辑,湖北秭归所进行的治理单元调整是将行政融合与自治,实现单元合一,促进治理单元的下沉与缩小。
3.3 行政与自治的均衡逻辑
如果说湖南和湖北对治理单元进行的改革都只单方面的考虑到行政逻辑或自治逻辑,那广东省清远市的改革则均衡了行政与自治。广东省清远市所实施的“将行政村发展为片区并且将村委会设置在自然村层级”改革的目标本就是双向的:即提高对农村地区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又激发乡村自治活力。基于这样的目标设定与治理单元的复杂属性,广东省清远市的改革措施就既要考虑对乡村社会服务的效率性又要考虑村民参与自治的便利性,因此,在这样的“行政有效”与“自治有效”的治理逻辑下,广东省对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的改革选择了将治理单元分设:通过设立片区与公共服务站将行政单元上移,通过将村委会下沉到自然村完成自治单元的下沉,既提高了服务效率,又使自治落地,实现了行政逻辑与自治逻辑的均衡,促进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如表1所示)。

表1 湖南、湖北与广东调整治理单元的逻辑对比表
通过三省对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单元改革的治理目标、路径选择与调整逻辑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改革治理目标决定了三省改革的不同逻辑选择与路径选择,导致不同的治理结果。湖南省基于行政逻辑实施的对治理单元的扩大与上移,的确提升了行政效率,实现了“行政有效”治理,却忽视了“自治有效”,导致乡村社会自治不足;湖北省秭归县基于自治逻辑实施的对治理单元的缩小和下沉,的确促进了村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自治,实现了“自治有效”治理,却忽视了行政有效,导致对乡村社会行政服务不足;而广东省清远市将治理单元分设——行政单元上移,自治单元下移的改革措施,不仅实现了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服务,而且方便了群众参与自治,达到了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4 结语
治理是治理主体基于一定的地域单元所开展的活动,因此治理单元的有效性决定了一定区域内治理的有效性。从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发展过程看,农村基层治理单元的内涵与功能属性不断发展,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自治单元理念,其包含的内涵逐渐丰富,所承担的功能逐渐多元。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的改革实践主要遵循三种逻辑与路径:基于行政有效逻辑的治理单元扩大与上移路径,基于自治有效逻辑的单元缩小与下沉路径,均衡行政与自治逻辑的行政单元上移,自治单元下沉的实践路径。这三种路径表明,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治理单元规模的设置与选择,而对治理单元规模的设置和选择需要权衡治理单元内各功能属性间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对自治与行政进行权衡。基层治理单元的规模应该设置在“既考虑行政效率,又考虑自治有效性”的规模上,即行政逻辑所能接受的最小规模与自治逻辑所能接受的最大规模。总之,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的选择与调整本身就是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的一种双向选择结果,只有均衡考虑治理单元的治理成本、国家治理能力与群众的内生治理需求,找回群众自治的单元治理才是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