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 夏
李岩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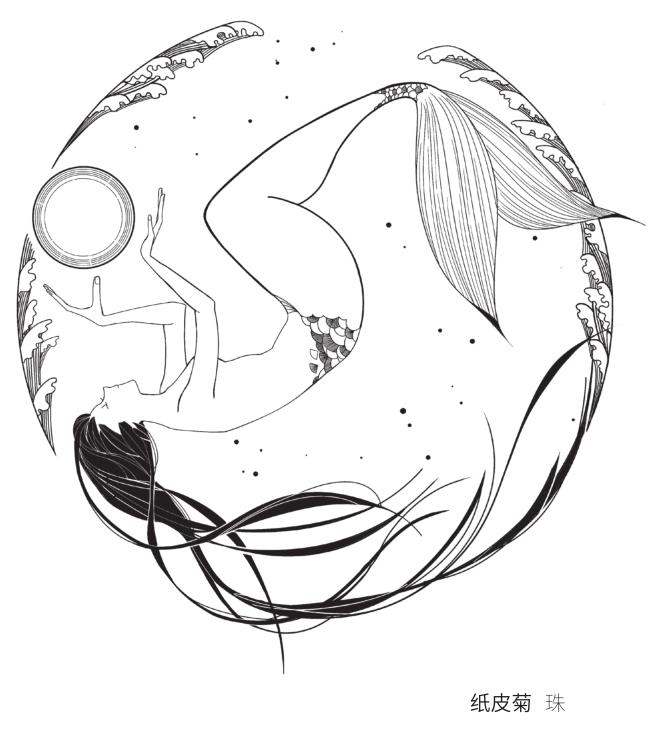
1
消毒水、白大褂与白墙,这确实是医院的气味。金属门外,罗文斌木然地坐在租来的轮椅上,恍如做梦。昨天,父亲听说他腿受伤,非要到市区来看他,他还百般阻拦,说不过是个小伤,养几天就好。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记耳光。
滑膜肉瘤。
一个完全没听过的名字。他打开百度,输入关键字搜索。“一种青少年和青年人中常见的恶性肿瘤,超过90%发生于四肢,约有一半病例会出现远处转移,多转移至肺部,早期通常为无痛的肿块……”他越看越心如死灰。
怎么会这样?他不过是为了减掉疫情期间胖起来的肉,在小区慢跑了两圈而已,肌肉拉伤或撕裂,已是他能想到的最坏结局。怎么会是肿瘤呢?肿瘤不都长在大脑或者五脏六腑吗?怎么肌肉里也能长出这种要人命的坏东西?
吵闹声把罗文斌拉回现实。父亲正在电话里和母亲争辩着什么,本就颇多皱纹的脸上,此刻写满了压抑和忧虑。但看到罗文斌望着自己,父亲还是努力挤出一点微笑:“这里查的也不准,明天我们到人民医院再看看。”
罗文斌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想要说些轻松的话,一开口却又没了精气神:“对,明天……再看看,走吧,先回家。”
父亲没接话,沉默地把罗文斌推到医院门口的公交站,扶着他坐下后,低着头耸着肩,推着空轮椅往回走。罗文斌目送父亲走远,站起来,尝试走两步,抽筋般的疼痛瞬间从小腿直达脑海。他放弃反抗,颓然坐回椅子上。
父亲从医院出来,招手打车。此时天已经黑透,路上的车极少。罗文斌看着隐藏在夜色中,佝偻着腰的父亲,有些伤感:教了父亲几次,父亲还是不会用滴滴打车。他喊住父亲,自己摸出手机,默默叫了一辆车。
车还没来,父亲手机却响了。原来是舅舅。他担心地问父亲:“文斌怎么样了,我听说是什么恶性的啊?”父亲偷偷瞄了瞄罗文斌,忙不迭把话筒音量调小,含含糊糊敷衍几句,以要打车为由挂断电话。
刚坐上车,在国外打工的大姑又发来视频。父亲脸上肌肉抖了一下,控制不住地抬高了分贝:“肯定是你妈到处说了,让她不要说,不要说。”他停顿一下,像是安慰罗文斌又像安慰自己:“根本就没确诊,我们还要去南京上海看呢,都不确定是什么病,她瞎说什么呀?”
罗文斌心中苦笑。在几十公里外的县城,母亲正陷入恐慌的沼泽。他说:“她肯定太担心了,也想找人说说吧。”
父亲不置可否,重又接通远在重洋的大姑电话。大姑说:“哥,这怎么了,怎么这种事就落在文斌身上了。”说着说着,她突然哽咽起来。父亲说:“你不要哭,这不还没影的事吗?”父亲话很硬气,可大姑的肩膀还是抖个不停。罗文斌眼眶一热,说:“没事呢,大姑,明天我们去南京看看,这小地方的医院不作数的。”大姑泣不成声:“好,你去了一定要告诉我结果。”父亲满口答应,挂断视频。
回到家,在父亲的搀扶下,罗文斌挪到床上。他翻来覆去,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也许是机器故障了,也有可能是医生误诊了。他总是心存侥幸,但内心深处的理智,让他接受了现实。回想之前的人生,碌碌无为,甚至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日子。
罗文斌突然后悔没有珍惜自己的人生。
2
看到那泛黄的照片时,解彩钰怔住了。十几年的时间一晃而过。数学书、菜市街、玄武湖等等,曾经的那些事与物飞速旋转。想不到,它还在呀。解彩钰捧着照片,像捧着什么宝物,小心翼翼地踱到沙发,把照片藏进包包。
钥匙转动的声音不请自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不由分说地闯进解彩钰狭小而杂乱的屋子。他抓起茶几旁不言自明的行李箱,变得张牙舞爪起来:“这些东西怎么回事?说!”
还是没来得及!她眼前一黑,像是被剥夺了看见阳光的能力。她转过身,鼓足勇气直视男人双眼,想理直气壮地宣告什么,嘴里溜出来的却是:“我……我要走了。”
“走?去哪里?”
“离开这里。”
“你能有什么地方去啊?”
她该怎么办,反抗还是束手?鬼使神差地,她想起那张照片。玄武湖边,一个花季少女,骄傲地笑着。背后不远,有个男孩,倚在假山上,比着剪刀手。在眼前男人越来越凶狠的眼神中,解彩钰一字一顿地说出男孩的名字:“罗文斌。”
3
罗文斌坐着轮椅,感觉世界和站着的时候完全不同。一切变得宏大起来,自己变得渺小而无助。他像回到了小时候,完全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掌控。不,他什么时候又掌控过这个世界呢。
专家的话始终在他耳边回响:“肿瘤有很多种,比如说肺癌就包括非小细胞癌和小细胞癌,非小细胞癌还包括腺癌和鱗癌,不同类型恶性程度都不一样。你现在还年轻,还是要抓紧治疗。穿刺吧,穿刺是金标准。我们现在没床位,你留个联系方式,一有床位就和你联系。”他来的时候还抱有期望,但现在,被击碎了所有幻想。他抬头看看父亲,父亲已经很苍老了,但依然卖力地推着轮椅,给他打气:“没关系的,我回去就找人联系床位。我们做个穿刺看看,说不定是一种比较容易治疗的肿瘤呢?大不了把肿瘤切除了,最多,可能影响走路……”
回到酒店,罗文斌躺在床上,一一回复来自同事们的问候。父亲也很疲倦,但是他仍在忙碌着,不厌其烦地和同学、朋友、亲人联络,千方百计打探谁在鼓楼医院有熟人,看看能不能安排到一个床位。有的人直白地说没办法,有的人说“我去问问”。父亲应该知道,这些“问问”能起多大作用完全不可知,他还是感动地各种道谢。
罗文斌很久没有和父亲同住一个房间。工作前几年,他周末还会回家。自打买房后,因为相亲、聚餐、加班等种种原因,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基本上,也就逢年过节,拎两瓶酒和父亲喝两口。现在,和父亲同住一个屋檐,他熟悉又陌生。
父亲终于打完电话后右胳膊用力地转起来,一连挥了十几圈,边挥边轻轻说“嘿”,像是给自己打气。父亲的肩膀居然还没有好?罗文斌想着。几个月前,父亲骑着自己给他买的电瓶车,不小心摔断肩膀住了院。当时,罗文斌匆匆看了父亲一眼,知道父亲不需要手术后,又匆匆赶回市区上班。这么长时间过去,他以为父亲早已好了。
父亲留意到罗文斌的眼神,笑笑说:“要加强锻炼,不然关节就不灵活了。你看,我这肩膀恢复得挺好。你知道吗?有的人和我差不多严重的,一直怕疼,不敢锻炼,到现在肩膀都抬不起来。”
4
罗文斌每天都能看到父亲不时地锻炼肩膀,接到大姑的电话。在生死边缘,亲情总是最紧密的。他告诉大姑,他想她了。这应该是他人生第一次对大姑说出这样的话。大姑的表情起先是惊愕,随后又欣然接受了他的想法。
第四天傍晚,有朋友告诉父亲,医院有床位,让他抓紧带罗文斌去住院。父亲忙不迭出去借轮椅,然后一步一步推着罗文斌。
“你肩膀怎么样了?”
“没事,推轮椅还是可以的。”
“我其实能走。” 父亲给罗文斌买了双拐,让他能扶着走路。但趁父亲出去时,罗文斌还是会尝试自己走两步。已经没那么疼了。他觉得自己可以走。这让他心中冒出一丝希望。
父亲说:“推轮椅算什么,小时候我还天天背你呢。”
罗文斌九岁的时候被摩托车撞过,左腿粉碎性骨折。打石膏康复的时候,都是父亲把他背到学校。那时,他理所应当地依赖父亲,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等他长大,才知道一个中年男人要处理的事情千头万绪。比如说,要忙着生计。父亲的人生应该不算太成功,始终拿着微薄的薪水,斤斤计较几块钱的得失,一生都艰难地盘踞在生他养他的小县城。
天已经黑了。防疫检查的帐篷依然灯火通明。父亲熟练地在手机上找到健康码,推着罗文斌进了大厅。等电梯时,罗文斌看到很多人或是裹着大衣,或是裹着被子蜷缩着,看起来像是要在这里过夜。罗文斌心情有些复杂。如果不是那“没有意义”的工作,他将没有医保也没有余钱,也许只能这样在医院里流浪。他想起自己开房间的时候,父亲感叹过“住旅馆真贵”。
罗文斌突然觉得,自己很失败。
5
屋子里黑透了。
解彩钰睁开眼,仰望四周,白日的一切都在和她捉迷藏。她在黑暗中吃力地寻找,吊灯在哪里,衣橱在哪,空调在哪。她觉得她已经抓住了它们,但也许,那不过是脑海残留的假象。身旁的男人已经打起了时断时续的呼噜,安心地睡着了。解彩钰不由得有些羡慕。她已经吃了半片劳拉西洋,以往,这已经足够。但今天,显然药效不足。她纠结半天,还是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箱子边蹲下,借着手机亮光翻出药来。她正准备起身,突然悲从心来。
男人并不爱她。即便她没把衣服从箱子拿出,男人也没有在意。他揍了她一顿,看着她的妥协,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就这么洋洋得意地哼着小曲,自顾自洗澡睡觉去了,完全不理会吃了败仗的解彩钰到底多沮丧。解彩钰苦笑,如果他能给予一点真诚的关心,她说不定都会倍加感激,甚至会小心翼翼地守护这点烛火,决不让它熄灭。
她缓缓起身,走到床边拿起水杯,试喝一下,水早已凉透。夏天,水也会凉透。她犹豫了一下,把半片药放进嘴里,就着凉水咽下。药像刀片,一寸一寸把她割裂。她被割成了两半。
解彩钰放下水杯,准备上床。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她余光扫到了床上的男人。突然,一个可怕的想法涌了上来。
6
这是一个有着三张床的病房。病房老旧,墙壁上的白色涂料已经呈现出衰老的黄色。
靠近门口的床上,罗文斌正静静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是他特意让父亲带来的。被车撞伤后,他就是学着保尔,百折不挠地忍痛康复。但此刻,看书的意义不止于此。他翻到52页,照片就在那里。就照片来说,倚着假山的他是主角,可对他来说,远方背景里的解彩钰,才是这照片存在的意义。如果,能和解彩钰在一起,这一生,才算没白活吧?不,幸好没和她在一起,幸好……
像是预感到什么,罗文斌把照片放回书里,倚在病床上。果然,也就几分钟之后,隔壁病房那个十八岁的男孩,又一次发出连绵不绝的“啊……啊……”,这一刻,整个世界只剩下这个房间、大哭的男孩以及快要崩溃的他。
滑膜肉瘤。
从病友的交谈中,他早已知道,那个男孩得的也是滑膜肉瘤。他不是那个男孩,没办法具体感受,但从那撕心裂肺的沙哑嚎叫中,他能明明白白地知道,他也会有这么一天,把嗓子喊破,失去一切体面?罗文斌内心泛起深深的恐惧,不由得涌起一种,爬到窗户上跳下的想法。他当然没有跳,现在,他还能克制住这个可怕的想法。但一个月后呢,兩个月后呢?
父亲从门外走进来,顺手关上门,以一种轻松的口吻说:“那小男孩家是农村的,特别穷。一年多前就发现大腿上长了瘤,但也不舍得花钱,就没管,一直到前几天摔倒了,没办法走路,这才过来治。”
父亲本来嗓门就大,喝完酒后嗓门更大,但今天父亲没喝酒,嗓门感觉比喝了酒还大。罗文斌知道,父亲是想告诉他,他发现得早,治得及时,不会那么痛苦的。可是,我也不是孩子了啊。罗文斌很想告诉父亲,这样的安慰没什么作用。但他几次张了张嘴,最终吐出的,只有空气。
护士悄无声息地推门进来,麻利地交代:“罗文斌是吧,换上病号服。一会准备去穿刺了。我提醒你,除了病号服其他什么衣服都别穿,连内衣内裤也别穿。”
护士递过一张纸,说:“这里有注意事项,你先看看。看完之后在末尾签个字。”
纸上内容很多,但罗文斌仍然清楚地看到关键内容:“手术涉及麻醉,存有0.02%的死亡率。”他问护士:“我会死吗?做这个手术我会死吗?”
护士怜悯地看着罗文斌:“一般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抓紧换衣服吧。”说完,她拉上病床帘子就走了。
帘子遮住了一切阳光,把病床包围得像一个棺材。罗文斌就在棺材里,脱掉衣服,穿上病号服。可他怎么扣,也没办法把松紧带扣紧。他拨开帘子,按响床头铃。护士过来问:“怎么了?”罗文斌有些难为情地说:“裤子的松紧带好像坏了,能不能给我换一条。”护士一下子笑了:“换也没用,这裤子一会还要脱的。没别的事我就走了。”
罗文斌还是觉得浑身别扭。想象要被脱掉病号服,他不由得产生一种羞耻感,感觉自己像是动物园里的动物。他来不及抱怨,一个护工已经把他推上车。不管他害不害怕,他注定要驶向那个地方。
7
解彩钰打开笔记本电脑,尝试登陆QQ,几次输入密码都不正确。QQ早已过时了吗?她自嘲地笑了笑。罗文斌早已丢掉QQ用起微信了吧。他是不是也帮别人注册微信号了?那时候,他会想起他帮她注册QQ吗?
上了年纪后,解彩钰愈发明白,兜兜转转遇到这些人,只有罗文斌真心地爱过她。分班后的两年,罗文斌每天都爬二十多级台阶,来到她的教室,给她辅导数学。她本是个考上大学都困难的人,最后成为博士,全赖他的帮助。每天晚自习放学,也是罗文斌陪她穿越长长的菜市街,看着她上楼才会离开。
她常常梦到那个菜市街。她始终记得,好几次碰触到罗文斌的肩膀时,都能感受到一种奇妙的火焰,从她的肩膀燃起。她战栗,她不安,脸烧得厉害。有时,她怕被罗文斌发现,拘谨得像个只会走路的机器人。有时,她会大胆地偷偷扭头,凝视罗文斌沉默坚毅的侧脸。也许夜路走多了,解彩钰喜欢上她最怕的黑夜。她几次想崴脚,或者佯装跌倒,顺理成章地靠近罗文斌一些。可内心的傲娇一次次阻止了她。她还是常常会不安地期盼罗文斌能牵起她的手,甚至拥抱她一下。可让她失望的是罗文斌只是默默付出,从无所求。
解彩钰往窗外探头。那个男人果然还在。这个宿舍,他是知道的。在没和他同居前,解彩钰一直住在这里。她知道男人会来,也大概知道,男人不放弃自己并不因为他爱她,只不过是不想丢掉一个可以四处对人吹嘘的名头。说白了,她不过是他的一面旗子。
她受够了。在那个失眠的晚上,她彻底想明白了。
第二天一早,她决绝地搬了出来,撤离了那个她曾以为会是她家的战场。出门的一刹那,一道阳光打来,如此耀眼,深深刺痛她的眼。她似乎听到男人的大吼:“你这不知好歹的女人,搬出去就不要回来。后悔了也不要找我。”她没有回头。尽管,她不知道路在哪里。
8
手术第二天,罗文斌就被“赶”出了医院。有十七个人在排队等着这个床位。
出院前,医生对罗文斌说:“穿刺结果要等一个星期,我们会电话通知。要是良性,那可能就要排几个月了。如果是恶性,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你住院。放心吧,既然给你穿刺,就会对你负责到底。电话留谁的?”
父亲刚想开口,罗文斌已经抢先报出自己的联系方式。父亲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最终还是选择沉默。罗文斌和父亲商量了一下,决定先不回家,还是在南京等结果。在宾馆办好入住,罗文斌点了外卖和一瓶酒。父亲几乎没什么爱好,除了喝酒,为这个,父亲没少挨母亲的抱怨。在母亲的教育下,一直到工作前,罗文斌都滴酒不沾。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会喝酒,直到他渐渐迈过三十岁这道坎。
父亲把酒倒出来,却没有喝。他说:“没心情喝。”罗文斌想,没心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许是父亲不想在这个时候,在他面前表现出脆弱。
“倒都倒了,少喝点吧,不喝也浪费。”
不知是“倒”还是“浪费”启发了父亲,父亲突然说:“你还记得,我骑车带你翻到过沟里吗?”
罗文斌笑笑说:“当然记得。”
那还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父亲骑着自行车载他,下坡时没掌好把,连人带车都翻到路边的沟里。酒瓶打碎了,酒汩汩地洒在了泥土里。如今,那沟早被填平变成了商业街,那自行车也早就退了役。父亲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老了。
父亲喝得并不多。以往,他一顿饭怎么也要喝个半斤酒。但这一瓶酒,他喝了足足五天。这五天里,罗文斌恢复得很快,他已经能够下地走路,看起来和往常并无两样,这让他总有一种虚幻的感觉,一切不过是场梦,醒来他还是健健康康,但左腿上那棕黑色的伤疤和不时的疼痛提醒他,他还是个病人。
9
那时,看见罗文斌时,解彩钰笑了。她根本想不到,在已经确定分班的暑假,她还能在几百公里外的南京,遇到这个傻里傻气的同桌。更想不到,明明他们一年之间也没说过几句话,她还是由衷地感到欣喜。她蹦蹦跳跳地挥手,大声喊着罗文斌的名字。
罗文斌没有反应。他像是中暑了,整个人是木然的。这让解彩钰的自尊与自信受到了极大的挫败。虽然罗文斌不爱说话,她还是可以感觉到罗文斌应该喜欢她的。是太热了吗?他应该像她一样,穿个裙子才好。解彩钰跺了跺脚,努力捡回自己的骄傲:“你愣着干啥,过来啊?”
他愣了一会,才后知后觉地跑了过来。他喘着气,双手局促地扭捏,满脸烧出血来。解彩钰笑了。罗文斌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做一个动作,但她已经收到了他的讨好。她又一如既往地占据了上风。轻松和自如都如潮水涌来,她可以轻松拿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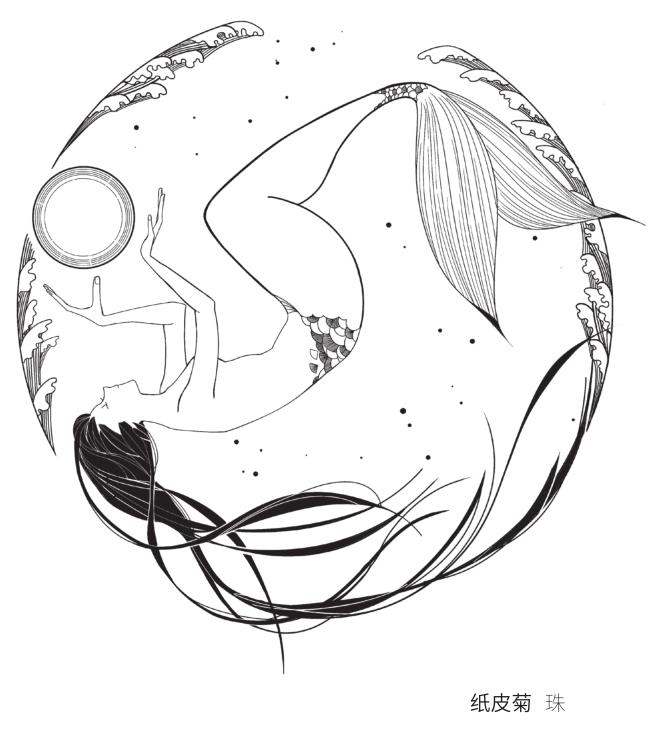
那是一个美好的仲夏日,他们说了远超一年的话。罗文斌始终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惹她不高兴。她却可以随心所欲地说着笑着。
但战局的转折,终究在她没发现的时候悄然来临。回家后,她拿到洗好的照片,却发现了罗文斌。她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却无人分享喜悅。她一次次渴望开学,终于等到了重归校园的日子。早自习刚结束,她就迫不及待地来到罗文斌的班级,大声喊他的名字。罗文斌抢先开了口:“我,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当时没看到你,但是照片洗出来,有你。”
“什么,你的照片里有我?”
“对啊。”
“你知道吗,我的照片里也有你!”解彩钰不可思议地尖叫着。
罗文斌眼神也浮上狂热:“真的?”
“真的,你看,我把照片都带来了。你的呢?”
“我,我的没带来。”
“那你看了我的东西,却没让我看你的,你要补偿我……”说完,解彩钰捂住了自己的嘴。罗文斌很爽快:“我记得你数学不好,我给你辅导数学吧?”
“真的?”
“嗯。”
那确实是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她的好朋友。她曾告诉他,有人追她。他却没有回答。她有了男朋友之后,便不再回复罗文斌的任何消息。
10
罗文斌转了两大圈,才找到记忆中的那个假山。他伫立了很久,很多事情像放电影一样从眼前流过。他忽然浮上一个念头,自己怕是马上要死了吧。不是都说,人死前,往事会在眼前闪现么?他没有感到太多悲伤,更多的是一种平静。突然,他像是感觉到什么,缓缓地回过头。
罗文斌曾想过无数种可能,在咖啡馆、高铁站或者转角的路口和解彩钰相遇。每个场景,他都有无穷无尽的话想和她说。但真正重逢这一刻,他却踌躇半天不知说什么了。
解彩钰脸上露出了不知道是快乐还是悲伤的复杂表情:“好久不见。”
“你还记得我吗?”
“当然。你结婚了吗?”
罗文斌愣住了,好久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直觉中,总觉得解彩钰已经结婚了。但此刻,他敏锐地察觉到,解彩钰应该还没结婚。他先是一阵狂喜,然后又跌入深邃的谷底。他思索半天,最后才说:“我结过婚了。”
解彩钰不冷不热地回复了一句:“哦。”
空气僵硬起来。罗文斌有些尴尬,又像当年一样,整个人似乎被施了定身法。他有些不舍。他不知道,是不是该找个措辞说再见。解彩钰主动谈起了她这些年的境遇。
罗文斌仔细端详解彩钰。她的五官依然生动,她的一切都那么令人熟悉,轻而易举把他拉回过去,一点一点让他陷入往昔。
讲到精彩处,解彩钰会无意识地吐吐舌头,而这总让罗文斌怦然心动,他几乎有种控制不住的欲望,想要在这人潮汹涌的地铁上,不顾一切地拥抱她。罗文斌觉得不可思议,他已经不年轻了,即便是年轻时,他也从不曾涌起过这样的想法。他忍不住猜想,如果不是腿上疼痛时刻提醒他,他很有可能已经抱了她。
离别的站台,罗文斌想说些什么,手机突然响了。他打开一看,是个陌生的南京号码。他敏锐地意识到什么,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去接个电话,你先别走。”說完,他远离了解彩钰几步。他余光看到,解彩钰的眼神里闪烁着复杂的神色。对方的声音已经传进鼓膜:“罗文斌吗?这里鼓楼医院。”
果然是医院打来的电话。是宣布死缓期限了吗?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肿瘤,难道是恶性程度最高的?他脑海里翻滚着,僵硬地回答:“我是罗文斌。”
电话那头的人懒得捕捉他的心情,程式化地叙述:“罗文斌,你的穿刺结果出来了。病理发现,你的腿部有大量凝固性坏死物,肌肉组织呈现纤维化,部分区域见薄壁血管影,结合病史,慢性炎症和血管坏死不能除外。”
罗文斌云里雾里。每一句话似乎都听得懂,但每一句话似乎都不明白,拼在一起的拼图更是让他无法理解。无论如何,“坏死”“纤维化”“血管影”这些字眼,都让他感到害怕。尽管他早做好准备,这一刻还是颤抖了:“这……是什么意思?我听得有些不太明白。能不能直接一点告诉我,没关系,我能承受。”
对方沉默了一会:“简单说吧,没有在你腿里发现恶性的东西。我们判断,你腿上可能有个血管瘤,因为运动破裂了,或者,你得了骨化性肌炎,急性发作了。而这些,我们都怀疑与你小时候受过外伤有关。所以,也造成了之前的误诊。还有疑问吗,没有的话,再见。”
不是恶性吗?那没有生命危险了?罗文斌有些发蒙,他木然地回答谢谢,然后挂断电话。他还是有些缓不过来,就像一个在山洞里独行的旅人,习惯了潮湿和昏暗,竟然不适应洞口扑面而来的亮光和新鲜空气。
他缓缓转头,发现解彩钰正站在地铁口,孤独地看着手机,在拥挤人群的衬托下,显得格外落寞。他的心突然刺痛起来,周身血液也不由自主地加速燃烧,沸腾的声音直入脑海。他清楚地意识到,他还有未来。一种念头也越来越强烈——他想要拥抱解彩钰,拥抱这个寄托他情感和记忆的女孩。不管她能否接受他,他起码要告诉她,他喜欢她。这么多年,一直喜欢着,这一刻,仿佛回到了那个十五岁的仲夏。
责任编辑 陆 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