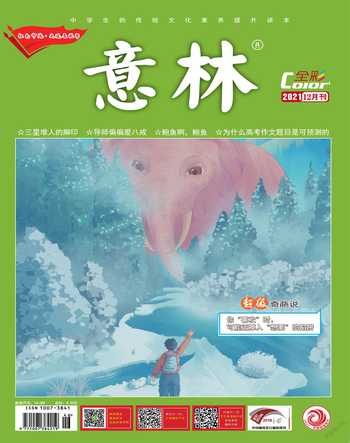伞的浪漫
王路

墨菲定律说,不小心把面包掉下来时,一定是沾着黄油的一面落到地上。同理,你带伞出门时,天气预报说好的下雨常常不会下雨;可每次忘带伞,降水概率或暴晒指数就会直线飙升。
因而无论是对伞多么挑剔的人,家中都难免会有那么两三把在地铁口买来应急的伞,通常是素色或格子图案,扔在家里闲置,弃之又可惜。
曾经的80后、90后广大电视儿童共同的记忆《新白娘子传奇》中,白娘子和许仙的缘分,就是从同船避雨、许仙赠伞而启。伞遂成为两人的定情信物,直到白娘子被压在雷峰塔下,依然是设法以伞向塔外的丈夫表达相思之情。伞之所以能激发浪漫想象,可能在于两个原因:一是雨和伞的结合天生自带从视觉到听觉的浪漫情调——当然,这里须是蒙蒙烟雨,绝不能是狂风暴雨。二是伞的遮蔽性,营造出的不但是一个物理空间,也是一个微妙的情感空间。
《新白娘子传奇》后来有数个翻拍和改编版本。版本一多,便免不了比较。雨中撑伞是必不可少的镜头,故而最常被拿来对比。老版本里,白娘子双手举伞,伞盖略微倾向夫君。短短一个镜头,撑出了夫妻情深、举案齐眉的味道。可到了2019年的新版本,不光许仙把伞偏到了自己一边,小青也自顾自地把白娘子晾在了雨里。不管爱情还是友情,都有点说不过去。由此可见,共撑一把伞,看似小事,却着实可以检验出感情的成色。无论爱情还是友情。那些肯在大雨中慷慨地把伞倾向你那边的人,都是值得珍惜的天使。
借伞、还伞,乃一个经久不衰的浪漫桥段。岩井俊二的《四月物语》中,松隆子扮演的女学生榆野卯月也正是借着一场雨,鼓起勇气与暗恋的学长交谈,留下了还伞的约定。
伞的浪漫不独为东方文化所有。18、19世纪的欧洲,贵族女性流行使用阳伞,发展出了一整套用于调情的“伞语”。譬如合起伞,握于右手,表示“跟我来”;左手撑起伞,表示“愿意与你交谈”;用伞轻触下巴,表示“我已另有所爱”;握住伞柄,在左侧摇晃,表示“我已婚”;把伞扔在地上,意为“爱你”,等等。
只能说,幸好我们生在了现代,不需要再熟谙如此复杂的撩与被撩的密码。
伞善于营造浪漫,其原因可能在于它本身就有浪漫的基因。即便是最普通平凡的伞,在雨中组成一个个移动的色块,也已经足够美妙。经典歌舞片《瑟堡的雨伞》开篇处,便是五颜六色的雨伞穿梭在人行道上的俯瞰画面。明艳的色彩,亦暗示着影片的浪漫基调。在大众熟悉的文学文本中,对伞最浪漫化的描述,要数戴望舒的《雨巷》。
美固然美矣,但这样忧伤而浪漫的雨中撑伞,需要至少满足三个条件:一是雨要合适,狂风暴雨、瓢泼大雨显然毫無浪漫可言,非温润的细雨不可;二是路要合适,须是“悠长而寂寥”的小巷。车流横行、一不小心就溅你一身泥点子的大马路显然不适宜;最重要的是,心境要合适。姑娘若是一手撑伞,一手提着电脑包,边走边咬牙切齿地在微信里和甲方周旋,当然也就再没有“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小时候,下雨意味着凉爽和快乐玩耍;长大后,下雨意味着积水、拥堵和挤不上的地铁。城市中,穿梭的伞像一道跃动的风景;风景之下,却是伞和伞互相碰撞、蹭一身水的狼狈。
但哪怕失去了撑着伞在雨中漫步的闲情逸致时光,我们依然忍不住买一把好看轻便的伞。也许为了打开那一瞬间的喜悦,也许为了能和我们一起撑伞的人。
(任羽天摘自《文学报》 图/ 李倩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