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明忽暗
李西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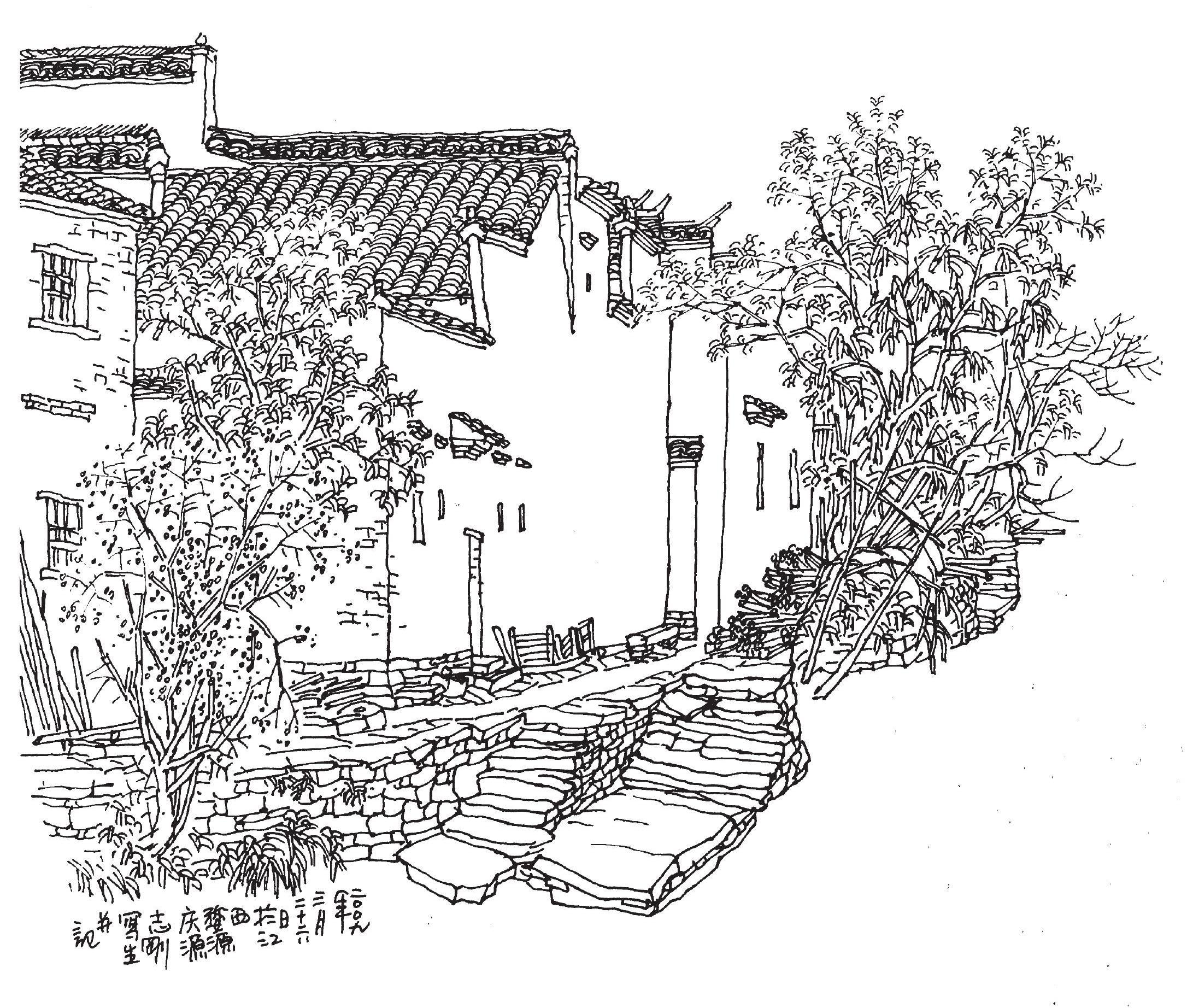
上篇
有时我会梦见阿婵,她像一只白蝴蝶朝我飞来,而我是一棵枯树,围绕着我飞了两圈,她就飞走了。我喉咙里发出暗哑的声音,企图挽留住她,可她还是义无反顾地飞走了。
阿婵是我的初恋,说是初恋也不准确,因为只是我的单相思,她根本就没有搭理过我。我是上高一那会喜欢上她的,她和我同班,坐在我前面一个位置。喜欢上她,是因为她长得白,柳镇那么多女人,数她最白了。她的脸蛋泛出白瓷般的光亮,刺得我的眼睛发痛。那时,她剪了一头短发,露出白生生的脖子,上课的时候,我的目光胶水般粘在她的脖子上,想入非非。我一直想伸出手,去摸摸她的脖子,可是我不敢。在阿婵面前,我显得胆小如鼠。
后来我想过,如果我胆子大一点,阿婵会不会喜欢我?这是个无解的问题。我喜欢阿婵,只是在心里,有很多夜晚,她会浮现在我眼前,想象着她和我亲昵的样子,心里燃烧着少年的欲望。可欲望之火很快就被父母吵架的声音浇灭,母亲变成母老虎的时候,父亲的声音就会暗哑。他们的吵架习以为常,我从来不相信他们有过什么爱情,而他们又相依为命。我发誓不要像他们一样生活,我要和一个心爱的女人相亲相爱过一生,那是我少年时代纯洁的梦想。那个心爱的女人是阿婵吗?这个问题让我心虚,于是,她的脸容会在黑暗中模糊,最后消失。
我把喜欢阿婵的事情告诉过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他是我最要好的同学朱可凡。朱可凡是阿婵的表哥,他和阿婵总是有说有笑的,我心里十分妒忌。有时放学了,我和朱可凡走在回家路上,阿婵也会和我们一起走,他们说很多的话,我一句话都插不上,仿佛是个多余的人。我会停住脚步,让他们先走,然后我独自回家。朱可凡和阿婵说着话,忘记了我的存在,我落在后面,他也没有发现,就是发现了,也只是回头看了看,继续和阿婵边走边说。那时,我就想和朱可凡绝交,不过,我和朱可凡的友谊无论如何也颠扑不破,因为我们臭味相投。
少年时代,物质并不像现在这样丰富,饿肚子是经常的事情。我和朱可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也许正是这个秘密,才使得我们的友谊坚如磐石。春夏之交是最饥饿的时节,很多人家的米瓮都空了,每家都节食,我家也是如此。早餐每人一碗稀稀的地瓜粥,到了第一节课结束,一泡尿撒掉之后,肚子就空空如也,唱起了空城计。朱可凡家里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俩和柳镇的其他人一样,饱受着饥饿的折磨。
有个晚上,我和朱可凡闲着无事,跑到柳镇收购站后面的小河边上捉萤火虫玩,我们把捉到的萤火虫放在一个玻璃瓶里,萤火虫多了,玻璃瓶就变成了一个荧光瓶,特别迷人。我想把这个荧光瓶送给阿婵,可我开不了这个口。朱可凡说:“余藤秀喜欢萤火虫,我们把瓶子送给她吧。”余藤秀也是我们同班同学,尽管长相一般,但朱可凡对她情有独钟,俩人经常眉来眼去的。我不好反对,附和道:“那就送给她吧。”我口是心非,心想,要是送给阿婵,那该有多好,说不定她会对我另眼相看。那个晚上月明星疏,我们发现收购站围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拖着一袋什么东西。我们躲在一棵柳树后面,看着那人用什么东西堆在围墙底下,然后扛起那袋东西,鬼鬼祟祟地消失在月光下。
我们走到围墙底下,扒拉开堆积的树枝和乱草,发现了一个地洞。我们都明白了,那人从地洞进入了收购站,从里面偷出了东西。那时的收购站,和供销社一样,是柳镇显赫的单位,主要负责收购一些药材、废铁废铜等物资。记得我和我父亲曾经将一口破锅送到收购站,换回了一块多钱人民币,那年月,破铜烂铁也是珍稀之物。我和朱可凡不知道那人从收购站里偷了什么,朱可凡却想出了一个主意,也进去弄点东西出来。他历来胆子比我大,比如说,他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勾搭余藤秀,我就不敢勾搭阿婵,尽管我那么喜欢她。朱可凡将荧光瓶放在草丛里,对我说:“我先钻进去看看,你守在这里,有人来了就扔个石头进来。”他钻进去之后,我提心吊胆,生怕朱可凡被抓住。过了一会,朱可凡在洞的那一边低声说:“李西虫,你听得到我说话吗?”我说:“可以听到,你快出来吧,我想回家。”朱可凡说:“胆小鬼,有我在,你怕什么?快,你也钻进来。”我有些迟疑,不过,还是在他的催促下,从狭小的洞里钻了过去。这是供销社的后院,一大堆破铜烂铁露天堆积。朱可凡不知从哪里找到一个旧麻袋,他朝麻袋里塞进了一些破铜烂铁,让我一起抬到了洞口,费了好大的劲才将那东西弄到外面。朱可凡又回到里面,伪装好洞口,出来后,又伪装好外面的洞口。他诡异地笑了:“以前我怎么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些宝贝。”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他说:“你的脑袋就是一砣铁疙瘩,你想呀,过两天,我们把这些东西卖回收购站,不就有钱了。麻袋里,估摸有三十多斤的废铁呢。”我没有说话,去寻那个萤火瓶,却发现萤火瓶不见了。那是卫生院打吊瓶用的装生理盐水或葡萄糖的玻璃瓶,况且里面还有萤火虫发出亮光,怎么就不见了呢。我找了一会,朱可凡说:“别找了,不见就不见了,明天管浦志高再要一个。”浦志高姐姐是卫生院的护士,那玻璃瓶就是他給我们的。
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舍,无奈,只好和朱可凡抬着装着破铜烂铁的麻袋,离开了现场。在夜色之中,我们鬼鬼祟祟地将破铜烂铁藏在小镇东头的一间破庙里,庙里挂满蜘蛛网的黑黝黝地坐立着,沉默地注视着我们。我先拔腿走出破庙,站在皎洁的月光下,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不远处传来几声狗吠,像是发现了我们丑恶的行径。周末,朱可凡找到我,去破庙里取出了从收购站偷出的破铜烂铁,拿到收购站去卖。我十分害怕,要是被收购站的人发现,那可惨了。朱可凡若无其事的模样,一直给我使眼色,让我沉住气。我在破铜烂铁过秤时,溜出了收购站,浑身大汗淋漓。等了好大一阵,朱可凡手上攥着一叠毛票,得意洋洋地走出来。那些破铜烂铁竟然换了两块八毛钱的人民币,朱可凡分了十四张一毛钱的纸票给我,说:“我们去买点东西吃吧。”于是,我们到镇上的食堂,一人买了两个糖包子,津津有味地蹲在小街旁边吃。有个小孩站在一边,流着鼻涕看我们吃,眼睛里充满了渴望,嘴角还流着口水。我掰下一块糖包,递给他,他赶紧塞进嘴巴里,连鼻涕也一起吞进肚子里去了。
我和朱可凡过上了几天好日子,我们第二次去偷东西的时候,却被埋伏在里面的供销社人员抓住了,因为他们抓住了一个盗贼,也就是那个月夜我们看到的那个人。朱可凡死活不承认,我吓得尿了裤子,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供销社主任和我父亲相熟,决定放了我们。他派人去找来了我父亲,气急败坏的父亲见到我,就是一顿暴揍,我被打得哇哇直叫。朱可凡冷冷地看着,一副没脸没皮的样子。见打得凶,收购站站长说:“老李,别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把孩子领回去吧,他们也没拿走什么,算了,算了。”尽管如此,我家还是损失了一只大公鸡,父亲不欠人情,大公鸡送给了收购站长,那公鸡可以换多少柴米油盐呀,反正我觉得亏大了。
朱可凡和我就断了去收购站偷东西的念头。
那年的暑假,朱可凡总是和余藤秀约会。每次约会都是在晚上,而且,朱可凡都会叫上我。余藤秀的家在一条巷子里,朱可凡和她约好了暗号,他在巷子口学两声狗叫,余藤秀就明白了,她就会偷偷的溜出来。我和朱可凡走在前面,余藤秀一个人走在后面,躲躲闪闪的。出了镇街,来到河边,余藤秀就欢腾起来了,说话还特别大声。朱可凡说:“你再这样大声说话,我就回家了。”余藤秀这才压低了声音。于是,他们俩钻进了河边的小树林里,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勾当,偶尔会传来余藤秀的一声娇笑。我像个傻瓜一样坐在河边的草地上,给他们望风,如果有人来,我就放声歌唱,小树林里顿时一片死寂。说实话,我极不情愿给他们当看门狗,但是想到我和朱可凡是死党,况且阿婵是他表妹,兴许他可以帮我追她,就忍受了这种不堪。
那个晚上,我们送余藤秀回家后,我对朱可凡说出了心里话:“我喜欢阿婵。”朱可凡笑了,笑得十分恶毒:“就你,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阿婵她爸爸是吃商品粮的,在县城工作,他们一家迟早要搬到县城里去住的,你恐怕高攀不上吧。”朱可凡轻蔑的话语,令我十分恼火,当即和他吵了起来。吵着吵着,我们就扭打起来。夜已深,我们吵架影响到了他人休息,街边的一扇门开了,一脸盆凉水泼出来,浇在我们头脸上,我们才松开手,我恼怒地悻悻而去。第二天傍晚,我和父亲从田野里回到家,就看到朱可凡嬉皮笑脸地坐在我家的门槛上。他站起来,把我拉到一边,低声下气地给我赔礼道歉,并且答应去和阿婵说。他答应帮我追阿婵,我原谅了他。
两天后的那个夜晚,我们去找余藤秀的路上,朱可凡兴奋地告诉我:“阿婵说,你还是蛮不错的,虽然个子矮了点,她还是可以和你做朋友的。”仿佛一股春风,吹绿了江南岸,我心中兴起了波澜。我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傻笑。这个晚上,我心甘情愿的当他们的看门狗,还不停地打着手电,在河面上照来照去。河水汩汩流淌,像是在唱欢乐的歌谣,那是我心底流淌出的歌谣。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我听到了一声惨叫,那是余藤秀从小树林里传出的惨叫。紧接着,朱可凡跑出了小树林,来不及和我说什么,就飞快地跑了。我冲进了小树林,发现余藤秀倒在地上,抱着脚,痛苦地喊叫。原来,她被一条蛇咬了小腿,白皙的腿上,两个小洞洞,流出了暗红的血。我没有想到朱可凡会逃掉,太不是人了。对于被蛇咬,我们从小就有些经验,我脱下背心,将余藤秀的小腿扎紧,然后背起她,疯狂地朝卫生院跑去。
我救了余藤秀一命,可是我担了恶名。所有人都认为我和余滕秀早恋,特别是她父亲还跑我家里闹腾了几次,害得我挨了几次父亲的毒打。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也另眼相看,在我后面指指戳戳,关于我的蜚短流长,弥漫整个校园。最要命的是,美丽的阿婵看我的眼神也充满了鄙视,朱可凡像个没事人一样,他和余藤秀都没有出面澄清事实,让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默默地远离了朱可凡,他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我也再不会和他有什么瓜葛。我的成绩也一落千丈,并且产生了厌学的情绪,经常逃学,一个人坐在河边,望着流淌的河水发呆。最终,我还是辍学了,和我堂叔学做泥水匠去了。
那时,我堂叔在一个山村里承包了大队部两层楼房的建筑。我的心里长满了野草,没着没落的,心里有时还会想起阿婵,想起她白瓷般的脸和脖子,那是无望的想象,越想就越凄惶。可以说,那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日子。几个月后,我回到柳镇,听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那件意外的事情,竟然和阿婵有关。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同学中,还有一个人喜欢阿婵,而且是丧心病狂的喜欢,那个人是我们的班长沈小如。沈小如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是老师们的宝贝,如果沈小如没有喜欢上阿婵,他上大学一点问题都没有。几乎所有人都看走了眼,沈小如疯狂地喜欢上了阿婵。可是,他多次的表白都被阿婵拒绝,而且阿婵把这事情告诉给了朱可凡,朱可凡又将这事情告诉给了他杀猪的哥哥朱可平。朱可平是个粗人,就找到了沈小如,把他拖到偏僻的地方,暴打了一顿。如果朱可平不打沈小如,沈小如可能还不会爆发,年轻气盛的沈小如跑到他父亲开山采石的工地,偷了几根雷管,绑在了肚子上,手上拿着火柴,四处找阿婵。那时阿婵和母亲在池塘边的菜地上浇菜。沈小如站在菜园外面,大声说:“阿婵,你答不答应做我女朋友。”阿婵说:“谁要做你女朋友。”阿婵母亲是个善良的女人,一直劝沈小如回家,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了再考虑终身大事。沈小如已经昏了头,阿婵母亲的话就是耳边风。
沈小如冲进了菜园,扑到阿婵面前,撩起衣服,露出肚子上的雷管,吼叫道:“阿婵,你要不答应我,我就和你同归于尽。”阿婵吓坏了,哭喊出来。阿婵母亲挡在了他们之间,大声说:“你要死自己去。”沈小如脸色苍白,浑身瑟瑟发抖,他颤抖着划着了火柴,点着了引线。母亲保护女儿的时候,会爆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她想一头母狮,朝沈小如扑过去,一直把他推进了池塘。水中响起了沉闷的爆炸声,冲起了一丈多高的水柱。如果沈小如没有落水,后果不堪设想,好在雷管在水中爆炸,威力减弱了,沈小如的肚子虽然炸破了,但还是救回了一条小命。
听到这件事情,我十分吃惊。
阿婵从那以后,就在柳镇消失了,去县城里念书了。过了一年,我内心平静了许多之后,也离开了柳镇,到西北从军去了。在部队的时候,我偶尔还会想起阿婵,想给她写一封信什么的,可是没有她的地址。她后来怎么样了,我也一无所知。我只是从父亲的来信中,得知朱可凡考上了福州的公安学校。父亲说,朱可凡走时,找过他,对他说出了余藤秀被蛇咬那个晚上的真相,父亲没有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我母親得知此事后,和父亲又大吵了一架。母亲可怜我,问题是,可怜有什么用,仿佛都是命运的安排。
下篇
去年春天,我回了趟老家,因为父亲摔了一跤,跌断了髋骨,需要动手术,换一块人工骨头。离开上海前,我妻子宋卉开了个玩笑:“李西虫,你回老家,能够碰到阿婵吗?”她一直记着这个名字,多年前,和宋卉谈恋爱时,我就讲过那段发生在1980年代初期的小镇故事。我笑了笑说:“我要见到阿婵,你会吃醋吗。”宋卉云淡风轻地笑了:“我吃什么醋,也就我这样的傻女人才会喜欢你这种乡下人。”宋卉以前是个女兵,她当兵的时候,我已经提干了,在机关负责新闻报道。她也爱写点东西,是通信连的笔杆子,经常来给我送稿,一来二去,我们俩就有了感情。她复员回上海后,我以为这段情缘就断了,岂料一年后,她回到部队要和我结婚,于是,我们就成了夫妻。后来我也转业到了上海,成了上海的一个小市民。我们的生活波澜不惊,反而是我少年时期的一些故事,会给宋卉带来无尽的想象,其实我不太愿意回想,想起来总归心里有点痛。
我中学同学浦志高是县医院的院长,我找到了他。浦志高还算热情,蛮给我面子的,说是要让最好的医生给我父亲动手术。父亲有些恐慌,他八十一岁,从来没有动过手术,我安慰他,不会有事的。其实我和他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话说,他和谁都没有什么话说,甚至没有朋友,他所有的话语都用在和母亲吵架上了。我凝视着躺在病床上苍老的父亲,想起少年时代一次次对我的暴打,心里有些波动,但是我已经不再恨他,一生辛劳的父亲,已经是一根枯木。他的眼睛里饱含着孩童般的恐惧,我尽量的不让他担心,此时,我是他的安慰剂。我微笑地对父亲说:“你放心,不会有事的,医院院长是我同学,他会用心给你治疗的。”恰好这个时候,浦志高来到了病房,礼节性地看望我的农民父亲。浦志高走后,父亲脸上舒展了些,我相信他心里有了安慰。我弟弟小声对我说:“要不要给浦院长塞个红包,这样保险些。”我点了点头。
父亲手术前那个晚上,我把浦志高请了出来,在一家饭馆。浦志高不喝酒,只是喝果汁。我们聊了些同学间的事情,说到了朱可凡。因为长期在外,和同学们也没有什么联系,偶尔回柳镇,也是匆匆忙忙来去,不会去问及他们,对同学们的事情知之甚少,浦志高说朱可凡现在发达了,财大气粗,口气中有点不屑。我说:“他不是警察吗?”浦志高冷笑一声,说:“早就不是了。”接着,浦志高就讲起了朱可凡的事情。
让我意外的是,朱可凡还是和余藤秀结了婚,当时余藤秀被蛇咬,我背着她去卫生院的路上,她边哭边骂朱可凡是王八蛋,以后再不会搭理他了,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几乎把柳镇人最恶毒的骂人的话都说遍了。朱可凡公安学校毕业后,分到了柳镇隔壁的赤岭乡派出所工作。余藤秀没有考上大学,连中专也没有考上,就在柳镇的小街上摆摊,卖些鞋子衣服什么的。有一天,朱可凡回柳镇,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神气活现的样子。路过余藤秀小摊时,余藤秀眼睛一亮,喊了声:“朱可凡——”朱可凡看到她,像见到鬼一样,撒腿就跑。余藤秀气得七窍生烟,破口大骂,直到不见了朱可凡的踪影。余藤秀一直没有恋爱,父母亲一直催着她出嫁,她就是无动于衷,动辄和父母亲吵架。通过和父母亲吵架,余藤秀练就了吵架的好功夫,柳镇人要是和她发生争执,休想占到什么便宜,最终父母亲也怕了她,不敢轻易和她提婚嫁之事,由她去了。因为她吵架出了名,也没有人敢到她家提亲,谁也不愿意娶她上们,请神容易送神难。
余藤秀见到朱可凡后,心里就有了想法,她打听到朱可凡还没有对象,就有了主意。突然有一天,余藤秀从柳镇消失了。朱可凡某天发现派出所旁边多出了一个小小服装店,在店门口叫卖的正是余藤秀。朱可凡怕见到她,她却送上门来了,躲也不是,和她搭讪也不对。余藤秀见到他,总会露出甜美的笑容,娇声喊道:“可凡——”朱可凡心惊肉跳,这可如何是好。余藤秀见人就说朱可凡是她男朋友,还对派出所所长也这样说。派出所所长对朱可凡说:“你小子可以呀,搞了对象也不说,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朱可凡百口莫辩,死的心都有了。他气呼呼地找到余藤秀,质问道:“你什么时候成我女朋友了?”余藤秀微笑地说:“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呀。”朱可凡说:“你不是和我分手了吗?”余藤秀柔声细语道:“我说过和你分手了吗,我不是一直默默等着你吗?”朱可凡脸红耳赤,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悻悻而去。余藤秀在他身后说:“你跑不掉的,迟早是我的人。”
余藤秀的机会终于来了,朱可凡到山上抓赌,不慎摔断了腿,住在乡卫生院里。余藤秀真像个妻子,无微不至地照顾起了朱可凡。半年之后,朱可凡和余藤秀结了婚。据说,结婚后的余藤秀变了个人,变着法子折磨朱可凡,有一段时间,朱可凡都不敢穿短袖的制服,因为手臂上有一块块被余藤秀咬的印记。朱可凡也有恼羞成怒的时候,余藤秀就会哭哭啼啼地跑到派出所长那里告状,说朱可凡打她。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后,他们的婚姻生活才正常起来,但是朱可凡怕老婆的名声传遍了全县。问题就出在第二个孩子身上,他们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不知怎的,他们又要了个孩子,第二胎是个男孩。怀上二胎后,余藤秀就离开了,到厦门她堂兄那里去了。堂兄在厦门开了个服装厂,余藤秀躲在厦门,把孩子生下来了,她不敢把孩子带回来,让堂嫂养着。那时计划生育可是一票否决,朱可凡和余藤秀生二胎的事情给人举报了,朱可凡就脱了警服,下海做起了生意。
我问道:“朱可凡做什么生意?”
浦志高说:“鬼知道他以前在外面做什么鬼生意,这几年在县城里搞房地产,建了一个小区,房子卖得死贵,县城里的房价都是被他抬起来的。”
吃完饭,我掏出准备好的一个红包,塞给他,他断然拒绝:“你是我同学,怎么能够收你的钱,谁的钱也不能收呀,你这是想把我送进去呀。”看他义正言辞的样子,我收回了红包。他连吃饭的钱,也抢着去收银台付掉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他笑着说:“老同学,别这样,不就是一顿饭钱嘛,虽然说我不像朱可凡财大气粗,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你大老远回来,请你吃饭是应该的。”我没再说什么。
出了饭店的门,恰巧碰到了朱可凡夫妇,他们好像也是来吃饭。浦志高轻声说:“朱可凡来了,我就先走了,你父亲的事情就放一百个心吧。”要不是他说,我根本就认不出朱可凡了,他发福了,红光满面。余藤秀倒是没有变化,只是苍老了些。朱可凡看到浦志高,立马变了脸色,大声吼道:“浦志高,你这个王八蛋,别跑。”浦志高没有搭理他,一溜烟跑没了踪影。朱可凡看了看我,我也看了看他。還是余藤秀眼尖,试探性地问我:“你是李西虫?”我说:“你是余藤秀?”
她点了点头,满脸堆笑:“多少年没有见了。”我说:“我17岁那年离开柳镇,都三十多年了。”余藤秀说:“你还是那个样子。”我说:“老了,白头发都有了。”朱可凡朝我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听说你小子发达了,在部队当了官。”那一掌拍得我肩膀有点痛,我揉了揉肩膀:“什么官,早就离开部队了,一个小职员而已,哪像你,成了大老板。”说心里话,我真不想和他说什么,只想逃。我说:“我有点事情,先走了。”说完,我就溜了。他在我身后大声说:“老同学,抽个时间我请你喝酒啊。”喝个鬼酒,我心里说,我不明白的是,浦志高为什么那么怕他,他为什么对浦志高那么凶。
父亲的手术十分顺利,家人们都放心了,父亲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我不急着回上海,宋卉也让我在家多陪陪父亲,父亲毕竟那么老了,见一面少一面了。我并不是那么孝顺的人,借这个机会,尽点孝心也是责无旁贷的。一天晚上,我给父亲削了个苹果,这时有人在门口,喊了我一声:“李西虫——”
我回头,看到一个护士站在门口,定睛一看,这不就是阿婵吗?
我将苹果递给父亲,站起来,走了出去。阿婵还是那张圆圆的脸,皮肤还是白得像雪,但眼角有了深深的皱纹,眼神黯淡,仿佛藏了许多忧愁。我心里有种酸酸的感觉,我没想到她也在这个医院里上班。她勉强笑了笑:“我表嫂说你回来了,在这里照顾你爸,我就过来看看,你爸没事了吧。”我也笑笑:“没事了,恢复得很好,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阿婵说:“没事就好,我还记得你爸养了很多鸭子。”我说:“他就是喂养鸭子时摔伤的。”阿婵说:“老人经不起摔,以后还是让他不要干什么活,该好好养老了。”我说:“和他说过,他是个闲不住的人。”阿婵说:“我要下班了,你能和我找个地方聊聊吗?”我点了点头。她说:“我去换衣服,你到医院门口等我。”
我弟弟刚好来了,我就去和阿婵会面。我忐忑不安,想起当年她对我不屑一顾的样子,弄不清楚她为什么主动找我,难道有什么事情要和我交流吗?时过境迁,我也有了自己的妻儿,她对我而言,只是一份遥远的记忆。她穿着灰色的无袖连衣裙,脸色忧郁,她带我到了一条小街上,找了家小茶馆,我们面对面坐在一个角落里。她问我喜欢喝什么茶,我说随便。她笑笑:“随便是最难点的。”我说:“很多朋友说我不像福建人,因为我并不喜欢喝茶,所以,什么茶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阿婵说:“我明白了。”于是,她点了壶正山小种,然后对我说:“我喝茶,你要不要喝点别的什么,比如啤酒什么的。”我想了想,说:“那还是来一瓶啤酒吧。”茶馆不卖酒,阿婵让茶馆的伙计到别处买了瓶啤酒进来。
我说:“你经常来?”
阿婵说:“苦闷的时候,就一个人到这里来喝茶,茶馆的人都熟了。”
“阿婵,你怎么会想到找我,好像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话,三十多年过去了,你我一直都是陌生人。”
“我还记得表哥说你喜欢我,我一直想,你自己为什么不和我说。你还是那样子,看你现在,脸都红了。”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那时无知,也不晓得什么是爱。”
“你和浦志高一直有联系吗?”
“没有,也就是因为我爸受伤,才找到了他,没想到他还念同学情,帮了大忙,他是个好人。”
“好人?”
“我感激他人不错,以前读书时,和他没有什么深交,这次回来,感觉到了他的情谊。”
“实话和你讲吧,他是我丈夫。他不是你想象中的好人,在我眼里,他就是个恶魔。”
我一时语塞,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阿婵是浦志高的妻子。接着,阿婵开始了对浦志高的控诉,我也从她的控诉中,得知了他们的一些情况。浦志高在我当兵那年,考上了福建医学院,毕业后在县医院当了一个外科医生,而阿婵毕业于护校,分在和浦志高同一个医院妇产科,做了護士。也许因为曾经是高中同学,他们就走到了一起,后来就结婚了。他们过了几年恩爱的日子,有了一个女儿。美好的日子几年之后就消失了,浦志高从来没有打骂过阿婵,但总是有意无意提起沈小如,沈小如在三十岁那年得了胰腺癌,很快就离开了人世。浦志高在阿婵面前提沈小如,其实就是用一把软刀子割着阿婵的心,沈小如是阿婵的噩梦,根本就不想记起这个人。她弄不明白,为什么浦志高要用沈小如来伤害自己。不光是在她面前提沈小如,就是同床共眠也不碰她一下。后来,阿婵知道,浦志高在外面有了相好的,他用冷暴力对待阿婵,就是想让她厌烦,主动和他提出离婚。他是个要名声的人,如果自己提出离婚,怕别人戳他的脊梁骨,影响他的升迁之路。阿婵得知真相后,下了决心,就是不和他离婚,说是要耗死他。而且,阿婵开始了反击,有一次,跟踪浦志高,把他堵在了那个女人家里,浦志高低三下四地求她不要张扬出去,乖乖地跟她回了家。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后,浦志高又故态复萌,冷暴力让阿婵痛不欲生,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女儿因为父母的关系不好,大学毕业后在福州工作,很少回来。
我听着阿婵的讲述,不知道说什么好。
阿婵抹了抹眼睛,幽幽地说:“西虫,这么多年,我自己闷着,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和你说这么多,心里舒服了许多。反正说给你听,你也不会告诉别人。有些事情,我表哥也晓得,他脾气不好,我总是怕他伤了浦志高,我不想让他因为我的事情受到牵连。表哥也和我说过余藤秀被蛇咬的那件事情,你的确很冤枉,表哥在这件事情上,也够王八蛋的,害了你。好在你去参军,有了好的前途,否则他罪孽就更深重了。很多时候,我也想一个问题,如果我当初不鬼迷心窍和浦志高结婚,或许我不会如此痛苦。我还想,我当初要是和你好了,会不会有个好结局,不过说这些话已经毫无意义。”
她缓缓地伸出手,要抓住我放在桌面上的手,我渐渐地感觉到她手掌的温热,就在她的手要接触到我的手之际,我突然收回了手,我想起了宋卉的目光。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近距离面对阿婵的脸,想起了那时在课堂上凝视她的脖子出神的情景,浑身触电般打了个寒颤。我的目光和阿婵的目光触碰在一起,她的双眼像忽明忽暗的灯火,被雨水打湿了的灯火。那一刹那间,我产生了逃离的念头,我想,从此以后,也许我再不会梦见阿婵,尽管她的脸还是那么白,白得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