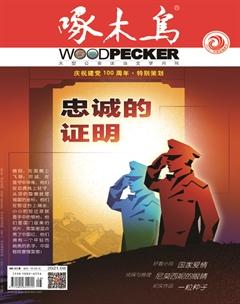沂蒙母亲
袁瑰秋

我很少收藏物件,但却珍藏着一双鞋垫。
在广州生活久了,很少穿袜子,更不要说用鞋垫。但是这双绣着“平安”二字的鞋垫,却是我的心爱之物,只要一换新球鞋,我就会垫上它,在大街上遛一圈,让它,为我每一次的“新步伐”剪彩,然后又郑重地把它收起来。
一
那是一个忘不了的时刻。
2016年6月26日晚,我跟随公安部“文艺小分队”走进山东省临沂市的“蒙山沂水大剧院”,小分队的第373场演出即将上演。
让我们沒有想到的是,“新时期的沂蒙红嫂”于爱梅和女儿高洁来到了现场,还送给我们小分队队员每人一双鞋垫。
当我从于大姐手中接过这双鞋垫时,一个又一个“沂蒙红嫂”在灯下一针一线绣鞋垫的身影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战争年代,送军粮、军装、草鞋是我们‘沂蒙红嫂留下来的传统,传统不能忘。一听说小分队来我们临沂,我们就赶紧做了这些鞋垫,送给部长和每一位小分队队员……请你们一定收下……”于大姐说。
抚摸着鞋垫上绣着的“警民心连心”“平安”……我心头一热,眼睛瞬间起雾了……
我问大姐:“为了什么?”
“不为别的,只是一个心意……希望咱们的民警站得端、走得正,为咱百姓保平安……”
六十五岁的于爱梅看起来才五十岁左右的样子,她是著名的“沂蒙母亲”王换于的孙女。
“大姐,沂蒙精神是什么?”我问。
“就是牺牲和奉献……”她说。
于大姐的奶奶和沂蒙老区人民,曾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牺牲和奉献……说起往事,于大姐一脸淡然,岁月的云烟悄然掠过镜片后的双眼……
于大姐的奶奶王换于1938年3月入党,接着,于大姐的父母、叔叔1939年3月入党。1940年部队转移时,党组织把一本二十六万字的《山东联合大会会刊》交给王换于保管,这一份信任与托付,让她豁出命去捍卫,日本人、还乡团、国民党都曾找过她的麻烦……她咬紧牙关渡过了一关又一关。直到1978年,九十岁的王换于才把它拿出来交给县政府,这份珍贵的文献现存于山东省博物馆……
苦难的岁月,镌刻蒙山沂水的光荣……也将“沂蒙母亲”这样的荣光赋予王换于这样从岁月深处走出来、挺过来的华夏母亲和中国女人。
陈毅、粟裕、徐向前、罗荣桓、谷牧、罗炳辉、谭震林、许世友等将帅当年都曾住过她们家,她们还办过一个战时托儿所。一些将帅家的“红二代”共计四十余个孩子,那时候都在她们这儿上幼儿园。“沂蒙母亲”们用乳汁喂养了这些革命后代,四十余个孩子一个不少……反而是王换于家中的孩子,死了四个……新中国成立后,王换于被誉为“沂蒙母亲”,1989年因病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当年陈毅元帅曾慨叹:“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人民。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于大姐的女儿高洁,今年三十六岁,也跟随母亲来到了小分队演出的现场。于大姐从小听奶奶、妈妈讲述当年的故事,高洁也重复着母亲的童年,在光荣的传统教育中长大。高洁是党校老师,这些年随着母亲传播“沂蒙精神”的路其实很辛苦,但她说,因为有意义,所以不怕苦……
二
遇见于爱梅大姐是五年前的事,而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沂蒙红嫂”的后代,大隐于市,让人肃然起敬。
她就是我的聂阿姨。
聂阿姨,名叫聂桂荣,今年七十七岁。虽然叫她阿姨,但在情感上,于我而言她如同母亲一般。
我们相识了十几年,因为都是广东这片热土上的“新客家”,过年过节常聚在一起,就连我父亲离世前过的最后一个春节,还吃过聂阿姨夫妇包的饺子。
两年前,我从小分队回来,兴奋地给她讲“沂蒙红嫂”的故事,她才不经意地说出来,她的妈妈就是“沂蒙红嫂”。
她的母亲叫范庆芳,生于1912年,山东省莒南县范家水磨村人,后嫁到十八里外的大山前村,生前是大山前村妇委会主任。
范庆芳,算得上是那个年代沂蒙山区最美的红嫂之一。1938年,鲁中南根据地初创时期,年仅二十五岁的范庆芳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沂蒙母亲”王换于是同年入党的红嫂。1947年深秋的一个夜晚,范庆芳把最后一筐军鞋结结实实地绑在手推车上,这一百多双军鞋是她带领四个村的妇女,在煤油灯下没日没夜、一针一线赶制出来的……她目送着“支前”的小推车车队,扬起尘土,走出村口,想象着这些军鞋就要穿在子弟兵脚上的景象,心中一阵暖意荡漾……然而,极度的疲惫突然让她两脚一软,还没能走回村口,就突然倒在了老槐树下……她被抬回她的母亲也就是聂阿姨的姥姥家救治,不出两日便撒手而去,留下十岁的儿子、三岁的聂桂荣和八个月大的小女儿。
地下党的同志们和村里人都说范庆芳是累死的。

范庆芳烈士最小的弟弟范庆云(前排居中,后改名范鹏飞,退休前是安徽省濉溪县县委书记)与当年的游击队员合影
她所在的这个大山前村,是根据地出了名的“模范村”,她这个妇委会主任,管着周围四个村的大小事情。前方的子弟兵在流血,她这位后方战士更拼命——
一个个沂蒙山水和无数“沂蒙母亲”的乳汁养大的孩子,经过她这一双灵巧而粗壮的手,将一个个战士、一担担小米、一车车棉被、一筐筐军鞋……推去前线;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伤员,被一个个担架抬回来……而这送军粮、抬担架的队列里,就有她厚重少言的丈夫聂文汉的身影。她忙得连合眼的时间都没有,半夜了,还要摸黑进山,把刚熬好的米汤送去后山的山洞里,一口一口地喂那些奄奄一息的伤员。
“最后的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正是范庆芳这些识字不多,却心里敞亮的“沂蒙红嫂”博大胸怀的真实写照。
范庆芳的母亲生养了八个子女,一头一尾是儿子,中间六个都是女儿。范庆芳是长姐,在她的带领下,兄妹八个除了留下一个二妹照顾家,全都参加了革命,四个妹妹是她亲手送进革命队伍的。她是鲁中南根据地最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抗战时期,是地下党组织斗争最艰苦的时期,地下党开会,常常都在他们聂家的“锅屋”,也就是厨房里召开。每次开会,范庆芳都在灶台边张罗着,屋外,她的丈夫聂文汉背着一个大粪筐,躬着高大的身躯,在家的周围转来转去假装装粪,实际上是在放哨。
范庆芳的乳汁,还养大了数不清的地下党托付给她的孩子。她是那些党交给她的孩子的“总妈妈”。
有一个叫“小老虎”的男孩儿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她把他安排给了村西头的郑家。解放后,“小老虎”的爸爸专门回村里来找恩人,村干部把他带到范庆芳的坟头,“小老虎”的爸爸扑通跪下,一言不发,泣不成声地在她的坟头添了一抔又一抔土。
人的记忆是奇怪的。聂阿姨说,母亲三十六岁走的时候,她才三岁。按理说母亲留给她的记忆其实为零,但她却神奇地记住了母亲出殡的那一幕:她十岁的哥哥走在最前头,她和妹妹被人抱在怀中。
母亲的灵柩,放在距离土地庙约一里远的场院里,停灵三日,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平时静静的村里,一时间冒出来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男的都戴着孝帽,女的头上都顶着白布。

范庆芳烈士的长子聂世基和妻子靳宝兰,两人退休前均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按照乡土习俗,有一个要给亡灵“送汤”的环节,应该就是“一日三餐”的意思吧!有一个明事理的人走在前面,左手提着小米汤罐,右手提着装纸钱的篮子,他后面依次跟着亡者的儿子女儿亲戚,再后面就是邻居好友等。给母亲送汤的有百余人。领头的人在土地庙供完汤烧完纸后就往回走了,后面跟去的人却还没起步……
母亲走后,全村有奶的婦女都争着来家里,抱着妹妹就开始喂奶。
那时只有三十多岁的父亲,从此没有再娶,一门心思把他们兄妹三人拉扯成人。三兄妹都很争气,在八百里沂蒙革命根据地上茁壮成长,他们都亲眼目睹过老区人民用手推车把中国革命推向长江以南,流淌着来自母亲温暖的骨血,从小就深深懂得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是绝处逢生的基石。后来,哥哥聂世基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聂桂荣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妹妹王桂荣(被姨妈领养后改姓王)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
范庆芳的大儿子聂世基,是我国著名的法学教育家,吉林大学法学院的创始人,在新中国法学教育历史上留下了光辉印记。后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多年,建校70周年时入选“70位公大杰出人物”。
大学毕业后,聂阿姨被分配去吉林,在银行部门工作。她把老父亲一直带在身边,直到父亲八十七岁在吉林安详去世。父亲生前话不多,但有一件事他很早就说清楚了:我迟早要回到沂蒙山,和你们的母亲在一起。
兄妹三人很少有聚在一起的机会。在父亲走后,他们终于团聚在了护送父亲骨灰回归沂蒙山的路上。
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母亲的坟茔闪亮在山野间,特别显眼,坟前的石阶锃亮,坟头的新绿如盖……村里的老人告诉他们:你们母亲的坟上总有新土,常常有一些不认识的人来村里,在她坟前烧纸,哭得很响……应该是她早年养大的那些孩子回来找她了……
后来大山前村变成了城市,父母合葬之后的坟茔,被双双移去了鲁东南烈士陵园。
离家之后,沂蒙故土成了回不去的远方。关于母亲的记忆只是一些不成形的碎片,这是聂阿姨一生的遗憾。她常常后悔没能在父亲有生之年,多问一些关于母亲的故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聂阿姨也七十七岁了。
聂阿姨退休后跟随女儿在广州生活了二十多年,关于沂蒙山以及“沂蒙母亲”的话题,如同她日渐稀疏的白发,如果不是我问,她从来不向别人提起。
聂阿姨的大女儿名叫:沂蒙。
十几年了,我从来没有追问过这里面的深意。
原来,聂阿姨是名副其实的“沂蒙母亲”,更是范庆芳这位伟大的“沂蒙母亲”的女儿。
这是永不更改的血脉,从来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
(文中照片由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张璟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