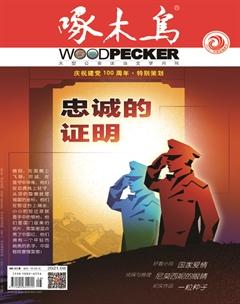一粒种子
贾文成

引子
无人区,戈壁滩,茫茫的大漠和草原。
他们常年驻守在荒寂的大漠,守护着一条贯通内地与边疆的铁路线。他们驻守在国门口岸、塞上草原,他们是一支专业化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他们因为职责与分工,而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铁路警察。
2020年4月17日这天,铁路公安民警警服上的胸徽,由“铁道”变为“铁路”,这细微的一字之差的变化,却是铁路公安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他们向公安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迈出了更加坚实的一步。
他们喜欢唱的歌是:“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
歌声代表心声,绿色代表希望。因为,他们在心中种下了心愿。
心愿的种子
派出所门前,去年种下的树又死了。
姚平均掰断了枯死的树枝,丢进刚刚挖树根时留下的树坑里,站起身说:“去敦煌。”
“敦煌可不近。”有人说。
姚平均说:“这是离咱这儿最近的地方了。”
民警刘文俊看了一眼姚平均:“丢了种树的念头吧,你看看戈壁滩上,哪儿有树?”
许彦林说:“你哪里知道,姚所三天前就和敦煌那边联系好了买树苗。”
许彦林是派出所的教导员,也是全所最年轻的民警,可也五十二岁了。他最懂姚平均的心思。
记得那是2017年9月里的一天,一大早,姚平均说:“早点儿出发,一千多里路呢。”
许彦林把一桶水拎上车说:“公安处配发的新车,路上不会抛锚。”
姚平均皱了皱眉头:“过了额济纳就是戈壁滩,一路上都是无人区,我们又是第一次去,路况也不熟,还是谨慎点儿好。”
许彦林说:“老李是老司机了,经验很丰富。”
老李叫李雁恩,离退休还有不到三年的时间。他以前做过专职司机,驾驶技术很娴熟。
李雁恩说:“咱们算是第一批到派出所的人。”
姚平均笑了笑:“我们这是去开张营业。”
说话间,警车已经离开了包头铁路公安处机关院子。城市越来越远,时而笔直、时而蜿蜒的公路,将陪伴着他们,向那个神秘的无人区挺进。
横亘在无人区腹地,有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线,一头连着新疆的哈密,一头连着内蒙古的额济纳。据说,这条铁路线将西北、华北、东北进入新疆的路程缩短了七百多公里。
在这条铁路线的中段,有个叫马鬃山的车站。按照铁路线管辖设置,马鬃山车站派出所由包头铁路公安处管辖。马鬃山是甘肃肃北县的一个小镇,而火车站离镇上还有八十公里,离县城有七百公里。马鬃山火车站周边,茫茫戈壁,除了车站职工,方圆几十公里,陪伴五十多名铁路职工和派出所民警的,是飞沙走石和低矮的荒草。
姚平均他们到达马鬃山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到半空。漫天的星斗,搅和着戈壁滩上习习的冷风,虽然是初秋,但马鬃山已经有了凉意。打开二层小楼的房门,新鲜的混凝土气息直扑鼻翼,打开灯,派出所除了四面墙一无所有。
三个人互相望望,姚平均说:“咱们是先头部队,从今儿起,就在这儿置办家业了。”
许彦林和李雁恩都没有笑,因为肚子里正咕噜噜地发出饥饿的肠鸣声。
车站有个食堂,但三人没有叫醒累了一天的做饭师傅,他们抓了几个冷馒头,回到派出所,算是吃了一顿晚饭。填饱了肚子,打开行李,和衣而卧,天亮之后,他们先把站区的单位走了一遍,车站职工、站区重点部位,子丑寅卯,全记在心里。
“走,到戈壁滩上去。”姚平均摆了下手,拉开了车门。
李雁恩不解地说:“戈壁滩上,荒无人烟。听车站的职工说,晚上,车站附近都能听到戈壁苍狼的嗥叫。”
一旁,车站的刘主任马上说:“是呢,修铁路的时候,戈壁滩上还有修路的工人,铁路修好,施工队撤走后,这一带除了车站职工,想见个生面孔还真难。”
这茫茫戈壁滩上到底有没有人烟?这里真的是无人区吗?姚平均动摇了。可他凭着几十年的警察经验,公安离开群众,就像鱼儿离开了江河,鸟儿离开了山林。一天的寻找,茫茫戈壁滩上果然没有人家。
到了第二天,姚平均他们扩大了搜索范围。许彦林在一堆芨芨草旁边发现了几个羊粪球。这一发现,令三个警察疲惫顿消。
太阳落山前,他们在离铁路线二十五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顶帐篷,更为惊喜的是,不远处隐隐约约像有羊群在移动。
“找到了!”三个警察异常兴奋。
放羊的牧民叫朝乐孟花,她用不太流利的汉语与警察沟通。朝乐孟花早年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来到这片戈壁滩,一待就是二十年。热情的朝乐孟花把三个警察请进帐篷,给他们讲这片戈壁,讲戈壁上的野狼、羊群和屈指可数的几户牧民。
朝乐孟花倒了三碗水给他们。在戈壁上走了一天,带的水早没了,他们也顾不上客气了,接过碗就喝,刚喝到嘴里,就感到一股苦涩的味道。
三天后,姚平均又来了。汽车的后座,放了三个大号桶装水。
朝乐孟花打开水桶,倒了一碗水,在嘴里咂巴了几下,眼里顿时闪现出惊奇的神色,接着便流出了眼泪。
她说:“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还有这样甜的水。姚所长,水是甜的!”
姚平均和所里的民警不敢直视朝乐孟花,因为,他们怕朝乐孟花看到他们眼里的泪水。此后,朝乐孟花家一直喝的是派出所送的水。
其实,馬鬃山车站也没有水。每周,铁路上用列车将生活饮用水,从近千公里外的巴彦淖尔市拉到马鬃山车站来。
民警们喝的水,也是限量供应的。给朝乐孟花家的水,是派出所民警一点点省出来的。
水是马鬃山车站的命根子。
派出所的民警增加到了十九人。虽然轮换倒班,但每天也有七八张嘴吃喝拉撒,每周一趟的供应车,带来了肉食蔬菜和桶装水,但水依然是困扰着派出所的难题。民警们除了刷牙、饮用和做饭,他们很少洗脸。
许彦林说:“姚所,咱去镇上开会,洗洗脸吧。”
姚平均一怔,笑了笑,说:“镇上的人也都知道咱缺水,你说洗不洗吧。”
省着水用,已经成了马鬃山派出所民警的生活习惯,平常洗澡和洗衣服,他们也都是要等到休班的时候回到有水的城市。
在缺水的戈壁滩上,民警们把水精确地计算到以杯为使用单位,而且必须做到合理利用。比如洗菜的水用来刷碗,刷碗的水用来喂猪。
为了改善戈壁滩上的生活,派出所养了猪,几年下来,大大小小已经有十多头猪了。有了猪,他们又在戈壁滩上建起一座蔬菜大棚。
民警们说,不为吃菜,只为在满目焦黄的戈壁滩上看到一点儿绿色。枯燥的日子,因为这点儿绿色而有了生机,有了生命的气息。
朝乐孟花就是派出所的流动哨所,在朝乐孟花的帮助下,他们又在戈壁滩上找到了两户牧民。从此,这条戈壁滩上的铁路线,多了几双值守防护的眼睛。
派出所民警到戈壁滩上巡线,总会带几桶水给朝乐孟花。朝乐孟花说,铁路派出所的民警不仅让她喝到了甜水,而且救了她的命。
那是2018年初冬的一个夜晚,茫茫戈壁滩,寒气逼人。汽车的灯光,在暗夜里摇晃颠簸。
尽管心急如焚,教导员许彦林还是提醒姚平均,开慢点儿,别爆胎了。
听到“爆胎”二字,姚平均就头皮发麻。不过,他刚放慢车速没一会儿,车又飞驰起来。
到了蒙古包,门敞开着,里面却没有人。
打着手电筒,开着车灯,在蒙古包四周查看,没有人;喊名字,也没有人应;拨打手机,无法接通。
其实,从派出所出来,朝乐孟花的手机就无法接通了。这会儿,她在哪儿呢?
许彦林沮丧地说:“姚所,会不会是狼来了?”
姚平均摇摇头说,“现在一点儿血迹都没有,应该不会是狼来了。”
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眼睛一亮,指了指远处的山坡说:“上山看看。”
许彦林恍然大悟,苦笑了一下说:“那儿才有信号。”
二人爬到山上。
在一个避风的山石下,朝乐孟花蜷缩着,奄奄一息。许彦林背起她就往蒙古包走,接着一路驾车,赶了五百多公里的路,才到了肃北县城。医生说再晚来一会儿,就没有抢救的机会了。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千多年后的大漠戈壁,依然是荒寂的,是这条铁路唤醒了沉睡的大漠,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机遇。
但坚守这条线路的守卫者,仍要面对各种困难和考验。不仅是朝乐孟花,就是派出所的民警,最担心的也是身体,一旦身体发出警报,就医是个大问题。所以急救包、急救药,总是放在派出所最显眼的地方。在姚平均等民警心里,那些药最好一次都别动。
朝乐孟花痊愈后回到了戈壁滩。她带来了羊肉,临走时,民警们又把水桶装在了她的车上。
在马鬃山车站派出所的院子里,种下的树活了六棵。今年,姚平均他们还在戈壁滩上挖到了三棵胡杨树,移栽到了派出所门口。
姚平均去了趟敦煌,买回来七棵枣树苗,挖出死掉的树,在原来的树坑里重新栽种上新的树苗。民警们攒下的水,集中在一个大桶里,用来浇树。
每天早上,姚平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蹲在树坑边,看树苗变软,看树苗长出嫩芽,看树苗长出绿叶。
树活了,但不知道能不能熬过戈壁滩寒冷的冬天,明年这些树能不能如期发芽吐绿。姚平均心里越来越没底了。
树反反复复地种了五年,除了为数不多的几棵树活了下来,其他的都如这新树一般,挺过一个夏天后,第二年还是死掉了。
民警老刘和老李要回远在千里之外的包头休班了。姚平均天不亮就给他们烙了饼,每个袋子里还装上了一只炖熟的鸡腿和一袋咸菜。他们回包头,中途换车顺利的话,也得两天才能到家,这些是民警路上带着的干粮。姚平均腌制的咸菜远近闻名,被人戏称为“姚氏酱菜”。据说,那味道不比京城里的著名酱菜逊色。
教导员许彦林正在给警犬换药。他们出去巡线,警犬赛花竟然也悄悄跟了出去,不幸被盗猎者放置的狼夹子夹伤了腿。所里的民警看着赛花的伤腿都掉了眼泪。
姚平均走过去说:“教导员,你也回家看看吧。”
姚平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平常不忙的时候,他和许彦林可以轮换整休几日,可新冠疫情出现后,本该休班的民警全都留守在了这片无人区,而回去休息的民警又暂时来不了。那些日子,驻守在无人区的这些民警们,快一个月没洗澡了,身上有了异味,换洗的衣服也带不回去,头发长了,也没地方理发。姚平均翻箱倒柜,找到一把还算锋利的剪刀,给留守的民警剪了头发。理完发的民警对着镜子一照,说:“咱派出所可以开理发店了。”
姚平均指着自己的头发说:“我这是赶鸭子上架,被逼成了一个剃头匠。你们说,我为啥被逼成这样?”
老民警刘文俊笑着说:“你想等退休后再多个手艺。”
姚平均摇着头说:“我们是警察,任何时候,警容警貌不能含糊。”
留守的民警坚持了三个月,疫情得到控制后,民警们可以轮换倒班了,可他们俩却还在坚守,所以姚平均动员许彦林回家看看,许彦林说:“我不想回去,我陪着你。”
姚平均说:“你和我不一样,我再有两年就退休了,到时候有大把的时间在家待着。”
许彦林当然知道姚平均的心思,他看了一眼树坑说:“移栽回来的胡杨树也活了。”
姚平均仰起脸,望着蔚蓝的天空说:“到我退休的时候,派出所绿树成荫的景象估计是看不到了,我就想讓这些树都活了,想证明戈壁滩上能种活树。有了树,咱这派出所才能在戈壁滩上扎下根来。”
在荒寂的沙漠里,姚平均的心里是一幅画,一幅被绿色浸染着的美丽图画。
而在铁路公安处,还有一些人也在画画。只是,他们的画不是景色,是人,或者说,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目标。
没有画笔的画像
犯罪嫌疑人杨某被抓了,进了看守所。他一直没琢磨透,自己是怎么进来的。
警察到底掌握了自己多少罪证?杨某一晚上没合眼,心里一直打鼓的就是这事儿,警察明天讯问他的时候,该怎么避重就轻。
讯问的警察,看上去是个头儿,戴着一副眼镜。看似文雅的背后,其实是一双犀利的眼睛。
后来,杨某才知道,主审他的那个警察果然不简单,是公安部的二级英模、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的刑侦处长——彭刚。
为了倒腾白粉,杨某可费了一番心思。而且几次得手后,杨某也为自己过人的智商沾沾自喜。不过,这是在钢丝绳上跳舞,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身份证是弟弟的,本来是去襄阳取货,可他一次都没在襄阳下过车,要么去武汉,要么在离襄阳或者武汉近一点儿的车站下车。
这次取货,也如往常一样顺利,列车离包头越来越近。车窗外,铁路边的小山村里,不时传来几声爆竹的炸响,春节就要到了。他打算收手一阵子,在家过个安稳的春节。
快到终点站包头了。杨某一路提心吊胆,这会儿似乎能松一口气了。
这时,他感觉车上有几双奇怪的眼睛,心里又不安起来。他在心里问了很多遍,是自己多疑了吗?不像,做这一行的,谨慎为妙。他离开卧铺的铺位,走了出去。
车到站了,他刚走出车厢,两名年轻男子就走了过来,说他们是警察。他下意识地回过头,身后是在车上看到的那两名年轻男子。
他暗自庆幸,把货甩了,只要死不开口,警察也找不到证据。
然而,令杨某意外的是,警察从列车的垃圾桶里找到了他扔的那包毒品,还把他这些年贩卖白粉的轨迹用图画了出来,有些路线竟比自己记得还清楚。
杨某撂了,扛著也没用,警察把他的作案次数摸了个底儿掉。
他交代完后,又问了一句:“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彭刚和在场的刑警笑了笑,竖起一根手指,指了指天花板,说:“人在做,天在看,法网恢恢。”
杨某眨巴了下眼睛说:“我活了五十多年,你们说的那网真就那么大?”
后来,彭刚在给刑警同行介绍经验的时候说,杨某哪里知道,我们的那个网是信息网,就是依靠情报数据构建犯罪模型,以此来导侦案件,锁定目标。
近年来,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把合成作战和信息化作战,作为侦查破案、打击犯罪的主攻方向。于是,在市公安局局长张晓华的支持下,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刑事情报中心挂牌成立了。
利用信息数据寻找犯罪线索,让警察如虎添翼。对此,李国栋的感受最深,他是包头铁路公安处客车刑警大队的大队长。
他说,从他师父的师父那时起,最头疼的就是这些流窜作案的“老贼”。早些年,他和师父,后来是他自己,为了对付“老贼”,穿个便衣,带几个冷面包,在车厢里一蹲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抓贼是依靠辛苦和经验练出的火眼金睛,警察不怕辛苦,可有时一蹲好几天也不见贼的影子。专吃铁路的“老贼”,也把与警察的周旋当作炫耀的资本。
马某就是京广线上的“老贼”,绰号老歪,河南籍。老歪每次上车前,要到站前的水果店买一个苹果,买苹果不为吃,只是想图个平安吉利。所以,他揣在兜里的苹果,就像过年挂在家里的年画。
车上,旅客熙熙攘攘。老歪盼着的就是这样的客流,人越多,他越好下手。
可是他刚得手,还没来得及窃喜,就被一副冰冷的手铐铐住了双手。这次案值不大,从拘留所出来没几天,他揣着苹果又登上了列车。
抓他的还是李国栋和打扒小分队的刑警。老歪晕了,说:“你们咋把我盯得死死的?”
这次,老歪被判了一年。刚出狱一个月,老歪故伎重演,在火车站站前广场买了一个苹果,然后买了一张短途车票,又登上了列车。
刚得手了两次,不到一个星期,老歪又被警察抓了,抓他的还是李国栋。
老歪崩溃了,瞪着李国栋和从包头来的铁路刑警说:“上辈子,咱们肯定是冤家。”
除了打击流窜作案,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的刑侦力量,组织管辖的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处和锡林浩特铁路公安处,接连破获了数起旅客列车财物被盗的积案。
熟悉铁路列车案件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在过去都是不敢想象的。这份自信就得益于信息化合成作战。
他叫小龙。2020年4月1日,因为遇到资金难题后,轻信网贷,雪上加霜,被电信诈骗黑手骗走了上万元。疫情肆虐的日子,全国人民都被组织起来同心应对疫情,而犯罪分子竟然丧心病狂,借机作案。警察愤怒了,发誓定要抓住罪犯,斩断黑手。
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处的刑警们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寻找蛛丝马迹。刑侦、网络、情报信息等多个部门的民警协同作战。
不久,一个居住在福建龙岩叫张红的女人浮出水面。
到了福建,能不能顺利找到张红?而且电信诈骗往往都是团伙作案,抓了张红,会不会打草惊蛇?
张红的落网,成功之处就是打破地域和案件限制,积极争取当地警方的配合,做到资源共享和警务协作。这一模式,在打击电信诈骗案件中显得尤为突出。福建龙岩警方有一支打击电信网络新型犯罪的专业队伍,他们派出精干力量,协助远道而来的铁路警察实施抓捕。
那天是5月1日,离案发整整一个月了。
五十六岁的张红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远在草原的铁路警察,会悄然而至。这天是五一小长假,而且受疫情的影响,出远门的人也很少。她像往日一样,按照团伙骨干的指令,继续干着违法的勾当。
她交代了同伙傅宝强。此人在哪儿?顺着线索摸下去。傅宝强登上了去扬州的列车。是闻风潜逃?还是出行的巧合?
事不宜迟,专案组立即请扬州车站派出所的警察协助抓捕。很快,傅宝强落网。
这一查,不仅专案组的侦查员震惊了,还惊动了铁路公安的高层。随着一个个犯罪嫌疑人的落网,案子就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专案组在当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下,一口气抓获了十二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涉案人员多达一百八十七人。他们中既有负责实施诈骗的,也有以公司名义参与洗钱的。而且团伙之间分工合作,有的成员互不相识,完全是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完成了犯罪的全过程。
而铁路警察则让这些互不相识的罪犯走到了“一起”。与此同时,铁路警察也让民警与老百姓走得越来越近。
国门守关者
能做国门的守护者,在众多的铁路警察中,这样的机会其实并不很多。
马煜,一个90后的女孩儿,报考铁路警察的时候,她填报了二连浩特火车站派出所。那个时候,口岸对她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至于诸如“中欧班列”这样的名词,更是陌生。她是和一百多个新民警一起到达二连浩特的。
二连浩特是蒙古语,它的汉语意思是色彩斑斓的盐湖,也有海市蜃楼的意思。国门口岸在这里,国徽和国旗显得更加庄严神圣。所以二连浩特也是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处的民警教育基地,新民警上岗前,公安处会组织他们来到国门口岸。这里,除了国门口岸,还有一个老字号的先进派出所,全国青年文明号、优秀党支部等各种荣誉摆满了“励警室”。从1955年建立派出所,数十载风雨历程,一代又一代的铁路公安,精心守护着这份荣誉,传承着一种精神。
来参加入警教育的小伙伴们要去上岗了,马煜留了下来,她目送着火车消失在火车站的尽头,那一年是2018年。她记住了那年,而随后她更记住了一个日子。
这天是2020年1月23日,第二天就是鼠年的除夕。马煜答应父母,今年不在所里值班,回家陪他们过年。
这天,她结束了春运宣传小分队的任务,从包头登上了回呼和浩特的动车,她准备下车后再转车回离呼和浩特二百多公里的父母家。那是一座縣城,县城里过年的味道很浓,她开心地给妈妈发了一条信息:我下午到家。妈妈很快回了一条信息:我和你爸在包饺子。
列车到了呼和浩特,马煜收到了另一条信息,是派出所关于新冠疫情的提示,希望民警做好防护。马煜愣住了,怎么办?是回家,还是回派出所?
马煜从手机中获取到各种信息,武汉封城,二连浩特出现了内蒙古第一例新冠患者。假如她现在回了家,等假期结束,还能不能如期返回派出所?
纠结,矛盾。她思索片刻后,拨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打给火车站问询处的,她想知道,回二连浩特的火车是否能正常发车。一问,还好,回二连浩特的火车没有停运。她坚定了主意:回二连浩特,回到那个悬挂着国徽和国旗的口岸去。
但是,她怕父母失望,更怕父母的思念动摇了她的决心。她想,还是等回到派出所后再发信息吧,而妈妈却不停地发信息询问:到哪儿了?饺子包好了,就等你回来下锅。
马煜擦了一下眼角的泪。都说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她这个独生女,选择了警察,就选择了奉献与付出。这个道理,进入铁路警察队伍后,马煜就懂了,就理解了。
回到所里,所领导和战友们都很意外,而让马煜意外的是第二天的客流高峰。内蒙古出现的首例新冠病例就在二连浩特,一时间,二连浩特成了被关注的地方。第二天一早进到候车室,马煜就惊呆了。她入警两年,头一次见这阵仗,平时倒没啥,可这是疫情期间,旅客的成分也特殊,全部是准备离境的外籍旅客,她的第一反应是向所里报告,请求增援。
接着,这个略显瘦弱的女警察,一头扎进了人堆里,从购票旅客最拥挤的地方开始疏导:大家有序排队,请保持安全距离。
她的蒙古语说得不好,也听不大懂对方的话。拥挤的旅客,沟通的障碍,零下三十摄氏度的气温,马煜却急出一头汗。
情急之中,有时候手势倒是最容易被读懂和理解的沟通方式。
派出所增援的民警到了,马煜总算松了一口气。此时,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出现在她的视野中,那个孩子没戴口罩,她走过去劝说道:“大姐,孩子那么小,赶紧把口罩戴上吧。”
那位年轻的母亲皱着眉头说:“我想给孩子戴,可没有口罩。”
马煜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口罩,这个口罩是她上岗替换用的,她把口罩给孩子戴上,那位母亲含着眼泪望着她。
从年轻母亲的泪光中,马煜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她有些想母亲了。
三百公里,其实并不远,而等她再次见到父母的时候,已经是半年以后了。
其实,像马煜这样坚守在一线的民警很多很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疫情在前,警察不退!
生根开花
王玲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到大,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幸福地长大。
她很争气,不仅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又顺利地考上了公务员,还穿上了警服。这一家人甭提多高兴了。
母亲逢人便说,我闺女在呼和浩特东站派出所当警察,那是西北最大的高铁站。母亲这一番夸耀,立即引来邻里亲戚艳羡的目光。父亲也为女儿能穿上警服高兴得合不拢嘴。
然而,不到三个月,家里竟然悲从天降,陡生变故。
201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大约十点多,王玲的父亲突发心梗,一头栽倒在了床上。
母亲慌乱地拨打了“120”。二十几分钟后,“120”救护车到了。医生查看后,叹了口气说:“叫殡仪馆的车来吧。”
母女俩蒙了,待回过神来,医生和救护车已经走了。
母亲瘫软在地上,王玲望着渐渐冰冷的父亲,一时不知所措。她看了一眼母亲,问:“妈,咋办?”母亲摇摇头,抹着眼泪。
其实,离王玲家最近的是她舅舅家,她拿起手机,却把电话打给了所长牛玉良。
此时牛玉良正在派出所里。王玲说:“牛所,我爸没了。”说完,就哭了起来。
牛玉良急忙安慰道:“你别急,我马上过去。”
放下电话,牛玉良扫了一眼值班的民警,目光停留在云鹏的身上。
云鹏抓起警帽说:“牛所,我跟你一起去。”
其实,牛玉良选择云鹏,是因为他是烈士的孩子。云鹏经历过警察父亲的生死,也料理过父亲的后事,尽管那个时候他才十几岁。为死者料理后事,近距离接触,除非至亲,一般人心里都有些抵触和畏惧。
王玲母女哪经历过这样的事,虽然牛玉良和云鹏到了,母女俩仍然不知所措。
牛玉良说:“王大哥事发突然,先擦洗身子,穿衣服,联系殡仪馆吧。”
母女俩听后,急忙翻找像样的衣服。牛玉良找来白酒,和云鹏一起为死者擦洗身子。
殡仪馆的灵车到了,王玲的舅舅也随即到了。幸亏王玲的舅舅赶到,三个男人总算把王玲的父亲从六楼沿着楼梯一步步抬到了楼下殡仪馆的灵车上。随后,他们又帮着料理完了后事。
安葬完父亲,王玲回到了所里,和所里的民警们说:“虽然我只来了三个月,可那天不知道为啥,我首先就想到了所里,想到了牛所。”
所里的民警笑着说:“那当然,有困难找警察。”
王玲眼里闪着泪花。
暖心,是思想政治工作最鲜活的元素,也是凝聚警心和民心的根本。
呼和浩特火车东站,一个阶段里由于管辖权限衔接上存在的问题,导致黑车宰客,出租车无序管理等交通乱象,被旅客和市民吐槽。
怎么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令人头疼的难题,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的思路是把责任担起来。可是具体怎么操作呢?成立铁路交通警察。马上有人反对,其实也是担忧。说铁路警察就是交通警察,不过管辖的是铁路线路的事儿,社会车辆、出租车乱停乱放,交通违法,那是地方交警的事儿,咱管不了。
管不了也得管,不能这么乱下去。经过向自治区公安厅汇报请示,再吸纳个别铁路公安局组建交警支队的经验和做法,铁路交通警察支队在内外部的各种质疑和反对声中成立了。
但随之而来的是执法的尴尬和困惑。
有的出租车司机干脆挑衅:“别看你们穿着交警制服,来呀,扣驾驶本呀,罚款吧,扣分吧。”
铁路交通警察也只能无奈地苦笑。
解决执法权限,加大执法力度。铁路公安局、铁路公安处两级管理层重新调研,决心打造一支全新的铁路交通警察队伍。
首先是换将,有地方公安工作经验的苏志强接任支队长;接着是协调管理体制,铁路交通警察支队办公楼前,挂出两块牌子: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处交通警察支队、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铁路大队。
有民警指着牌子说:“老苏,那块牌子小了,你老苏从支队长变大队长了。”
老苏笑着说:“称呼不重要,要看疗效。”
苏志强还不到五十岁,但交通警察支队的人习惯叫他老苏。老苏来了,整日在忙。车站周边的交通归了铁路管辖,站前的路标换了,更醒目,更合理。出租车管理吸纳了“北京西站模式”,并做了更加合理的调整。
有常來呼和浩特出差的旅客,感到最明显的变化是,出租车好叫了,人车按序排队,旅客不再为争抢出租车打架了,黑车消失了。车站的交通秩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天,几个农民工搀扶着工友,冲进了岗亭:“快救救我们这个兄弟!”
备勤交警一看,一个工人的手指被轧断了,血流不止。交警立即打开警车车门,工友搀扶着受伤工人坐进了车里。副驾驶的交警启用与市公安局交警同频道的电台呼叫,请求路上的交警实施交通疏导。
这么一联动,路上果然顺畅,不到十分钟,伤者就被送到了医院。
紧急时刻,十分钟的意义,可以保住一个农民工的手指,可以挽救一个家庭免遭贫困,可以让一个年轻的汉子留住未来与希望。
医生说:“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工友们说:“出了事儿,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警察。平常干活儿,一仰脖子,看到的就是火车站落客平台上的警察。”
警察们擦了擦脸上的汗。正午的太阳,很大,也很温暖。
如果说每一位铁路警察都是一粒种子,那么完全可以说,他们已生根于一片忠诚的沃土里,在广袤的大地上生根开花。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季伟
文字编辑/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