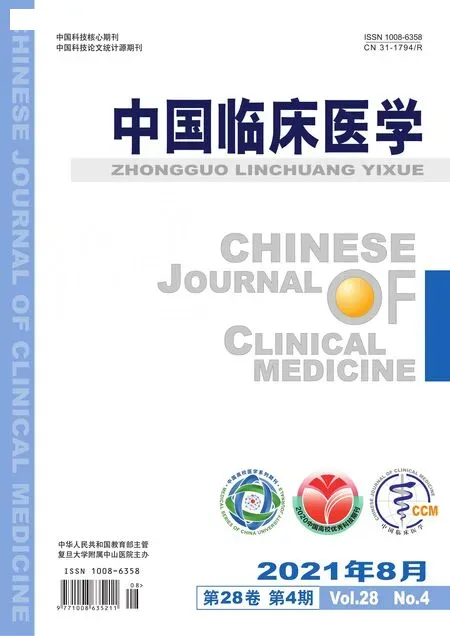冠状动脉负性重构冠心病患者的治疗:2例报告
吴轶喆,张英梅,钱菊英,葛均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上海 200032
1 病例资料
1.1 病例1 患者女性,62岁,因“活动后胸闷2个月”就诊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诊断为劳力性心绞痛,于2020年4月26日在行冠状动脉造影术,发现左主干狭窄99%、右冠状动脉中段狭窄80%,余血管未见狭窄病变,行左主干介入治疗,术后患者症状缓解。于2020年6月26日再次行冠状动脉造影术,拟行右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中左主干原支架未见再狭窄,右冠状动脉中段狭窄80%(图1A),先行血管内超声检查(图1B~1D)。将OptiCross血管内超声导管送至右冠状动脉远段,连续自动回撤成像,可见右冠状动脉病变远段参照血管面积17.85 mm2,血管直径4.5 mm×5.0 mm;病变最窄处血管面积12.58 mm2,血管直径3.6 mm×4.2 mm,最小管腔面积4.67 mm2;病变近段参照血管面积21.48 mm2,血管直径4.9 mm×5.5 mm。病变部位的血管重构指数(remodeling index, RI)为0.64,提示血管负性重构。因患者无症状,病变最窄处最小管腔面积大于4 mm2,未植入支架,给予药物治疗。
1.2 病例2 患者女性,71岁,因“胸闷2年”入住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患者外院冠状动脉CT造影提示前降支狭窄90%伴钙化。患者入院心电图正常,心脏超声提示轻度二尖瓣狭窄、主动脉瓣反流,轻度肺动脉高压,左室射血分数69%。2020年6月16日行冠状动脉造影术,可见前降支中段分出粗大对角支后变细,狭窄80%(图2A)。进一步行血管内超声检查,提示病变远段参照血管面积5.08 mm2,血管直径2.5 mm×2.6 mm;病变最窄处血管面积5.54 mm2,血管直径2.4 mm×2.9 mm,最小管腔面积2.19 mm2;病变近段参照血管面积14.42 mm2,血管直径4.1 mm×4.5 mm(图2B~2D)。病变部位RI为0.57,提示血管负性重构。前降支血流储备分数为0.9(图2E),给予药物治疗。
2 讨 论
冠状动脉负性重构于1995年首次被描述[1]。依据不同的检查方法,该病变检出率为15%~34%。冠状动脉重构以RI来定义,表述为病变部位最小血管面积与病变远、近段参考血管平均血管面积的比值。RI大于1.05,为血管正性重构;RI小于0.95,为血管负性重构[2-3]。负性重构早期常出现血流动力学异常(剪切力、牵张力和流速等异常)。一般认为负性重构是细胞增殖、迁移、凋亡和细胞外基质重塑的过程,但具体机制仍不明确[4-5]。在重度狭窄的病变中,负性重构约占1/3;而在轻中度狭窄的病变中,负性重构约占50%[6]。

图1 右冠状动脉造影及血管内超声影像

图2 前降支造影及血管内超声影像
正性重构和负性重构病变中斑块性质常有较大差异。正性重构病变通常以薄纤维帽斑块和脂质斑块为主,而负性重构病变通常以纤维斑块和病理性内膜增厚为主[7]。正性重构病变通常表现为轻中度狭窄,斑块负荷大、炎症程度较高,斑块易损性高,常出现斑块破裂。而负性重构病变通常表现为重度狭窄,斑块负荷较小、稳定程度高,常是斑块损伤、破裂后修复、愈合的结果[8]。近年公布的PROSPECT研究[9]重新定义了RI值。该研究入选了697例三支病变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通过血管内超声评价了3 223处非罪犯病变,其中1/3的病变通过计算RI,确定正性重构和负性重构的最佳界值,余2/3病变通过病变形态学和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来验证此界值。结果显示:两种方法预测正、负性重构病变最佳界值分别为1.004 6和0.878 9;所有患者随访36个月后,未发生显著血管重构的患者中MACE发生率为0.7%,而发生正性重构和负性重构的患者MACE发生率显著升高,分别为2.5%、2.1%(P=0.025)[9]。
冠状动脉重构对冠状动脉介入策略有很大影响。本报告中的2例患者有明确的证据提示存在负性重构,且无介入治疗的依据,故未植入支架。对于这种从造影显示“简单”的病变,如按常规介入治疗策略进行介入治疗,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如血管穿孔、破裂等。
近年来中国冠状动脉介入数量爆发式增加,但因腔内影像使用率低,介入医师普遍对血管负性重构认识不足。而且,近年来与冠状动脉负性重构相关的文献数量很少,提示此领域并非临床关注的热点。然而,如果忽略冠状动脉负性重构对介入治疗中的影响,可能导致严重的介入相关并发症。因此,对于冠状动脉临界病变,须考虑负性重构可能,必要时进行腔内影像和血管生理学检查,评估介入治疗的必要性和策略,以保证患者安全。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