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国小说的“传奇”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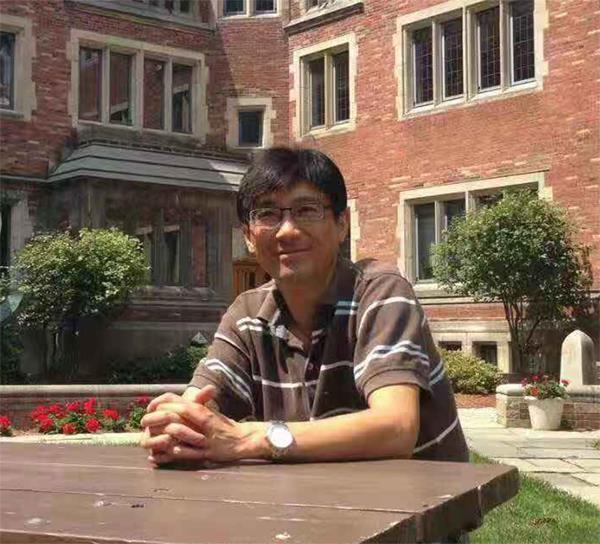
叶立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有《史铁生评传》等多部专著。兼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曾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屈原文艺奖等多种奖励。
本期讨论於可训教授开设于《长江文艺》的“临街楼”专栏。从2019年6月至2020年底,该专栏共推出了“乡村教师列传”系列10篇与“乡人传”系列9篇。因其立意新颖、写法卓异,故而广受读者欢迎。虽说批评家写小说近年来并不少见,但就此类创作内在的变革诉求而言,“临街楼”专栏却称得上是挑战了我们习见的“现代小说”模式。按李遇春教授的说法,中国现当代小说多为西方小说影响下的“正体小说”,然则在中国文学传统内,还有一个与此迥然相异的“原小说”谱系。它不是发轫于晚清和五四,随后又历经百年兴衰而不坠的小说现代性模式,而是一个出于稗官野史,取材于道听途说和街谈巷语里的杂体小说,它即便是内容散漫、形态粗粝,但那些名物观时、辨析义理的边缘秘史和饾饤见闻,却常能吸引读者去寻幽探胜和拍案惊奇。由是观之,说於可训先生的“临街楼”系列有别于文学现代性谱系似不为过。
李遇春的文章,以阐述“衰年变法”为开篇,直陈於可训先生的艺术秘密,其实就是向中国传统小说“传奇”种子的回归。在他看来,於可训先生“为民间野生人物树碑立传,打造不同于正史正传的野史杂传”,恰好反映了“中国小说家的永恒艺术冲动”。
吴道毅的文章,则以“重回乡村文化的精神原乡”为题,剖析了“临街楼”专栏中的精神流脉。他认为,“这种精神重回不仅是重拾对往昔乡村生活的珍贵回忆与对故乡父老乡亲的不断念叨,而且是对乡村人行为准则、人生观念与伦理规范的认同乃至某种程度的皈依。”
周新民的文章,用“事实”这个关键词立论,同样分析了“临街楼”专栏与中国传统小说之关系。在他看来,作为“史馀”的传统小说,“最主要的功能是实录人物言行”,但“晚清之后随着外来小说观念的引进,中国现当代小说所接受的实录传统发生了‘变异,对于事实的重视转化为对于真理的苛求”。如果以此为对照,那么於可训先生在小说里“重构事实和真理的关系”,无疑会有助于我们“洞悉当前小说创作的弊端”。
於可训先生近年来醉心于小说创作,长篇短制,多管齐下,斐然成章。先生自谓此举乃“衰年变法”,其中有深意存焉。所谓变法云者,其实乃古人以复古为革新的成例,不过是想回到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去寻找种种有价值的资源,因旧开新、以新化旧,其旨归在于新旧文学的艺术融合。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向来以诗文为正宗,小说作为俗文学的文学史地位长期得不到承认,甚至小说的概念长期以来也莫衷一是,处于学术的灰色地带。直到近人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依旧把小说与戏曲混搭在一起。其实混搭也有混搭的好处,文体界限过于分明也会带来文体固化的流弊。所以与其写那种过于像小说的小说,或者说一看就是小说的小说,还不如写点不像小说的小说,或者说看上去不像小说而实际上想想又是小说的小说。这种小说摒弃了过于欧化、过于洋派的做法,径直返回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小说”传统。说“原小说”是相对于西方近现代小说的定义和定型而言,其实中国古代小说也有自己的定义和定型,其中最有名的小说概念和体制就是唐人的“传奇”。按照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说法,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就高度概括地肯定了“传奇”作为中国小说的文体形态与文学地位。此后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断言“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则就此发挥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可见“传奇”是中国小说文体形成的标志,它不仅吸纳了唐之前的各种文体资源,而且唐之后的中国小说文体无论如何变化,总归是能到唐人传奇中去寻找到文体的种子。而於先生以《乡村教师列传》和《乡人传》为代表的小说系列,从中国小说文体演变的角度看,其中正隐藏着中国小说“传奇”文体的种子,这大约就是先生“衰年变法”的艺术秘密。
中国传奇虽然号称文备众体,但实际上还是以史传为宗,故而宋人说传奇中可以见史笔。中国人素来有写史传统,除了官修的正史外,还有大量的民间书写的野史笔记,这野史笔记中就有许许多多的小说家者言。所以中国传奇以史传为宗的本义,就在于书写野史杂传。从汉代太史公司马迁的正史正传《史记》,到清代异史氏蒲松龄的野史杂传《聊斋志异》,中国小说的传奇文体演变可谓渊源有自,不绝如缕。于是我们发现为民间野生人物树碑立传,打造不同于正史正传的野史杂传,成了中国小说家的永恒艺术冲动。於可训先生近期的小说创作大抵正致力于此。不仅他的《乡村教师列传》和《乡人传》系列是如此,他的中篇小说《特务吴雄》《才女夏娲》也是如此,而《幻乡笔记》同样可作如是观。《乡村教师列传》包括10个短篇,作者在这个系列中并没有陶醉于各种离奇曲折故事情节的编织,而是以鲜活的野史雕刻传主的灵魂,让新中国建立以来最早的两代乡村教师的民间形象在朴素的叙述和简洁的白描中得以凸显,由此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乡村知识分子人格展现在读者面前。这里有吴先生的隐忍人格,她在新旧时代变迁中完成了从私塾先生到民办教师的转型,尽管新生活依旧曲折难平,但她始终坚守有底线的人生哲学,育人有方;这里有张先生的刚直人格,他以军人身份成功转型为民办教师,并以其独特的教学方式深受学生爱戴,即使遭遇不公正待遇,但其依旧拖着残躯守护校舍,直至献出生命;这里还有熊先生的狷介人格,在常人眼中其性情古板平直,不善變通,被人讥之为书腐,但在特定的浮夸时代里,正是他那种执拗的不肯与时人同流合污的言行举止,折射出乡村教师的独立人格力量。此外还有说聱声话的胡先生,他坚持不懈地推广着自己独特的“普通话”,他的人格朴实而峭拔,令人钦敬;还有痴情至死的白先生,她高洁而浪漫的人格如屈子诗中的香草美人不朽;还有得了饿痨病的梅先生,他在饥饿年月里展现出的真性情和真人格,虽卑微却率直,足以令伪士自惭形秽;至于那位写了一辈子诗体文学史的徐先生,最终将心血之作在亡妻坟前坦然焚祭,其人格之淡泊高蹈,颇有魏晋风度。而说到小一辈的乡村教师们,小吴先生摆不脱的宿命与颓唐,小徐先生辗转尘埃而不改初心,小张先生子承父业的最后精诚,其命运无不令人感慨唏嘘,其人格无不令人仰之弥高,足以泽被后世。
《乡人传》由9个短篇构成,与《乡村教师列传》的10个短篇相映成趣。从乡村教师这个特定的民间知识分子群体转向更广泛的乡村异人系列,显示了作者深厚的生活积淀与广阔的文学视野。这个系列的小说让读者不禁想起新时期流行的“寻根小说”,诸如“异乡异闻系列”“葛川江系列”“商州系列”之类,作者早年也曾大力倡导所谓“新轶事小说”“新笔记小说”,可见广义上的“寻根小说”依旧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区别在于,於先生的这些小说系列写实性和历史感更强,更接地气,不像当年的“寻根小说”那样刻意去淡化小说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语境,人为制造所谓的荒蛮野趣,让读者超拔于现实时世之外。《乡人传》照例以野史杂传为宗,但不像《乡村教师列传》那般着力凸显乡村底层人格的正義与崇高,而是更多地展示了乡村底层人格的斑斓与驳杂,由此平添了更多的民间趣味。这里有在旧社会里当过扒手的细爹(《看相细爹传》),当过神婆的二奶(《阴婆二奶传》),当过拳师的夏叔(《教师夏叔传》),当过黑社会头领的齐大爷(《汉流大爷传》),当过雕花木匠的“我外公”(《博士外公传》),他们在新社会里的遭遇不一,虽然也有像齐大爷那样因对革命有功而或活得有滋有味的,但大都命运起落浮沉,作为新社会里的边缘人或另类人物而苟活,因此留下了不少辛酸而诙谐的往事。比如在乡民眼中会看相的细爹,其真实身份是旧社会的一个扒手,但细爹的扒手前史被作者写得谐趣横生,远非正统道德评判可比。再如阴婆二奶,其实是民间能通阴阳两界的神婆,她的旧职业在新社会里遭遇到不可避免的尴尬。而夏叔虽然治过解放军司令员的伤病,但他毕竟是戴罪之身,一直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生存地带。还有细木匠外公,他在旧社会里为二外婆精心打造的婚床,后来在政治运动中成了母猪喂奶的猪窝。即使是解放后风光无限常坐主席台的齐大爷,到晚年也逃不了被新环境遗弃的命运。至于写乡下疯女人爱情故事的《歌子三嫂传》,借乡村饭铺女主人写民间世情的《饭铺冯奶传》,写被革命胜利者遗弃的乡村女性婚姻悲剧的《伤心三姨传》,还有写被时代所遗忘的革命老人的《凉亭吴奶传》,无不立足于民间立场讲述乡野故事,塑造出了个性鲜明、性格鲜活、人格迥异的艺术形象。
如前所说,虽然中国传奇以史传为宗,但少不了抒情与议论。这正如中国古代文章,在史传散文之外还有诸子式说理散文与辞赋体抒情散文。於先生的传奇体小说系列中,同样也在史传叙事中渗透着说理与抒情的因子。就说理而言,主要表现在《乡村教师列传》每一篇的末尾都有一段“临街楼主曰”,这无疑借鉴了“太史公曰”“异史氏曰”的笔法,但其中的议论文字绝非陈词套语,而是饱含着作者深刻的当代生命体验,有着强烈的时间交错感和浓烈的命运意识。至于抒情因素,大多不像议论文字那般直接呈现,而是通过诗意化的白描含不尽之情见于言外,或将绵绵深情寄寓在人物命运的娓娓叙述之中,让读者掩卷低徊。如《吴先生列传》中描写女主人公寒夜课读的场景,温馨而动人。《白先生列传》中描写女主人公的美丽、活泼与死亡,残酷中沁透着诗意。《看相细爹传》结尾写幽暗的猪屋里划出一道白光,神秘而精警。《博士外公传》开头写漂亮的外公喝蛋汤的记忆,余韵悠长、笼罩全篇。凡此种种,无不提升了中国传奇的格调与神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