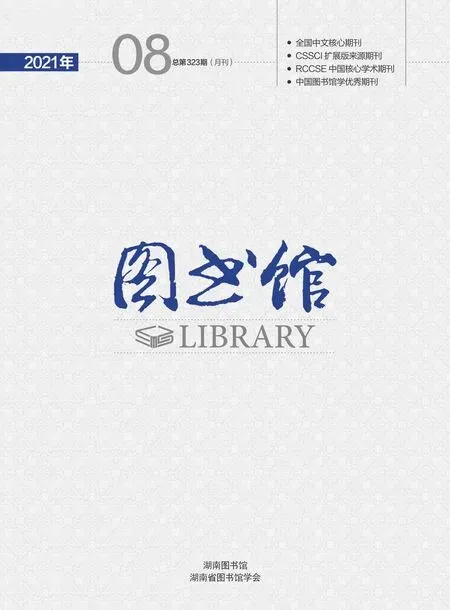“九一八 ”前后图书馆界对民族危机的预警、认知及应对*
——以杜定友先生为例
刘寿堂
(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1331)
作为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历史来看,‘九一八’事变都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 ,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在战争阴影下,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发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激愤与痛骂之余,知识界被迫直面国难,在反思的基础上,开始以“埋头硬干的新态度——学术研究要为民族复兴服务,担负起了振兴我们的国家民族的新使命”[2]。王云五、沈祖荣、杜定友等图书馆学人纷纷立足于本职工作,致力于实现文化传承和社会动员的目标。“图书馆界的本位救国,是对日本文化侵略的一种因应,突显了图书馆界的民族意识,为民族危机下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3]38
杜定友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图书馆学家,他在图书馆学术、教育、管理等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严文郁先生曾指出,民国9至17年为中国图书馆学术发轫期,“以戴志骞、刘国钧、杜定友等专家之论文最为突出”[4]。杜定友着力探索图书馆事业中国化道路的精神为时人所肯定:“他融东西图书馆学为一体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尤为值得称道。”[5]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图书馆界本位救国的代表人物,杜定友先生在“九一八”前夕敏锐地预警到危机的可能性,国难发生时他沉痛而深刻地反思了国耻的根源,事变后他以图书馆为战场,积极投身民族救亡运动,“辄以未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憾,其磅礴抑郁于胸中之血诚,往往流露于笔墨语言之间。每执笔为文,无不以国族前途为重。行文论事,着重实际,一字一泪,非空言无补者可比”[6]4。所以,今天我们检索杜定友先生留存的数百万字作品,除了大量编目类专业论文,还能发现不少与民族危机相关的文章。如《杜定友文集》中的《国难杂作》(第十册)、《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民众反帝之第一声》(第十五册)、《鸦片战争以来史料目录》(第十六册)、《广东人民在三元里抗英斗争简史》(第十七册)、《对日问题与圕》(第二十册)、《图书馆与国防文化》(第二十一册),还有很多讲稿及随笔散见于报刊。尤其是部分篇什发表于“九一八”后,结集自刊于1938年的《国难杂作》,集中体现了一个图书馆学家面对民族危机时的所思所为,为诠释杜定友先生本位救国思想做了生动注脚。
1 “九一八”前对危机的敏锐预警
1926年杜定友应邀访日,受到以间宫不二雄为代表的日本图书馆界的热情欢迎。此次出访使他成功开启了中日图书馆界双向交流的“圕”时代,得以以“一个图书馆学家的眼光对日本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状况进行调查分析”[7],更重要的是,他近距离考察了日本学界和日本社会。敏锐的眼光、冷静的头脑、理性的判断,使他从细节中发现了日本觊觎中国的蛛丝马迹。归国后,他在《日本国民性之观察》和《日本图书馆参观记》等文章中均传达出对危机的预感与隐忧。
1.1 日本民族独特的义利观国人应重视
他游历日本十七埠,“未尝见有途中打骂争夺之事,凡有所问辄和颜悦色以答,绝无骄傲态度”。但他发现,“若讲求政治,则主义不同,党派纷歧,争辩自属不可幸免之事。”日本人重视整体利益,“团体力异常坚厚,倘为国为党,辄以全力赴之,不少退让。”所以,他清醒地认识到,“此次日人之盛意招待,倘谓出于优意,殊不敢必,但遇有利害冲突时,其必以力争,足可断言。”[8]因此,他给国内当局提醒,“即因政治上之利害冲突,为正谊而战,似犹不失为大国之风度也”。他发现日本人尚实用、贱形式,比如交通设施,“须先求便利,铺陈装饰,不过次要之务而已”。他尤其欣赏日本人孜孜以求的学风,赞赏其善于模仿、长于改良的能力。他惊诧于日本各图书馆读书人数之多,其管理未必良善,但是,“该国图书馆学者之毅力研究、及馆员之热心从事,实为他国人士所不及。将来进行,未可限量。”[9]
1.2 日本对中国研究之精深当局应警惕
访日期间,专藏关于中国和东亚书籍的东洋文库让他印象深刻。该文库是由前中国总统顾问莫利迟博士所建,藏量丰富,涉及广泛,包括了诸如《永乐大典》国内佚失部分卷册的珍贵版本,更有甚者,“各种关于中国的外国杂志,有数十年不缺一册者”。面对那些中国无而外国有的孤本,他虽爱不释手,但是,“观之,倍加悲痛。可惜那些故乡遗物,竟漂流异域,一去而不返了!”在他看来,日本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宝库,才能对东亚各国历史民情洞若观火。“我们年来在外交上、政治上受外人的侵略,他们也不是贸然而致的。他们一般政治家,天天在那里把我国当作一件试验品。我国人知道也未?政治家拿了图书,就可以筹划政策,指定方针。日人对于我国情形,这样熟悉,东洋文库,亦与有功焉。”[10]正是鉴于日本对中国研究之深、之广、之精的警惕,他在1928年即着手编辑研究日本的书目,在后来扩展书目的补序中写道:“拿句旧话来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11]2
1.3 日本对涉外事项的谨慎军方须关注
日本对待外来文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既大胆采择西洋各国工艺之长,又固守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杜定友发现日本国内虽不乏穿洋服者,但洋装之质料,却全属日本土货。“日当局及学者亟亟以欧化侵入为患,努力防救,未尝或懈。”杜定友在日本考察期间,虽受优渥待遇,但除图书馆较为公开以外,很多地方均以机密为由谢绝前往,一些并非军事之地,亦不能尽数公开。据他在《日本国民性之观察》中记载,游历所到之地,大多禁止拍照和记录。对于军事与政治方面事项,则更为秘密。虽然他理解这几乎是各国通例,但他仍然感觉“日人犹为甚耳”。20世纪20年代日本军部法西斯形成后,朝野弥漫着甚嚣尘上的侵华情绪,他从这些蛛丝马迹中敏锐地捕捉到不祥气息,后来的事实验证了他的预判。1927年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发表,1930年日本法西斯攫取政权后加速战备,着手实施武力侵华。
2 “九一八”时对危机的深刻认知
“九一八”发生后,举国震惊,社会各界纷纷谴责日帝的暴行,批评蒋氏政府的妥协退让。《大公报》撰文指出,“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在政治上负责之人,虽自责亦无法谢国民。一笔误国殃民账,实已不堪算,不能算!而今日外患频临,兆民水火,国家人格被污尽,民族名器被毁尽!”[12]在愤怒与失望之余,知识界开始探讨导致国难的内在根源。时人曾指出,“自历史上观之,凡一民族在极危难的周遭中,必有一种深刻而沉痛的反省,进而有努力挣扎向上的态度与民族复兴的冀求。”[13]这种痛定思痛式的自我解剖,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宝贵财富和精神力量。
图书馆学人同样做出了深刻反思。沈祖荣在《国难与图书馆》中列举了欧战时德国、比利时以及后来的美、日等国皆曾因国难而致本国图书馆事业遭遇浩劫,但是,“卒能奋发有为、而益发扬光大,堪足以为吾人国难中之借鉴者”。他沉痛呼吁:“国难!国难!你是我们自知警惕的晨钟,愿我们同人,警醒罢!能警醒罢!”[14]藏学家于式玉女士在“九一八”时还只是图书馆界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她于1930年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日文部担任编目。在评介日本东方学论文书目时她亦有类似反思,“吾人观于东西学者所努力,则知彼邦盖非纯以军事争胜者而知所以自奋矣。”[15]“九一八”事变将杜定友心中的隐忧变成了现实,虽然“愤火中烧,心胆俱裂”,但他仍以一个图书馆学家的独特视角来冷静地看待这场危机。
2.1 民族危机发生的必然性
“九一八”事变前,杜定友先生在政治方面服膺三民主义,拥护南京国民政府,支持党化图书馆建设。但他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吏治腐败、经济衰退、社会混乱有着清醒的认识,反观日本的国民性及国家政策,他认为在列强环伺而国弱民贫的环境下,民族危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纵此次暴日不发难于前,列强未必不瓜分于后。”[16]他的这一认识与胡适的观点不谋而合。“九一八”之后,胡适指出,“九一八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的,他不过是五六十年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一个危险局面的一个爆发点。”[17]虽然他职司文教,但他敏锐地认识到经济在国家综合实力中的关键作用,所以他判定民族危机中国民经济必将首当其冲,“现在列强对我鹰瞵虎视,用尽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种种侵略,制我死命,而其中以经济侵略为害尤甚。”[18]这些预言不幸被后来的事实所印证。
2.2 文化教育的严重失策
东三省的沦陷,时人莫不归咎于军事外交不力。而在杜定友看来,一夜之间失地千里,军政当局固然难辞其咎,但文教的严重失策才是重要原因。新教育没能培养出披坚执锐、以身许国的勇士和国士,倒养成了很多洋货的拥趸,教育不过是洋货的急先锋而已。“所谓智识所谓文明者,仅略知欧美物质之美而已。数十年来,教者学者,埋首于物质的追求,而竟忘学术之研究。于是长袍短褂,目为迂腐。洋装革履,方称时髦。……人人惟物质文明是图,上下唯利是征,无怪乎学生之不务实学,生活之竞趋浮华矣。”[19]所以他建议,今后之教育,“当力矫虚伪之习,以养成勤俭实践之士为宗旨……尤应注意于人格之陶冶,质朴之养成”。作为20世纪著名的“图书馆界留学一代”的成员之一,杜定友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主张“运用世界图书发明中国真理,采取西洋方法养成中国学者”[20]。但他批评过于功利化倾向的教育,泯灭了受教育者的责任意识、服务观念与实际能力,最终培养出了一群浮华、虚骄、沽名钓誉的唯利是图者。他尤其强调文化强国的意义,在抗战后期,他甚至提出:“没有文化,就没有国防。”[21]
2.3 缺乏对对手的必要研究
他痛感国人昧于时势,对日本只是一味地排斥和反对,却不愿做深入研究。他认为很多中国人就像戴季陶先生所说的“思想上的闭关自守者”“智识上的义和团”:既不愿看日本字,也不愿听日本话,甚至不愿见日本人。中国总是疏于研究对手,可对手却把我们里里外外研究个透。他引用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话来批判国人,“‘中国’这个题目上,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到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千百次。”[11]1他主张,日本这个民族无论在学术、思想、种族还是文化上,都是远东地区的大国,与世界很多国家都紧密相关,不容忽视。他建议今后要切切实实地下工夫去研究日本,要对他们的性格与思想、国家和社会的基础等诸多问题展开研究。“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才晓得他的现在是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去向是怎样。”杜定友认为,国内普遍对日本的疏忽,正是“九一八”败绩的重要根源。
3 “九一八”后对危机的积极应对
“九一八”后的知识分子直面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以振兴国家民族为己任,在痛苦的反思中寻找出路。史学家傅斯年于东北沦陷一周年之际,在谈了四点失望、四点希望之后提出,“浅看来是绝望,深看来是大有希望。这希望不在天国,不在未来,而在我们的一身之内。我们若以民族的希望为宗教的信仰,以自身之勤勉工作各尽其职业为这信仰之行事,则大难当前,尽可处之泰然,民族再造,将贡一份助力。”[22]图书馆学家沈祖荣表示,“目前虽临万难之中,千钧一发之时,亦应积极前进,不可推诿,以达到这个事业的健全与合理的发展,也可以改进现在,紊乱颓败简陋的各种现状。”[23]图书馆界纷纷将爱国情感转化为实际行动,1932年“九一八”一周年之际,浙江省立图书馆新民分馆儿童阅览室门前的条幅极为触目:“杭州各界诸君,你们习于目前的安平,沉醉于西湖的浏览,就忘了九一八么?”[24]该次展出了大量与“九一八”相关的实物、照片和书籍,当日虽凄风冷雨,但观者云集,络绎不绝。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藏量丰富的东方图书馆被焚,多家图书馆被毁,多处私人藏书被劫,日帝的嚣张气焰和罪恶行径激起了图书馆界的强烈愤慨,也激发出了图书馆界人士更强烈的使命感。次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发布宣言,“今日吾华民族对于国家前途,己身存亡,其所负荷,实千百倍于重前贤,艰于他国!吾辈职掌近代知识之宝库,典守先民之遗藏者,丁兹时会,尤应以知识之明灯,出有众于幽暗。”[25]杜定友先生终生以图书馆为志业,以“圕迷”自居。他深知图书馆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意义,更懂得一个图书馆人在国难时期的责任与担当。“九一八”一周年之际他曾写道:“圕是一个教育机关,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专门教育,和家庭教育,都有直接关系。所以服务于圕界的,职责很重,范围很广……于是刻苦奋斗,以求打破恶劣的环境,增进圕的效用,孜孜矻矻,数十年如一日,澹泊宁处,不为外界虚荣所诱。只有为民众服务之心,而无升官发财之想,这就是‘圕迷’了。”[26]“九一八”后,杜定友先生“于敌机狂轰,烽火满天之际,以极力保存文献为己任。于圕参加救亡工作,策划尤多”[6]4。
3.1 编辑了解日本的图书目录
杜定友认为,国内各界对日本研究的阙如,是导致国难的原因之一。所以,他先后多次编辑不同版本的关于日本的书目,为国内研究者提供阅读路线图。图书馆史学者刘劲松先生曾肯定,“在各种中日问题研究书目中,杜定友的著作开了先河。杜氏的书目在济南惨案后即已开始编印。”[3]59“九一八”事件后,杜定友对1928年撰写的研究日本的书目进行了拓展。在新版序言中他写道:“旧仇未报,新创又起,回思国难,悲愤填膺。友服务于图书馆,愧无干城之力,而报国有心,未尝后人。敢不就我所知,尽一份子之义务。前者有研究书目之发行,以期唤起国人之注意,不图研究之工作未完,日人之暴行又作;乃将近来所有关于日本书籍再为增补如左。”[11]2新书目主要包括了《日本社会运动史》《满蒙秘密》等共计六十部著作。每书皆有简短数语之评介,以供读者索引参照。《对日问题研究书目》是一篇长文,其内容分节刊载于1932—1933年《活力》杂志的第8、9、10、11、12、17、18期。该书目是当时最为系统的专业书目,备受同行和读者好评。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各种版本的日本研究书目纷纷出台,一时蔚为风潮。被收藏于他的文档中的《五中周刊》有一份“本校图书馆对日问题研究书目”,即在其指导下编辑完成(见表1)。

表1 1932年《五中周刊》列出的“对日问题研究书目”[28]
3.2 探讨研究日本的科学方法
杜定友随时提醒国人,“这次日本不顾人道公理,在东北悍然出兵。我们所受的创痛,实在较前更甚,那末我们研究对日问题,应更加努力。”他认为,要研究日本,除了较全的书目,还应有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为此他撰写了《“对日问题”研究方法》的长文进行探讨。他反对以功利化的目的去研究,“切忌存一个要发表结果的心理”,否则容易落入苟且与肤浅的俗套,这样的研究毫无价值。他主张研究学术首要的是占有充分的材料,然后才可能有精确的见地。至于搜集材料的方法,他推荐了三种:卡片制度、剪报、裁剪。“总之,研究学术都在平常努力。尤在乎首先确定目标,随时留心,有了充分的材料,才可以研究比较,用演绎或归纳的方法,求得相当的结果。”[27]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研究对日问题的大纲,包括“日本之研究”(涉及背景、人口、经济、近代史、政治等十二个方面)、“中日关系之研究”(包括政治、外交、军事、交通等四个方面)、“东北之研究”(包括交通商业、最近东北事件之研究等四个方面)。他根据该研究大纲,附录了包括《日本民族性研究》《暴日侵占东省特刊》等总共311本参考书。

?
3.3 开设抗日宣传的专题讲座
“九一八”前后的一些专题讲座真实地反映了杜先生在面对国难时的所思所为。“九一八”事变后,他定期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开设关于时事与读书方面的专题讲座,不少内容是围绕国难展开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九一八”发生的第二天即1931年9月19日,他为交大师生所做的《对日问题与圕》的演讲。他告诫学子,“从今天起,我们该觉悟了,我国现在国势阽危已经到燃眉的时候了。”他相信,若是各人都有一管枪、一口炮,没有一个不愿效力疆场、为国捐躯的!但是作为一个理性的图书馆学家,他并不鼓励学生追随当时青年人所热衷的投笔从戎、弃学从军的潮流。相反,他提醒学生,“诸君要记得,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我们第一要主持镇静”,“还有许多许多事要待你们去干的,所以我希望诸君不要操之过急,好预备将来为国家努力!”[29]他认为如果草率地把大学生送上战场为国捐躯了,国家未来建设将无由承担。所以,他认为学子应“努力学问,将来制造许多枪炮,发明许多机器,比较现在自己拿一管枪去杀一个敌人的效力,何止千倍”。其观点与六年后全面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所主张的“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完全一致。

表2 杜定友《“对日问题”研究方法》中收录的交通大学救国联合会分会宣传组工作大纲
3.4 指导学生抗日社团活动
杜定友不但有精深的专业技能,还有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在任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他积极支持学生抗日社团活动。他不但为交通大学救国联合会分会开列对日研究的书目,为该会举办抗日讲座,还在抗日宣传品设计、印刷、张贴等方面给予方便。“一·二八”之后,上海情势越发危险,有的时候,“已闻炮声隆隆,飞机翼翼,此稿能否完毕,殊无把握”,他却仍不余遗力地工作,积极支持学生抗日社团活动。在《“对日问题”研究方法》中,他还特地将“交通大学救国联合会分会宣传组工作大纲”作为研究案例收入其文档中,其支持学生社团由此可见一斑。
在“九一八”前后,像杜定友先生这样能够在事变前预警危机、事变时反思危机、事变后积极应对危机的图书馆学人不在少数。如燕京大学图书馆青年馆员于式玉女士,在热河被占后,她翻译了借高僧身份掩护而长期活动于中国的日本间谍水野梅晓的著作《现存热河的贵重文献》,揭露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事实。可以说,那一代图书馆人虽然人生际遇各不相同,但都延续着忧国忧民、舍我其谁的精神传统,在国难关头以一己之力推动国家民族艰难前行。
(来稿时间: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