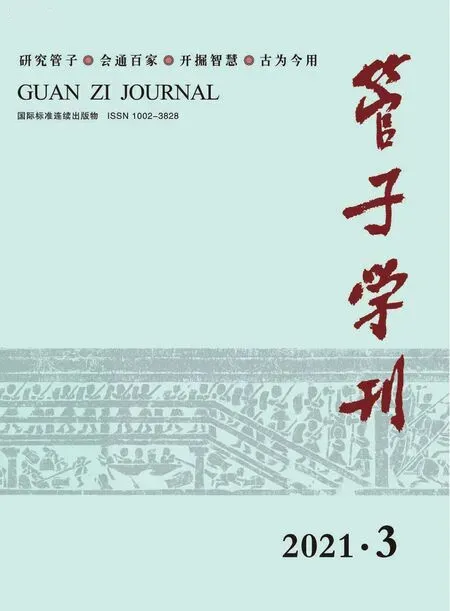利用出土文献校释《尚书》三则
王坤鹏
(吉林大学 历史系,吉林 长春 130012)
《尚书》大部分篇章本是商周时期的行政纪录,在秦汉以前以古文字的形式书于竹帛。秦汉以后,《尚书》历经文字的转写隶定,复经历代经师的口耳相传,其间出现字词讹误或注释歧异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清末以来,随着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不少学者开始利用古文字资料校释《尚书》,取得了重要成果(1)例如清儒吴大澂利用金文资料指出《尚书·大诰》“宁考”“宁人”“前宁人”“宁王”“宁武”之“宁”当是“文”字的讹误,其校释成果已为今人广泛采用。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67页。。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曾论称:“《尚书》,古籀之书也,不循古籀以求之,徒据后人窜改伪啎错集之迹,奋臆骋辞而强为之解,无当也。”(2)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其说法有一定道理。笔者在研习甲骨文、金文的过程中,亦发现有关资料有助于《尚书》部分词句的释读与理解,故不揣谫陋,试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作考释三则,以求教于方家。
一、《盘庚》篇“凡尔众”考
《尚书·盘庚上》云:“凡尔众,其惟致告。”(3)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页。关于“凡尔众”的“凡”字,伪孔安国传、唐代孔颖达疏乃至清儒所作注疏中均缺乏专门的考释。当代专家例如顾颉刚、刘起釪等先生释为“凡,所有”(4)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948页。,屈万里则将该句整体译作:“凡是你们众人。”(5)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57页。可见专家一般将“凡”当作一个副词,乃“所有”“凡是”之义。专家的解释粗看似无问题,仔细推敲起来仍觉有未安之处。不管是“所有你们族众,加以告诫”,还是“凡是你们众人,加以告诫”,均是不通顺的。从语法上分析,“凡尔众”句实际上省略了主语,整个句子是一个动宾短语,“凡”字所在的位置应当是一个动词,而非副词。
在“凡”的位置当是一个动词,于此还有一个旁证。《盘庚》篇中与“凡尔众”句类似的有“格汝众,予告汝”(6)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4-225页。一句,两个短语的句式和内涵均十分相似,“凡”与“格”在句中的位置也是相同的,因此可作类比。清儒孙星衍引《尔雅·释言》将“格”释为“来”(7)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第225页。。另外,《尔雅·释诂》亦云:“格,至也。”可以看出“格”是动词,意思是来、至,“格汝众”应是聚集、召致众人的意思。与“格”位置及内涵均相似的“凡”字不当是副词,应该也是一个具有聚集、召致之义的动词。


《盘庚》篇“凡尔众,其惟致告”原本应即是“同尔众,其惟致告”,译成白话文就是“召致你们的族众并加以告诫”,读起来文从字顺。“同”的这类用法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并不鲜见,例如《合集》11171:
(1)贞:呼同多沚。
《合集》10132反:

《合集》6354正:


概括以上所论,《盘庚》篇中“凡尔众,其惟致告”之“凡”,无论释为“所有”还是“凡是”,都存在语法以及释义方面的问题。“凡”应是一个意为召致、聚集的动词,而非是副词。“凡”很可能是商代甲骨文中的“同”字的讹误。在甲骨文中,“凡”“同”字形非常相似,学者在隶定及考释时经常误将“同”隶释为“凡”字。“同尔众,其惟致告”即“召致你们的族众并加以告诫”的意思。商代后期的甲骨文中经常用“同”字来记述召集族众之事。“同”的这类用法在西周早期的铜器铭文中还可以见到。对“凡”“同”的辨析虽只是文献的校勘,却有助于我们探讨《尚书·盘庚》篇的文本形成问题。现在一般认为《盘庚》原文内容应当出自商王盘庚,由史职人员记录下来,不过现在所见到的文字,其中不少字词体现的是周代的使用习惯,可知是经过周代加工润色写定下来的(17)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964页。。裘锡圭曾讲到:“《商书》用词行文的习惯往往与甲骨卜辞不合。如《盘庚》喜欢用‘民’字,在卜辞里却还没有发现过同样用法的‘民’字。但是《商书》各篇所反映的思想以至某些制度却跟卜辞相合。看来,它们(《汤誓》也许要除外)大概确有商代的底本为根据,然而已经经过了周代人比较大的修改。”(18)裘锡圭:《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裘锡圭学术文集·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9页。学者的看法是恰当的。目前来看,带有“口”这一区别符号的“同”字,最早出现在西周前中期。《盘庚》篇的润色加工应当在此之后。此时的学者已经不认识不带“口”的“同”字了,因此将“同”误隶作了“凡”。
二、《多士》篇“有册有典”句考
《尚书·多士》篇云:“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敢听用德。”关于“有册有典”一句,孔传云:“言汝所亲知,殷先世有册书典籍,说殷改夏王命之意。”孔颖达的疏解大致相同(19)孔颖达:《尚书正义》,第503页。。今天学者均沿续了这种解释,例如周秉钧云:“此言殷革夏命之事,殷之先人册典皆在,惟尔知之,革命非我周创举也。”(20)周秉钧:《尚书易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屈万里云:“典册中载有殷革夏命之史实。”(21)屈万里:《尚书集释》,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98页。顾颉刚等云:“如你们所周知:殷家的先人传下来的典册,上面记载着殷革夏命的故事。”(22)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525页。可以看出,古今学者关于“有册有典”一句的解释大体为:商代先世有册书典籍,其上记载着殷革夏命之事。
这类解读尚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首先,学者将“有册有典”与“殷革夏命”联缀在一起,中间增加了谓语动词“说”“载”“记载”等,实际上是增字解经,而且所增加的部分是原本不可或缺的谓语动词,这说明将“有册有典”与“殷革夏命”联缀成一句并不可行。其次,《多士》该段文辞为周公称述周王的诰命,从情景上看,周公讲述殷革夏命之事,不必强调该事件记载在商人的典册上,实际上后文所述主要是简选官员及册命职事的内容,与商人典册并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将“有册有典”解释为商人先世已经有典册图籍,这在整个前后文语境里是比较突兀的。
另外,学者解释该段内容,大多认为“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一句所说为一件事,即商人典册上记载着殷革夏命之事,又认为“今尔又曰”之后的内容所说的是另外一件事,主要是讲周王朝用人之法的。例如孙星衍云:“惟汝知殷先人有典册记识革夏命之事。今汝又曰:夏进用在王庭者,有殷之众士,治事在百官。怨周之不用殷士。”(23)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第429页。曾运乾云:“典册记载殷革夏命之事,汝所稔知也。汝等所致疑者,周代用人之法也。”(24)曾运乾:《尚书正读》,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17页。可见学者一般认为该段内容所记述的是前后并列且没有关系的两件事情。
南宋时期的蔡沈已意识到这种理解所存在的问题,并设法加以弥缝,其云:
殷之先世,有册书典籍,载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尔何独疑于今乎?周公既举商革命事以谕顽民,顽民复以商革夏事责周,谓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启迪简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间,今周于商士,未闻有所简拔也。(25)蔡沈:《书经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
蔡沈将“商革夏命”作为前后两件事的连接点,商代先世的册书典籍记载了商革夏命之事,而有关商革夏命之事又成了商遗民责备周人的根据:商革夏命之初,曾简选夏遗民担任官职,周取代商后则没有类似的作为。
当代学者也有与蔡沈相类似的看法,例如顾颉刚、刘起釪等将《多士》篇该段译为:
如你们所周知:殷家的先人传下来的典册,上面记载着殷革夏命的故事。现在你们中间有人根据了这些历史,说道:“[在夏亡之后,]有许多夏人是被召而选择于商王的朝廷的,商朝的百官之中少不了他们的职位;[但为什么现在不这样呢?]”(26)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525页。
顾颉刚等学者对该段内容的理解思路与蔡沈基本相似。这一思路可简要概括为以下几个环节:1.殷先世有典册图书;2.典册上记载着殷革夏命的历史;3.殷革夏命的历史包括商人简选夏遗民进入王庭为官的内容;4.商遗民因此得以援引这些记载责备周人。可以看出,无论是蔡沈还是顾颉刚等学者的解释,首要问题仍然是在“有册有典”与“殷革夏命”之间增加“记载”一类的谓语动词。再者,学者为了通读该段所作的弥缝颇为曲折,其中增添了不少细节,假设的环节太多。例如商人典册上记载着商人简选夏遗民担任官职、商遗民根据典册的记载责备周人等说法多属臆测之词,均找不到切实的证据。
实际上,《多士》篇此段内容无需增加谓语动词即能说通,而且其所阐述的是一事而非二事。其关键就在对“有册有典”的理解上。“有册有典”一句中的“有”只是一个没有具体含义的语气助词,并非有无之“有”(27)王引之云:“有,语助也。一字不成词,则加‘有’字以配之……说经者未喻属词之例,往往训为‘有无’之‘有’。”例如《尚书·盘庚》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有比”即“比”;《尚书·盘庚》曰“民不适有居”,“有居”即“居”;《尚书·召诰》曰“有王虽小”,“有王”即“王”等。见王引之:《经传释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1-62页。,“有册有典”不是讲商人先世有典册图书之意。“册”与“典”在文献中的意思相同,均指册命,这里所说的是商王册命官职之事,也就是下文所讲的“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士》该段内容从头至尾所讲的都是选拔与册命官员之事,并不涉及商人典册图书记载殷革夏命之事。
“册”与“典”在商代甲骨文中均有册命之义。甲骨刻辞中常见“爯册”一词,例如《合集》6087正:
到了西周时期,册命已经成了周王任命官员的一种通行的程序,一般由作册一类的史官来进行。商代以及西周时期铜器铭文中常见“作册”一职,又称“作册内史”“作命内史”“作册尹”“内史”等,王国维谓“作册、尹氏,皆《周礼》‘内史’之职”(32)王国维:《观堂别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23-1124页。。史官所负职责较多,其中之一即是书写并宣读册命文书(33)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例如《集成》4277师俞簋盖铭文记载周王任命师俞官职:“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在周师彔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司马共佑师俞入门,位中廷,王呼作册内史册命师俞,兼司(34)“兼司”依据陈剑的考释。见陈剑:《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228-230页。保氏,赐赤巿、朱黄、旂。俞拜稽首。”铭文中的师俞,本为军事类职官,周王在周师录宫命作册内史追加册命,让师俞总司保氏一职,并赏赐与职官相应的服饰、旗帜等。
概括以上所论,关于《尚书·多士》篇“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一段内容,学界的理解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在“有册有典”与“殷革夏命”之间添加谓语动词“记载”,释为“商代先世有典册图籍,其上记载着殷革夏命之事”;其二是将“有册有典”与其后所述周人选官之事视为不相关的两件事情。实际上,“有册有典”指商代先世曾册命官员与职事,“有”为语气助词,非“有无”之“有”,“册”“典”指册命职事。而且该段内容前后一贯,所讲述的均是周王选拔商遗民、册命官职之事。整段内容可译释为:“你们知道,商代先世即行册命官职之事,商革夏命,你们说商人曾简选夏人在商王廷任职,负责相应地职事,我周王也是以德行作为简选官员的依据。”
三、《洛诰》篇“王在新邑”句考
《尚书·洛诰》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孔传云:“明月,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岁’。古者褒德赏功,必于祭日,示不专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白尊周公,立其后为鲁侯。王宾异周公,杀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庙亲告也。”(35)孔颖达:《尚书正义》,第494页。孔颖达疏大致相同。可见旧注疏均将“岁”释为年岁,认为以骍牛祭文王、武王为特加之祭,作册祝册是为了册封周公之后伯禽为国君,“王宾”的对象是周公。《洛诰》该段内容涉及诸多祭名或祭祀方式,诸如“祭”“岁”“祝”“册”“告”以及“王宾”等词汇,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常相联出现,关系十分密切。两者可作比较研究,相关句读及注释,可以根据甲骨卜辞作出一定的调整。
其一,“祭”为专门的祭祀名称,并非泛称,当单独成句。据孔颖达疏中所引,郑玄即读“王在新邑烝”绝句,并未将“烝祭”连称。先秦文献中“烝”后通常并不加“祭”字,例如《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36)贾公彦:《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0页。唐兰曾在上世纪30年代据甲骨文提出“烝”为卜辞中的“登”祭,即登新米之祭,“祭”亦是卜辞中所出现的专门祭名(37)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页。。遗憾的是,由于其论述比较简略,其说并未为学界所广泛接受。这里我们在唐说的基础上加以补充论述。卜辞中有以下几条辞例,《合集》22862:
(7)丁丑卜,尹贞:王宾,中丁祭,亡忧。
《合集》22863:
《合集》27168:
《合集》34615:
其二,“岁”指祭祀中切割牲体的环节,当下属作“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而且“岁”并非祭名,它是从属于其前“祭”的一项具体内容。关于《洛诰》“祭岁”,南宋蔡沈释为“岁举祭祀也”(39)蔡沈:《书经集传》,第101页。,清儒吴汝纶释为“祈年也”(40)吴汝纶:《尚书故》,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224页。。当代也有学者在蔡说的基础上复援引《仪礼·少牢馈食礼》认为“祭岁”即“用荐岁事”,指岁时向先祖进献祭物(41)屈万里:《尚书集释》,第193页;周秉钧:《尚书易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页。。以上意见均将“岁”释为年岁或岁时。郭沫若在考释毛公鼎铭时曾引吴闿生的意见认为“岁”指祭岁,“岁祭之名,卜辞多见”(42)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139页。,但其并未进一步解释何为“祭岁”,似乎仍将“岁”字理解为年岁之义。
裘锡圭曾指出“岁”是卜辞常见的祭名,《洛诰》篇的“岁”字也应与卜辞同义。(43)裘锡圭:《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载《裘锡圭学术文集·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页。这种意见可取,只是其并未对卜辞中的“岁”作具体讨论。唐兰则认为卜辞及《洛诰》中的“岁”当读为“刿”,“谓割牲以祭也”(44)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第121页。。相较而言,唐说更为准确。这里在其基础上加以补充。卜辞中有以下几条辞例,《屯南》1131:
俗话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是只能看见别人的错误,却往往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在小学的语文教学中,也会有部分教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作为一名教师,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对自己及时进行自我反思是不符合师德建设的标准及要求的。所以作为教师要积极的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反思,善于发现自己的问题并改正。每一个人都会犯错,重要的是知错就改。尤其是教师这么重要的职业就更加要善于认识自己。所以说为了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加强师德建设,教师要注重自我反思。
《合集》23217:
(12)丙申卜,行贞:父丁岁,勿(刎)牛。在五月。
《合集》32334:
(13)告上甲,三牛岁于父丁,即宗。
《合集》27386:
(14)戊辰卜:其[有]岁于中己,王宾。/戊辰卜:中己岁兹用。
辞(11)以及上引辞(10)均讲在“祭”商王先祖时,使用“”“岁”等具体的方式。卜辞中“祭”是祭名,而“岁”以及“”则并非祭名,应只是祭祀的具体方式,也即以前学界所常讲到的用牲法(45)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4-108页。。《洛诰》与卜辞相似,亦是“祭”后紧跟着“岁”,“岁”亦应指用牲法。辞(12)“勿牛”之“勿”,当读为“刎”,乃分割、切断之意(46)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144页。。“刎牛”与“岁”所指是相同的,都是指在祭祀活动中依某种具体要求来宰杀牛牲。可见,学者将“岁”释为“刿”是有道理的。辞(13)当于“告上甲”处绝句,“告”即祷告之意。“告上甲”的同时,又刿三牛于父丁。《洛诰》中在刿牛牲之后,亦有“惟告周公”的内容。辞(14)“岁于中己”后跟“王宾”,《洛诰》“岁”于文王、武王,其后亦有“王宾”。
其三,“祝”与“册”指祭祀中并列的两种向神灵祷告的方式,并非指册命周公留后之事,《洛诰》此句当作“王命作册逸祝、册”。卜辞中的“岁”作为祭祀活动中的一种具体用牲方式,常与“祝”“册”联用,这与《洛诰》中的情况是相似的。例如《合集》30648:
(15)惟辛求(47)此从李孝定等学者将该字隶释为“求”。见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卷二),第2737页。。/册、祝。
《合集》22919:
(16)乙巳卜,喜贞:祖乙岁,惟王祝。
《屯南》173:
辞(15)显示,卜辞中“册”“祝”是并列的两个词,指祭祀活动中向神灵求助祷告的两种方式。郭沫若认为:“‘祝’与‘册’之别,盖‘祝’以辞告,‘册’以策告也。《书·洛诰》‘作册逸祝册’乃兼用二者,旧解失之。”(48)郭沫若:《殷契粹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343-344页。其说法应该是恰当的。商王在求告之前,往往会刿割牺牲来供奉祖先神灵。辞(16)中“岁”于祖乙之后有“惟王祝”,《洛诰》中在“岁”于文王、武王之后,由作册逸进行“祝”的活动。辞(17)“岁”之后的“”字为甲骨文表祭祀之“册”的专用字(49)于省吾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964页。,即向神灵册告之意,后世通常以“册”字表示。《洛诰》中同样记载在刿牛牲之后,由作册逸进行“册”的活动。可见《洛诰》与卜辞所记的祭祀程序是十分相似的。
“册”“祝”的目的当是远罪疾祸患而非册封。王国维认为《洛诰》“祝册”指的是“因烝祭告神,复于庙中以留守新邑之事册命周公”(50)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页。,应该是弄错了“祝册”的内涵。《周礼·春官·大祝》云:“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六曰策祝。”郑司农注云:“策祝,远罪疾也。”(51)贾公彦:《周礼注疏》,第540页。《尚书·金縢》篇记载周武王有疾,周公“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周公“册、祝”于先王的目的正是为武王攘灾去疾。
其四,“惟告周公”四字为一句,“其后”为时间副词,当下属。关于《洛诰》该句的解释,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孔颖达的疏解:“祝读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后为国君也。”(52)孔颖达:《尚书正义》,第494页。将“其后”解释为周公的后代;第二,朱骏声《尚书古注便读》谓:“使史逸读祝册,以告周公留洛也。”(53)朱骏声:《尚书古注便读》,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将“其后”解释为命周公留后(即留洛)。今天的学者多从后说。前文所论已显示《洛诰》该段所涉及的宗教祭祀方面的内容与商代卜辞具有很高的相似度。“告”亦属于商代后期一种常见的祭祀方式,在卜辞中有大量辞例。实际上若与卜辞内容加以比较,除以上两种意见外,《洛诰》该句还可以作其他理解。
卜辞中有与“告”相关的辞例,例如《屯南》4049:
(18)辛未贞:其告商于祖乙,若。
《屯南》135:
(19)于大甲告望乘。
《合集》3957;
《合集》6131正:
学者已指出,卜辞中的告祭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关敌对方国来犯、商王出兵征伐、商王田游巡视、灾害疾病等,商王都一一上告鬼神,以求得福佑,去除灾难(54)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第233页。。辞(18)中的“商”为商王朝一位诸侯的私名,《屯南》1066记载有“侯商”(55)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4页。,商王为侯商举行告祭,向祖乙求取福佑。辞(19)“望乘”以及辞(20)“沚”都是臣服于商王朝的强宗大族的族长。商王为他们举行告祭、求取祖先的福佑,实质上是利用宗教神权对异族群加强控制的一种手段(56)王坤鹏:《商代异族邦伯考》,《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21页。。其中“王告沚”与《洛诰》“惟告周公”在句式上亦是十分相似。“惟告周公”大意即周王为周公举行告祭、求取祖先的福佑。“其后”当为时间副词,“其”同“之”,为虚词(57)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9页。。古文献中的“之”字分化为虚词的时间较晚,《尚书》周初八诰中并没有虚词“之”,在需用虚词“之”的场合,一般用“其”“兹”等词加以代替。例如《大诰》“若昔朕其逝”,即“若昔朕之逝”,《康诰》“朕其弟”,即“朕之弟”等。
概括本节所考,《洛诰》此段当作:“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其中的“祭”“祝”“册”“告”“王宾”等与祭祀有关的词语在商代甲骨文中均已存在,而且两者的内涵也是极为相似的。“祭”是专门的祭名,“岁”是祭祀过程中切割牺牲的环节,是“祭”的一项具体内容。“祝”“册”指两种求告神灵的祭祀方式。“惟告周公”指为周公举行告祭,求取祖先的福佑。“其后”意为“之后”,为时间副词。该段大意谓:在戊辰这天,周王在新邑举行了“烝”以及“祭”两种祭祀,在“祭”中为文王、武王各刿割一头牛牲。王命作册逸进行了“祝”与“册”,向先王“告”,为周公求取福佑。之后,周王傧导神尸入位(58)“王宾”指时王傧导神尸入位。见晁福林:《卜辞所见商代祭尸礼浅探》,《考古学报》2016年第3期,第360页。,举行“杀”“禋”之祭,神尸都到位了,周王进入宗庙大室举行祼祭。
- 管子学刊的其它文章
- 楚简《五行》心灵哲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