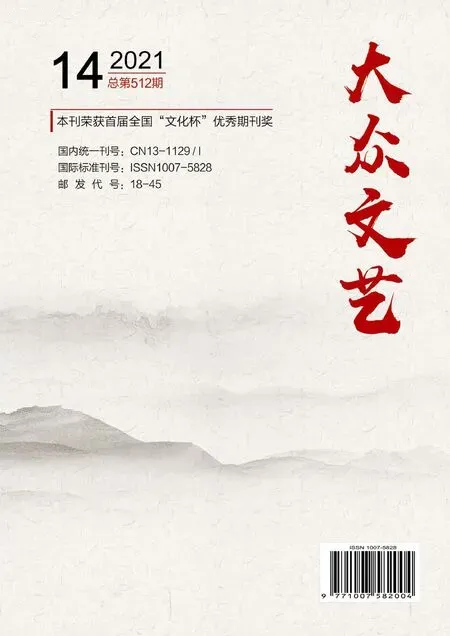《喜剧》:多重矛盾冲突下的异化表达与泛娱乐化批判*
姚宝香
(西京学院,陕西西安 710123)
小说《喜剧》是陈彦继《装台》《主角》之后的又一部反映秦腔舞台生活的作品,“以更强的故事性和更尖锐的当下思考引人注目。”小说在浅层结构中讲述了丑角演员贺氏一家父子三人的从艺生涯,其间通过舞台剧场的碾转给读者展现了艺术从业者与观众的错动,人物的情感纠葛贯穿故事始终,深层结构中却有着对异化、泛娱乐化、传统情感伦理在现代化的矛盾等诸多方面的思考。
一、艺术从业者在资本面前的异化与坚守
马克思主义把文学艺术理解为人的一种活动,是文学创造者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然而人的片面化,即人的异化和人的劳动的“异化”却被首先发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性: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人自身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交往关系的异化。作家作为艺术的生产者来说,当他的产品一旦进入资本运作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与艺术生产也就被异化了。简单地说异化的实质其实是被物所奴役,成为物或货币的奴隶,是人的本质的改变和扭曲。当代德国理论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进一步指出作家和读者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依靠语言文字可建立一定的交往关系,然而货币的异己媒介性却使得交往异化。强烈的逐利动机最终让艺术从业者为迎合受众而不断丧失立场、品质和格调。
在小说《喜剧》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贺加贝喜剧事业的发展经过,从武大富的红石榴度假村到贺加贝的小剧场梨园春来再到贺氏喜剧坊,以及资本加持的喜剧帝国,喜剧编剧也是走马灯的一换再换,从南大寿到镇上柏树再到王廉举、史托芬,我们能够清楚地发现在金钱、名利之下他们各自的异化与坚守,南大寿他强调的丑角艺术,强调高台教化,强调喜剧的净化与纯粹,武大富下三烂的要求让南大寿愤然离去。
镇上柏树一个居无定所的人,即便最初也抱着古今中外的一系列名著寻找创作灵感,但在现实的观众需求与资本面前其作品趣味低下,充斥着生殖想象、性与床戏。潘金莲、李鬼、阎婆惜在他的改造中都变得理直气壮起来。现实的沉重与舞台的轻浮形成了错位,潘银莲的美好让他全身而退。王廉举游走于放纵与净化的边缘,恶俗又低级,在成功面前资本面前逐渐异化,最终妻离子散,精神失常,走向毁灭。史托芬一个被职称、论文、课题、职权异化的大学副教授,他的喜剧,包袱、笑点、都要用电脑,数字模型往出计算,工具理性进一步将其异化。房子、车子、票子、职称评定、明星婚外情成了主打内容。他为舍得掏腰包的人寻找生存优越感,无视价值和道德感,把可怜人的病痛、残疾、痴憨、当成笑料,不仅使自己异化,也使贺加贝和众学生异化,盗用了“喜剧之父”的名却根本没有喜剧之实。也不像阿里斯托芬“以喜剧为批判的武器,辛辣地讽刺当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教育中的丑恶现象。”最后倾家荡产。作者陈彦在小说《喜剧》中塑造了一只柯基犬,以狗的视觉给我们展示了人被物驯化的过程,发出了“要挣上这一口,就得出卖我的狗格、心智和体能”的哀叹。
二、不同空间场域的审美与审丑矛盾
在小说《喜剧》中读者可以清晰地发现存在两个经济与文化的空间场域,一个是充斥着白领、精英、富裕阶层、知识分子的都市剧场,一个是充斥着贫穷、传统、落后、朴实农民的乡村舞台。这两个空间展示着不同的审美与审丑矛盾。在《喜剧》的都市空间场域,审丑却沦为丑的展览。
接受美学认为:在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相反,他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在姚斯看来,期待视野是接受者在接受作品前的定向预期。在此基础上观众心理需要就成为一种默然的力量塑造着艺术。在小说《喜剧》中多处可见对都市文化及生活状态的描述:生活节奏太快,压力太大,一天抓钱抓经济够累的,上班压力山大、需要释放、宣泄、搞笑。观众喜欢油腻,喜欢荤腥,喜欢轻松的,别整那些高深莫测的,人挣钱都累得要死要活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之间存在不平衡关系,一是有些文艺类型只能兴盛于生产发展相对低级的阶段,二是两者之间并不是成正比例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在文学艺术上反而领先。”经济虽是最终的支配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纵观小说《喜剧》所呈现的时间与时代过程,当下社会无疑是作者笔端的对象,城市观众的低俗、恶俗、低级趣味审美需求,与时代与社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房贷、车贷、孩子、内卷等诸多压力抑或参与其中,加之整个社会道德的整体滑坡以及泛娱乐化倾向的充斥其间,厚重、深刻、精致的文化不再被大众所青睐,“浅薄的调侃与无知的嬉笑代替了关怀内在心灵的理性解读、意义追问与现实思考”,“泛娱乐化”的背后隐藏着文化消费的深层次资本逻辑,这在小说《喜剧》中也不难发现,武大富是贺加贝丑角错误道路的推手,更是其喜剧帝国大厦倾塌的主要原因。小说中写道浮士德跟魔鬼墨菲斯托的约定:墨菲斯托可以满足浮士德的一切要求,尤其是一切远离人类道德的娱乐至死方面的要求。1985年,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呈现了泛娱乐化的雏形。泛娱乐化时代容易把低俗、庸俗、媚俗的“三俗”作为基本的审美价值导向,导致审美的平庸化、崇高的消解、精神的懒惰和虚无主义,反而对“崇高”价值的追求缺乏动力。
相反小说《喜剧》里,贺少天的喜剧有三不为:不惟财、不犯贱、不跪舔;还有三不演:脏话连篇的不演,吹捧东家的不演;狗眼看人低的不演;三加戏:给懂戏的加戏,给爱戏的加戏,给可怜看不上戏的人加戏,可谓之艺术之匠心。潘银莲一再重申戏曲的干净、行善积德、行侠仗义,以及现实的沉重、高台教化等。贺加贝在河口镇演出所意识到的:城里演出特别精彩的那些语言,在这里毫无效果。反而是前朝后代、悲欢离合、家长里短、儿女情长那些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十八扯”倍受欢迎,而这恰是丑角的精华所在。村里打工的人都爱看忆秦娥的苦情戏,潘银莲认为演员质朴、诚实、实在。忆秦娥的《哑女告状》戏散后带给潘五福莫大净化感、舒坦、受活。作者借那只被恶搞成张驴儿的狗之口道出了:喜剧最好看的地方,恰恰是它的温情部分。一旦喜剧没有了温情,没有了对柔软东西的怜惜、爱抚,那就是一堆臭狗屎。顾教授在给贺火炬解释喜剧与悲剧的本质时谈道喜剧的根本,是端正的心性和良知,要在人道上着力,而不是一味地消遣、消费什么。
三、潘金莲式的母题叙述展示着伦理道德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小说《喜剧》中蕴含着潘金莲式的母题叙述,《水浒传》里的潘金莲故事有着这样几个相互联系的逻辑关系,一是潘金莲的美貌;二是潘金莲的道德失范,与人通奸以及谋杀亲夫;三是美女嫁丑男的境遇设置所造成的情感秩序的不合理,进而引发的对郎才女貌的合理期盼。
小说《喜剧》在原有母题的基础上进行了三个向度的阐发和演绎,一是好麦穗与潘五福这一对农村贫穷式美女与丑男的形态,好麦穗的美貌与对传统婚姻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背叛,作者注入给好麦穗的更多是人的伦理意识与自然情感冲突,好麦穗停留在通奸以及对合理婚姻的追求中,潘五福的勤劳、大度、宽容、理解以及对儿子潘上风的无私付出,好麦穗的善良、无辜以及愧疚、病故都让读者看到了这一母题在变化中的人性价值。好麦穗是美而坏的,潘五福是丑而善的,这里面没有武松,只有一个耿耿于怀的婆婆和把人折磨而死的癌症。西门庆在这里替换成了河口镇某家银行营业所的主任张青山。
二是潘银莲与贺加贝这一对影子美女与著名丑男的形态。潘银莲只是贺加贝这一知名丑角演员对万大莲痴爱的替代品,武大郎式的贺加贝因丑角技艺加身在与潘银莲的爱情与婚姻里似乎有了底气,有了主动权、话语权、决定权,抑或成了现代版的陈世美。而在万大莲那里却又经历了求而不得的万般痛苦,遭受了英雄救美的一次次幻想,“剧帝”与喜剧帝国的狂想让他膨胀到“朕要废后”的状态,子对父的人伦教化背叛,徒对师的喜剧匠心背叛、夫对妇的真情背叛,穷对富的任性追求,爱情、名利、金钱让其不辩真相、枉对良善,丑而卑琐,其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确认是通过实现对万大莲的拥有为指向的,其对万大莲以及潘银莲的情感评价也是通过物质来界定的。而潘银莲无疑是美和善的化身,忠诚、本分、懂礼、谨严,是人中的凤毛麟角。
三是万大莲与三位男性的情感纠葛,郎才女貌、腰缠万贯是万大莲的婚姻爱情原则,第一次婚姻廖俊卿年轻帅气两人郎才女貌,因廖的背叛而离婚,第二次婚姻牛乾坤帅气多金,万大莲也因此开上了玛莎拉蒂,住上了豪华别墅。而在牛乾坤出事破产后,两人离婚。贺加贝的千万别墅、重获自由甚而让她愿意与之同床共枕,产业园区的破产,别墅和剧场的毁灭,让万大莲瞬间变得生硬,也让贺加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幻想彻底破灭。真情在万大莲那里一文不值。小说从贺加贝蹲守廖俊卿万大莲开始,最后也在万大莲廖俊卿再次复婚贺加贝自杀未遂时接近尾声。万大莲美而不美,贺加贝丑到可笑。
四、结语
陈彦曾在他的《说秦腔》一书中谈道:“戏曲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在大规模城镇化中必然遭此(消亡)一击。戏曲艺术的继承和创新应向传统学习,不仅学习深厚的艺术积累、学习生命演进方式,更要学习传统戏曲关注民生、关注苦难、关注卑微生命、关注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在接受采访时陈彦也曾表示过“我一直希望能够写出有中国文化质地、体现中国人的审美情绪、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的作品。”小说《喜剧》立足于当下社会,给我们展示了艺术从业者在资本、名利、金钱与物质之下的异化,思考且批判着泛娱乐化时代城市与乡村不同的审美与审丑品性,演绎了潘金莲式的母题下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社会的矛盾。肯定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和生命价值,是陈彦作品一贯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