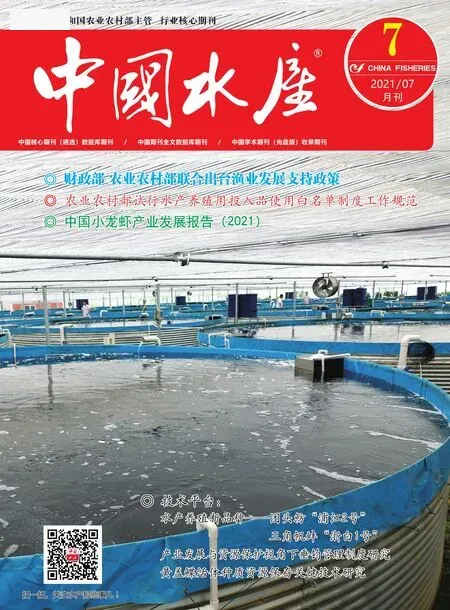产业发展与资源保护视角下垂钓管理制度研究
文/刘江

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水生生物资源,降低因过度捕捞造成的渔业资源衰退,减少人类活动对水生生物栖息地的破坏,是国家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规划。垂钓作为涉及水生生物资源利用的活动之一,对其进行有效管理也是保护资源的重要一环。如何实现既有效保护资源,又促进休闲渔业产业繁荣发展,提高法治的核心竞争力是关键。本文通过分析现有制度规定的不完整与矛盾性,提出解决垂钓管理问题的思路与对策,以期促进产业发展与资源保护共赢。
一、问题的提出
(一)制度背景
1986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以下简称“《渔业法》”)颁布;1987年10月20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其中,第十八条规定“娱乐性游钓和在尚未养殖、管理的滩涂手工采集零星水产品的,不必申请捕捞许可证,但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具体管理办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自此,垂钓(游钓)在我国渔业行业管理行政法规中开始有了明文规定。
实施30余年中,部分地区出台了有关垂钓的管理规范,2005年,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南昌市城区河流垂钓管理规定》,规定了可以垂钓的区域,设定了部分法律责任,“违反本规定,使用联体钓、串挂钓、甩杆以及捕捞等方法钓鱼的,由南昌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处以2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2009年,河南省洛阳市人民政府发布了《洛阳市城区河流垂钓管理规定(试行)》,规范了垂钓相关工作的部门职责分工,规定了“不得在晚上9时至次日早晨6时垂钓”“不得使用联体钩、串挂钩等方法垂钓”“禁止在禁钓区、禁钓期内垂钓”以及“禁止驾船入河垂钓”等,并对上述行为设定了法律责任“拒不改正的,处以3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2020年7月31日,江苏省修订了《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增加在长江干流江苏段和水生生物保护区违法垂钓的相关法律责任条款,成为全国第一个在省级地方性法规中设定垂钓管理法律责任的省份。
从全国关于垂钓管理的立法情况来看,各地立法积极性并不高,究其原因,一方面,在长江流域尚未大范围实施捕捞渔民退出捕捞作业前,垂钓获取渔获物的数量相对较少,管理矛盾与管理需求并不十分凸显;另一方面,2000年《渔业法》进行大幅度修改后,《实施细则》未做过实质性修改,目前国家层面对于垂钓的规范均以文件形式发布,没有法律规范出台,垂钓管理的基本制度建设相对滞后,规范体系还不完善,在执法管理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各地在制定垂钓管理规范时,客观上具有一定难度。
(二)产业发展与资源保护的矛盾
1.垂钓产业发展是我国休闲渔业发展的重要一环。2017年,农业部发布《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要积极培育垂钓、水族观赏、渔事体验、科普教育等多种休闲业态,引导带动钓具、水族器材等相关配套产业发展,推进发展功能齐全的休闲渔业基地,促进休闲渔业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根据我国公布的《中国休闲渔业发展监测报告》,2017年~2019年休闲钓具、钓饵的销售额年均约66.74亿元,垂钓产业相关消费人群数量众多。
2.渔业资源衰竭严重。以长江为例,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到了最差的“无鱼”级别,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20世纪50年代长江渔业年捕捞量是45×105t;随后的几十年中,长江年捕捞量不断下降,到2017年已经不足1×105t;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2020年12月3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自2020年起,农业农村部先后发布了《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长江流域禁捕执法管理工作的意见》《农业农村部长江办关于加强和规范长江流域垂钓管理工作的通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流域垂钓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加强垂钓管理、制定垂钓管理办法,结合实际规划垂钓区域和垂钓时间,规范钓具钓法、钓饵类型、钓获物处置等,将天然水域垂钓监管作为水生生物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
3.产业发展与资源保护的矛盾亟待解决。在产业发展与资源保护的双重背景下,若无完善的管理规范,必然形成无序的粗放式的发展,而这既不利于产业发展,也会给环境资源带来一定的影响。如何妥善解决矛盾,实现产业发展与资源保护共赢,本文从我国现有渔业法律体系的建设与垂钓管理的关系着手,分析垂钓管理规范的不足与矛盾,提出解决的对策,以此促进垂钓管理法治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二、垂钓管理规范现状
关于《渔业法》是否可以规范垂钓行为,一种观点认为,垂钓是“捕捞”行为的一种,《渔业法》中所有关于“捕捞”的法律责任条款对垂钓行为均有约束性;另一种观点认为,《渔业法》规范的“捕捞”行为均为狭义的“捕捞”,即通过借助船舶并使用捕捞网具开展的“捕捞”行为,因此不能用于约束垂钓行为。本文从阐释《渔业法》着手,对以上两种观点涉及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考量:
(一)从行政许可角度看,关于捕捞管理的部分条款不适用于约束垂钓行为

首先,根据《渔业法》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国家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第四十一条配套制定了“未取得捕捞许可擅自进行捕捞作业”的法律责任条款,可见此处所讲的“捕捞”是要以取得行政许可为前提;同时,根据《实施细则》第十八条中“娱乐性游钓不必申请捕捞许可证”的相关规定,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垂钓许可的相关制度,可见此处所表述的“捕捞”应为狭义的“捕捞”,《渔业法》第二十一条、四十一条等关于捕捞许可的规范对垂钓行为没有法律约束力;其次,《渔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取得捕捞许可证需要具备的条件为“有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有渔业船舶登记证书”“符合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的捕捞许可证,应当与上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捕捞限额指标相适应”等,不难看出,我国现行的捕捞管理体制以船舶为主要载体,通过对船舶功率指标的管理,实现对捕捞总量的控制,由此看来,垂钓的管理与该处的“捕捞”截然不同。根据以上两点可以判断,行政执法机关不能因未经捕捞许可实施非法垂钓而使用《渔业法》第四十一条来进行行政处罚,《渔业法》中以上部分关于狭义“捕捞”的条款均不能约束垂钓行为。
(二)从资源保护的角度,部分条款可以约束垂钓行为,但具有一定局限性
现行《渔业法》法律责任章节共计12条,其中涉及捕捞管理4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除狭义的“捕捞”所对应的3个有关捕捞许可管理的条款外,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范了三种违法行为的处罚,一是通过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二是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三是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其中第一种、第三种已具体指向违法行为所使用的渔具或者渔法,与垂钓管理无直接关系,第二种“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对应《渔业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的相关内容,本文做重点讨论。
1.《渔业法》对垂钓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条第四款“珍贵、濒危的水生野生动物以外的其他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适用《渔业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渔业法》除用于规范、调整渔业生产行为,还肩负有保护水生野生生物的使命,《渔业法》第一条中,“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也体现了这样的立法目的。《渔业法》第三十八条中“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的表述,意在保护水生生物资源,通过划定禁止捕捞的区域与时间,禁止除科研等特殊需要以外任何形式获取水生生物资源的行为,换而言之,在禁渔区、禁渔期只要产生损害水生生物资源的结果,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均应当认定为违法,故此处所述“捕捞”,应为广义的“捕捞”。

2.《渔业法》对垂钓的约束存在局限性。根据《渔业法》第三十条第二款“重点保护的渔业资源品种及其可捕捞标准,禁渔区和禁渔期,禁止使用或者限制使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最小网目尺寸以及其他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规定,“禁渔区、禁渔期”一旦设定,即禁止在该区域开展一切捕捞行为,若以设定“禁渔区、禁渔期”之手段来约束垂钓行为,其他使用船舶、网具的捕捞行为同样不可开展。
分析此“绝对禁止”的方式,首先,其并非直接针对垂钓管理的措施,无法实现分类管理的目的,与实际需求有一定差距;其次,依据《渔业法》第三十八条来实施垂钓管理,是以广义“捕捞”的结果来判定其违法性,并未区分“捕捞”采取的方式,对于是否区分钓具的数量、钓法、钓饵等,均无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行政裁量带来不便;再次,“禁渔区、禁渔期”是仅因保护水生生物资源的特殊需求而设定的特别保护范围与期间,除此之外仍有相当大范围的天然水域有垂钓管理的实际需求。由此可见,设定“禁渔区、禁渔期”的管理模式,对垂钓管理而言并不完善,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渔业法》作为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的法规,应对垂钓行为起到约束作用,既体现法律属性,也要满足现实需求,关于“捕捞”的概念即有广义所指、又有狭义之分。《渔业法》关于捕捞许可相关的条款不适用于垂钓行为的约束,关于渔业资源保护的相关条款可以部分适用于垂钓行为的管理,但对于垂钓管理的现实需求而言,这部分条款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同时需要结合其他配套制度,其效果需要在具体的执法中开展进一步验证。
在加强水生生物保护、落实长江流域禁捕退捕的背景下,加快修订《渔业法》《实施细则》等渔业行业法律法规,重新构建我国垂钓管理的法律规范体系,从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的角度,规范垂钓管理基本制度与法律责任,实现水生生物保护与渔业休闲娱乐活动同步健康发展,在新阶段、新时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对策与建议
(一)在渔业法律法规制度上建立垂钓管理相关条款
《实施细则》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垂钓管理办法”,虽然在管理上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但同时带来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造成区域行政执法尺度在相邻交界水域、上下游水域以及不同行政区域有较大差别。二是由于立法权限的限制,对垂钓行为的地方立法带来一定难度,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四条“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地方政府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通报批评或者一定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对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权限做的设定可知,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在立法时,可以设立的行政处罚种类、幅度都非常有限,政府规章的立法难以满足垂钓管理的需要,虽然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在行政处罚的设定中有较高的权限,但就无上位法依据新增设行政处罚方面也有严格限制,并且仍存在地区制度差异较大的问题。三是在没有国家统一的法律规范前提下,地方立法容易造成垂钓管理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产生偏差,当国家出台相关法律规范时,易与地方制度冲突,缺乏制度的稳定性,从而违反信赖保护原则。因此,对于垂钓行为的规范,应当修订《渔业法》,增加专门章节,或者通过行政法规来进行规范,为地方立法提供法律依据。
(二)对于垂钓行为的规范应当考虑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建立垂钓的法定概念,区分垂钓与其他获取渔业资源的行为;二是建立垂钓的基本制度,比如钓具、钓法、钓饵的规范,钓获物的品种、数量、规格的规范,是否经过垂钓许可或者进行备案,是否可以进行钓获物交易以及是否缴纳税费,是否可以借助辅助设施进行垂钓等,以此促进垂钓基本制度的统一;三是建立基本的法律责任体系,规范行政处罚的种类与幅度,做到在违法行为处置中过罚适当、区域相对统一;四是建立钓具的准用目录及禁用目录;五是建立禁钓区的标识规范以及准钓区的安全建设规范,为划定禁钓区、选取准钓区提出基本要求;六是规范垂钓地方立法的范围以及权限,为地方立法提供依据与立法空间。
(三)完善钓具钓法相关国家标准,加强生产销售环节监管
市场销售的钓具、钓钩等种类繁多,加强垂钓行为管理的同时,应结合立法情况,修订完善钓具、钓钩等的国家生产标准,建立更为规范的生产销售体系,并加强对其生产、销售环节的行政执法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