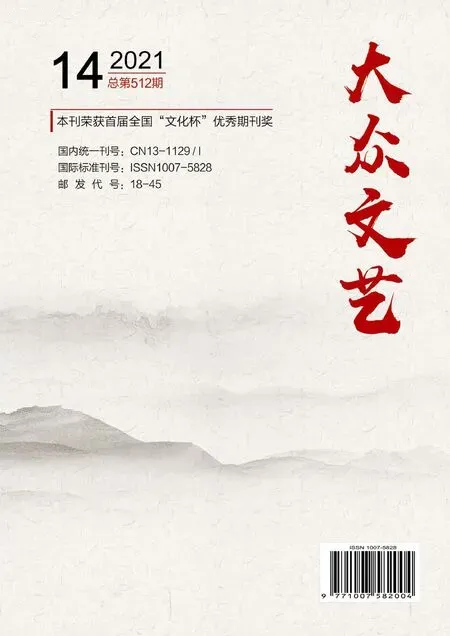笛福小说《摩尔•弗兰德斯》的真实与伪装*
万 锋
(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贵阳 550000)
丹尼尔•笛福的小说《摩尔•弗兰德斯》讲述了同名女主人公跌宕起伏的一生。她在监狱里出生,随着吉卜赛人流浪过,做过女仆,结过几次婚,也做过妓女和小偷,最终因偷窃罪被判流放,却因母亲留下的遗产在殖民地过上富足的生活并虔诚地忏悔过去的罪恶。在她送走无力抚养的孩子时,对帮助她的老保姆说,希望能够在不让孩子知道她是谁的情况下时不时见到孩子,老保姆告诉她“你不可能同时既隐藏又现身。”在此种情况下,摩尔的确不可能既能现身见到孩子又隐瞒身份,但在整本小说中,她却是不断游走在隐藏和现身之间,用叙述的语言、身体的符号、衣着的伪装来构建身份,调和讲述真实历史与隐藏真实身份之间的矛盾。
一、语言层面的真与谎
在小说的前言中,叙述者声称自己即将讲述的是“个人历史”,只是因为诸多原因无法透露真实姓名,因此以她为人所知的“摩尔•弗兰德斯”作为代号,除了被编辑隐去粗俗不宜阅读的文辞外,所讲之事均出自其真实回忆。声称自己为“历史”而非“故事”或“小说”是十八世纪小说的惯常做法,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的历史》更是直接将“历史”放在了正式题名中。这种对于“历史”的执着源自这类作品的特殊处境,在小说刚兴起的十八世纪,虚构故事被认为是不入流甚至有害的,所以作者们纷纷为作品冠上“历史”的头衔,并在其中充分加入道德说教成分,使其具有真实性和教育意义,更为读者和评论家所接受。摩尔的故事即是这种伪装成真实的虚构。
摩尔很早就明白了语言的欺骗性,也学会了利用语言符号来构建的仅停留在能指层面的真实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语言符号是她惯常利用来隐藏和伪装的手段,如艾伦•波拉克指出,摩尔在利用语言和社会文化符号进行假面武装上天赋异禀。但这种能力并非天赋,而是摩尔通过惨痛经历习得的。
小时候,摩尔对语言符号的指涉关系处于简单直接的层面,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就是纯粹的一一对应关系,因此会被她服侍的人家的大少爷以谎言欺骗。大少爷口中的“爱”和承诺最后都没有兑现,而是停留在能指层面。年少无知的摩尔经历了那次心痛之后,不仅不再相信男人和爱情,也不再相信语言的可靠性,她明白了语言是可以创造出子虚乌有的所谓“事实”并用来欺骗他人为自己服务的。于是那之后的她学会了用编造的故事为女性朋友重新赢得情人青睐;也学会了用诗句和谎言构建自己“贵妇”的身份来吸引男子;在一次行窃中,她还未开始行动就被错误地当作小偷抓住了,摩尔当即编造出一个寡妇身份,说了许多翔实却无法证实的细节,让符号为自己编织了一个正当合法的身份,顺利逃脱。
可以说,语言在摩尔眼中逐渐成了武器和伪装的手段。然而摩尔对这种语言武器的使用并非不受拘束,据她宣称,她对于谎言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人不应该说谎和欺骗,但她实际的做法又明显违背这一态度。一方面,她在成功利用语言达到目的之后表现出来的是沾沾自喜的心情;另一方面,她反对说谎并非因为道德原因,而是不愿意面对谎言被戳穿带来的后果。在散布谎言将自己伪装成贵妇之后,她对着即将成为第三任丈夫的男子“假装”不承认自己的富有,而男子却认为她是故意试探自己的真心,所以明确表示不在乎她的钱财多少。于是,摩尔似乎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坦然接受他的追求,她自我思忖:“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上当受骗了,只能说是被骗了,不能说是被我骗了。”似乎这样她就获得了良心上的安宁。
除了通过语言符号创造“事实”和身份以往,摩尔还善于利用身体上的符号,让它们参与到表意和身份建构中,为她谋取利益。
二、身体符号的真与伪
与对语言符号的认知和使用类似,摩尔对于身体上可展示的符号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信任到有意识利用的过程,这类身体上可感知的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类似,也承担了指涉功能、参与了意义表达和生成。这类身体符号主要以表达情绪和情感为主,其中,摩尔较多笔墨描摹的是她流泪的场景。眼泪作为直观可见的情绪表达,有时能够达到比语言更有说服力的效果。
初入社会时的摩尔在情绪的表达上是自然流露的,当时的眼泪传递的是真实的情绪,无论是对大少爷讲述自己的担忧,还是对女主人袒露心扉,流下的都是真诚的眼泪。眼泪是摩尔为数不多的真实。尽管遇到了背叛和欺骗,遭到了贫穷的威胁,经历过身处孤立无援的境地,她在面对每一个原本只是想要利用的男性时,内心依然会有感情,依然会为他们落泪,尤其是与叫杰米的那任丈夫分开后,她的悲伤无法抑制,不停落泪;在她灌醉路上遇到的绅士还偷走了他的财物后,看着他熟睡的样子,摩尔心中想到一个体面的绅士竟然会因为喝酒的缘故就落到如此地步,非常惋惜,以至于流下眼泪;在狱中遇见了同为阶下囚的丈夫,摩尔更是泪如雨下;而在流放到殖民地与儿子重逢之后,她再次流下了欣慰和感动的泪水。可以说,自始至终,摩尔的眼泪中都保存着一份纯真。
尽管摩尔大多数情况下的流泪是真诚而自然的,有时她也会有意识利用眼泪,正如她自己所说,眼泪是“女人的修辞”。在偷窃被抓住时、被带到监狱时,以及劝说丈夫时,摩尔都会有意识地掉下泪来,这些情况下的眼泪,就如同她编造的故事一样,是空洞的外部符号,并不与内心的情感或情绪有对应指涉关系,只是一种“修辞”,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
伊恩•瓦特认为英国小说自笛福起表现出对空间的现实主义呈现,辛西娅•沃尔在回溯英国小说对细节描写的发展史时也曾指出,笛福小说较以往的叙事文学,在空间的呈现上更加细致和具体,细读小说不难发现很多对于空间物质性细节的描述,同时,笛福对于人物身体的物质性细节也描绘得较为详尽,摩尔就时常利用扑过去、靠在柜台、轻挨着门等动作和姿势将物质性的身体符号与空间细节相结合,再配合以流泪、编造的故事等等符号的手段,让在场的人完完全全相信她。摩尔正是利用了身体符号,创造出极具真实感的谎言,为自己服务。
三、衣着的“得体”与伪装
摩尔沦为小偷后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敛财,在行窃的过程中,她常常乔装打扮,有时是扮成采买的仆人,有时是独居的寡妇,有时又是穿着光鲜还带着手表的贵妇人。这些服饰的主要用途在于为她建立一种身份,让她能安全混入人群,并为自己的在场提供合理证据。衣着与语言、身体表征一样,是摩尔建构身份的手段。
摩尔的一生和衣物、服饰关系紧密,不仅她的名字弗兰德斯与进口布料有关,她第一次有安定下来的居所和微薄的收入即是通过帮大户人家做针线活,可以说,织物从一开始就将摩尔编织到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大网中,从编织缝补开始,摩尔进入了她充满罪恶的一生。几乎每次出门行窃,摩尔都认真装扮,这样即使被怀疑,也可以通过衣着洗脱嫌疑。在她偷盗生涯的很长一段时间中,给她提供住处和指导的老妇人坚持要她女扮男装去行动,跨性别的乔装让摩尔心中十分不舒服,因为她感到另一种性别的衣着违背了自己的“本性”(nature)。但在实际操作中,摩尔却从未露出马脚,连与她配合行动、睡一张床的合作伙伴都没有发现她真实的性别。女扮男装最后也救了她,让她在差点被抓住时逃回家中迅速换装逃过一劫。
在这次异装经历中,摩尔原先担忧自己的内在本性会与外在衣着相悖,从而暴露真实身份。但事实上,本性并非内在固有的,而是由外部符号构建的,当她通过衣着展露的是另一种性别外在时,构建的也就是与另一种性别相对应的“本性”。摩尔自己所认为的“真实”是被外部的伪装所消解的,外部伪装构建了另一种具有欺骗性但更具实际用途的虚假的真实。
朱迪斯•巴特勒在谈道性别身份时曾指出,性别身份其实是一种操演性的身份建构,外部的身体特征并不是内在身份的表达,内在身份是由外部特征,包括姿势、衣着构造出来的,主体通过不断重复与文化期望相吻合的外部性别特征,获取了自身能被社会解读和认可的身份。摩尔的女扮男装正是一种自我赋能式的性别操演,将自己从并不存在的“真实本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建构外在身份、拥有行动自由的主体。摩尔每一次“得体”的装扮和女扮男装的行为,都让她暂时获得了对自己有用和有利的身份。
摩尔充满罪行的一生,游走在真实和伪装之间,利用语言、身体、衣着三重符号系统编造对她有利且具真实效果的诸多谎言。在整本小说的叙述过程中,摩尔数次说她真诚忏悔过去的罪恶,直到小说结尾依然是声称自己在忏悔中度过余生。但在叙述中摩尔对自己常常是持肯定态度的。她的忏悔如同她编造的那些故事一样只停留在语言能指符号的层面。但当我们批判摩尔的罪行时,又不得不思考逼迫她一步步滑向犯罪深渊的根源。十八世纪的英国,留给贫苦出身的女性的出路并不多。与其说笛福暗暗赞赏摩尔,不如说笛福通过描述困境中依然努力生活并利用一切可利用条件去获得经济独立的女性,是在批判那个催生出这类人生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整本小说其实可看作穿着得体道德教化外衣的批判现实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