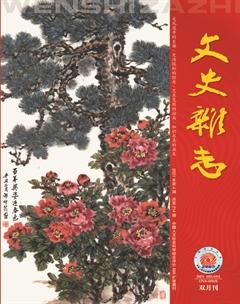近代以来中国出路的四次历史选择
赵映林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受到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斯大林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即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1]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胜利,冲击了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雅尔塔体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赢得了巨大声誉,其影响不仅是一国的,也是世界性的。翻开中国的近代历史,人们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历史的第一次选择: 洋务派的自强求富
鸦片战争(1840—1842年)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唤醒了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出现了一些反映初步革新思想的议论和著作,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的《救时揭要》、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等。编著者们无不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承认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优于中国的专制制度,西方有长处,中国有不足,需要向西方学习。他们在强调学习西方目的的同时,又要求“不必仰赖于外夷”,含有独立自主之意。不过,这些认识当时还仅限于极少数士人的一厢情愿,既没有握有实权者的青睐,更未上升为统治集团的共识。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再次丧权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社会上涌现出又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代表人物,如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他们抨击专制极权统治,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主张建立“君民共主”的政体。严酷的现实也唤醒了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曾国藩在围剿太平天国时,看到的是“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2]。薛福成在《庸盫笔记》中说到一件事:1861年3月,胡林翼在安庆江岸,目睹两艘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为之“变色而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可见洋人轮船给他的刺激之深。不仅如此,曾国藩还领教了太平天国从洋人那里购买的“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厉害,为之惊心动魄,嘱曾国荃与李秀成交战时一定要“小心坚守”。[3]这年8月,曾国藩在安庆首办军械所,将精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华衡芳、徐寿、李善兰、张斯桂等人尽悉延揽,制造西式枪炮轮船,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集团中一部分身当其冲的官僚在西方优势面前开始了寻求自强的道路,开启了“师夷长技”的帷幕。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批官僚,开展了挽救清政权的洋务运动。
“师夷长技”的自强运动,在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的原则下,制造枪炮轮船。其时除最早的安庆军械所外,比喻著名的军工企业有: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南京的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号称四大军事工业。除此之外,洋务派还相继在西安、兰州、济南、成都、昆明等地和湖南、广东、吉林、山西、浙江、台湾等省设立机器局,制造军火,规模虽然小于四大军事工业,但都能为各省清军供应军火。在军事工业之外,又成立海军衙门,管理与海防有关一切事宜;还购买西方国家的铁甲兵船,成立海军舰队,建筑旅顺等军港船坞,到中法战争前夕,建成了北洋、南洋、粤洋三支海军。
洋务派在“求富”口号下,创办了诸多民用工业,涉及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纺织业等。规模较大的民用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基隆煤矿、天津电报局、兰州机器织呢局等20余家。兴办的铁路有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后延长至天津,成立北洋铁路局。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湾铺设了两条铁路,路线为:台北—基隆、台北—新竹。
民用工业的兴办,刺激了民间投资实业的热情,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办企业,仅较大规模的就有50多家,资本超过了500万元,较著名的民营企业有:广东南海的继昌隆缫丝厂、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汕头的机器豆饼厂(机器榨油与压制豆饼)、上海的公和永缫丝厂、上海的同文书局、上海均昌机器船厂、广州的造纸厂、天津的自来火公司、宁波的立通久源轧花厂、上海的燮昌火柴公司、北京的机器磨坊(面粉厂)。洋务运动使买办、外贸商人、商行的高管,以及民办企业的投资、管理者共同形成中国的第一批资产阶级。至于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4]。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不同于以前的新变化。
洋务派还举办了西式教育。1862年,同文馆设立,以培养外语翻译人材为主。这是中国的第一所外国语大学,初设英文馆,以后次第增设俄文馆、法文馆、德文馆、日文馆、算学馆;所授课程甚广,除了外文,有算学、代数、几何、三角、博物、化学、天文、地质、测量、矿务,以及政治、经济、国际法等,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由此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之后,在上海、广州先后建立了相同性质的广方言馆。与近代教育相应的是译书。京师同文馆30年中翻译西方书籍近200部,以外交、史地、政法一类为多,其中有中国人首次见到的第一本国际公法著作。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40年里译书199部,其中绝大部分是自然科学、实用科学方面的著作。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供职几十年,为以翻译事业沟通中西作出巨大贡献。他虽是传教士,主旨却不在传教,而在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尤以《格致汇编》影响为巨。
为了培养“自强”需要的人材,洋务派兴办了一批专攻军事和工艺的专门学校:设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于天津,办广东水师学堂,派军士往德国学习水陆军械技艺,在江南制造局办了附设机械学校,在福州船政局办了船政学堂,在天津、上海辦了电报学堂,还在天津办了军工学堂,等等。
这一阶段,最值得一提的是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中国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1854年于耶鲁大学毕业,抱着教育救国的宗旨,一心要报效祖国;但一直等到1871年,从26岁等到43岁,这才最终促成朝廷外派留学生这一“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1871年9月9日,容闳的幼童出洋留学计划在曾国藩、李鸿章等的力促与保举之下,终于获得批准办理的圣旨。之后,便是“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成立,从1872到1875年,一共四批120名幼童出洋留学,费用全部由朝廷承担。世人所熟知的詹天佑、唐绍仪就是这一时期的幼童留学生。
洋务派“自强”新政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制夷”。“制夷”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为了统治者“天朝大国”的体面,很难说是真心为了中国的近代化,故李鸿章说自己是裱糊匠。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李鸿章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明白地讲:“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5]。“西學”因“中体”不变,“西学”嫁接到“中体”上,势难成长,也就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洋务派所追求的“自强”“求富”两项具体目标,故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一败涂地。甲午战争宣告了仅在经济、技术层面上进行器物变革,并不触动上层建筑根基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中国出路的第一次选择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其时大清国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中体西用”的自强求富结出的果是“器”,是表面的变化进步,而“道”却未变;两千年的“未变之局”并没有随着“器”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有所进步,有的只是行政机构的增添或易名而已。中国自强求富时期,正是日本明治维新阶段。彼时的东洋,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大化革新”以来1200余年的学中国的传统,转向学西方,开始了制度的变革创新而迅速成为近代文明国家。中国3000年的皇皇文明,却败给了尚处幼冲近代文明的日本,教训是十分的深刻。
历史的第二次选择:改良派的戊戌维新
甲午战争(1894—1895年)后,“天朝大国”梦的幻灭,催生出维新变法。一些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移到政治方面。他们当时已看出中国问题之所在,如留学法国的马建忠指出:“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6]维新运动的兴起正是要解决、弥补导致“自强”新政不足方面的问题。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强调“民可顺而不可逆”。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更是积极主张开议院,认为“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有了议院就能上下同心,“君民相洽,情谊交孚”,自无敌国敢相凌侮。简言之,是要解决制度层面的问题。
将上述观念付诸于实践的当首推康有为。当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后,康有为与他的学生梁启超等即于5月2日发起了“公车上书”,提出三条“权宜应敌之谋”:“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之后,他们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并继续上书推动变法……直到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弈去世,长达三十余年的洋务时代结束,变法随之骤然加速。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然而至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戊戌变法仅仅103天就夭折了。百日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经济方面是保护农工商业,奖励发明创造,鼓励私人办企业,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文化教育方面,设立新式学校、译书局,开办京师大学堂,派留学生,自由办报,成立学会,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军事方面,训练新式海陆军,裁撤绿营等;政治方面,精简机构,裁汰冗员,长期不劳而食的“旗人”须自谋生路,广开言路,准许、鼓励官员和民众论政,等等。除此之外,康有为还力主尽速开设议院。上述内容反映了康有为的急速心态:快速全面推进。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当时就说他 :“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措太大,当此在排者、忌者、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7]结果不幸说中: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帝被囚,谭嗣同六君子被杀,康、梁逃亡日本。杨天石先生总结百日维新失败的影响说:“它激起了人们对满洲权贵的愤恨,此后,以武力推翻清朝统治为宗旨的革命党人即进入历史舞台中心,并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的成功。”[8]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贵族利益集团的政变,促成了改良派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联合。
甲午中日战争最严重的一个后果不是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台湾,而是开启了西方列强进一步觊觎中国的野心。进入20世纪后,国家危机愈加严重。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1901年1月29日,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在形势已如危卵之下不得不发布了一份态度鲜明的上谕,实行变法,终于开启了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
历史的第三次选择: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其变法基本精神有三点:第一,变法的目标是“富强”——继承了此前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部分目标;第二,变法革新的方针是“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含有既承认当前中国政治体制需要改革的迫切性,也明确了社会改革的最终方向,与戊戌变法这部分内容一致;第三,革新的内容包括“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事、财政”,涉及的内容广泛,与康梁要求变法的内容不悖。从上谕内容看,体现的是全面的改革思维,几乎是戊戌变法《明定国是诏》的翻版。清统治者面对内忧外患,总算明白不变不行了,遂于4月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人组成的“督办政务处”作为改革的最高规划、指导机构。新政推行几年,取得了一定实效,如颁发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新政的成绩还可从财政收入上看出:戊戌变法前,朝廷每年财政收入一直在白银8000万两上下徘徊;推行新政后的1910年,财政收入高达30200万两,其中的商税、实业税是重要的一块收入。这是有清一代历史上的最高。[9]
然而,日俄战争日本大胜,俄国惨败。这件事深深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不少国人认为这是立宪对专制的胜利,呼吁效法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在时议压力之下,1906年9月1日,朝廷宣布预备立宪;但同时又声称,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只能先从议定官制、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务等事情做起,作为“预备立宪的基础”。上谕表示,要在数年后查看情况,再行妥议实行立宪期限。1907年9月,朝廷成立资政院;10月后,各省筹备设立咨议局。1908年8月27日,朝廷正式批准颁行《钦定宪法大纲》《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清单》。此后,预备立宪进入实施阶段。[10]不过,《钦定宪法大纲》却遭到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普遍不满与反对,这主要是因为这部宪法的实际内容仍是竭力突出皇权、维护皇权。它虽然规定“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但限于“法律范围”之内;倘无法律规定,不得擅自。这些“自由”实际上只是一纸空头支票。
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不满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由其父醇亲王载沣摄政。这时的清政权已经陷入彻底的权威危机。为了保住满洲权贵利益集团的统治,朝廷试图通过加速变革来赢得人心。载沣的具体措施是重申预备立宪。孰料此时全国各大城市推动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的请愿活动已是风起云涌。面對汹涌澎湃的舆情,朝廷被迫于1910年10月宣布于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将原定9年的预备立宪的时间缩短了4年。1911年5月8日,清廷公布了第一届内阁名单,共计13人,其中皇族7人、满族2人,汉族4人,皇族超过一半。这7名皇族成员中的奕劻声名狼藉。他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弄到更多的钱,是最大的贪官。其他几位不是昏庸无知,就是纨绔少年,让世人大跌眼镜,被人讥为“皇族内阁”。对此,连西方记者都看明白了,《泰晤士报》记者发回国内的报导说:“在目前,改革作为一个热门词汇挂在了每一个清国人的嘴上,但是在这个官僚体系中,究竟有哪一个部分作了严肃认真的改进?”[11]官员之所以不作“严肃认真的改进”,就在于各级官员无不借口“改革”“新政”而上下其手,在改革的名义下捞钱。因此,这场“预备立宪”在一批贪官污吏的操纵下,完全变味,失去民心。恰如莫理循在给《泰晤士报》的电文中所说:“清朝危在旦夕,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皆同情革命党,很少有人顾惜这个使用太监、因循守旧、腐朽没落的朝廷。”[12]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没落王朝来说,最后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而国进民退的铁路政策成为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1911年5月保路运动兴起,迅速扩展至川、粤、湘、鄂四省大地。随之革命军起。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各省纷纷响应,辛亥革命势不可挡。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由张謇起草的宣统皇帝退位诏书,统治全国268年的清王朝结束了。
历史的第四次选择: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辛亥革命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从此以后,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复辟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的人或政治集团,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失败。清王朝被推翻,打乱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秩序,从而为更进一步的革命发展开辟了道路。对辛亥革命,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革命。[13]
由于民主共和观念的深入人心,北洋政府官员亦或多或少受到影响,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社会思潮纷纷涌入,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界。不过,民国建立后的种种乱象,则使知识分子于失望之余,继续探求救国的出路,鲁迅曾回忆说:“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新的社会起来,但不知道这种‘新的该是什么。”[14]鲁迅的回忆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的新觉悟,其中一部分先进分子深感以往努力的方向,过于偏重欧美的模式。这样一批探求救国救民出路而不得其解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把寻找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爱国主义,再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青年》的出现,是知识界觉醒倡导新思想的一面旗帜。新文化运动唤醒了愈来愈多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思想基础。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首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震动了富于政治敏感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给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中国社会已不可阻遏地进入转型期。两次鸦片战争以来各种反抗外来侵略与本国反动势力的失败,或改良中国的努力,无不证明了不论是满洲权贵利益集团,还是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以及中国同盟会等革命派,都无法解民于倒悬,保障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更不用说去改变一个世纪来的积贫积弱,去促进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制度的重建,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了。白话文的推广运用,则愈加广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协助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虽有国际因素,却是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历史选择了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诚如陈旭麓先生所指出:“从戊戌变法仿效日俄、辛亥革命仿效法美到‘五四之后仿效苏俄,表现了每个时期先进中国人的选择。但三者又构成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环节,因此,这又是一次历史的选择。”[15]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中国历史这才进入一个新纪元。之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100年前的历史选择的无比正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今天,我们告别了旧的百年,开始了新的百年!
注释:
[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35页。
[2]《曾国藩家书》卷之七,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年,第273页。
[3]《曾国藩家书》卷之八,第311页。
[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7页。
[5]转引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1页。
[6]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记言》,中华书局1960年,第31页。
[7]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7页。
[8]杨天石:《帝制的终结》,岳麓书社2013年,第70页。
[9]《中国财政史》第七卷《清代财政史》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2页。
[1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
[11]英《泰晤士报》著,方激编译《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重庆出版社2014年,第280页。
[12]转引自张功臣:《洋人近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
[1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7页、666页。
[14]《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8页。
[1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6页。
作者:江苏省工运研究所研究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