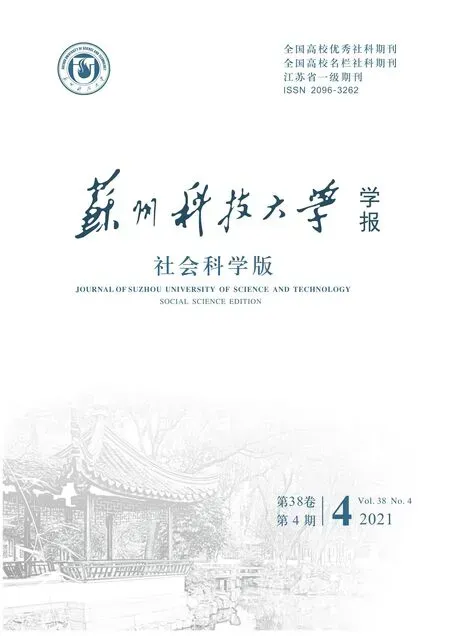潘祖荫与陆心源交游新考
杨 斌
(陕西理工大学 图书馆,陕西 汉中 723001)
潘祖荫与陆心源皆为晚清著名藏书家、金石学家。因潘祖荫搜辑黄丕烈题跋,二人始结缘,在潘氏丁父忧回家乡苏州守制期间,以及潘氏服阙回京后,二人书信往还频繁且多书籍及金石交流。关于二人的交游情状,散见于他们各自的题跋、日记、书信以及前人研究成果中,学界至今未有专文对此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注]目前,学界涉及潘祖荫与陆心源交游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潘佳《潘祖荫研究》(复旦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在“潘祖荫年谱稿”部分,以潘氏日记为材料,对潘、陆二人的交往情况进行了历时性梳理;吕亚非《陆心源致潘祖荫书札三通释读》(《文献》2013年第5期)重在陆心源致潘祖荫三通书札的文本释读和系年,而关涉二人交游的论述较少;陶其铁《陆心源金石学研究》(西北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学术背景与陆心源的金石交游”部分,通过陆心源致潘氏书札一通和潘氏致陆氏书札两通对二人的金石交往情况进行了考述,因所引信札较少,论述显得粗浅。,许多问题尚待解决。例如,潘、陆二人何时相识?潘祖荫丁父忧在苏州守制期间,二人有哪些书籍以及金石的往还或赠答?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潘祖荫守制结束回京后,二人还有无交往?鉴于以上种种,有必要对二人的交游过程作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梳理。笔者最近有幸获观陆心源所辑《潜园友朋书问》,此书收有潘祖荫致陆心源的书札共计二十通,皆为前人较少关注之原始材料[注]潘祖荫颇好书法,其日记多次记载他临写草书名帖《书谱》的信息,其书札也多以草书为之,较难识读,故学界对潘氏信札关注者较少。,对于还原潘、陆二人的交往极具史料价值。笔者试以此批书札为主要史料,结合潘、陆二人题跋、日记等文献,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二人交游情状进行考述,如有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谬。
一、二人订交始于潘祖荫辑黄丕烈题跋之际
吴中藏书大家黄丕烈题跋之搜集与刊刻,潘祖荫可为“导夫先路”者。潘氏搜集黄跋约在同治末年至光绪二年(1876)期间[1],因潘氏身居显职,公务繁剧,故黄跋之搜集多托其门生和好友杨绍和、缪荃孙、汪鸣銮等完成。光绪八年(1882),潘祖荫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回记,黄跋之搜辑,是“从杨致堂河督之子协卿太史录得先生手跋百余条,又从平斋、存斋录寄跋若干条,柳门侍读、筱珊太史、茀卿太史助我搜集若干条,聚而刻之”[2]。存斋即陆心源。虽然潘氏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未言明陆心源在何时通过何种方式为潘祖荫录寄跋文,但缪荃孙后来重编《荛圃藏书题识》,曾在跋文中谈及黄氏题跋系自己于光绪二年(1876)“乞假入川,因怀其稿游江浙,钞之于罟时瞿氏、钱塘丁氏、归安陆氏、仁和朱氏。时于坊间得一二种,即手钞之”[3]。此应为文献中有关潘、陆二人交往的最早记载。有关陆心源为潘氏录寄跋文之事,潘氏于光绪二年六月八日[注]此年吴云曾致信潘氏云:“存斋辱执事,以文字知爱,遇事关垂,渠甚感戴。”吴氏函中所述“以文字知爱”应指潘氏请求陆心源录示黄跋之事,故潘氏此札当作于光绪二年。参见吴云《吴云函札辑释》,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236页。致陆心源书札中有所言及:
存斋仁兄年世大人阁下:奉手书又承雅惠,谢甚,谢甚!惟起居清吉,著述日富为颂。天生阁下而困顿之、厄塞之,其意有在。阁下命世之才,何悉不遇也乎?获古之福,并时无俦,羨羡!所刻各书,先睹为快。弟辑《黄荛圃题跋》四册,属门人缪小山太史校之,门人汪柳门书而刻之,今年未必能竣事,若成,当先奉呈。吾兄见闻甚广,若得荛圃题跋,祈录示,以便续赠。千里神交,所谈只此,此亦绝无仅有之事也。弟碌碌无片刻闲,幸上侍康绥,足以报慰。筠仙丈[注]郭嵩焘(1818—1891),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筠仙,号云仙、筠轩,又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久无书,此君甚拳拳于执事,真肯留意人才者也,然亦大不悦于庸俗,岂非天乎?草草布谢,恕不庄书,即颂著安。年愚弟荫顿首,六月初八日。[4]
潘氏书札与缪荃孙跋文所记叙在时间上相合,故二人订交,至迟在光绪二年六月。至于陆氏藏跋为缪荃孙游江浙钞录,还是陆心源直接钞录后寄与潘祖荫,尚待进一步考证。
考潘、陆二人行迹,潘氏于光绪初年在京任职,光绪二年正月署刑部右侍郎;五月,派考试差阅卷大臣。陆心源于同治十三年(1874)署福建盐法道,“后因人际关系奉旨送部引见”,陆氏“殊觉为官之难,决定隐退,以吴太夫人年高需归里陪母为由,上疏准辞闽职”[5]7;光绪二年,陆氏被参劾擅自改税,致使盐务亏损,从而被革职[6]。从上揭潘札所述“千里神交”云云可推知,潘、陆二人在此年还未曾晤面,但已经相识,且有书信往来。
二、在潘祖荫丁忧居吴期间二人始频繁交往
(一)光绪九年(1883)潘、陆二人的交往
光绪九年正月二十二日,潘祖荫父潘曾绶逝世,四月初四日,潘氏即收到“存斋信及《藏书志》、及集、及《丛书》二集”[7]。虽然我们已经无缘获观陆氏书信,但依据潘氏日记与下文所揭潘氏手札可以推知,陆氏寄信的主要目的是吊唁潘氏父亲之丧,再付寄新刻之《皕宋楼藏书志》及《十万卷楼丛书》。
此年四月二十日,潘氏扶榇南下,“二十四日抵津,二十五日乘船,二十九日抵家”,归家后,于五月初三日赁屋金太史场[8]103,在故乡守制近三年。潘氏在日记中感叹,三十余年未回家乡,已经巷陌不识,取己酉(1849)日记阅之,恍如隔世。潘氏家乡苏州在太湖之东,陆氏家乡归安在太湖西南,故在潘氏丁忧期间,二人所处地理位置较近,无论是乘车或乘船,均较为方便。在潘氏归苏州后的五月十一日,潘氏即致信陆心源:
在都时,迭承赐唁……前惠大集及《藏书志》为朋好王廉生[注]王廉生即王懿荣(1845—1900),字正孺,一字廉生、莲生,晚署直庐花衣、养泉居士、养潜先生,登州府福山县(今烟台市福山区)人。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授国子监祭酒,官至侍读。自幼酷嗜金石文字,收藏金石碑刻,精于铭文考订,清代著名金石古物收藏家。诸君持去,顷刻而尽。不得已为此,再渎乞赐大集及《藏书志》各二部,……世愚弟制荫顿首,十一日。[4]
潘氏作此函的主要目的,即请求陆心源再寄《皕宋楼藏书志》二部。对于潘氏之请求,陆氏自然不会含糊。故在收到潘氏书信后不久,陆心源便再奉寄《藏书志》,并致信问候潘氏归苏州之后的近况。
五月二十五日,陆心源首次登门拜访潘氏[7],二人以前仅为书信往还的千里神交,至此初次晤面。潘祖荫位高权重,富藏金石古籍,声名显赫;陆心源虽家资雄厚,藏书极富,但在此际并无任何官职。故陆心源与潘祖荫的交往,自然存在着中下层士子与朝中权贵的攀附关系,陆心源为图其子陆树蕃晋身之计,不得不仰仗潘氏[注]已有学人注意到,在清代,“不少文人士子将与官场权贵鉴赏、交流金石碑拓视为亲近权贵和获得升迁的工具”。参见赵成杰《社会史视角下的清代金石学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96~102页。。诚如陆心源致潘氏信中所云“积年钦佩之忱,藉以快慰,复蒙挚爱,感激尤深”[4],应为陆氏肺腑之言。
潘、陆二人虽身份地位有别,但皆酷嗜金石、书籍,二人晤谈自然少不了金石彝器、古籍椠本的搜访。潘祖荫请借拓陆氏所藏彝器数件,并命陆氏搜访南中所藏金石。陆心源于五月二十七日抵家,即致书潘祖荫:

六月初一日,潘氏收到陆心源所寄之兕觥、金石拓本及信函,随复信对陆氏所寄之兕觥以及拓本进行鉴定:
兹荷手翰并兕觥一具,不胜铭泐。嘉礼壶乃宣和器(不足存也),格伯簋及召夫尊既尚未归清秘,若蒙为作缘,尤感。奖彝等或赐借拓,或惠拓本,仰乞尊裁。……年愚弟制荫顿首,六月朔。[4]
从函中所述内容可知,潘氏认为“嘉礼壶”为宋代宣和年间之仿品,但格伯簋及召夫尊皆为真品,既然仍未被陆氏购入,赐请陆氏作缘,购得此两器。
潘祖荫收到陆氏呈览之兕觥后,钟爱之极,故“遗书请效苏、米博易之举”[10],请求将自己所藏宋本《九经》与兕觥交换。《潘祖荫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光绪九年(1883)六月十九日载:“存斋以子燮兕觥赠。”[7]由此可知,陆氏最后答应将兕觥直接赠予潘氏,并不再接受潘氏欲“博易”的宋本《九经》。在陆氏允赠兕觥的第二天,潘即“复存斋”[7]一函,云:“得手书乃蒙慨允,此诚有一无二之珍,非常之赐,古人之谊,何以加兹。《九经》四本仍当奉赠,……八月中枉过,当以奉呈,并将宋元椠之一鳞片爪悉请鉴定也。”[4]从书信内容可知,虽然陆氏不接受潘氏欲“博易”的宋本《九经》,但潘氏仍坚持将《九经》与兕觥作交易;从函中所述“此诚有一无二之珍”推知,潘氏对兕觥确实珍爱。
此年七月二十一日,潘祖荫再致信陆心源,一方面表达了对陆心源所赠彝器及拓本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再次确认“王作又将彝最精,格伯簋非伪”,并论及格伯簋“流传有五六器”所以“据拓本已可定为真也”[4]。至于召夫尊之真伪,因陆氏并未将原器物送来,“故非见器不敢定也”[4]。陆心源于第二日即将彝器三件奉呈潘祖荫鉴定并请其模拓[注]潘祖荫七月二十二日致陆氏函:“手教具悉,彝器三件俱收到,拓后即缴。……弟制荫顿首,廿二日。”,并附寄书信一通,信中指出了当时颇为风行的张之洞《书目答问》存在的问题:
张中丞所刊《书目答问》,世颇风行。如《考古续图》,流传绝少,惟天禄琳琅及叶氏平安馆有其书。《答问》列之“通行”,朱石君《知足斋文集》乃散行,而列之“骈体”,毛岳生、吴仲伦、刘孟涂、管异之,称姚门四杰,而独遗毛氏,亦百密一疏也。[11]
潘祖荫从信中获知,陆心源藏书虽富,但无《考古续图》,恰好自己藏有手摹本。故他在七月二十一日函中询问陆氏:“《考古续图》弟有手摹本,如欲观,当即奉呈也。”[4]《考古续图》即《续考古图》。陆心源曾刻入《十万卷楼丛书》,在《刻续考古图序》中记叙从潘祖荫处借录之经过:“甲申之夏,晤潘伯寅尚书于吴门,见插架有之,从翁覃溪手抄过录者,后有二跋,覃溪所据,即遵王影摹之本,其第一跋即《四库全书》馆《提要》之底稿也。”[12]陆氏在序文记叙此书系光绪十年(1884)从潘氏处见到,其所记年份有误,应在光绪九年。

早在同治元年(1862),吴云[注]吴云(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又号愉庭,晚号退楼,浙江归安(今湖州市)人,道光举人,官苏州知府。精鉴赏,富收藏,凡金石彝鼎、法书名画、汉印晋砖、宋元书籍皆一一罗致。颜其居曰“两罍轩”“二百兰亭斋”。所著金石彝器图释诸书,皆亲自绘图,甚为可贵,著有《两罍轩彝器图释》《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古官印考》《考印漫存》《焦山志》。归隐苏州,吴氏性喜金石彝鼎、古籍椠本。在苏州隐居期间,吴云与南浔著姓大族交往频繁,为“真率会”主要成员,陆心源、顾文彬便是吴云时常往来的好友。[13]而潘祖荫早年与吴云因金石同好就已订交,吴氏女后来嫁与潘氏叔弟潘祖颐,两人来往更密切。早在潘祖荫返回家乡前,吴氏已病逝。潘氏丁忧返回苏州后,追忆往事,悲伤不已。吴云殁后,其家藏书籍椠本、金石器物散出,故陆心源在此年八九月期间,致信潘氏咨询吴氏所藏百衲本《史记》以及《营造法式》之下落。在九十月间,潘祖荫回复陆氏:
吴丈之《史记》即钱遵王之百衲本也(凡四种,中有蔡梦弼本,余不记矣)。辛未年,欲以千二百金出售,无人能得之。后仲饴[注]仲饴即吴重熹(1838—1918),字仲饴,号石莲,无棣县人,同治元年举人。历任河南陈州知府、开封知府,福建按察使,江宁、直隶布政使,护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江西巡抚,河南巡抚等职。解职后,闲居天津,闭门谢客,编辑印行《吴氏文存》《吴氏诗存》《世德录》等。出守陈州(重熹,弟之门人也),此漾亦止。至《营造法式》,未闻其有此书,盖仲化[注]仲化,其人不详,疑即潘祖颐,潘祖荫叔弟。内弟一力提携,若有之,必言与也。敬复,存斋仁兄同年大人。制荫顿首。[4]
潘祖荫在函中详细叙述了吴云所藏《史记》之版本及此书在同治十年(1871)之售价,并交代未在吴氏处发现《营造法式》。此年十月二十七日前数日,潘祖荫终于在吴云处找到陆氏欲借观之《营造法式》,二十七日潘氏即致信陆氏:
得奉手毕……前说及影宋本《营造法式》,适已检出,书册太大,如欲观,当设法寄。观此想见原本之精妙,真是异宝,不知何所归也。浙丁氏[注]浙丁氏即丁丙(1832—1899),字嘉鱼,号松生,晚号松存,浙江钱塘人,著名藏书家。之宋元有异本否?能见其目录否?……年小弟制荫顿首,十月廿七日。[4]
参照此日之潘氏日记可知,陆氏将七月间所借《续考古图》归还潘氏,潘氏将吴云处所发现之《营造法式》借予陆心源。另,潘祖荫喜藏宋元旧刊,其藏书印曰“分廛百宋,迻架千元”[14],他自然会询问陆心源浙江丁丙处有何种宋元珍本古籍。
除互赠、互借书籍外,将书籍作为礼品转赠好友也是潘、陆二人交往互动的另一种方式。《日记》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载,潘祖荫曾将陆氏所赠书籍转赠好友李鸿裔[注]李鸿裔(1831—1885),字眉生,四川中江人,晚清学者。潘氏日记载,潘祖荫在苏州守制期间与李鸿裔往来极密。二份[7]。
(二)光绪十年(1884)潘、陆二人的交往
光绪十年,潘祖荫仍在苏州寓所会友、刻书,而陆心源也在归安家中忙于书籍的编写、出版并联系组织校核人员。二月下旬的苏州,天气渐渐回暖,又到了草长莺飞的季节。《日记》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五日载:“存斋借《史载之方》《石林奏议》。”二十五日载:“存斋来。”二十六日载:“至界石浜春祭,答存斋。”二十九日载:“送存斋英笔记、汪退谷四种。”[7]由此可知,陆心源将潜园所藏《史载之方》《石林奏议》亲自恭呈潘氏,在二月下旬潘、陆二人交往颇密。
三月初八,此日清明,潘祖荫至狮子林为父亲念经,在回家途中因“风日所迫”[15],双目红肿,久治不愈,故在致友人信札中皆要求来函务作大字。因眼疾,四月十四后潘氏之日记亦命仆人长太代为书写。五月二十六日,此日初伏,潘氏又“得陆心源信”[7]一通,札云:“宫保钧座:顷聆钧谕,感怀交并,如蒙赏寄书函,或交永和信局或交萧家巷典当皆可。宋刻史方、叶议,祈勿邮寄,源秋间必到苏也。《营造法式》俟抄完即当专人奉缴。”[9]154从函中所说“宋刻史方、叶议,祈勿邮寄”可知,陆氏对此两书之宝爱。陆氏《重椠石林奏议序》记潘祖荫借阅之事:“潘伯寅宫保从余借阅,怂恿雕行,遂摹写而付之梓。”[16]由此可知,潘氏曾怂恿陆心源将《石林奏议》刊行。《石林奏议》和《史载之方》后来均刻入《十万卷楼丛书》。七月十八日,陆心源再次登门拜访潘氏。潘氏因双目肿赤仍未消,故未接见陆氏[7]。陆氏离开潘府后,潘祖荫即致信陆氏:
贱恙目疾,五阅月而未愈,医所误也。《贞石志》稿失于庚申前,赐书敬谢,敬谢。至今来谕,尚看不见矣,又拙刻二种敬呈。恕其大字草也,眵粘满匡,努肉红赤,见人更胀痛,现点拔云丹。三月承前借二书,须手自检点,可少迟否?一动目动手辄胀痛,及眵粘不止也,敬复道安。年小弟制荫顿首。[4]
信札字大行疏,一页寥寥数字,应是潘氏眼疾期间勉力而书。函中所说《贞石志》,应为潘氏所著《海东贞石志》,此书稿本失于咸丰十年(1860),“拙刻二种”应指潘氏新刻之《滂喜斋丛书》[注]《日记》光绪十年七月十八日载:“陆心源来,未见,送《滂喜斋丛书》一部。”。另,函中所说“三月承前借二书”,应为上文所揭陆氏借予潘氏之《史载之方》《石林奏议》。此年冬,潘氏目疾终于痊愈,但无论是潘氏现存信札还是日记,均没有二人交往的记录。
(三)光绪十一年(1885)潘、陆二人交游
转眼到了光绪十一年正月,潘祖荫在家乡苏州已经两年多。按古代的丧服制度,此年四月,潘氏将除服。正月二十日,潘祖荫曾以陆心源所赠《皕宋楼藏书志》等书转赠于李鸿裔。[7]此年潘祖荫继续忙于书籍的刊刻,在服阙回京前,先后“续刻《古籀疏证》六卷,《范石湖诗补注》三卷,编入《功顺堂丛书》”[8]107。
三月十三日,陆心源再至苏州,但因潘祖荫在“庄祠春祭”[7],二人未能把晤。陆氏将新刊之《秋室集》《仪礼今文异同》《三续疑年录》及书信留下后,即返回归安。第二天,潘祖荫即致信陆氏:
得手示适有客,未即复为罪。《石林奏议》重摹真盛事,能将李中麓[注]李中麓即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自称中麓子、中麓山人、中麓放客,山东章丘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文选郎中、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等职。嘉靖二十年(1541)因抗疏罢归乡居,近三十年。李开先文名籍甚,为“嘉靖八才子”之一。著述甚丰,有《闲居集》十二卷,杂集二十一种,今存十四种。一印,并用双钩摹之为妙,李藏本海内绝少。明晨至先茔,恐失迎,为此布闻。新刻钮《说文校录》乃弟极力搜得于其家,而属刻者,兹以奉呈。此复著安。弟制荫顿首。[4]
有关潘氏此日作信之事以及二人的书籍往还,可与潘氏此日之日记相参证:“答存斋,送以《功顺堂丛书》一部,《补注》《释地》《辨伪》各二部。还存斋《史载之方》《石林奏议》《翰苑集》一册……钮《说文》一,送存斋。”[7]从潘氏日记可知,原本陆氏欲在上一年秋亲自取回之《史载之方》《石林奏议》,至此日方由潘氏寄还。
陆心源收到潘氏书信后获知,三月十五日潘氏将至先茔,故十五日未再造访潘氏。三月十六日,陆心源再次拜访潘氏。[7]二人在潘氏苏州寓所把晤,潘祖荫曾询问陆氏闽中故家之藏书,可能因前来拜访潘氏的客人较多,陆氏当天未及详细作答[注]据潘氏日记记载,此日拜访潘氏的先后有俞樾、陆心源、吴卓臣。。故陆氏回家后即致信潘氏,信中详细陈述了闽中故家藏书之情况[注]陆氏信札。参见吕亚非《陆心源致潘祖荫书札三通释读》,《文献》2013年第9期第155~158页。吕亚非将此札系于光绪十年,误。。潘祖荫收到书信后,即致信陆氏:
承示尔见缕,欣羡之至,胜读十年书也。曾见翁叔平[注]翁叔平即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叔平,号韵斋、瓶生、瓶庐、瓶庐居士、瓶庵居士、松禅、松禅老人、松禅居士,江苏常熟人,心存三子。咸丰六年(1856),二十六岁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官至协办大学士,两度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典馆正总裁等职,同治、光绪两朝皆值弘德殿,为两代帝师,垂三十年。光绪戊戌(1898)年,因赞助光绪帝变法罢职归里,卒后谥文恭。有刘燕庭所抄各家书目,至八十册之多,到京后拟向借来,以活字板印之,未卜其允否。活字板闻潘谟卿之弟名骏宣者有之,亦拟向借也,但不知到京后有此闲暇否耳。闻合肥[注]合肥即李鸿章(1823—1901),晚清名臣,安徽合肥人。亦有活字板,拟过津一询之,此复著安。弟制荫顿首。[4]
信中谈到,到京后潘氏欲借翁同龢所藏刘燕庭所抄各家书目,可知此札确实作于潘氏服阙归京前不久。四月一日,潘氏再次收到陆氏书信并附寄“师望鼎拓本及朱晦庵尺牍墨刻”[7]。陆氏寄潘氏师望鼎拓本的目的,主要还是请求潘祖荫鉴定此鼎之真伪。四月十五日,潘氏为父举行“禫”祭,即丧家除服的祭礼,“寅正”,潘氏“奉先君神位进义庄宗祠”[7]。归家后,潘氏即致信陆氏:

信中谈及师望鼎的真伪,潘氏认为此鼎虽字字有来历,但“文气不属”,故疑不真。函中谈及晚清时期青铜器作伪风气之炽,这是因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商人便运用新技术、新材料作伪,使作伪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7]
四月十八日,潘祖荫将书架及部分藏书寄存叶昌炽处。四月二十二日,潘氏“挈眷北上”,返京任职,近三年的守制生活结束。此后,潘、陆二人虽相隔千里,但仍保持书信往来。
三、潘祖荫服阙返京后与陆心源的交往
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初四日潘祖荫抵京,五月初十日即被召见于养心斋,署兵部尚书,十二月初四日派管理火药库事务。[8]109潘氏抵京后,此年的日记未再出现二人交往的记载。
光绪十一年,在潘祖荫的建议下《石林奏议》在潜园刊成。光绪十二年(1886)五月陆心源寄《石林奏议》十部,潘祖荫于五月十二日收到书籍与陆氏信后即复,并回赠陆氏“庄、沈、《东古文存》”[7]。潘氏函云:
得手教并承惠《石林奏议》十部,谢甚,谢甚。恍如从前借观,而今真得之也,喜不可言。……今则又目赤肿作痛,如前年夏间,是以乞假,不能看书,闷极,闷极。恕其作字草草,素承厚爱,勿怪。近刻三种送上四部,闻近得古器,敬祈拓寄,又得古书几许,祈示知以为快也。弟则一无所得,忙不可当,力疾布复,即请道安。弟期荫顿首,五月十二日。[4]
考潘氏光绪十二年行迹,二月十六日潘祖荫扈跸东陵,三月十八日派查估河道[8]110,四月初二日潘氏被派覆勘会试卷,四月初四日潘氏查估天坛工程等处,四月十七日又被派阅覆试卷[8]111,故潘氏在函中云“忙不可当”。函中落款之“期”应指潘氏季父潘曾玮之丧。[8]109此年,陆氏所著《金石学录补》三卷(实为四卷)在潜园刊竣,此书系对光绪五年《金石学录补》二卷之再补充。[5]9潘氏在苏州期间借与陆氏之《续考古图》也在潜园刻竣,九月十一日,潘氏又“得陆存斋信”[7]并收到陆氏所赠《续考古图》;九月二十三日,潘氏复信感谢老友的雅赠:
得手书并《续考古图》及鬲比攸鼎拓本,敬谢,敬谢。……近得二石,拓以奉呈,一乃魏建义石刻,许印林[注]许印林即许瀚(1797—1866),字印林,一字符翰,山东日照人,清道光举人,任滕县训导。四次赴京会试均落第,乃致力于金石方志、文字音韵、校勘目录之研究,其著述及校订之作多至近70种。外从未著录;一见《山左金石志》也。鬲比攸鼎再求拓本三四分(不必全形,只求拓本足矣)。此器诚为至宝,获古之福,可羡,可羡!兄近得古书否?祁示知为幸。弟今年得黄氏所藏《嘉祐集》及《梅花喜神谱》及《唐氏蒙求》,此外别无所得。……弟期荫顿首,九月廿三。[4]
“鬲比攸鼎”即鬲攸比鼎,又称“鬲攸从鼎”,《吴兴金石记》有著录。陆心源曾以此鼎颜其藏器之室曰“鬲鼎廔”,可见对此器之珍视。惜此器后流失日本,现藏于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函中所述潘氏得黄荛圃经藏之书事,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十二年十月十六日载:“郋亭学史前日云,新为郑盦丈得宋刻《梅花喜神谱》,亦荛圃物,即载之《读书敏求记》者。又北宋刻《嘉祐集》,金刻《政和本草》,宋刻《读史蒙求》,计直七百金。”[18]121两者所述内容均若合符节。
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十五日,皇帝亲政,三月十七日派潘氏查估雍和宫,四月二十日“派查估供用库工程”。六月十一日潘氏“奏大婚彩绸核减三分之一折”[7],六月十五日潘氏“得陆心源信及《金石学录补》”[7],六月十六日潘氏“复陆存斋,寄以建首、温虞、盂鼎、铸簋、遇卣一,古匋九”[7]。潘氏复函云:
得手书《金石学录补》,敬谢,敬谢。……即已近派管□学刻《说文建首》及少年所摹《温虞公碑联》以示之,附呈三分。又,盂鼎拓、卣拓、簋拓各一,又古陶拓九分。敝处拓人已盲,现觅人拓不得,且又无片刻暇。……弟荫顿首,六月十七日。[4]
函中所说《温虞公碑》即《虞恭公碑》,又名《温彦博碑》,唐欧阳询书丹,现藏昭陵博物馆。此碑拓本经陆恭、费开绶、潘祖荫递藏,后为吴湖帆“四欧堂秘籍”之一,此拓为所有现存拓本中字数最全者,现藏上海图书馆。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廿一日记载:“郑盦丈见示宋拓《崔敦礼碑》……又欧碑四种,《温虞恭碑》最胜,松下清斋藏本也。”[18]91可见,潘氏摹刻并赠与陆心源三份《温虞公碑》应是此本。
光绪十五年(1889),陆氏长子陆树蕃中恩科举人[19],中举第二年,树蕃即入京参加会试。因潘祖荫多次担任会试复试阅卷大臣,陆心源自然会利用与潘氏之关系,为其子陆树蕃谋一出路[注]潘祖荫与翁同龢是晚清科举盛兴金石学、公羊学的推动者,王懿荣、叶昌炽等人科举之路的成功与潘祖荫有莫大关系。参见安东强《张之洞与晚清科举考试风气》,《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第83~92页。。由《日记》光绪十六年(1890)闰二月初四日所记“晤兰孙、陆树藩(存斋子,号毅轩)。存斋寄来新刻书”[7]可知,陆树蕃确于会试前携带潜园新刊书籍拜访潘祖荫。陆树蕃离开潘府后,潘祖荫于闰二月初五日即“手复存斋”[7]书信一通:
存斋仁兄大人阁下:文郎高捷,来京得手书并惠尊刻各种,谢谢。文郎经荣绝异,真不愧家学也,可胜叹服。弟积劳多病,现又有扈跸之行,京兆公事之烦,竟无暇刻,年来未刻书,仅有三种,又二刻呈教。尊著《吴兴金石存佚目》,乞赐寄为感。……弟荫顿首,初五日。(近闻振济极劳,真造福无量也。可胜钦佩,又拜。)[4]
考潘氏此年行迹,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四日,潘氏扈跸东陵,故函中有“现又有扈跸之行”之语。函中所说《吴兴金石存佚目》应为陆心源所著《吴兴金石记》,此书于光绪十六年刻竣,故此年陆氏有赠书之举。
四月,陆树蕃会试结束后,陆心源再次致信潘氏,询问此次树蕃会试之结果。潘氏于四月十五日“手复陆存斋”[7],回信云:
存斋仁兄大人阁下:得手书敬悉,唯著述日丰为颂。弟历碌从公,几无片睱。文郎鹏程偶屈,殊深慨惋,而学粹词高,加以俭门积庆,指顾壬科,定当高选矣。日前得失,不足计也。近来搜罗益富,愿闻其目(京师近来直无所见,偶有一二,皆归盛伯希[注]盛伯希即盛昱(1850—1899),字伯熙(或伯希、伯羲),号意园,爱新觉罗氏,满洲镶白旗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历官编修、侍讲、侍读,十年出任国子监祭酒,十四年任山东正考官,著有《郁华阁集》。诸贝也)。所得彝器,请赐拓本为感,近见二钟、一壶,拓呈清鉴。敬请道安,惟鉴不备。年小弟荫顿首,十五日辰刻。[4]
函中所言“指顾壬科,定当高选矣”,“壬科”应指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殿试,潘氏在函中希望陆树蕃能在两年后的壬辰科殿试高中。光绪十六年七月十六日,陆心源堂弟“陆学源交到存斋信”[7]。陆氏书信虽已无缘得见,但参照《缘督庐日记》七月十七日记“郑盦师赠陆存斋《仪顾堂题跋》,即命代作一序”[18]190可知,陆氏书信的主要内容即请潘氏为《仪顾堂题跋》作序。由于潘氏事务繁重,《仪顾堂题跋》序文最终由叶昌炽捉刀。七月二十日,潘氏即“复陆存斋,并《仪顾堂题跋》作序,并克鼎、汉大砖拓本”[7]。七月二十四日,又“函致陆存斋,汉画一、唐石十一”[7]。此后,潘氏之日记再也未出现二人交往的记载。至于七月二十日、二十四日潘氏函札,为何未收入《潜园友朋书问》,是陆氏丢失或是其他原因,我们已经无从知晓。数月后的十月三十日,潘祖荫终因忧劳久疾,与世长辞。
四、结 语
晚清时期,金石之学极盛,形成以潘祖荫为中心的“京师金石文化圈”。潘氏虽长期在京师任职并生活,但因其家乡在苏州,加之潘氏在政坛的地位,其金石、古籍搜访和研究活动自然会辐射至苏州、湖州地区。晚清金石、目录学大兴局面的出现,与诸多志同道合且交往密切的士人群体共同推动不无关系,潘祖荫和陆心源的交游就是当时士人群体合力的一个缩影。虽然潘、陆二人的爱好几乎相同,但潘终以金石博得美名,陆终以藏书称雄其时。二人交往时间跨度长达十六年,他们虽地位相悬,但皆为晚清史上有较大贡献的文化名流,二人对于宋元古籍、金石彝器的狂热持续了大半生。他们的交往可以说是晚清江南文化史上颇具意义且值得深入研究的“雅事”。二人密切的交集虽仅仅在潘氏为父亲守制、闲居苏州的三年,但因志趣相投而惺惺相惜。潘祖荫一生识人无数且擅于发现人才,对于陆心源之才能,潘氏赞许有佳,认为陆氏“之学问博雅闳通,已为心服,而其为当世之务,目光直透过数十百年,真医国名手也”[4]。以潘祖荫的身份和学识,陆心源对潘氏更是敬重有加,故在陆心源致潘函中会出现“钧座”“钦佩之忱”等语。二人的交往,既丰实了各自的学问,充实了各自的收藏,又保存了晚清时期一些几近失传的古籍。
-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国外面向婴幼儿STEAM教育教材的内容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