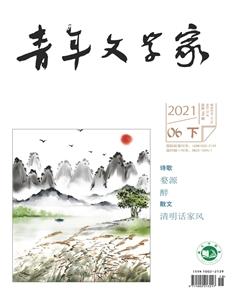从“爱邻”到“知邻”
周琳
《庭院中的女人》是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又一部中国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从江南大户人家的主母吴太太过40岁生日那天写起,讲述了作为当家主母的吴太太怎样尽心操持家中各种事务:为丈夫纳妾,为小儿子请洋教师、娶妻,调解儿子和儿媳之间的关系……而在内心深处,吴太太却有着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活的思考,在和洋教师安德烈的相处和交谈中,吴太太不知不觉受其影响,更在安德烈不幸遇害之后,在长久的思索中有了更深的领悟。
在《庭院中的女人》中,多处可见西方文化因素,比如笨拙善良的夏修女,多年来一直试图向吴太太传福音、讲圣经;而在一个如饥似渴学习西方文化的年代,年青一代如若兰、丰漠都从现代学校中吸收了很多来自西方的观念。但赛珍珠似乎并不认可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因此,作为启蒙者的安德烈,既在向吴太太传递着西方文化中的精髓,又在试图将其“中国化”,将其与中国文化精神贯通融合。
一、“爱邻”在作品中的体现
作品十三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爱邻如爱己。”他慢悠悠地读着。
“爱!”她大叫起来,“这个字儿也用得太重了。”
“你说得对,”他说,“这个字不该是‘爱。谁都没法爱上自己的邻居。不如这样说吧,‘知邻如知己。也就是说,须知其困厄,解其境遇,碰上他犯错的时候,务必要对待自己的过失一般和风细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太太,这里的爱就是这个意思。”
安德烈作为一个洋牧师,因宗教观念的不同被同胞离弃,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白人而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相反却尽力理解那些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并默默行善:他收留那些被抛弃的无家可归的孤儿,接济那些贫苦的无衣无食的流浪汉和乞丐;他也尽力开导那些对生活怀着热情、渴望或困惑的人,如丰漠和吴太太,却又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们。在安德烈身上,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的“邻人之爱”,而他也把这种爱传递给了吴太太。
当吴太太做出为丈夫纳妾的决定时,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依然认为自己是爱丈夫的。但随着她所建造的房子相继出现裂纹并崩塌,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和动机,才惊讶地发现自己心里并没有真正的爱。“爱”这个词汇在安德烈死后,成为作品最重要的主题。夫妻之情、男女之爱、肉体之欢、灵魂之爱,成为吴太太经常思考的对象,但最能体现在行动上的,是吴太太对于曾经不怎么喜欢的二儿媳妇若兰、三儿媳妇琳仪的接纳、教导和对安德烈留下的十几个孤儿的收留、照看。
安德烈去世之前,对吴太太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养活我的小羊。”
安德烈则放心不下他收养的那些孤儿并把他们托付给了他精神上的门徒吴太太。
吴太太不理睬任何非议,毅然决定收留她们。她为那最小的还没有名字的孤儿起名为“爱爱”;她把她们安置在祖庙里,不仅供应她们日常所需,而且施以教化,使她们在行为举止和见识上都无可指摘;她还亲自关切她们的婚姻,为她们婚姻的选择把关。值得一提的是,吴太太这样做并非为了使自己博得一个“慈善”的好名声,而是从和安德烈的一次次精神对话中,明白了“爱”之含义。
二、“爱邻”的中西方文化内涵
那么,中西方文化背景中的“邻人之爱”,各自有何内涵呢?
(一)西方文化中的“博爱”
“爱”是西方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眼。西方文化中的“爱”,不限于父母之情、男女之爱,更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普世性的爱。这是因为其数千年来的宗教信仰传统。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犹太人在路上被强盗抢劫并被打伤。强盗抢了东西走了,留下這个人在路上呻吟。不久之后相继有三个人经过:祭司、利未人和一个撒玛利亚人。祭司当然是犹太人中地位比较高的神职人员,利未人则是犹太十二支派中唯一有资格从事神职活动的人,但他们都装作看不见,从受伤的同胞身边走过去了。只有撒玛利亚人向伤者伸出了援手,他用油裹他的伤处,又把他带到附近客店里,付钱嘱咐老板好好照顾他。这个故事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那受伤的人的邻人呢?
由于历史遗留原因,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彼此怀有敌意且互不往来的,但这个撒玛利亚人却出于怜悯之情救助一个异族外邦人,这和那真正属于同胞的两个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帮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这才是真正的邻人之爱。
(二)儒家文化中的“差等之爱”
首先,我们回顾中国传统文化,会发现儒家思想中也有“爱人”思想。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仁爱”,而墨家思想则为“兼爱”。对于“仁爱”与“兼爱”的异同笔者不予赘述,但儒家思想历来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正统,赛珍珠也对儒家学说推崇备至,因此,在这里仅简要探讨儒家学说中对“仁爱”的一些阐述。对于 “仁”,曾有这样的解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朱熹也说“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孟子集注·梁惠王上》)。这些都指出“仁”的精神是“爱人”。
一般认为,儒家的爱是一种“差等之爱”,儒家的“差等”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去理解:其一,人的仁爱情感是有差别、有次序的,是自然生发、由近及远的;其二,针对不同的对象,人们在爱的方式上会有所不同。简言之,人的关系有亲疏,爱便也有亲疏:关系亲近,爱便深;关系疏远,爱便浅,爱的方式也随之不同。因此,从概念内涵上来说,“差等之爱”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吴太太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去看待圣经中的这段教导,她自然便觉得要如同爱自己一样爱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甚而关系疏远的邻人,这是不可能的。
三、从“爱邻”到“知邻”
作为一个对基督教文化不甚了解的中国女性,当初次听到“爱”这个词语时,吴太太觉得对邻人的感情用“爱”这个词,实在别扭。安德烈是一个牧师,但他更有一种兼容并包的视野。因此,在吴太太的质疑下,安德烈认同了吴太太的观点:“这个字不该是‘爱。”安德烈改动了被信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书中的字眼,却代之以一个中国文化气息很浓的字—“知”,这有何意义呢?
安德烈敏锐地看到了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通之处,儒家的“仁爱”和西方文化的“博爱”并非不可调和。他解释说:“须知其困厄,解其境遇,碰上他犯错的时候,务必要对待自己的过失一般和风细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太太,这里的爱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强调的“推己及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正是儒家文化的精髓。
《论语·里仁》篇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什么是“忠”?什么是“恕”?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忠”是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孔子在《雍也》篇里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有所作为,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有所作为;自己想发达,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发达。
“恕”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就是孔子在《卫灵公》篇里回答子贡“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的问题时所说的:“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推己及人,就可以知道别人的愿望、需求,并以达成自己愿望的态度去帮助别人达成。推己及人,也可以知道别人所害怕、所厌恶的,并避免把这样的事强加于人。
儒家的“爱”虽是一种“差等之爱”,但是,通过“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这种爱就由“爱亲”开始而不断地向外推扩,最终实现对他者的关爱。儒家的“差等之爱”注重“亲亲”之爱,但不会置于爱亲这种自然亲情之中。它强调“亲亲”之爱只是“差等之爱”的一个开端,还要由爱亲这种情感出发去“推己及人”,慢慢推扩出去,关心他人以至万物。对于别人的过错,“推己及人”就能够去理解其境遇和困厄,并反思自己处在同样境地中是否也会犯同样的错,因而饶恕其过错。
因此,虽然儒家的“仁爱”和西方文化中的“博爱”有很大不同,但是,安德烈却看到了两种文化可以对话与沟通的方面,把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比较空泛的概念落实到一個能用理性去理解的层面,落实到一个能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呼应的层面,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所以,安德烈去世以后,吴太太在他的启发下,能原谅昔日的闺密康太太,能发自内心地喜爱上自己原先不怎么喜欢的儿媳妇并帮助她,也能对那些孤儿产生某种怜爱之情,而以前她是并不怎么喜欢小孩子的。到作品结束时,吴太太已经越来越习惯使用这个对中国人来说因为很“重”而不宜使用的字眼:
“是啊,现在她信了,有朝一日,即使肉身死去,灵魂仍将永存。她不崇拜上帝,也全无信仰可言,可她有爱,绵延不绝的爱。是爱唤醒了她沉睡的灵魂,让她生生不息。”
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从小耳濡目染在西方文化的精神中;作为成长在中国大地上、从小接受中国民俗文化熏陶的孩子,她又深深感佩孔夫子和儒家文化。双重的文化背景使得赛珍珠的作品具有一种可贵的跨文化品格。在《庭院中的女人》这部作品中,我们尤其能感受到中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这特别体现在书中的男女主人公身上:安德烈是来自遥远欧洲的洋人牧师,吴太太则是出身于传统书香门第的中国闺秀,他们带着各自传统文化的印记打量彼此,又怀着宽容开放的心互相对话,在他们身上,读者看到了冲突对立,更看到了彼此理解与融合的希望。
课题项目:文化传递与赛珍珠笔下的女性形象研究,课题号:2019SJA2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