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暴风骤雨》“真实性”的几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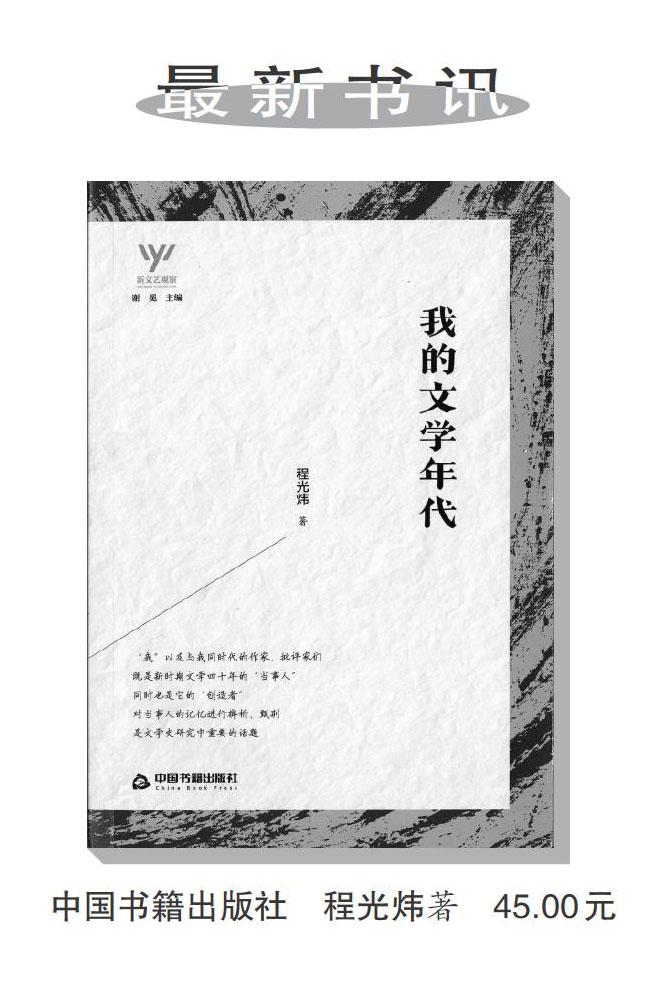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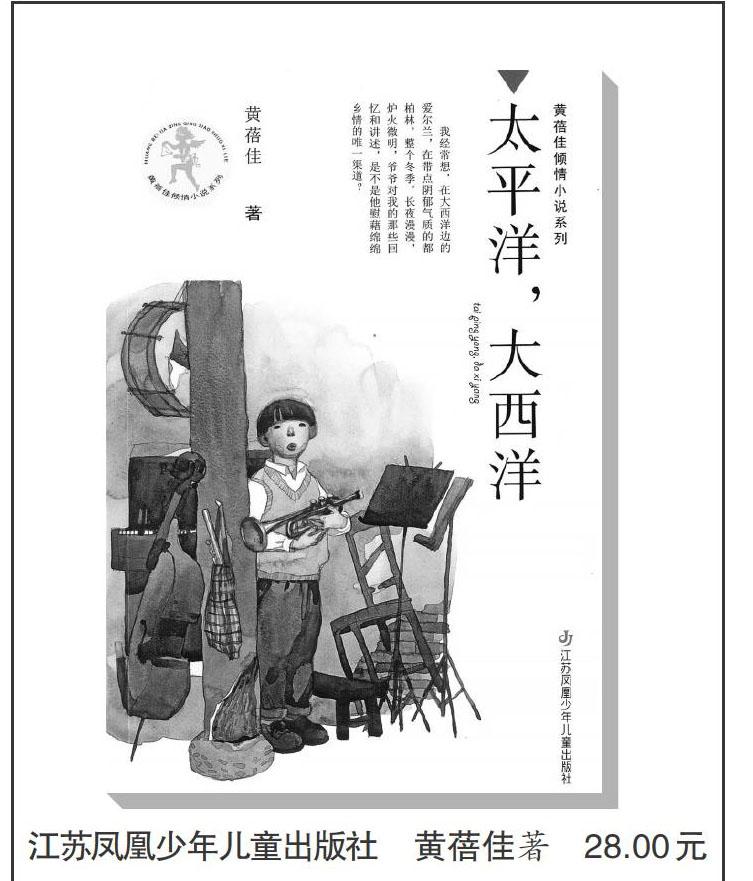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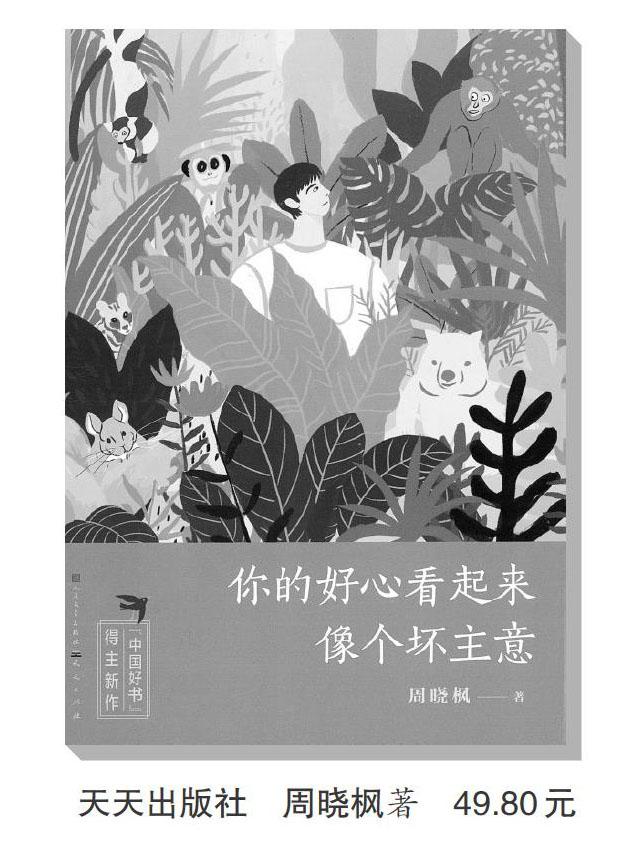
《暴风骤雨》自从问世以后,就命中注定它将成为一部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因为1948年6月,在东北局所组织的讨论会上,与会者虽然充分肯定了周立波的创作热情,但却并不认为《暴风骤雨》是一部成熟的作品。比如,马加质疑“元茂屯”与东北农村“有些距离”,舒群认为赵玉林这一人物“不够真实”①。到了新时期以后,一些富有批判精神的青年学者,不仅全盘否定了它的艺术审美价值,同时更是否定了它的历史认知价值②。
人们之所以会诟病《暴风骤雨》,问题就出在周立波坚持认为,《暴风骤雨》是以“编年史的手法”,去真实反映东北土改的历史小说③。然而,周立波1946年10月才来到东北,尽管他“目击了这个轰轰烈烈的斗争的整个过程”,但不满一年的生活体验,不可能真正了解东北农村的实际情况。所以,周立波无意中又透露出他对东北土改的情况了解,主要还是源自于“当时东北日报的土地改革新闻和上级党委编的许多关于土地改革的小册子”④。因为“在乡下前后只有八个月,在元宝时,醉心于当时的工作,对所见所闻没有好好的详细作笔记”⑤。为了能使《暴风骤雨》的土改叙事生动逼真,他只好从“报刊和其他地方”去寻找材料,比如“听别人的详述——渗进自己的经验”,并认为这样的“间接材料是可以变成直接材料的”⑥。所以《暴風骤雨》里的“东北”二字,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地域符号,并不具有黑土地文化的实际内涵。
一
《暴风骤雨》的创作背景,是《五四指示》与《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的贯彻执行。“八一五”光复以后,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国共两党之间发生内战,已是迫在眉睫、不可避免。所以,他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⑦。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实力悬殊,共产党人若想取得全国胜利,就必须尽快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军事上扭转处于劣势的不利局面。可是经过长期的抗战,中国农民出于民族大义,已经做出了巨大牺牲;现在又将进行国内战争,这就意味着无论他们是否愿意,仍然要再次付出牺牲。故当民族大义失去了作为战争动员的宣传效应,共产党人只能以“平分土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策略,去引导中国农民踊跃地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战争,不觉疲倦;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到这一点。”⑧而东北局文件说得更为直白:“土改的目的——是支持长期战争与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⑨
作为一名党的宣传工作者,周立波当然理解土改运动的重大意义,尽管他并不熟悉东北农村,却依然以他在元宝镇时的短暂所见,并掺杂了大量的“间接材料”,仅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暴风骤雨》的宏大叙事。因此学界一直都在怀疑,《暴风骤雨》里的“元茂屯”,究竟是不是尚志县的元宝镇?甚至有研究者还通过历史考证,直接否定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⑩。我个人认为,考证“元茂屯”的真实性固然重要,但考证“东北”的真实性更为重要;因为“元茂屯”是可以虚构的,但“东北”却不能虚构。令人遗憾的是,周立波还真把“东北”给虚构了。
首先,东北地广人稀居住得非常分散,“群居”并不符合东北农村的生活习性,而周立波却让“元茂屯”里住着400多户人家与2000多人口,把“元宝镇”直接写成了“元茂屯”,犯了一个明显的常识性错误。汉语词典对于“屯”和“镇”,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解释:“屯”是专指农耕人口居住的村落,“镇”从宋代开始便形成了一种有“较多工商业的居民区”;“屯”在行政上隶属于“镇”所管辖,而“镇”则又是“屯”的政治经济中心11。仅以尚志县元宝镇为例,1927年11月才撤“屯”改“镇”,到1942年共有400多户人家,镇上既有酒坊、学校又有赌馆、妓院,四周还建有“土城墙”和“四个炮台”,已经初步具备了“城”的规模12。而“屯”却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人口规模。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东北农民基本上都是以“屯”居住,大屯不过是百余户,小屯甚至只有几户。到了日伪统治期间,为了隔断农民与“抗联”之间的密切联系,曾在城市附近地区采取过强行“并屯”的野蛮政策,但大多数“屯”的人口都不到百户。据东北土改时期的资料统计,合江省绥滨县绥东区25个屯平均每个屯68户人家13,萝北县肇兴镇5个大屯平均每个屯80户人家14,而松江省宾县的刘才屯和王九兴屯合计才17户人家15。由于周立波是把“镇”当作“屯”去描写,故《暴风骤雨》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出东北农村的土地关系。
其次,东北地区是个新解放区,“元茂屯”农民对于萧祥和土改工作队员,不可能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因为“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人民遭受了日伪14年的残酷统治,他们既不了解国民党也不了解共产党,故“民族恨”要远大于“阶级仇”。另外,1945年9月,国民党与共产党同时进军东北,从农民保守性与务实性的人格出发,他们既不会轻易地暴露自己的政治倾向,更不可能主动去接近土改工作队。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把东北农民在政治上的一度暧昧,直接归罪为是韩老六等人的反动宣传,其实用不着任何人去做宣传,当时“北满2/3以上的县城掌握在顽匪手中”,老百姓不但不配合民主联军,甚至还“缴我主力部队士兵的枪”16。所以土改工作队员深有感触地说,“群众不了解我们,所以也怕我们”,土改工作开展得十分艰难17。但“元茂屯”里的情况却截然相反:萧祥和工作队刚一进屯,无论是老孙头、赵玉林还是郭全海、老田头,很快便消除了他们的心头“误解”,热烈欢迎土改工作队的闪亮登场。不仅贫农老田头说,“人家几千里地到咱们关外,为咱们老百姓翻身,谁不知道是抱的好心”;就连中农刘德山也认为,“八路军是咱们自己的队伍”,“是正装的人民军队”。周立波无疑是在套用老解放区的军民关系,完全遮蔽了东北土改的历史真相。
再者,为了突出“元茂屯”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性,周立波还明确地告诉读者,“元茂屯”里共有400多户人家,其中300多户都属于一无所有的“精贫”状态,几乎占去了全屯人口的75%以上。我查阅过黑龙江地区的文献资料,土改工作队通过调查所得出的统计数据,都不支持周立波有关“元茂屯”贫富悬殊的那种说法。东北土改划分成分的基本标准:100垧(1垧=10大亩=关内15亩)以上为大地主,40垧以上为中地主,30垧以上为小地主,5垧左右为中农,而贫农“自己有三两垧地,有一两匹马”18。东北农村的“精贫”情况,也不像《暴风骤雨》所描写的那样夸张。据中共合江省宝清县委书记孙英所做的农村调查,全县总户数11537户,划为雇农的1630户,占14%;划为贫农的5500户,占48%;划为中农的2794户,占24%19。中共桦川县委所做的农村调查也显示,全县总户数19948户,划为雇农的5126户,占25.7%;划为贫农的9016户,占45.2%;划为中农的3730户,占18.7%20。通过这两组数字我们不难发现,东北农村中没有土地的“雇农”所占的比例都很小,而贫农和中农则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由此可见,“元茂屯”里绝对性的贫富差距,在东北农村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
周立波自己当然十分清楚,“元茂屯”与东北农村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但他却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新的现实主义要看清现实的本质,要看到社会的本质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新的现实主义的教育的任务。”21他认为“新的现实主义”就是世界观与政治立场的正确性,作家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上”,才会做到对“一切真实之上的现实的再现”22。换言之,周立波并不否认《暴风骤雨》对于“东北”的虚构性叙事,因为在他本人看来作家政治立场的正确与否,要比作品中的艺术真实性更为重要;所以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立场上,去描写“元茂屯”的土改运动,其实与“东北”二字并无太大的关系。
二
《暴风骤雨》书写“东北”的失真性,第一大败笔就是赵玉林这一人物。周立波说“赵玉林的穷苦,他的全家缺衣少食的情景,源出于穷乡元宝镇的贫农”23,同时又综合了“东北土地改革中好些贫雇农积极分子的特点”24。按照周立波本人的说法,赵玉林这一人物是他对“东北”贫苦农民的高度概括。但有学者却依据历史资料,驳斥了周立波的这种说法:赵玉林等处于元宝镇边缘的那些农民,“都是一些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而不是什么真正的贫苦农民25,故彻底否定了这一人物形象的历史真实性。
我个人认为,赵玉林不可能是东北农村的真实人物,“他”和郭全海、老田头、小猪倌等“精贫”人物一道,都是周立波为东北土改运动所设计的政治符号。赵玉林外号“赵光腚”,他自己说:“‘民国二十一年,山东家遭了荒旱,颗粒无收,我撇下家人奔逃关外来碰运气。”可是到了东北,他先后被抓过四次“劳工”,结果是混得惨不忍睹:“一家三口都光着腚,冬天除了抱柴火、挑水、做饭外,都不下炕。夏天,地里庄稼埋住人头时,赵玉林媳妇每天天不亮,光着身子跑到地里干活,直到漆黑才回来。”如果不是八路军送给他家两套灰布军装,赵玉林都不敢“让人到屋里坐坐”。仅就写“穷”而言,恐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个贫苦农民的艺术形象,能够“穷”过赵光腚了,因为周立波一下子便将他打回到了原始社会。其实,东北人所说的“光腚”,并不是指一个人赤身裸体,而是指他的裤子破得快要露出了屁股,往往是在嘲讽他的老婆太懒惰。另外,赵玉林租种了韩老六的一垧地(15亩),又租种了杜善人的2亩菜地,按照东北产粮的基本标准,1亩地产粮一石(120斤),15亩地则是十五石(1800斤),除了交地租(在《暴风骤雨》的下部里,白玉山曾说“元茂屯”的地租一畝为三四斗,即50斤左右)750斤,赵玉林应该还剩1000斤左右。再加上租种的2亩菜地,可以“填补粮食的不够”,他自己又会编靰鞡鞋,怎么会“穷”得连裤子都没有呢?可能周立波自己也觉得,让赵玉林“穷”得实在有点离谱,还不足以“真实”地揭示“元茂屯”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所以他便决定“穷”不够便用“惨”来凑,让郭全海、老田头、李铁匠、小猪倌、张寡妇等“精贫”农民接连登场,并通过他们各自家庭的血泪控诉,从不同的角度去表现东北农民说不尽的“悲苦”。比如,郭全海的父亲被韩老六活活地气死,老田头被韩老六霸占了房产,小猪倌的母亲被韩老六卖到了窑子里,张寡妇被韩老六害得家破人亡。“惨”得最不可思议的,则是那位李铁匠,他身强力壮且有着一副好手艺,却做了14年的“跑腿子”,“身上常常穿不上衣裳,十冬腊月常常盖不上被子”,混得甚至连赵玉林都不如。“元茂屯”里的那种“穷”和“惨”,至少我们在萧红和萧军的作品中是看不到的。
周立波以赵玉林为核心人物,竭力去描写“元茂屯”农民的“穷”和“惨”,其真实目的就是要唤起农民的阶级觉悟,进而去阐释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但无论是赵玉林还是郭全海,他们都不具有东北农民的典型意义。在《暴风骤雨》里,周立波曾向读者透露过一个重要信息:“元茂屯”里的绝大多数农民,几乎都是“闯关东”的山东农民(比如赵玉林是1931年,白玉山是1938年),由于他并不了解“闯关东”的历史背景,因此也就不可能去真实地表现东北农村的复杂关系。东北地区大部分都是山东移民,从1911年到1949年,仅山东人“闯关东”就有1836万26。导致山东人“闯关东”的主要原因,除山东地少人多之外,则是东北地方政府不断地“放荒”。比如1925年,东北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山东移民到东北垦荒,不仅给予垦荒者以半价车票的优惠,而且还对“移民随带之农具,均予一律免收车费”。到了1930年,更是颁布了《黑龙江省腹地各县民荒抢垦章程》等法律文件,明文规定“凡属官荒,任令难民自由垦殖,限期升科纳租”27。早期“闯关东”的山东农民,正是通过垦荒率先完成了从土地到财富的原始积累(《暴风骤雨》里就曾提到韩老六祖上给他留下了100多垧垦荒地);而“九一八”事变后“闯关东”的山东农民,像赵玉林、白玉山等人当然还处于解决温饱的初级阶段——他们既没有土地也没有生产资料和工具,只能靠替别人种地打工去自谋生路,当然还谈不上去积累财富。另外,山东农民“闯关东”基本上都是采取投亲靠友的方式,“如果移民缺少这些社会关系,要想到一地落脚扎根,那是很困难的”。比如有人就回忆说,到东北仅“两年我家就开垦了两垧地。头一年是借粮吃,收了粮食再还。好在邻居大都是山东老乡,都乐意相助”28。而在《暴风骤雨》里,“整个元茂屯的社会关系很‘简单——就是简单的暴力关系暴力统治与被统治、财产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不存在宗法性质”29。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周立波把“元茂屯”的社会关系,只赋予了一种“亲不亲、阶级分”的政治属性;而“乡亲”与“宗亲”等众多人性因素,全都被作者剔除得一干二净。
另外,东北土改工作队还做过深入调查,以打工为主的农村“劳金”(长工),并不像《暴风骤雨》所描写的那样苦不堪言,一般的长工家庭“大部分够吃”,而“短工工资很低,一般的每天五十元,但小米一斗就一百二三十元——一般的两天赚一斗小米”30。这充分说明,无论“长工”还是“短工”,只要他们“做工”,就能够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至于那些农村里的所谓贫困户,很多都是不劳而获的“懒人”,比如佳木斯地区的柳树屯,全屯一共有50多户穷人,其中30多户不是“吸过鸦片”便是“好吃懒做”,故剩下的那20余户贫农,坚决反对他们参加农会和分配土地31。这曾使土改工作队感到非常棘手,真正拥护“平分土地”的“积极分子”,“从成分上看,有的是劳而不苦,中农以上的成分;从出身上看,有的是苦而不劳,流氓,地痞,扎吗啡,吃大烟”32。这种人在桦县“三个区三百十九名积极分子中,竟占了二百零三名,达百分之六十三以上”33。这充分说明,东北农民贫穷的原因是多样性的,阶级矛盾与阶级压迫当然存在,但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因素。
三
韩老六这一艺术形象,也只是一个政治符号,周立波在他的身上,赋予了地主阶级的全部特征。周立波说元宝镇上其实并没有韩老六这样的人物,“我所写的韩老六是别的富屯的典型”。但“借”来的韩老六,毕竟不是真实的韩老六,为了能够使这一人物站住脚,周立波给出了这样一个理由:“东北土地十分集中,大地主极多,往往超过一千垧。”因此根据“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革命道理,他当然可以按照艺术典型化的创作原则,去合情合理地虚构这一人物了34。在《暴风骤雨》中,周立波这样写道:“韩大棒子韩凤岐,伪满乍一成立时,是中等人家。往后,他猛然发家了。”在“江北置一千垧地,宾县有二百来垧,本屯有百十来垧”。这就等于是在暗示读者,原来韩老六家祖上传下来的一百多垧地是合法的,其他一千多垧地都是在日伪统治时期掠夺来的,平均一年就掠地近百垧,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天文数字。
韩老六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发家暴富?周立波告诉读者,那是因为有日本人为他撑腰:日本宪兵队长森田就住在韩家,韩老六为他提供吃喝玩乐,森田则为他提供武装保护;贫苦农民稍有反抗,便由森田出头去进行镇压,“搁枪崩掉的人,本屯就有好几个”。我个人对此存有很大的疑问:森田作为日本宪兵队长,不在城里抓捕抗日分子,成天无所事事地待在韩老六家里花天酒地,任务就是为了保护中国农村的一个地主,像这种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和可信度呢?周立波还为韩老六罗织了八宗罪:一、他勾结日伪政权,欺压百姓、抢夺农民的土地和财产;二、他亲自带领日本鬼子,杀害过9名抗联干部;三、“八一五”以后,他又当过国民党“中央先遣军”的参谋长;四、他利用手中的权势,残害过屯里的17名农民;五、“他家派官工,家家都摊到”;六、“他家租粮重”,租种者全都倾家荡产;七、“他家雇劳金,从来不给钱”;八、糟蹋良家妇女,玩够了就卖到窑子里(比如小猪倌的母亲、张寡妇的儿媳)。仅从这八宗罪来看,韩老六要比黄世仁更“坏”。
杜善人是“元茂屯”里的另外一个大地主,同时也是《暴风骤雨》下部主要的斗争对象。如果说韩老六是反映地主阶级的凶狠残忍,那么杜善人则是反映地主阶级的巧取豪夺。在斗争杜善人的大会上,萧祥让黑大叔给大家算了这样一笔账:他每年雇30个劳金,从每个劳金身上“剥削十石粮食”,“三十年,不算利息,光血本,他欠穷人九千石粮食”。至于这一数字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周立波本人却并没有交代,他只是告诉读者,杜善人用剥削农民的不义之财,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院子里每天都是“猪肉香,鸡肉味”,“白面饺子白花花地漂满一大锅”。另外,土改工作队员和贫苦农民还从他家里起出了30多口大箱子和麻袋,里面装着“一丈一丈的绸子,一包一包的缎子,还有哔叽、大绒、华达呢、貂子皮、狐狸皮、水獭帽,都成箱成袋”,仅“士林布”就有“一千来尺”。周立波对杜善人的集中揭“富”,客观上弥补了《暴风骤雨》上部的一大缺憾,即:只注重去描写韩老六的“坏”和“狠”,在经济方面却算账不够。所以,杜善人作为韩老六的形象补充,既可以揭露地主阶级的反动面目,又可以表现地主阶级的贪婪本性。不过,杜善人这一地主形象同样令人生疑。因为地主的本质其实就是占有较多土地和财富的农民,而农民的人格特征则是崇尚节俭绝不铺张(《红旗谱》里的老地主冯兰池就是一个例子)。实际上,杜善人就是周立波自己的主观想象,与现实生活并不发生直接关系。作为一个农村地主,杜善人不囤粮食却囤绫罗绸缎,他又不是开绸缎庄的商人,要那么多绫罗绸缎干什么用呢?恐怕只有一种解释,周立波是在以这种“炫富”式的地主描写,去刻意表现东北农村中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但最终却适得其反,既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也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
在《暴风骤雨》的开篇,周立波曾交代说:韩老六、杜善人和唐抓子,“并称为元茂屯的三大户——他们三家都有一千垧以上的好地”。我专门去查阅了一下东北地区的土改文献,发现周立波所说的并不是事实,除了少数伪满大官僚占有土地可达千垧以上,真正以土地为生的农村地主,根本不可能拥有那么多土地。比如,松江省哈东地区最大的地主李凤悟,占地也只有500垧35,而嫩江省通肯县的大地主陈万顺,“素日依靠一百五十垧土地剥削农民”36,都没有达到周立波所说的“千垧以上”。更令人称奇的是,周立波甚至自己也搞不清楚,“元茂屯”这三家地主究竟有多少土地。前面交代说,韩、杜、唐三家有地都在“千垧以上”,可是到了后面,赵玉林却说韩老六家里有地“二百来垧”。如果说韩老六等在“外地”還有千垧土地,那么周立波为什么不交代这些土地的最终去向呢?而“元茂屯”农民从唐抓子那里,也只分到了“一百二十垧地”。像这种极其混乱的叙事现象,在《暴风骤雨》中还有很多。最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是周立波借白玉山之口,对地主剥削本质的一段阐释:他认为农民租种的土地虽然属于地主,但这些“土地也是穷人开荒斩草,开辟出来的,地主细皮嫩肉,干占着土地。咱们分地,是土地还家,就是这道理”。这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逻辑,即地主的土地全都是来自于“剥削”。周立波不仅彻底否定了地主获得土地的合法途径,同时还彻底否定了农村以土地出租去获取利益的正当行为。如果完全否定了地主通过劳动发家致富的可能性,那么“生产发财、四季发财、贫者变富、富者更富”的土改口号37,也就变得自相矛盾令人难以理解了。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往往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去看待他们同地主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租佃双方,并不是阶级对立,而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关系:“我年年给人家扛活,人家不惹我,我也不得罪人,得到劳金钱就回家过年,也没有人欠我的。”故谈不上是什么剥削和压迫,无非就是一种平等的价值交换38。在东北农民的情感世界里,他们最痛恨的还不是地主,而是那些打家劫舍的“胡子”:“纯粹是一些土匪,只要你种地,不论是谁,都要钱——辛辛苦苦十多年并未积攒下多少钱。”39即便是“积了几个钱,可是当自己从关外回关里时,路上碰见劫道的,钱都被抢去了”40。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描写的正是这一历史时期东北农民与土匪之间的深刻矛盾,而不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
四
《暴风骤雨》虽然并不具有历史认知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但它的政治意义和宣传效应却不能低估。因为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与东北解放战争同步进行的,周立波深知东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不仅“是决定我们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事关中国未来命运的一场大决战41;如果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他们迅速地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那么就不可能使人民军队在粮食和兵源方面得到有效的保障,共产党人也很难在东北地区站稳脚跟。故他在《暴风骤雨》里,把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描写成是一种革命与农民之间的利益交换,就像西方学者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分配给贫下中农,农民就更有动力支持地方民兵和人民解放军。”42所以这是“该党历史上许多时期获得大众支持和吸引人们加入革命的一个根源”43。故《暴风骤雨》的创作主题,并非是在表现“建构新的社会秩序”44,或描写“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45;而是在营造一种从“拯救”到“报恩”的叙事模式,目的就是要去敦促广大农民应心怀感恩、知恩图报,自觉地融入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洪流中,并成为共产党人最忠实的同志和朋友。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就等于没有读懂《暴风骤雨》的思想灵魂。
“拯救”在《暴风骤雨》中,被周立波分解为三个步骤:首先是“解放”,即在萧祥和工作队员的带领下,“元茂屯”的贫苦农民斗倒了恶霸地主,从政治上获得了翻身;其次是“给予”,即土改使农民分到了土地、房屋、牛马和财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愿望,从经济上也获得了翻身;再者是“感恩”,即得到实惠的“元茂屯”农民,纷纷表示“共产党,民主联军是咱们的大恩人”,“过好日子,可不能忘本啊,喝水不能忘挖井人”,“就是有人用刀拉我的脖子,也要跟共产党跟到底”。《暴风骤雨》的上部,仅仅用了短短的两个月时间,便彻底解决了中国农村贫富不均的阶级矛盾,并使“元茂屯”农民具有了革命现代性的坚定信念,这当然只是周立波本人的一种乐观想象。但他却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农民之所以为农民,就因为他们是农民,几千年来所形成的自私、保守等小农意识,绝不可能弹指一挥间便消失得一干二净。作家舒群就曾对此批评说:周立波“对于生活的体验不够,理解得不深”,以至于他对农民思想变化的描写过程,“简单得如同一条直线”46。这真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因为“简单得如同一条直线”,正是《暴风骤雨》最致命的一大缺陷。整部《暴风骤雨》给人的直观印象,就是农民思想改造的儿戏化:仅仅两个月时间,赵玉林便完成了世界观改造变成了中共预备党员,并自觉地接受了“一人为大伙,大伙为一人”的共产主义理想;郭全海在“分马”时更是高风亮节,自己留下那匹“热毛子马”而把“青骒马”让给老王太太。还有比这更为神奇的地方,比如在《暴风骤雨》的下部,已经晋升为县委书记的萧祥,竟然说他想把还在预备期里的郭全海,尽快地培养成区委书记,这简直是令人目瞪口呆、大跌眼镜。但周立波本人并不认为这样描写有什么不妥,他说中国农民是具有阶级觉悟的,只要通过思想教育把这种“觉悟”激发出来,使他们“认识了共产主义的真理,成为共产党员,就会坚决地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斗争到底,必要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47。这就是周立波的政治眼光。
革命对于农民的“拯救”,当然需要他们做出“回报”。比如在整部《暴风骤雨》中,一直都回荡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革命歌曲,目的就是要提醒“元茂屯”的贫苦农民,“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不能只是“感恩”,更是要去“报恩”。到了《暴風骤雨》的下部,“报恩”细节更是不断地闪现,像刘德山和李大个子等农民自觉地去“支前”,白玉山大谈农民参与这场革命战争的政治意义——“一切为前线,不为前线,‘二满洲整不垮台,还有你穷棒子娶媳妇的份?”周立波正是通过这种引导方式,让萧祥第三次出现在“元茂屯”时,便向农民提出了“报恩”的切实要求:动员青年农民积极参军。只不过令他没有想到,开了三天的大会小会,主动报名者却寥寥无几。仅就这一点而言,周立波并没有违背历史真实。因为1948年,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同时进行,客观上需要补充大量的兵源,但各解放区的逃“兵”现象却十分严重。在华北解放区,有许多青年农民就公开说:“你不是说俺分了地,不参军就是没良心吗,俺情愿不要地,俺也不参军。”48东北解放区的情况更不容乐观,“行政命令和摊派现象比民主动员的成分重——发生送到前线的士兵、民夫,逃跑、怠工等不良现象”49。逃“兵”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仅以东北地区为例,八路军1945年9月出关时,只有10万多人,可是到了1948年底,第四野战军已经发展到了120万人,其快速增长的部分,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东北地区的青壮年农民。土改的确使农民分得了土地,可是青壮年都去当兵了,许多土地“撂荒”没有人耕种,却仍要按土地的占有量去征收公粮。比如,淮海地区农民“公粮负担重,平均占农民总收入五分之三”,可青壮年多去参军和支前了,故导致“很多的地,都荒着”50。东北地区的农民负担,恐怕并不比淮海地区轻。李富春在财经大会上放言,东北土地肥沃,“单就北满来说,就等于陕甘宁边区的二十一倍的收获”。所以“我们要负担起比老解放区更大的任务”,“支援全国日益扩大的解放战争”51。这就意味着土改以后的东北农民,必将要对全国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牺牲。仅以安东省为例,1946年农业人口才200多万,就要上缴公粮“三万万斤”,同时还要上缴6000万斤草和3亿斤柴52。这个数字不可谓不大。因为“东北每户平均只有1.2个劳动力”,而这一年安东省就有32717名青壮年农民参军,“使劳动力更为缺乏——更增加了生产的困难”53。
中共中央当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1948年7月专门下达指示说:“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今后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你们及各军对此应有精神准备。”54中央从大局出发体恤民情,但周立波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土改受益后的逃“兵”行为,其实就是农民忘恩负义的一种表现。因此,他首先是让郭全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去进行深刻地自我反思:“忘了你是共产党员了?家也不能舍,才娶了亲,就忘了本?”然后再让“元茂屯”的贫苦农民,在思想上达成了一致的共识:“这天下是咱们贫雇中农的天下,还得叫咱们贫雇中农保——要是反动派再杀回来,咱们怎么办?”经过这样一番巧妙的艺术结构,《暴风骤雨》的“报恩”叙事,便从革命对于农民的主观要求,转变成了农民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咱们翻身了,南边的穷人还没有翻身,光咱们好,忘了人还掉在火坑里,那是不行的”。所以,《暴风骤雨》的故事结尾,还是由老孙头套上马车,拉着郭全海等41名参军青年,离开“元茂屯”去往前线。如果说老孙头开篇拉来的是“拯救”,那么他在结局送走的就是“报恩”,这种农民与革命的双赢结局,无疑是周立波本人所希望看到的一种效果。
读罢《暴风骤雨》,我不禁想起了东北作家萧军,他当时就生活在北满地区,受报纸关于土改宣传的影响和触动,也曾萌生过要去创作一部土改小说的强烈念头,甚至还拟好了这样一份创作大纲:“由光复、分地、参军等写起。”可是当他下到龙江县去参加土改运动以后,目睹了农民对于土改运动的冷漠态度,看到有些土改干部的野蛮作风,他突然发现土改“并不如报纸上所说的那般美丽”。于是,他果断终止了原先那种不切实际的幼稚想法55。萧军还对《暴风骤雨》等反映东北土改的文学作品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说那都是“平塌塌一堆垃圾”56。我个人认为,这话虽然有点过火,却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注释】
①1746《〈暴风骤雨〉座谈会记录摘要》,载李华盛、胡光凡编《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周立波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第258、259、259页。
②可参见黄科安:《重构新的社会秩序与意识形态的修辞立场——关于周立波〈暴风骤雨〉的一种解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张均:《小说〈暴风骤雨〉的史实考释》,《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
③⑤周立波:《〈暴风骤雨〉是怎样写的?》,载《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第316、317页。
④⑥41周立波《〈暴风骤雨〉的写作经过》,载《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514、516、513页。
⑦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126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78页。
⑨《中共辽东分局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载《中共中央东北局辽东分局档案文件汇集(1946—1948年)》,辽宁省档案馆,1986,内部发行,第145页。
⑩25张均:《小说〈暴风骤雨〉的史实考释》,《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
11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350、2914页。
12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尚志市政协合编:《哈尔滨文史资料第26辑: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哈尔滨科学印刷厂,2004,内部发行,第4-5、15、56页。
13中共绥滨县委党史办:《松黑三角洲上的风暴——记绥滨县土改运动》,载中共佳木斯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合江土改》,1988,内部发行,第213页。
14白如海:《回忆萝北土改运动》,载《合江土改》,第143页。
15《财神岗村深入土地斗争工作过程》,载黑龙江省档案馆编《土地改革运动(下)》,1983,内部发行,第102页。
16《关于东北剿匪的工作报告》(东北局1947年4月10日),载《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42-43页。
18《双城县委关于群众工作报告》,载《土地改革运动(下)》,第31页。
19孙英:《在宝清土改运动的日子里》,载《合江土改》,第123页。
20中共桦川县委员会:《扫除封建势力,实现土地还家——桦川县土改运动》,载《合江土改》,第184页。
21周立波:《选择》,载《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第50页。
22周立波《现在想到的几点——〈暴风骤雨〉下卷的创作情形》,载《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248页。
2334周立波:《深入生活,繁荣创作》,载《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406、403页。
24周立波:《关于写作》,载《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第565页。
262839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第20-49、125、125页。
27于春英、衣保中:《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1860—1945)》,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第80-82页。
29袁红涛:《“真实”的“改写”与“新中国”想象——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叙事意识》,《学术探索》2011年第1期。
30《庆安县大罗镇村发动群众工作总结》,载《土地改革运动(下)》,第11页。
31李岳鹏:《忆柳树岛上的土改斗争》,载《合江土改》,第171页。
32《哈北地区煮“夹生饭”的点滴经验》,载《土地改革运动(下)》,第121页。
33《桦川县五个月工作总结》,载《土地改革运动(下)》,第53页。
35邹问轩:《关于群众斗争中对待工商业的几个问题的调查》,载《土地改革运动(下)》,第284页。
36丁秀:《通肯县挖穷根斗财宝经验》,载《土地改革运动(下)》,第143页。
37王首道:《目前财经工作的方针与任务》,载《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5页。
3840李云峰、章力:《汤原太平川的巩固工作》,载《合江土改》,第73、74页。
42[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對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313-314页。
43[美]詹姆斯·R.汤森、布莱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12页。
44黄科安:《重构新的社会秩序与意识形态的修辞立场——关于周立波〈暴风骤雨〉的一种解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45刘云:《土改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重读〈暴风骤雨〉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
47周立波:《谈思想感情的变化》,载《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381-382页。
48冀南七分区参委会:《参军通报4》(1947年3月29日),河北省档案馆藏,编号28-1-42-1。
49哈尔滨市档案馆:《哈尔滨市支援前线1946—1949》,1985内部发行版,第60-61页。
50滕代远:《滕代远关于群众战勤负担情况的报告》,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267页。
51李富春:《在财经会议的报告与总结(1947年8月)》,载《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55-57页。
52《中共辽(安)东省委关于征收一九四六年度公粮的决定》,载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满分局、辽(安)东省委档案文件汇集》,1986,内部发行,第208页。
53朱建华:《东北解放战争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120、131页。
54《中央关于兵源补充问题的指示(1948年7月7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八)》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250页。
5556见《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第64-84、333页。
(宋剑华,暨南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文学伦理叙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AZW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