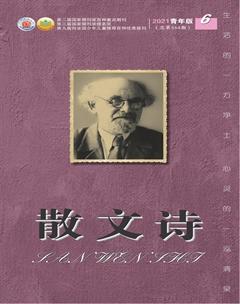他是他所不是的那个人
2021-08-09 06:09
散文诗(青年版) 2021年6期
阿隆索·吉哈達是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吗?可怜的乡绅是荒唐的骑士吗?或者,更究竟些,一个人何以是他自己?
问题在答案的阴影中漫漶如蔽——典型之一是,关于铜盘是不是头盔的本体论争议,经由无记名表决的民主方式获得了一个毋庸置疑的答案:铜盘即是头盔。依此类推,我即是非我,爱即是不爱。如此撕裂与悖谬,正是现代性的原初形态。
作为一种被精心选择的结果,现代性貌似偶然、实则必然地释放着前所未有的噪音,以至于最后它不得不堂而皇之地成为一切审美的窄门、一切话语的背景、一切存在的基础。这一粗暴的奠基式翻转对于古典悲剧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悲剧因此而喜剧化,荒诞因此而本体化——阿隆索·吉哈达脸上的悲哀正是我们的喜剧,而我们脸上的悲哀则是人类的荒诞剧。
悲剧因失去了意志的帮扶而空核化,现实却因获得了虚无的加持而因循往复;精神降格为聪明,思想趋近于缄默。噪音(无论它是官僚体系还是消费狂欢,抑或其他)以其不可阻挡的普遍性和经久性从一种恶转化为一种需求,曾经动辄就能挑动人们敏感神经的,如今不仅是一种习惯,也成为一种必要。这就是我们时代被历史强行赠予的、唯一的真相。
毕竟,历史经由现实业已被彻底重构了—— 一道帷幕的落下伴随着另一道帷幕的升起;而一个人只有在永恒的失落和撕裂中才能完好如初。
猜你喜欢
智能建筑与工程机械(2019年4期)2019-09-10
汽车博览(2018年9期)2018-09-04
汽车博览(2018年9期)2018-09-04
环球时报(2018-08-16)2018-08-16
商情(2018年12期)2018-06-03
智族GQ(2018年9期)2018-05-14
世界家苑(2017年7期)2017-08-27
户外探险(2017年3期)2017-03-11
环球时报(2017-03-10)2017-03-10
小学生导刊(低年级)(2016年8期)2016-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