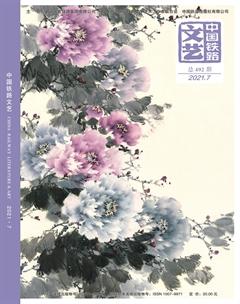铁路旁边的村庄
烟驿
铁路遍布在大地上,把每一个村庄串联起来,寂静的春夏秋冬被经济的原动力激荡出火花。流动,带来活跃的思路。时间的苍茫里,村庄与行人摸索着行进,那里有一条路,我们看到过,又似乎没有看到,村庄在火车的呼啸中演绎着各自的悲欢。
芝兰庄
出姚哥庄,沿胶济铁路斜插向东南。三伏天,庄稼满坡葱绿。路是水泥路,不宽,若是对面两车交会,要各自贴到路边。前行大约三公里,穿过一座高速路涵洞,道路已经完全成为东西方向,村庄出现在铁路南侧。
村头一棵垂柳,在大路边迎送进出村庄的人。一百多年的老火车站,已经不再使用。济南铁路段的工人却在此坚守,做着养护工作。村庄在车站南侧几十米外,百年来,与这条铁路纠缠不清。
1899年,德军借“巨野教案”入侵山东。为便于掠夺,把物资输送到青岛海港,决定在山东修建铁路,实现他“筑路圈地”的侵略阴谋。清朝老百姓在几百年的闭关锁国中,尚不知大洋彼岸现代工业已经如火如荼。侵略者强行在百姓土地上修铁路,欺辱霸占,破坏村民生存环境,阻断泄洪河道,受到生存威胁的老百姓热血沸腾,奋起反抗。高密的抗德筑路事件,就从芝兰庄拔标开始。芝兰庄自古既有尚武之风。乾隆四十八年武举人戴清乾曾得御赐“武魁”大匾,村北他骑马射箭的“马趟子”至今留有传说。抗德筑路事件中血流漂橹的民众,把一股倔强不受欺辱的血气灌入这片土地。我站在一百多年后的这一片宁静祥和的土地上,看着火车轰隆隆地从铁路上驶过。路边的向日葵慢慢低下头,吞噬雨水、阳光,膨胀延续后代的籽实。时光是新的,也是古老的。它修筑著万物轮回的路,在沉默中,有着永无宁日的骚动与喧哗。未来是一只灰色飞雁,穿过当下,藏起平静下的风暴。
我调转车头沿大街向村庄驶去。与普通村庄相比,芝兰庄更像是一座城镇。路两边是家庭式工厂,一家一家毗连,门前种植花草果木,不时有大货车开过去。我在一户大门前看到一块蓝色门牌,西后芝兰村。与门前带着孙子玩耍的老人攀谈。他说,芝兰庄有五个行政村,东后芝兰、西后芝兰、芝兰一、芝兰二、芝兰三。村庄原本是一个自然村,村内住户彼此混杂,本村人都分不清哪些人是哪一个村的。说到村庄内成片的工厂,他笑着说:“芝兰庄靠近铁路,交通便利,会做买卖,这几十年大多做劳保产品,全国各地都有,还销往海外。”芝兰庄商路宽广,是不是与铁路火车站有关?每一个流动的地方,民众思想也活跃开化。
我来之前约好三村书记冷壮。按照他遥控指挥的路线行走,因为对方向不敏感,我不确定自己走的路是否正确,在水湾旁边的十字路口再次停下车问路。路边有一块标志牌,上面写着回车岭。我想起听说过的典故,战国时,孔夫子巡游列国,某日路过这里,见几个小孩在路中间用石子土块垒城,他的弟子吆喝他们躲开。其中一个眉清目秀、聪颖伶俐的娃站起来,望着马车上的一干陌生人理直气壮地责问:“只能车给城让路,哪里有城给车让路的道理?”孔老夫子随调转车头,说了一句:“好一个小子拦村。”
小子拦村是不是真有其事,在历史的浩渺中,民间传说的真实性并不重要,我倒愿意相信,芝兰庄曾经有过这样一群天真可爱、不畏不惧的孩子。我站在当年夫子回车碾压出的岭上,微笑着,看经典中辩日的小儿,又在这里留下震响千古的城车之论,不禁喜欢上村人可爱的一面。关于村名的起源,另一则记载更真实一点。相传明初,肖姓先祖从山西迁来立新村,把“小子拦村”改为“肖紫兰庄”,后来,清末德国侵略者修胶济铁路,把“紫兰”翻译成“芝兰”,就错改为“芝兰庄”沿用下来。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对植物有着天性的亲近。特别是古树名木,总是我进入村庄要寻访的目标之一。回车岭有一棵高大的柳树,树干要三四人合抱,枝干茂盛,笼罩在一片墓地之上。我想起铁路北冷氏墓地那棵神奇的柘树,在平原地区,柘树成材很少见到,而生长三百多年,历经战火却没有遭遇毁灭,也是一大造化。村庄内还有两棵古槐,我不知道今天是否有缘遇见。
过回车岭继续南行。路西是田野、庄稼、果园、菜园,呈现盛夏的茂盛。一个推着独轮车的老农,从田间小路走出来,看到我在拍照,笑着招呼道:“吃桃子吧,真正的水蜜桃。”他六七十岁年纪,黝黑干瘦,脖子上搭着一条蓝毛巾,黄球鞋沾着泥巴,车子上放着两筐新鲜桃子,有着说不出的朴素与生动。我抱着相机,从筐中拿出一只鲜红的桃子,轻轻剥去皮,猛吸一口,一股纯正甘甜的桃子味道,沿着记忆迅速回到八十年代的小时候。心底莫名出现一阵柔软的感动,很多远去的人和事,跟着桃子的味道跑了回来。我望向小路蜿蜒的深处,几棵没有砍伐的老桃树遮掩在菜园中,不难看出主人对桃园的偏爱,没有全部砍伐。
阳光已经躲入云层,我终于看到冷壮描述的围着蓝白色矮栅栏的村子。芝兰三村是五个村中最大的,在整个村落西侧最南部,约呈正方形。房屋规划整齐,路边栽植着花草垂柳,工厂明显少于后边的村子。大街宽阔,沿街两侧用统一色彩的栅栏围起,整洁美观。我在村委所在地,也是芝兰庄社区所在地停车。一群人在门前修线路,联通公司的机线员爬到了水泥线杆顶端,我随口问:“怎么回事?”冷书记说宽带坏了,一个信息时代,没有网络非常不方便。云层变厚,淅淅沥沥的雨开始落下。我们在办公室泡上一杯绿茶,聊芝兰庄的过去与现在。他轻言慢语,从传说到历史再到现在,一件件,一层层娓娓道来。
我对村庄的描述,必须是村庄的每一个角落仔细走一遍,用我自己的眼与心去辨识去认知,才能形成文字。也许它是片面的,单薄的,但却是我眼见的真实。我说起村庄那棵老柘树,冷书记让刚好走进来的冷氏后人带我去观看。天阴得更沉了。我们驱车穿过一村、二村,一直抵达铁路北侧一大片空旷场地。
因为前两天的大雨,道路有些泥泞。两边茂密的芦苇,说明这里曾是一片湿洼荒滩。向前走,一排几十米高的本地杨生长在铁路边上。不远处一堆层层郁郁的绿树,以中间最高点为中心,向四周覆盖,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老柘树。柘树又叫黄桑,属于桑科,多生长在阳光充足的荒野,百年以上的大树极为罕有,有“南檀北柘”之说,现今凡五十年以上的树木都属于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柘树枝叶具有药用价值,《本草拾遗》中记载:味甘,温,无毒,入肝脾二经。在《诗经》中亦有记载。
我穿过层层荒草,进入树丛内,近距离观察这棵有着无数传说的古树。它枝叶繁茂,周围分生出无数大大小小的树子树孙。突然想起这棵桑柘古木与我尚有些渊源,它所守护的冷氏祖先,亦是我祖母的先人,我儿子身上也流着冷氏六分之一的血脉,莫名产生一份亲切,人就是一种奇怪动物,在血缘中,有着永远不可磨灭的血脉宗亲。我一直想来这里看看,是不是冥冥中真有看不见的力量指引我们的某些选择?
一列火车从身边跑过去,远处的田野与云层连接在一起。回身看铁路南侧的村庄,绿树覆盖下,高耸的烟囱像天空的支柱。我想到路,这纵横交错,看得见、看不见的路,它们都通向了哪里呢?它们是来路还是去路呢?心灵与肉体在尘世间行走,万物是否都是殊途同归?
北李家庄
北李家庄在大牟家镇西六公里处,四面环水。村南村北各一条土路向东延伸,通到周蔡路。初春,万物尚在半睡半醒的昏昧状态,土地虽无绿色,但是已经绵软。杨树、槐树板着面孔萧瑟、肃穆,柳树却是枝芽泛绿,一支春天的序曲喷薄欲出。
沿村庄南侧东西路入村,两侧是干涸且布满枯草碎屑的深沟,贴近村庄东南角,一个存水小池塘,四只麻鸭在“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句里嬉戏。停下拍照,西岸整土栽树的大叔走过来,笑着寒暄,我问起小村居民人数。他想了想说:“年轻人很多都去城里或镇上居住了,如果算房子,应该有四十多户吧。”
他家的房屋独立于村庄外,在大路南侧,宽阔的院子沒有院墙,西侧一排简易养殖大棚,已经废弃不用。南侧一个露天木材加工厂地,堆着不少收购的本地生软木。院子东侧是一个伸入水塘的小园子,种植果树与菜蔬。五间房屋除了北面依着大路,其余三面环水,东侧是池塘,南侧是鱼池河,虽然已经无水,河道也变成一条窄小的土沟,但是站在小河道南侧麦地里向西望,五六十米外的堤坝上长着一溜大白杨,显示出这儿曾经确实是条大河。
我问女主人为什么叫鱼池河,她说:“这河奇怪,无论干旱多少年,只要有水就有鱼。”我突然记起,沿河向西一里左右就是新胶莱河,鱼池河应当是通到那里。
西侧向北的河沟,贴着村庄流过去,沿居民房又向东,在村东复绕向南,形成四面环水的天然护村河。兵荒马乱的年月,村庄为防流寇兵匪,修建土围子,而这里却有天然护村河。只可惜,在村庄沉痛的记忆中,1939年春天,日军入村杀人放火,毁掉房屋一百八十多间,失去房屋的村民无力重建,只好下了关东流落异乡。此后,村庄住户一直没有超过五十户。
沿着村中大街向北,几棵大榆树吸引了我的注意,它们在一座住户门前,贴街东侧耸立,树龄在四五十年左右,树干有一抱多粗,北侧三棵挨靠一起,南侧一棵则独自耸立,站在村庄里俯视着四季风景中不远处的田野,想象飞鸟间的秘密以及护村河里游鱼的梦想。它们是不是都洞若观火,一一印记于心。我仰头望着树枝间密密麻麻等待吐露的苞芽,猜想阳春三月,对着春风招手,一串串翠绿色榆钱,整个村庄都沉醉在榆树黏稠的气味中。放学归来的顽童,把书包扔在树下,抱着树干噌噌爬上树采摘榆钱,母亲的喝骂、父亲的巴掌,早抛到九霄云外。
日子是琐碎的,也是真实的。三四十户的村庄,有十几个姓氏,每个家族都是一个小团体,古老的血脉关系根深蒂固,形成特殊的社会结构。这些即独立又彼此联系的小团体,居住在同一村落,形成一个大群体。无论走到哪里,一句“亲不亲故乡人”就能把彼此的情感拉近,若是同村人相逢于异乡,更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了。乡土文化在农耕为主要模式的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传承。共同处境与共同担当,使同村人的关系复杂又微妙。
除却外力侵扰,内部之间的矛盾就会凸显,主要是一些人的狭隘与自私,也可能是过去半封闭状态下,交通与交流都不通畅时的产物。如今,全球都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运转流通,信息共享,已经做到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乡村里一些盘桓久远的封闭、自私、狭隘的小农心态,可能会被渐渐冲淡。
是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影响思想与观念。一个人的观念决定了眼界,而你目之所及就是自己世界的大小。《易经》中有时与位之论,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是成事外因。无论神佛也好,圣贤也罢,能决定一生的,还是取决于性格态度。
从村北最后一排房屋沿河道向东,西北角多是八九十年代修建的房屋,而东北角却有一排废弃不住的泥土房。大齑垒砌的院墙已倒塌,门窗封着,院子里种着越冬韭菜、菠菜。因为避风向阳,韭菜早早发出紫红色嫩芽,木格窗的影子慵懒地斜照在地上,如果不去观望东侧田野里正在施工的大型器械,有种回到简单、安静的年代的感觉。
村庄东侧,高铁已经破土动工,不知道高铁旁边剩余人家是否还在这里居住,睡梦中久居偏僻村庄的村民,能否被火车唤醒去远方的渴望,通过高铁带来与世界接轨的新思想。或者北李家庄这个建于明末的小村子,举村搬迁,在新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
绕村一圈,用了近两小时,边走边想,这些泥土色时间的小鱼,凸立在一个概念中。动静有常,存续于物质世界的规则下,启程或者止步,暗循着一个恪于日月的内因。对于自然发生己所不能逆转的变故,圣人道是顺其自然。顺中蕴含延续的生机。我无意沉陷于那些无穷尽的生存智慧中,一个人穿过自然与人群的风,去走,去看,去想,去感受,把每一刻,融入内心,让睁大眼睛好奇地望着外界的小人儿,跟我一起走过苍茫人寰。
村前一群孩子在追逐嬉戏,春天,阳光与风一样和善。我拍下石头,拍下老树,拍下废弃的旧器具和即将消失的老屋。坐在轮椅上的大婶,目光中含着村庄的淳朴。她说:“是不是像一件旧衣裳?”我有一丝惊讶,如此确切的比喻呢。村庄静卧在初春的简朴中,确实像一件留有体温的旧衣裳,高铁,将给她印上一条时代的花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