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槎
灼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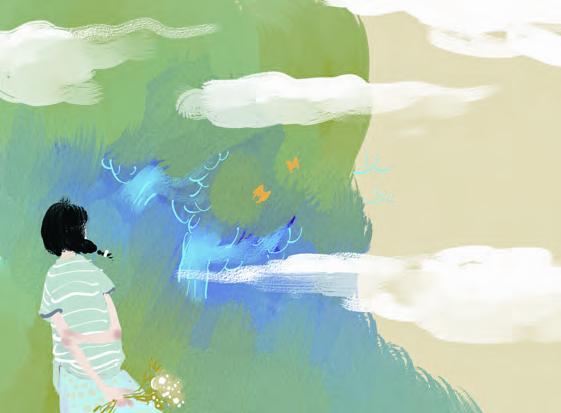
1
文科班有男生7名,女生39名。凭借一米七四的出众身高,我成功被分配到了男生聚集区。
张陆棋,男,担任本人同桌从高二至高中毕业——你问他长什么样?
他估计和我差不多高……长得吧,呃,就那样。
高二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一定要痛改前非、好好学习。在这股热情的引领下,我不仅和同桌张陆棋,还和前桌的李扬帆、冯雨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所谓革命友谊,即一起吃饭,一起讨论题目,一起痛斥年级优秀作文云云。
其实,就末一项而言,我是不太热衷的:都是出来混分的,人與人之间应该多点宽容和理解。但张陆棋却不以为然,并时常大放厥词。
张陆棋这样做也是有底气的:他作文写得好,好到能上年级优秀作文,但老师不舍得让他上——怕被别班坏心的同学抄了去,故而仅供本班专享。
一次作文,主题大约是“物各有性”。张陆棋对一篇高分作文很是不满。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先深情背诵了文中引用的一小段《偶然》,然后嫌“俗”。他说,这种故事写得最有味道的,还是《八月槎》。
说是从前天河和大海连成一片,每年八月,都有人乘槎来去。一人抱持奇志,也备好干粮、扎一筏子去了。一路上,他望见日月星辰,茫茫忽忽,不觉昼夜轮转。十几天后,他漂到一处,遥见宫中女子纺织,男子饮牛。后还家,问高人此为何处,高人乃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他一算,发现正是自己到天河的时间……
冯雨一算时间,看了眼手表:“快吃,就剩你一个了。十二点半语文老师来默写。”
张陆棋伸出两根手指,含糊道:“等我两分钟。”
2
高二上学期,我有满腔的学习热情,加之脑子不太笨,因此考得还不错,每次考试稳居年级前三。以至到了高二下学期,我得知自己有望获得P大的校荐名额。
只有一个,但非常有希望。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都震惊了:那可是P大啊,我从没梦想过的学校。虽然本人资质平庸,显然会给学校丢脸……但那可是P大啊!
我的竞争对手是潘果和方可意。她们成绩也好,但没我稳定——每次排名我都记着的。
那时将近期中,我决意加倍努力:考得怎么样其实已经无关紧要,我只是不想让自己后悔。
反正我是这么盘算的。
一天中午,我正在想题目,李扬帆突然说外面有人找我。我一出门,就看见一个圆头圆脑的男生,手里拿着一杯“奶茶三兄弟”——好家伙,还是大杯的。他局促不安,欲言又止。他周围一圈人也挤眉弄眼,欲言又止。
看这情形,就算是傻子也明白了。
一片喧嚣中忽而有点静默。
看来只能我先开口了:“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你、你好,我、这……这岂不是很尴尬……这杯奶茶给你!”
我双手抱胸,深吸一口气:“第一,我不认识你。第二,我不喜欢喝奶茶。所以,你还是找一个喜欢喝奶茶的男生或者女生吧。”
周围一阵哄笑。
我突然很惶恐:我好像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不会留下心理阴影吧——应该不至于。首先,他可能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其次,做这种事可能就是需要百折不挠。最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拒绝他。时间如此紧迫,我一没经验,二没参谋,我自认已经尽力了——啊,我又在给自己找借口了……
表面上我依然双手抱胸,但天知道我已经紧张得双手攥拳了。
他张口结舌,讷讷良久后又被兄弟们簇拥着回去了。
这事大概就这么结了。回教室后,我欲盖弥彰地翻过一页草稿纸,开始在上面画椭圆。“画错了,焦点在y轴上。”张陆棋的声音从天而降。
我想我当时的脸色一定很精彩。
第二天,当张陆棋从课桌洞摸出一盒水果糖时,他的脸色也一样精彩。李扬帆热情地提供了解说:约二十分钟前,一个头很圆的男生,左顾右盼,鬼鬼祟祟,在思索再三后,终于还是把糖放进了张陆棋的桌洞。
我们听完后都在笑,教室里一时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张陆棋还着意钻研了一番糖盒,笑得尤其不怀好意:“啧啧,还是德国货。老实说,这个糖我吃过,还挺好吃的……哎,陈越,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
“呃,要么扔了,要么我们分着吃,要么还给他……”我越说声音越低,神情是显而易见的忧愁——
而另一边的张陆棋未免太高兴了些。
“张陆棋,你比较有经验。遇上这种情况,你觉得怎样比较合适?”
张陆棋瞪大了眼:“我为什么会‘比较有经验?你不要血口喷人!”
他可能是真急了,声音一时有些收不住。
一片喧嚣中忽而有点静默。
“……张陆棋,班主任在看着你。”我悄声说。
张陆棋转而瞪我一眼。
好了,这下班主任也看着我了。
3
这盒糖最终还是托李扬帆还回去了。
事后证明,这个篓子还是李扬帆捅出来的。那个男生是她的小学同学。此人举世之物,咸无所好,唯好听上世纪老歌。好巧不巧,我跟他听歌喜好相类,加之长得比较端正,他因此有了“知音”之许,很想与我交个“朋友”。
其实现在想想,交个朋友也不是不可以。但我那时很不成熟,处理得不太好。
那天,他又把我叫到了教室外面。
我很不耐烦,说:“我很忙,要去做题了。”
他又期期艾艾起来:“那、那岂不是很尴尬……我就耽误你一小会儿。是这样的,我马上要出国了,不会再来了……这个给你!”
我一瞧,是幅画。
“我和朋友熬夜画的,”他有些得意,“我画速写,他画素描……”
我其实大约知道这是什么。按照一贯铁石心肠的原则,我应该像之前还糖一样还给他。
但我还是收下了画。
最后,我对他说“谢谢”,他说“再见”。我们之间的氛围仿佛第一次融洽起来。
回到教室后,冯雨和李扬帆极力要求看一看。我虽然和她们要好,但就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自己应该拒绝她们。
但我还是摊开了画——愣了一下,又很快收起来,说:“就是很普通一幅画,没什么好看的。”
张陆棋意味深长地对我笑。
高二下学期的期中考试,我只考了年级第七。但之后的考试,我没跌出过前五。
可能是期中的问题,也可能是高一时考得一般,名额最终给了潘果。
4
冯雨在本市念书,却是新昌人。高二的暑假,她邀请我们,连同她几个室友一起去新昌玩。我们都拍手称好:马上高三了,将来毕业也各有各的忙处,大抵少有机会能这样好好玩一场。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最终男生还是仅有张陆棋一人。
对此,张陆棋并无多大异议。他本不是扭捏之人,况且在文科班浸淫已久,他早对自己“妇女之友”的身份安之若素。
我们在山上过夜,住两栋小别墅。地势低的那栋设施齐全些,有厨房,也有客厅。冯雨、李扬帆她们打牌的时候,张陆棋剖了个丝丝冒冷气的西瓜,切成好几瓣等人来拿。我不会打牌,玩了会手机又觉没意思,眼神飘忽,不知行到了何处。
“陈越,想吃就来拿,这瓜还挺甜的。”张陆棋豪放地吃着西瓜,一脸笑嘻嘻。
我大人大量,不与他计较,一径捧了片西瓜,凑在水池跟前大快朵颐。这时张陆棋又吆喝起来了,说什么冷气散了的瓜没有灵魂,叫大家这局结束后歇一歇。
于是众人都来吃瓜,满手狼藉的,洗了手后,也再无打牌的兴致。这时,李扬帆提议玩真心话大冒险,大家都说好。冯雨不知从哪找出几听啤酒,又给每人配个塑料杯,想喝的就自己倒。
我们玩了几轮。李扬帆和我正谋划着要问出张陆棋的罗曼史,突然听见有人问我:“到达过人生巅峰吗?如果有的话,稍微形容一下。”
估计是冯雨的室友。
我喝了点酒,控制不住地想笑。我边笑边给自己加酒:“有啊,我现在就处于人生巅峰。你看,我身高一米七四,之前和之后都不会比现在更高了。”
“不对,我还可以穿高跟鞋,还能去爬山……”我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漏洞,想了想又道,“话是这么说,但既然说是‘巅峰,不就是为了‘过去的吗?”
“你这话好有哲理。”大家都捧场地笑笑,又开始下一轮。
李扬帆果然厉害。没过多久,她就如愿以偿问出了张陆棋的情史。这是个悲伤的爱情故事:初中的时候,教张陆棋的数学老师是名师,他每天给学生布置一道思考题,别班同学基本无缘一见。有个女孩子,先和张陆棋表白了,然后又和他说以学业为重。紧接着,她复印了张陆棋的思考题全集,还让他每天把新题发她一份。张陆棋很快觉出不对来,及时结束了这段“恋情”。
“所以还是你甩了别人?”我总结了一下。
“这倒和那个与外国人谈恋爱只为练口语的故事很像。果然艺术源于生活啊!”冯雨啧啧道。
对此,张陆棋表示很无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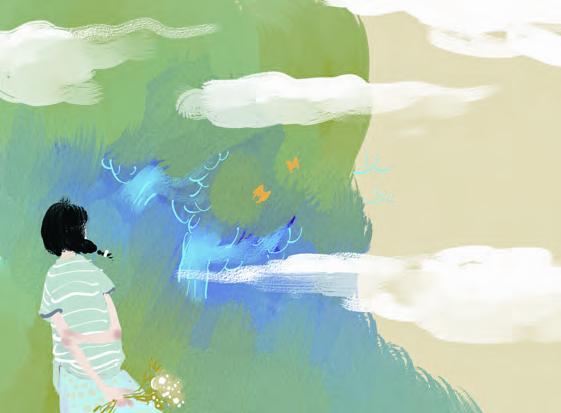
我们又玩了一会儿,渐渐没了兴头。冯雨适时牵头说,今天晚上没云,山上的别墅有望远镜,看星星正好。
众人于是准备上山——说是上山,其实不过多攀几级台阶罢了。
不知为什么,我不太想出去。可能是因为眼镜在包里,我懒得去拿。
张陆棋说要收拾东西,又说一个人收拾不完,让我留下来帮忙。望着桌上桌下的啤酒罐、西瓜皮、瓜子壳,我承认张陆棋说的有理。
大家都走了,张陆棋把易拉罐、一次性杯子挨个放到垃圾袋里。而当我洗了抹布,开始擦桌子时,我突然觉得房子里有点过于安静了。
想起某个圆头男生的名言,我决心说些什么。“张陆棋,你有多高?”我脱口而出。
张陆棋愣了一下,答道:“一米七六还是七七吧……”他仿佛又想到什么,故意曲起腿说:“没你高,没你高,我懂的。”
哦,忘了说了,我一直有个不成器的爱好:和人比身高。和冯雨比,和李扬帆比,当然还和张陆棋比。有时好好走在路上,我突然就踮着脚比起来了。
但今天我没这心情。
我习惯性地应了一声,突然没来由地觉得委屈:“长高是我妈的期望,考好也是,情书或许也是——情书不能算,那是因为我很虚荣,虚荣又残忍……张陆棋,今天大家都很高兴,我却很扫兴,为什么会这样呢?”
张陆棋没见过这场面。他扔了垃圾袋,洗完手想找纸巾,却怎么也找不到,一时手忙脚乱:“陈越,你别哭啊……不是,你想哭就哭出来好了。我虽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每个人都有不开心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
他终于找到纸巾了:“你听我说,考好很重要,但活得开心也很重要。光靠考好是找不到快乐的,它只会把你带到一个更需要努力的地方,你可能会越过越辛苦……”
“陈越,你要自己找点开心的事。你那么聪明,一定能找到的。”
说完,张陆棋笃定地望着我。我抬头看见他的眼神,我知道——他是真那么认为的。
山上虫多。那天半夜,冯雨和李扬帆的卧室进了飞虫,还是我手持拖鞋剿灭了它。
我想我是真的好多了。
5
然而巅峰就是要过去的。高三时,我再不复高二时的势头。但最终,我还是考上了一所差强人意的大学。
其實没什么可遗憾的。八月槎的故事真好啊,很多人和事,都是命中的牵牛宿。偶然的、一闪而逝的星光,无法抓住,但值得珍念。
高中毕业,我们四人即将天各一方。
“以后还是可以聚在一起吃饭的。”我们都这样说。说着说着,又都不做声了。
这种沉默是必要的,不容我打破。
但一瞬间的冲动也是不容否认的——有那么一小会儿,我很想再问问张陆棋,你现在有多高?
编辑/胡雅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