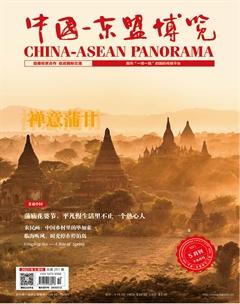杜拉斯的印迹,是这座城市在我心中的底色
Young


1975年,《印度之歌》导演见面会。扬坐在第一排,就坐在杜拉斯对面。他掏出《毁灭,她说》,请求签名:“我想给您写信。”杜拉斯写下地址:巴黎圣伯努瓦路5号。在康城火车站的出发小酒吧,他们一起喝了酒。第二天,扬就开始写信,没有回信,没有停,几百封,直到1980年夏。
1980年7月的一天,杜拉斯说:“来吧,我们一起喝一杯。”两个月以后,《80年夏》出版,献给“扬·安德烈亚”,这是杜拉斯为扬取的名字。那一年,扬27岁,杜拉斯65岁。
他们在一起,写作,口述,打字,做饭,吵架,辱骂,唱歌,跳舞,喝酒,兜风,写作。永不结束。扬,我的脸被酒精摧毁了。扬,我的皮肤很嫩,因为季风雨。扬,我舞姿完美。扬,写作就是跳舞。扬,你看,勒阿弗尔港,塞纳河,轮渡,这就是湄公河,世界上还有比它更漂亮的河吗?他们开着车,在河边兜风,唱《粉红色的生命》。
杜拉斯把扬的手提箱扔出窗外:为什么留下?没有人爱我,连我的母亲也不爱我,别再回来。他们又约在火车站附近的酒吧见面:“她来了。化了妆。脸上扑了厚厚的粉,嘴唇涂得红红的,很艳,像个妓女。她微笑着,像是100岁,1000岁,也像是15岁半,她要过河,中国人的那辆非常漂亮的小轿车将载着她穿过稻田,直至西贡的沙瑟卢-洛巴中学。”扬是中国情人,是小哥哥,是大哥,是副领事。
直到1996年,杜拉斯去世。1999年,沉寂了3年的扬·安德烈亚才又出现在圣伯努瓦路街角的花神咖啡馆里。记者问扬:“这场爱情究竟是不是一场美丽的艳遇?”扬目光炯炯,好像杜拉斯的目光一样:“不,这不是一场艳遇,这是一件非常神秘的事情。”粗鲁,自傲,孤独,杜拉斯,有时像漆黑的夜晚。“当一个作家,首先要穿过黑夜,林中的黑夜,随身带着写作,忍受着对黑夜的恐惧,穿越黑夜。”杜拉斯在黑暗的孤独中,探索童年的秘密。
15岁半,在湄公河的渡船上。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在法属殖民地,越南南部,盛产稻米的乌瓦洲平原,湄公河支流上的永隆和沙沥之间。女孩穿着一件旧的真丝连衫裙,腰上系着哥哥的皮带,脚上穿着嵌箔片的鞋子,头戴一顶平檐男帽,两条辫子垂在前胸。脸上敷浅红色脂粉,涂了口红。体形纤弱修长。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个人,臂肘支在船舷上,伫立在泥泞河水的闪光之中。男人走出黑色小轿车,穿着浅色柞绸西装,向女孩走过来,递烟给女孩……女孩说:“不,我不抽烟。”
1984年春,扬·安德烈亚在黑色打字机上一字一句敲下杜拉斯口述的《情人》。同年,《情人》出版,风靡全球。2005年,我读到这本书,很快读完,再读一遍,像参加一场舞会,一支接一支,是杜拉斯用文字创造的跳舞方式。简单的词,词的沉默,音乐一般的句子,脆弱的句子。耳语一般的独白,咬耳朵的独白。王小波说:“《情人》写出了一种人生韵律,使我满意了。”
小说改编成了电影,杜拉斯不满意。广告商!讨好观众!好莱坞垃圾!杜拉斯大叫大嚷,说专横的图像葬送了文字的想象。然而这部电影比她的任何一部实验电影都成功,湄公河上的女孩,海报张贴得到处都是。一场殖民地的艳遇,观众喜闻乐见。杜拉斯穿越茫茫黑夜,挖掘出的巨大秘密,却消失了。她脑海里的图像,倾其一生建造的诗意世界:悲惨荒蛮的亚洲土地,法国梦的陷落,粗暴野蛮的家庭,巨大的失败,生存的痛苦,疯狂的意志,河流和丛林到处可见流放和死亡的痕迹,早早经历了生命的孤独,女孩靠着船舷,在渡船上,随着浊流流浪。她的脸,混杂着妄自尊大、自嘲与耽于安逸的面容,“光彩夺目又疲惫憔悴”。
杜拉斯摧毁了小说的传统,也痛恨电影讲述的廉价故事。她一再编织着印度支那的图像,在自我探寻的黑暗道路上越走越远。她又写了一本书,《中国北方的情人》。她用这本剧作来报复那部电影。“好好看这天空,它在黑夜与白天一样碧蓝,看这明晃晃的大地,一直看到它的尽头,仔细聆听黑夜的响声,人们的呼唤,他们的歌声笑语,以及同受死亡困扰的犬类哀怨的吠声,倾听所有这些呼喊,它们同时诉说难以承受的孤独,诉说这份孤独歌声的瑰丽。”
無论如何,让·雅克·阿诺的电影还原了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旧日景象,如果仔细观看电影中的美术与置景,会不由自主地赞叹,这是越南风光的最好广告。如果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堤岸唐人街的小屋,目光只消从完美的“亚洲臀部”稍稍往上,还能看到完美的亚洲表情演绎。如果你格外关注了那几场动作戏,一定不会忘记一组快接特写镜头,充溢着热带的潮湿与迷乱。这部电影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以精致的画面提供了一份杜拉斯少女时代的旅游指南:沙沥女子学校、西贡利奥泰寄宿学校、西贡沙瑟卢-洛巴中学、永隆河岸边的蓝屋、中国人聚居区堤岸、中国饭店、泉园舞厅、河岸酒吧、法国大仲马邮船、西贡码头,还有沙沥、永隆之间的渡口与渡船。
2011年,我第一次到达西贡,即胡志明市。正值越南春节前夕,与满车的货物、盆栽植物、小动物一起,从大叻被运送到这座昔日印度支那联邦的首都。当时住在范五老街一条狭窄巷子的普通民宅,只有两三间客房。门口挂着褪了色的五角星红旗,房东老太太满头白发,喜欢穿一身雪青色衣裳。赤着脚穿过一楼客厅,里面楼梯口是厨房,墙面绿漆斑驳,从狭窄陡峭的楼梯上去,便是我在二楼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平米左右的小阳台,从阳台望出去,更见巷子狭小。骑楼联排房屋是最常见的越南民居建筑,两户人家若不是墙壁相连,便是隔着仅容擦肩而过的距离。5年之后寻访旧址,发现民宅已经改造成民宿酒店,而范五老街夜里越发喧闹,两边餐厅酒吧门口,全部摆上桌椅,不同肤色的人们隔街对望,激动的音乐声铺满整条街道。如果你在这条街上留宿,“城市如同一列火车,这个房间就像是在火车上”。
除夕,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主街如同庙会,乌压压挤满人。盛装女子多着奥黛,飘飘然穿梭在人群间。织布、编竹、捏小糖人,爆米花、棉花糖、鱼干、串串,民间手艺与街头小食叫我想念故乡儿时。故乡也正是除夕,我的父亲母亲,正因我第一次离家过春节而哭泣。后来我们一家人把它当作笑话讲,我每念及还是感到无限温暖。杜拉斯幼年丧父,母亲一味偏袒长子,大哥性情暴躁,抽鸦片赌钱,在家中处处施威。被抛弃的感觉,成了杜拉斯摆脱不了的魔障。杜拉斯的印迹,是这座城市在我心中的底色。
胡志明市是越南的商业中心,旧时代的线索隐匿在繁华之中。西贡沙瑟卢-洛巴中学是杜拉斯的母校,也是柬埔寨前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的母校,现在叫做Lê H?ng Phong High School,是电影的实际取景地。西贡利奥泰寄宿学校,据说由圣保罗大教堂借景。堤岸位于西贡河西岸,是胡志明市最大的华人聚居区,20世纪中期,是鸦片烟馆、妓院、赌场的集中地,不仅吸引华商驻足,想必也吸引了不少扬这样的法国人。钟屿石岬角位于芽庄以北1.8公里处,据说是电影外景地之一,吸引不少影迷前往观瞻,在那里,女孩向情人介绍了母亲的租借地,然而实际租借地远在柬埔寨的海岸边。至于蓝屋,有说是沙沥的华侨故居,有说在马来西亚槟城取景。对于这些,我无心打卡求证,更不愿伫立于城市洪流中感叹物是人非。毕竟,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早在我亲身前往之前,便已印刻心底。
春节期间,花市繁茂,黄灿灿红彤彤粉嫩嫩的一片片,孩子在其间戏耍追逐,色彩更加活泼生动。有一些市民在广场跳舞,大喇叭咿咿咿地流转着越南语歌声,让我想起热爱跳舞的杜拉斯和小哥哥。在街角找个摊位迎街落座,等着咖啡从滴滤壶中一滴滴掉下来,摩托车声不绝于耳,四周大大小小政治宣传画穿插在崭新楼宇与旧时法式建筑之间,宽敞的街显得紧凑团结。呷一口咖啡,目光没着落地涣散着,如果有卖鱿鱼丝的叫唤着从身边经过,喊下来,要一袋,海鲜加咖啡,管它搭不搭呢。
到了夜里,河岸边,天空蓝得深邃,男男女女依偎闲坐,与对岸兀自发亮的红色胡志明雕像相互张望。鸟在河面盘旋,忽上忽下,几只船晃悠悠地靠在码头,身后是喜气洋洋的蓬勃都市景致,真是一转身便可抖落疏离的心情,一步踏进滚滚尘世间。
让娜·莫罗说出湄公河名字的时候,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魔力。渡船上女孩的形象呼之欲出,随之涌现的,还有无边无际的稻田,被水淹没的土地,浑浊的水,一触即发的激情,不知疲倦的欲望,羸弱与颓唐,统统随着这个名字一起流淌。如果要实实在在地感受这条河流,最便捷的方式,是参加湄公河一日游,你可以乘船进入湄公河,观赏船屋,坐马车参观河边村庄,欣赏传统乐器的演奏,了解手工椰子糖的制作,享用新鲜美味的炸象鱼春卷,如果旅行时间不多,这是一段值得推薦的行程。
从西贡出发,我前往湄公河三角洲,前往柬埔寨海岸边的租借地,前往女乞丐流浪的洞里萨湖,前往安娜的沙湾拿吉,我甚至沿着湄公河一路向北,直到金三角地带。我乘船,沿着河岸走,走在季风雨里,也走在旱季的干涸里,心里总是摆脱不了杜拉斯、扬和她的一家人。炎热的印度支那,是杜拉斯穿越的丛林黑夜。《情人》出版后,杜拉斯说:“我原谅了所有人,原谅了全家,大家都变得可爱了,他们全是一些可爱的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