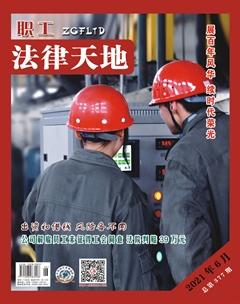抖音抖傻了人生
李春晖
安迪·沃霍尔曾预测: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事实上,老头的预测保守了。
抖音的出现,让一个人的成名时间缩短为15秒。每天点开应用,就能过上看似五彩斑斓,实则千篇一律的“抖音式”生活。
这种满足感太容易获得。而一旦习惯了这种“唾手可得”的满足,谁还要去做那些“高投入”的事情。于是以往的学习、娱乐,统统给短视频让路。其余不管是搞长视频的、搞音乐的、搞影视的,都要向抖音的玩法看齐。抖音的口号是“记录美好生活”,但显然,手机里的生活比现实“美好”太多。
算法机制的优越性,表面上是你喜欢什么,就给你什么,让人沉浸其中不觉时光飞逝,但事实上,抖音又是一款强运营的产品。于是,被抖音给予更高推荐权重的东西,总是更易获得你的喜欢——算法+运营通过制定你的视野,来掌控你的喜好。
当你看着抖音,刷着朋友圈,沉浸于虚拟的心理满足而欲罢不能的时候,也许正中了“算法”的圈套。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毁掉自律。
亚当·奥尔特写了一本书叫《欲罢不能》,戳穿了算法背后的算计:“设定诱人的目标,提供不可抗拒的积极反馈,让你毫不費力就感觉到进步,给予逐渐升级的挑战,营造未完成带来的紧张感,增加令人痴迷的社会互动。但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可能会失去真正的自我。”
为了增强用户黏性,抖音的界面交互设置相当巧妙。与传统的需要返回上级界面再进人下一条的浏览模式不同——抖音只需上滑屏幕即可轻松切换到下一条,使用户停下来变得极其困难,“一刷到天亮”成为了部分用户的日常。
喜欢小哥哥,就是满屏鲜肉;喜欢小姐姐,就是满屏美女,就像贾瑞不舍得放下风月宝鉴一样,谁忍得住空闲时不点开抖音?
长期沉浸在个人兴趣的满足中,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和接触机会。不知不觉间,贴心的APP就为人们制造了一个茧房。迅速变化的时代里,抖音成为新“权威”,指导人们不知疲惫地开始表演。
从抖音公布的用户的年龄分布情况来看,85%的抖音用户在24岁以下,主力达人和用户基本都是“90后”“95后”甚至“00后”。这些用户群体归属感和排他性都很强,在看到抖音上好玩有趣的内容后,他们就会自发模仿。
大家生而戏精,抖音来者不拒。正如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在《时代精神》中所言:“文化和个人生活从未如此地进入商业和工业的流程,世界的梦呓从未如此同时地被工业地生产和商业地销售。”
媒介制造娱乐,大众痴迷娱乐。娱乐过度,便挤占了生活。抖音里的美好生活,是被无限虚化过的生活。而在虚幻的满足中,演戏的和看戏的最终都会把自己搞丢。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两种方法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在抖音,这两种方式其实并行不悖地交互作用。不断表演和模仿的用户,成了滑稽戏的主人,充当千千万万个表演劳工的角色;而投入其中的看戏者,不知不觉也成了戏中人。鼓掌呐喊,成为虚拟空间的永恒囚徒。